2015文藝氣象·戲劇篇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5年12月29日13:19 來源:人民日報 任藝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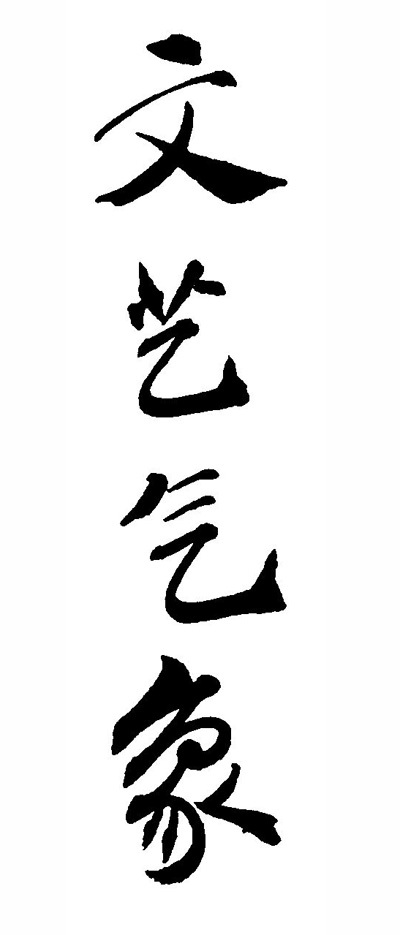 |
|
標題書法:梁永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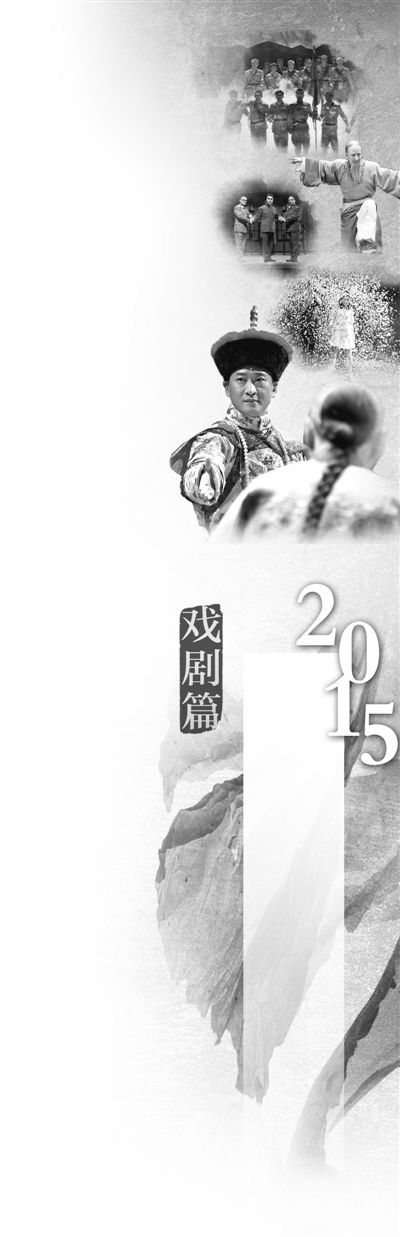 |
版式設計:李姿閱
打進傳統,匯入當代(年度話題)
任藝萍
今夏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支持戲曲傳承發展的若干政策》,將近年來政府對傳統戲曲藝術的大力扶持推向新的階段。戲曲在當代乃至未來能否再煥生機的關鍵,不僅在于政府的扶持力度,更在于釋放戲曲本身就蘊含著的與當代審美相契合的特性,推動戲曲走進當代生活。
以傳統戲曲講述尚未走遠的故事,可被視為戲曲主動走進當代生活的表層涵義,如今年首演的抗日戰爭題材評劇《母親》、京劇《西安事變》。
悠久的歷史為中華戲曲積累了豐富的劇目資源,以今人的價值觀與人文視野對傳統題材進行當代解讀,是讓戲曲為今天的觀眾所喜愛的重要手段。在今年舉行的“上海戲曲藝術中心北京新劇目展演”中,昆劇《景陽鐘》、京劇《春秋二胥》皆脫胎于傳統戲,同時具有鮮明的當代指向。前者在再塑了崇禎的人物悲劇性,突出歷史辯證性、批判性之外,強調了今人對民族歷史的文化心理認同;后者在尊重千百年來人們對伍子胥、申包胥“全忠孝”的價值判斷基礎上,對二胥進行了超越傳統忠孝的解讀,賦予這一傳統題材以“復仇—寬恕”“個人忠義—大道至上”這一道德倫理層面的反思,讓春秋二胥在當今社會具有了現實意義。這兩部作品既尊重前人對傳統劇目的經典解讀,又或辯證或反思地在此基礎上拓展原作的精神向度,使古老的人物獲得新生,進而讓傳統戲曲與當下生活接上了氣口,可為借鑒。
如果說用傳統戲曲手法講述現代故事、用今人眼光解讀傳統劇目,是戲曲得以與當代人的生活相契的外部手段,從藝術本體出發、深入發掘戲曲原本就具備的超越時空的先鋒性藝術精神,戲曲將在當代因為被理解、被尊重而被激發并釋放出它內在的生命力,進而為其自身乃至其他藝術門類的發展開拓出更多的可能性。
比如,挖掘戲曲演員表演多重性的當代價值。以統領了中國話劇表演近半個世紀的蘇聯斯坦尼表演體系來說,這一體系注重演員放棄“第一自我”,深入到對角色的體驗,強調“我就是(角色)”。在今年舉辦的首屆上海小劇場戲曲節中,戲曲名家曾靜萍在《御碑亭》中細膩呈現女主人公微妙的心理變化,化身為角色本身,可又跳出角色,客觀審度自己的一招一式是否符合“十八步科母”嚴苛的程式要求,以在表演上葆有梨園戲的古早味道。傳統戲曲演員的表演從來都在“既是(角色)又不是(角色)”中自由切換,演員身份的多樣性帶來表演空間的豐富性,這一點勝于古典的西方寫實主義,對于打破中國當下話劇表演的虛假與僵化不無啟發。
再如發揚“用最少的筆觸表現最深刻的藝術真實”的戲曲美學精神。如梅蘭芳所說,戲曲的景都在演員身上。《秋江》的舞臺上不必有船有櫓,僅憑兩個演員的表演就可以鋪展出有驚無險的水上泛舟;《夜奔》也不必有月有風,一個演員的唱念做打就是工筆與寫意兼具的英雄末路圖。《伐木》《驚奇的山谷》《酒神狄奧尼索斯》《哈姆雷特》,四位當今國際一流戲劇家的代表作今年相繼走進中國,在極度風格化的同時都體現了對深刻真實的準確表現,其中兩位戲劇家明確表示受到了中國戲曲的影響。
戲曲假定性,更是可在當代乃至未來大放異彩的有待開掘的藝術特性。戲曲不僅不以在舞臺上如假包換為目標,而且從來都是主動凸顯舞臺與觀眾間的界限。從“三五步走遍天下,七八人百萬雄兵”,到檢場人登臺更換道具、主演當眾飲場,戲曲觀眾不得不帶著自己活躍的想象力入場,和演員共同填滿舞臺上的留白,也讓觀眾自覺地對舞臺上的故事有所審度和思考——由是,創建出多重、積極的觀演關系。今年口碑上佳的原創話劇《北京法源寺》,其藝術特質之一,就是對戲曲假定性的密集化用。20世紀的戲劇家布萊希特用間離手段創造史詩戲劇,推動觀眾思考,同時代另一位戲劇家梅耶荷德創造戲劇假定性理論與詩性戲劇,也莫不源于中國戲曲的啟發。
事物原初的模樣往往已蘊含未來發展的諸多可能。戲曲綿延千百年,因后人傳承,也因其“最傳統最先鋒”的生命力使然。今人賦予古老戲曲以當代生命,不是要“京劇話劇化”“地方戲京劇化”,而是要“打進”傳統深處,對它古老的藝術理念、美學精神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在深入傳統、學習傳統的過程中,實現文化上的自我認同;在此基礎上,為人類當代乃至未來的精神家園貢獻力量。對待戲曲如此,對待以戲曲為代表的中華傳統文化亦如是。
原創(年度關鍵詞)
賡續華
今年是戲劇大年。7月,支持戲曲繁榮發展的文件《關于支持戲曲傳承發展的若干政策》由國務院辦公廳頒發。與國家對戲曲發展的高度重視相呼應,今年的戲劇藝術生產力倍增,原創作品的數量與質量令人鼓舞。
原創能力終不減
哲學家黑格爾說,“哪個民族有戲劇,就標志著這個民族走向成熟……戲劇是一個民族開化的民族生活的產物。”回眸歷史,中華民族從不缺乏戲劇,所謂“鑼鼓響,腳底癢”,形象地描繪了老百姓對戲劇的喜愛。
2015年,文藝評獎得到整飭規范,評獎數量大大減少。諸多藝術節、戲劇節將重心由評獎轉向評論,一戲一評,專家暢所欲言,主創人員受益匪淺。不過,這一變革絲毫沒有影響各地戲劇院團參加藝術節的熱情。以中國戲劇節為例,全國各地申報參加戲劇節的劇目近150臺,經過篩選30臺入圍,在申報院團的強烈要求下,又增加了9臺。
各地積極參加戲劇節展演的劇目,讓我們得以集中看到了戲劇人的原創能力。中國兒童藝術節集納了24臺劇目,優秀作品亮點迭出。第七屆中國黃梅戲藝術節,23臺原創劇目依次亮相。《大清名相》《小喬初嫁》《妹娃要過河》《活字畢昇》《寂寞漢卿》等作品,思想性、藝術性都達到較高水平,關注時代,為民謳歌。
其中,黃新德、熊辰龍、王琴主演的《大清名相》格外引人矚目。該劇從大清禮部尚書張英的一首打油詩切入,“千里家書只為墻,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表現出當讓則讓的曠達態度。該劇主角張英之子張廷玉,一生為官清廉,曾輔佐多位清朝帝王,在整治吏治、完善軍機制度等方面立下功勞。該劇通過講述張廷玉在朝堂上、生活中的三次主動退讓,表現出他嚴于律己、嚴于治家、甘于犧牲的精神與情懷。同時,他堅守原則和底線,宅地可以讓三尺,懲腐肅貪沒商量,這一點在當今具有鮮明的現實意義。第六屆中國昆劇藝術節則集中了17臺優秀劇目,北方昆劇院的《李清照》、浙江昆劇院的《大將軍韓信》、上海昆劇院的《墻頭馬上》尤為出彩。
直面歷史和現實
201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一批抗日題材的原創劇目紛紛涌現。抗日戰爭是永恒的題材,可以說,這其中的優秀作品并非“應景之作”,而是以藝術家的良知直面民族的苦難與涅槃。
遼寧人民藝術劇院的話劇《祖傳秘方》,展現了東北人民在國難之際的道義擔當,不神化、不矮化、不娛樂化。故事緊湊,人物性格鮮明,演員個個精彩,臺詞鏗鏘有力。國家話劇院的《中華士兵》,則是一部立志高遠的民族史詩,正面反映抗日主戰場中華兒女浴血奮戰的壯舉。中國評劇院的《母親》,以魔幻現實主義的風格,將一個真實的故事藝術化地再現于舞臺,讓今天的觀眾為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遭遇的苦難哀傷,也對戰爭做出反思。京劇《楊靖宇》、錫劇《林徽因的抗戰》、評劇《安娥》、音樂劇《猶太人在上海》等多部原創作品,也都以飽滿的熱情、獨特的角度,展現了戲劇人“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開創未來”的責任擔當。
當前反腐倡廉的題材難寫難演難突破,但作為戲劇創作者,不僅不能回避現實,而且應當深入開掘現實。豫劇《全家福》獨辟蹊徑,選擇貪官之舉是對自身家庭的毀滅這一主題,在觀眾中產生共鳴。話劇《鏡中人》是劇作家孟冰又一部現實主義作品,表現反腐,直面人性。創作者不回避矛盾,不藏不掖,直指人心幽暗處,同時實現對人性的叩問與救贖。
百花爭艷領風騷
回望這一年集中亮相的原創作品,我們看到主創者的創作心態大多回歸了藝術創作本身,注重愛護自身與團隊的口碑。在這一創作心態的影響下,今年出現了多部有望“叫得響、傳得開、留得住”的原創佳作。
比如,河南豫劇《風雨故園》。這部劇并非創作于今年,但經過打磨后在今年第十四屆中國戲劇節甫一亮相,就為觀眾與專家交相稱贊:原來印象中粗獷、豪放、張揚的河南梆子可以如此細膩、婉約、內斂。劇作家陳涌泉寫出了一個躲在歷史角落里的小腳女人的心思與絕望。劇中以魯迅的原配夫人朱安女士為主人公,朱安對大先生高山仰止,自喻小蝸牛,再努力攀爬也只能抵其人生的高度——小矮墻。人物的悲劇是制度的、社會的,更是性格的。在大先生和朱安的情感世界里,沒有贏家。在《風雨故園》中,魯迅的形象未受到損毀,相反,讓觀眾得以走進他的內心世界,進而更深刻地理解他的作品。主演汪荃珍塑造的朱安十分生動,她忍著盼著憧憬著失望著絕望著,一汪清泉蒸發成枯井。汪荃珍善用唱念身段刻畫人物,出嫁時如閨門旦,鶯聲燕語;中年時似青衣,端莊大氣;老年時若老旦,深沉蘊藉。唱得飽滿,收放自由,張弛有道。她的圓場,不踩蹺但小腳步態輕盈,每一步都透出功力與內涵。
陜西商洛花鼓戲《帶燈》根據賈平凹同名小說改編,劍指當前中國基層現實,尖銳震撼,但充滿善意。主人公用自己微弱的“螢光”照亮黑夜、照亮人心、照亮希望。與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作品相比,《帶燈》以真誠的創造意識實現了一次精神上的突圍。杭州越劇院的《鹿鼎記》在題材上“劍走偏鋒”,首次讓韋小寶這個金庸筆下的人物走上越劇舞臺,凸顯了武俠世界里蘊藏的中國傳統文化神韻。
戲劇“原創年”百花爭艷,各領風騷。為觀眾而作、為藝術而作、為時代而作,正逐漸成為戲劇藝術工作者的共識。辭舊迎新之際,讓我們共同期待戲劇人新的創造,期待生活中的中國精神、中國故事在舞臺上得到精彩演繹。
晉劇 《于成龍》
太原市晉劇藝術研究院
讓現實照進歷史(年度推薦)
傅謹
晉劇《于成龍》的主人公于成龍被康熙皇帝譽為“天下廉吏第一”,但該劇沒有表面化地停留在主人公的清正廉明,而是通過主人公毅然承擔起平息民變之責的艱難經歷,揭示了一個真理:執政者風清氣正,清正廉明,才能獲得百姓的信任和擁戴,才能實現國泰民安的目標。可以說,主人公最大的貢獻不僅是肅貪,更是維護穩定。于成龍個人的清廉固然值得充分肯定,但官員清廉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它是社會穩定的重要政治基礎。
晉劇《于成龍》融歷史觀照與現實關懷于一體,融思想于人物和故事的自然進程之中,擺脫了急功近利和觀念先行的陋習,內容的深刻與表現的完美相得益彰。鄭懷興的劇本結構精巧,人物鮮明;曹其敬的導演處理簡潔明快,流暢生動;謝濤和太原市晉劇藝術研究院眾多演員的表演,既體現了傳統戲曲的深厚積淀,更有新的演繹和追求。尤其是謝濤瀟灑飄逸的表演和蕩氣回腸的唱腔,具有很強的現場感染力,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提升了晉劇的文化地位,也有效地豐富了劇目的情感內涵、深化了劇目的主題思想。
晉劇《于成龍》在一定程度上堪稱當代戲曲創作的代表性作品,期待它在不斷的舞臺演出中更趨成熟,成為叫得響、傳得開、留得下的舞臺藝術精品。
京劇 《西安事變》
國家京劇院
現代戲突圍之作(年度推薦)
彭維
京劇《西安事變》以傳統戲曲直接表現現代題材“西安事變”。這一重大歷史事件曾多次在電影、電視、話劇等藝術形式中再現,登上京劇舞臺尚屬首次。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主創者充分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決定性作用,周恩來成為劇中重點,與張學良、楊虎城,以及蔣介石建起三方力量,共同推動劇情向前發展。
在藝術呈現上,《西安事變》突破流派和行當限制,充分發揮劇種優勢,進而塑造出血肉豐滿、情感細膩的人物群像。周恩來、張學良雖同由須生演繹,但流派不同,前者為馬派須生朱強,后者為楊派須生于魁智。劇中楊虎城、蔣介石則歸由花臉行當,前者是偏重做工的架子花臉胡斌,后者是偏重唱功的銅錘花臉王越。梅派青衣李勝素的挎刀配演也為此劇增加了不少光彩。全劇既挖掘人物的思想與情感,又給予不同行當、流派的唱腔與表演以充分發揮的平臺,從而讓全劇可觀可聽。
歷經“戲曲改革”和“樣板戲”的探索,觀眾對戲曲現代戲的藝術標準要求頗高,戲曲自身在表現今人生活時也有頗多掣肘之處。在此背景下,《西安事變》不僅勇于繼續戲曲現代戲的探索,而且直接表現重大歷史題材,其創作精神值得肯定。當然,作為一出新戲,還需要在演出實踐中繼續打磨。
話劇 《北京法源寺》
國家話劇院、天橋盛世投資集團
當代戲劇勇擔當(年度推薦)
張之薇
《北京法源寺》撼動人心,首先因為劇中人的崇高和家國情懷。劇中人近乎獻祭般的問道精神與傳統中國文化情懷,曾經在我們古代精英士子的身上綿延不絕,而今難得。創作者觸探到戊戌變法前后十天每個人物的心靈,是與非碰撞出的結局被審視、被撕開、被重構,劇中的康有為、譚嗣同、袁世凱、慈禧、梁啟超等人物顯現出骨骼與血肉。導演田沁鑫拋出一個多棱鏡,將對歷史與人物的判斷、思考交由觀眾。
《北京法源寺》給人以驚喜,在于導演通過對戲劇時空的打破、重構、交叉、跳躍等嫻熟技巧,將話劇舞臺團塊式的時空徹底打碎,自如、自信地游走于中國戲曲與西方戲劇觀念之間。傳統戲曲中司空見慣的“勘破”等做戲原則,為田沁鑫化用。舞臺上的人物行動、人物亡魂、人物內心,甚至演員自身,既合而為一又可隨時切換。劇中人也如他們自由穿梭的思想一樣,在不同的時空中自由跳躍。于是,《北京法源寺》的舞臺神奇地發酵,理性思辨的存在也毫不削弱戲劇性的魅力。正所謂“廟堂高聳,人間戲場”。
自16年前話劇《生死場》橫空出世,家國情懷與舞臺上的時空自由就是田沁鑫劇場的內在魂魄與藝術特點。此次《北京法源寺》不僅濃墨重彩地突顯了這兩大特質,而且因其對歷史題材、對傳統文人風骨的現實觀照與思考,體現出了寶貴的文化自覺與擔當。
話劇 《中華士兵》
國家話劇院
史詩再現民族魂(年度推薦)
馬也
2015,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表現戰爭的戲劇作品不少,真正優秀者不多:我們的藝術家還是缺少駕馭現代重大戰爭題材的能力。
然而由查明哲導演的《中華士兵》卻給劇壇帶來驚喜。《中華士兵》沒有拘囿于狹隘的民族主義、膚淺的民族情緒,而是超越了歷史、超越了政治、超越了戰爭。它既發掘了五千年來中華民族向死而生、不懼苦難的英雄氣節,又對人性進行反思;殺身報國、舍生雪恥,表達的是我們民族的自省、民族的高貴與尊嚴。“中華士兵”,是指每個中華民族的子民“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都是士兵、都是戰士。這部戲是一部民族史詩,也是一次民族洗禮、一次民族煉獄與涅槃。
《中華士兵》在敘事方法上的突破和創新,對當代中國話劇有所貢獻。全劇采用立體結構、板塊結構、交響結構。四段幕間的小板塊是正在進行時的故事,編劇馮俐在此過程中巧妙插入四個大板塊即故事主體,全劇的外在統一性則由兩位中日高級軍官形而上的論辯貫穿。導演把整個演出澆筑得天衣無縫。整部戲如同恢宏大氣、磅礴奔涌的血色浮雕,在這流動的血色浮雕里刻畫著壯懷激烈的形象,講述著驚天動地的故事。面對這一切,我們有可能已經麻木了的靈魂,被震顫、被激活、被喚醒。
兒童劇 《木又寸》
中國兒童藝術劇院
藝術闡釋生命觀(年度推薦)
歐陽逸冰
《木又寸》是新中國兒童戲劇史上第一部大型獨角戲。它以兒童般純真爛漫的想象和充滿摯愛的悲憫情懷,傳揚了太陽底下所有的生命都有權快樂成長的信念,或許這是當今人類的偉大良知,是保護地球生態環境、呼喚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初衷與歸宿。
這是一部舞臺樣式洗練而又豐富新穎的獨角戲。在如同打開的大自然百科全書的頁面里,在現場多種樂器的擬聲和旋律中,自由地演繹著主人公(小銀杏樹)曲折多變、跌宕迷離的命運。演員巧妙地將臺詞、表情、肢體動作融為一體,不但細膩刻畫了主人公富于變化的內心世界,而且轉瞬間即可展現出對手形象的神采,銀杏樹哥哥、山鷹、嬰兒、奶奶、路人、流浪貓……盡在其中,活靈活現。如是,十余個“人物”形成了以小銀杏樹為中心的情感與情節的繁衍渦旋。在這個渦旋中,無論是玩具火車頭,還是畫著貓頭的皮箱,都被神奇地賦予了生命,它們既是道具又是“人物”,甚至成為女主演的物化延伸,在戲劇動作中“講述”著令人驚嘆的故事。
近在咫尺的主人公讓小觀眾直接成為她傾訴的對象,也成為可以扶助她的知心同伴。《木又寸》尊重兒童視角,得到小觀眾們的喜愛。或許,長大后的他們也會反復回想起小銀杏樹的心聲:“終于有人開始懂我們了!”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學術論壇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