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王十月:我為一個時代“收腳印”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6年04月01日09:42 來源:文學報 鄭周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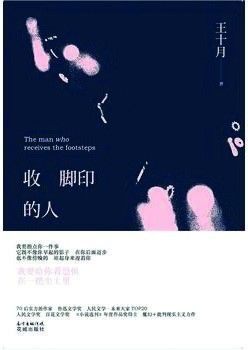
歷時五年,“70后”青年作家王十月在2015年與2016年相交之際提交了新作《收腳印的人》。對待這部作品,王十月很嚴肅,不僅嚴肅,他傾注了自己太多心血與記憶,于是他說寫完之后感到痛而哭了一場。
熟悉王十月的人都知道他被視為當下扛起“打工文學”旗幟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大多數作品聚焦打工群體的命運,自然,也包含了他自己的故事。即便是幾部看似非打工題材的作品,如 《無碑》《米島》,講述的也是打工者進城前的“前傳”,他們的窘迫與宿命共同啟動了那個決定進城的動因。在他的寫作里,我們往往能體悟到切入肌膚的感受,他毫不猶豫地將自己打工經歷一點一滴拼湊出來,裹挾著時代鋒利的烙印,沖擊讀者的閱讀感受。他的寫作不僅是為自己,更為“70后”一輩的寫作增添了風格鮮明的獨特質感。
《收腳印的人》同樣如此,暫住證、收容所、黑戶……它們有的已經進入歷史角落里,被更新被改善,有的仍然不時見之于媒體報道,對于王十月而言,他希望借助小說完成對遺忘的抵抗、對遮蔽的還原,他與主人公王端午合二為一,借角色之口道出了一個龐大群體曾面對的現實,有時他甚至跳過角色,直接對社會種種現象坦露自己的觀點。
每個人都身處一個真實世界,王十月則帶來了一個更真實的現實世界,他說新作是一次自白、一次懺悔、一次救贖,主人公去世前慢慢撿拾起自己過往的“腳印”,這也是作家在為身后的沉默群體以及他們的時代,收“腳印”。
我遺憾于缺乏勇氣
記者:開篇主人公王端午一直強調自己是理智的健康的,而后不斷在闡述自己對社會的看法及思想片段,這里面是否在反諷一種偏見,即想法太多的人很容易被劃入瘋人瘋語之列,繼而“非人化”?
王十月:是反諷,也是悖論與困境。即,王端午要用瘋人瘋語來證明自己不是瘋子。但現實不正是如此么,王端午對社會與人的看法,在許多人眼里,不也正是瘋人瘋語?讀者、審判者皆以為王端午是在說瘋話,殊不知,他的話,除去瘋狂的外衣,何嘗不是靈魂泣血的自省與吶喊,視他為瘋子的人,不正是瘋子么?這也說明偏見堅如冰川,一本小小的《收腳印的人》自然也無法融化堅冰。不同的社會階層,對中國當下的認識截然不同,于是,“非人化”也就成為了一種實在的精神鏡像。但這“非人化”,倒不在于“想法太多”,而在于,“非我類”的想法哪怕很少,也是不被理解與接受的,也是要被“非人化”的。
記者:第一章俄羅斯之行看似與后文無關,但引用了《荒原》《復活》以及莊周夢蝶典故,這些似乎都在暗示主人公的人生觀,趨近于悲觀和虛妄感。
王十月:第一章,許多讀者反映不好讀,但于我來說,很重要,這一章,誠如《紅樓夢》的第一回,是全篇的精神密碼所在。這一章的意義在于,作者反復重申《復活》與《荒原》,也在將這兩部偉大的作品作為本書的精神底色。兩部書與這部小書,也因此而形成互文。每個讀者讀完此書,都會想到這兩部書并由此引發對比與思考,從而得出自身對這時代的復雜判斷。這本書自然是悲觀的,王端午是絕望的,他試圖自審與救贖,卻無法成為涅赫留朵夫,北川、阿立們,也沒有成為瑪絲洛娃的機會,王端午不得不采用暴力的手段。很多讀者不能接受本書的結尾:施虐者終于逍遙法外,而自審者被送上審判臺,接受女士先生們虛偽的裁判。但他若完成了復活,施虐者如受到了審判,則不是真實的現實。荒原之荒亦在于此。
記者:你的這種認識與過往的親身經歷分不開,就像小說中,王十月與王端午常常合二為一,對讀者評議社會種種現象,閱讀這部小說是能夠感受到來自寫作者的痛苦和勇氣的。
王十月:我有意將作者王十月與敘述者王端午合二為一,即,我試圖盡可能讓我的讀者明了,我不試圖以王端午為虛構人物從而使得他的言論并不代表作者言論為逃避指責的藉口。王端午所言,即王十月所言。當然,此書寫作十分痛苦,區區十余萬字,我自2008年汶川地震后動筆,故書中有北川這個人名,但先后廢了兩個十五萬字,第三個才有了現在這樣的小說。中間許多細節,是盤踞我心頭之傷。但,慚愧的是,我的勇氣沒有經受起檢驗,我還是不夠尖銳,并回避了太多東西。這本書是充滿遺憾的,藝術上可以更精致一些,可以更豐滿一些,但最大的遺憾,是我不夠勇敢,在我最想寫的一本書中,有太多回避。
記者:你不止一次說城市最初對打工者就像卡夫卡筆下那座城堡,被允許進入,卻并不真正接納。而那些所謂的“成功者”以為自己真的成功了,立即與底層大眾區別開來,漠視一切,這里面實則產生了很多道德危機。
王十月:我自然是肯定“進城潮”是中國之今日繁榮的推動,而且是巨大的推動力。但我悲憤的是,這偉大的群體的付出、被漠視、被侮辱、被損傷,卻淹沒于各種成功故事的“雞湯”里。諷刺的是,我本人也被當作了某一方面草根奮斗的典范,被煮了“雞湯”。
記者:主人公王端午的覺醒、懺悔、求之于審判之旅,與你提到的致敬托爾斯泰《復活》形成對應,但這一前提是他自知自己不久于人世,這是否可以說人性面對罪的問題是需要絕境來啟動的?
王十月:這也是中國式復活與俄羅斯式復活之不同。王端午若不是生命到了盡頭,加之妻離子散了無牽掛,也絕不可能走向復活。這也是中國人至今缺少對罪的自審與復活的緣故。故我們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之將亡,其鳴也哀。”卻忽略了,人終將死,何不早言善。也暗含了我對中國式復活的批判。
記者:“收腳印”也非常“中國式”,你家鄉傳說人去世前需要回顧人生去收回那些足跡。換個角度看,王端午收回的腳印,也是打工群體的集體回憶。
王十月:是的。我在書中說,所有的回憶都是不可靠的。但過往已沒于塵埃,于是只有通過收腳印穿越回過往并重新審視這過往。但悲哀在于,這所謂的回到過去,依然是不可靠的。事實上,小說是無力做到準確重現歷史的,只是局部的喚醒與揭示,可我手中只有小說這把兵器。
我將更多書寫打工者的未來
記者:故事中的王端午說自己進城三十年,去年也是打工文學三十年,有許多討論放在了它的意義上,以你寫作而言,打工文學最大的價值是否就是緊緊關注底層命運?
王十月:文學的意義之一在于為時代作見證,直面時代主要的真實。打工文學的價值在于,當中國主流作家長期漠視這三十年推動中國發展的人口紅利中的主要人口時,打工文學以粗糲而樸素的方式用了30年來記錄他們的生存狀態。你可以以藝術的標準指責它的若干問題,但你不能無視它的意義,五百年以后,我們的后人試圖從先人的文學作品中了解當時的中國,打工文學無疑是重要窗口。
記者:“打工文學”這個概念仍然有許多歧義,你是偏向于有打工經歷的作家寫作,還是任何打工題材都可以進入?
王十月:我的定義更狹窄,是打工者所寫的描寫打工生活的文學作品,打工者、打工生活、文學作品,三要素缺一不可。
記者:那么那些純然依靠虛構沒有底層生活經歷的作家,便難以寫作這樣的題材故事?
王十月:并非只有底層者對底層的書寫才具有合法性,而是對于擁有底層生活的寫作者而言,他們的挑戰是如何將生活轉化為文學,而對沒有底層生活的寫作者,他們面臨的最大考驗是對底層生活的想象。我們常常指責中國作家沒有想象力,但有一個誤區,以為寫人憑空飛起或在樹上生活才是想象力豐富的表現,殊不知,描寫你所陌生的人群的日常生活,需要更加強大的想象力。
記者:你的寫作被認為是扛起打工文學旗幟的作家之一,你怎么看待這個標簽?
王十月:對標簽,我歷來的態度是不主動貼,別人貼了也不拒絕。因為打工是我的胎記、紅字,不容我拒絕,但同時,我又認為,文學就是文學,無所謂打工文學或什么主義,所以也不主動貼。
記者:你近年有些作品看似游離到了非打工題材上,但實則是在接上“打工人生”的前半章,回答一個為何要進城打工的困境問題。面對如此復雜的時代話題,你期待小說實現多大程度上的呈現?
王十月:是的,我力圖書寫這個完整的群體,既有他們的此刻,也有他們的來處。而接下來,我會更多關注他們去往何方,肉身的、靈魂的,并以此,構成對中國的書寫。
記者:近年有許多優秀的非虛構作品聚焦于一些時代重要題材,你會考慮以非虛構方式來呈現更多自己真實經歷嗎?
王十月:其實《收腳印的人》中的收容遣送問題,我最初的想法是非虛構,它將更有力量,我也做了一些準備,但最后放棄了,我的勇氣不夠。另外,采用虛構會有更多的精神空間,也更自由,我還是更喜歡這種表達方式。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學術論壇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