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張曉風:考試是一種制度,與文學無關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6年03月29日10:21 來源:新京報 張婷 對自然與愛的贊頌,是張曉風作品里的重要主題。
對自然與愛的贊頌,是張曉風作品里的重要主題。 張曉風 臺灣散文家、小說家、劇作家。1941年出生于浙江金華,8歲隨母赴臺,曾任教于東吳大學、香港浸會學院、陽明大學。
張曉風 臺灣散文家、小說家、劇作家。1941年出生于浙江金華,8歲隨母赴臺,曾任教于東吳大學、香港浸會學院、陽明大學。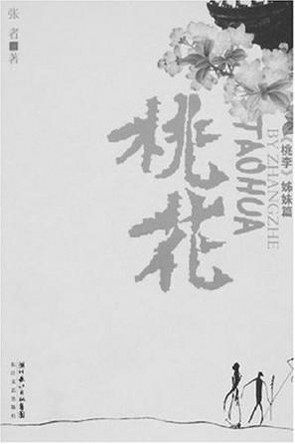 《放爾千山萬水身》 作者:張曉風 版本:廣東花城出版社 2015年8月
《放爾千山萬水身》 作者:張曉風 版本:廣東花城出版社 2015年8月 提問:文中的“白色纖維”是指什么?作者描寫這些白色纖維的用意是什么?
“那是一個夏天的長得不能再長的下午,在印第安納州的一個湖邊。我起先是不經意地坐著看書,忽然發現湖邊有幾棵樹正在飄散一些白色的纖維,大團大團的,像棉花似的,有些飄到草地上,有些飄入湖水里。”
這是一道初中語文考試題,或許我們對這樣的問題設置都不會感到陌生。這段話節選自臺灣作家張曉風的散文《敬畏生命》,如果讓作者本人來答題,她會都能答對嗎?
面對這個提問,張曉風只是笑著擺擺手,示意她從沒有要嘗試回答這些題目的意圖。“考試是我們自古以來說的‘舉業’,我不認為那個跟我有什么關系。我只是寫我要寫的東西,至于別人要拿它來做什么,跟我沒有任何關系。”在“進入”教材多年后,張曉風日前來到了北京,接受了《新京報》書評周刊的專訪。
“讀者通過教材第一次讀到我的作品,也沒什么不好”
盡管張曉風本人對自己作品與“舉業”產生的關聯并不在意,但不可否認的是,對今天許多的年輕讀者來說,人們對她的最初認識,恐怕就是源于中學時代的教科書。除了《敬畏生命》,還有《行道樹》《我喜歡》等等都曾被收入過不同的中學教材,有些甚至常常作為閱讀理解題出現在語文考卷中。
張曉風常常會被問及自己作品與考試的關聯,在她看來,文學是私人的,而考試則是公共的。這從來是兩條不同的路。“我當然希望我的讀者會自己買我的書來看,但是如果他第一次讀到我的作品是從教材里,我也不會覺得有什么不好。重要的是他讀了這些作品的感悟。”
與一代人的考試記憶緊密相連,使得張曉風的散文容易陷入被標簽化的境地。她的文學形象也常常與“溫暖”、“勵志”、“雞湯”這些頗為可疑的字眼聯系在一起。許多年輕讀者結束學生生涯之后, 便再沒有讀過她的作品。但在這些標簽背后,張曉風有著更豐富的內涵。她的文學寫作不僅局限在散文領域,更橫跨小說、戲劇。有一段時間,她還借用“可叵”的筆名在臺灣的報章雜志上發表了不少文風潑辣的時評文章。
“希望我的文章讓學生感受到和《背影》同樣的感動”
跟張曉風聊天,你很難不注意到她對自然風物濃厚的興趣。在她居住的賓館,每當看到廊道里擺放的鮮花,她總會不自覺地上前看看那花的真假。看到飯店桌上擺的綠色植物,她又忍不住湊上去看看花盆里的土壤是否足夠濕潤。談話間提到鳥兒,山川,張曉風的眼神也會一下子明亮起來。
近年來,她對環保問題日益關注。她提到每次外宿酒店,都會自己帶肥皂、毛巾、牙膏等洗漱工具;去飯店用餐也不會使用一次性餐具。前幾年,因為臺北的一塊空地用于商業開發,張曉風還撰文在報刊批評,呼吁城市中應當多一些綠地。
對中國的山川河流、自然風物的喜愛很自然地成為張曉風散文的一大主題。而她散文中總是充盈的溫情和愛的力量則與她的基督徒身份緊密相關。張曉風自己概括,“如果有人分析我,也只有兩種東西,一個是‘中國’,一個是‘基督教’。”中國與基督教,這兩個詞正是理解張曉風文學世界的關鍵。
張曉風的個人生活也一直從經驗層面確證了她對愛的信念。她的婚姻生活幸福美滿,獨生女兒也順利成家立業。如今75歲的張曉風,仍然保持著時時閱讀和寫作的習慣。在采訪中她提及,她最喜歡的作家是托爾斯泰,年輕時常常閱讀的作家則是冰心。從這樣的閱讀脈絡中,我們也很容易理解張曉風寫作風格的由來。如果張曉風最喜歡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魯迅,那么她的散文寫作會是迥然相異的面貌。
對自然與愛的贊頌,是非常適合給中小學生講授的主題。張曉風認為,這正是她的文章常常被選入教材的一大原因。“不是說被選入教材或應試教育體制當中的文章就會跟讀者產生隔閡。我初次在課本上讀到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也同樣感動。我希望我的文章也能夠讓年輕學生感受到這樣的感動,并且吸引他們感受到文學和閱讀的美好。”
■ 對話
“選我的文章進教材,出版社從來沒有付稿費給我”
新京報:你的散文經常被收入教材,甚至常成為語文試題。你對此現象怎么看?
張曉風:我對此沒有特別的感覺,不會說希望被收入教材,也沒有不希望。自古以來,考試是一種舉業,它已經形成了一套完備的制度,文章寫出來了,別人要把它選入教材或者考試題目,那是制度的一部分,跟我、跟文學沒有關系,我也不會介意。不過有一點我倒是很介意的,就是他們選我的文章進教材,出版社從來沒有付稿費給我。這個倒是可以幫我呼吁一下啊,哈哈。
新京報:你有沒有做過那些閱讀理解題,你有把握都做對嗎?
張曉風:看到自己的文章被用作考試題,會有點不自在。我記得有一次,我正在臺北街道上開車,交通繁亂。我手機接到一個電話,是香港的一個中學國文老師打來的。他在電話里問我對香港的一個中學會考題目怎么看。那個試題是拿我的文章來做閱讀理解。我能感覺到他是希望從我嘴里說出一句話,說作家本人也做不對這個題目。那他可能可以拿這個話去為他的學生申訴。他一直在電話里跟我講了半個小時,可能那個會考對他的學生來說也比較重要,不是學校內部的小考試。但是我最大的感覺是考試的制度、試題,那些是與我無關的,那些考試答案也是考試制度內部的事情。我希望讀者讀我的文章是因為喜歡它,而不是想要拿高分。文學從來是一個人的事情,而考試是一個制度,這是完全不同的兩條線。
新京報:那你認為是什么因素使得你的文章經常被選入教材或考試題目呢?
張曉風:第一是篇幅適合,我的散文字數都不會太多,不長不短正好可以用作一篇課文的閱讀容量。第二個原因是我寫的常常是中國、傳統、自然這些題目,這些題目非常適合跟學生們討論。我不太寫美國啊、歐洲啊相關的題目,不是說那些不好,而是我們的傳統文化里頭有很多好的東西,讓我想寫的東西。我回想自己讀書的時候,也曾經在教材里讀到很多有觸動的好文章,比如讀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不是說課本里的東西就不好,有的小孩子如果不是把文章放到教材里,他就是不會去讀的。如果我的文章能夠讓一個學生感覺到文學的美、文字的美,那是很好的事情。
新京報:你曾經罹患癌癥,跟病痛斗爭了很長時間。生病的經歷對你的寫作有沒有改變和影響?
張曉風:那是大約十年以前了,現在我仍然需要密切注意和檢查自己的身體狀況,防止復發。我剛剛知道自己得這個病的時候,也很平靜,并沒有覺得非常恐懼。人都會有死亡、離開的時候,如果它來了,那就是到了離開的時候。可是我希望我活著的時候,每一天是過得很清醒的,能夠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寫自己想寫的文章。
新京報:你認為自己的寫作從年輕到現在經歷了怎樣的變化?
張曉風:我從十幾歲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寫作,最開始的時候寫作的題目都集中在朋友、家庭、戀愛這些身邊的事情。大約從25歲以后,我開始會關注更大的話題。比如環保、政治、戰爭這些題目,這跟個人的成長歷程是聯系在一起的。從寫作的題材上說,我的確很難坐下來寫一個大部頭的長篇小說,寫得比較多的一直是散文、劇本和短篇小說。
新京報:為什么說很難坐下來寫長篇作品?你現在還保持每天寫作的習慣嗎?
張曉風:寫作當然很重要,但是對我來說,我的生活里還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說教書,比如說照顧我的家人。我覺得生育一個孩子,把她養大、教育好也是很重要的事情。所有這些事情我都想要,那寫作就不是我生活里唯一重要的事情。我現在還是保持閱讀和寫作的習慣,但是我不會強迫自己說每天必須閱讀、寫作幾個小時,順其自然。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學術論壇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