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羅偉章:以虛擬的英雄氣概,來凸顯現實世界的荒蕪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6年01月29日11:10 來源:中華讀書報 夏琪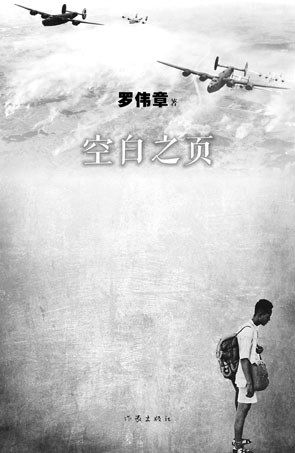 《空白之頁》,羅偉章著,作家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29.00元
《空白之頁》,羅偉章著,作家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29.00元
2012年,我出版了長篇小說《太陽底下》,是一部以重慶大轟炸為背景的作品,寫完這個小說后,我心里還硌得慌,需要完成另一部小說來釋放自己,于是從“太陽底下”溜走,鉆入一片陰影之中。《空白之頁》就是那片深長的陰影。可以這么說,《太陽底下》是從宏觀的角度書寫人心的廢墟,《空白之頁》是從微觀的角度探究廢墟是如何形成的。
“聲音消失,就意味著一個村莊的消失。天賦異稟的楊浪,縱然對聲音有著極端的敏感和出色的模仿能力,如今也僅能用自己的絕技回味那些逝去的鮮活。鄉村空殼化的現實,被楊浪鮮活得近乎繁復的感觸和作家溫潤綿密的敘事,映襯出一種地老天荒的枯寂蒼涼。”2015年12月26日,第十二屆十月文學獎在宜賓李莊頒獎,中篇小說獎頒給了四川作家羅偉章。
羅偉章,曾因較多作品關注中國教育而被稱為“中國教育小說第一人”。他的起步很早,早到大學時便能夠以寫作維持生計,但是畢業之后,他有十年沒再動筆。
“不寫簡直受不了,于是又開始動筆。我在2005年之前發表的作品,多從痛感出發,某個地方讓我痛,那痛就成為核心,輻射出小說。”羅偉章發現,盡管痛感是文學中的好東西,但好東西不止一種。此后,他在文體和語言上有一些自覺。如《不必驚訝》《大河之舞》《太陽底下》,包括去年發表的《世事如常》,便是“自覺”的產物。
同時,他的寫作越來越慢,也覺得越寫越難。一是庫存的問題,二是“不滿足”,對題材的不滿足,對結構的不滿足,對敘述方式的不滿足,對語言表達的不滿足,這些不滿足以及由此設置的難度,恰恰都是自己給的。“每當一個難度橫在面前,除了讀書和更切近地擁抱生活,似乎也沒有別的出路。”羅偉章說,最近大半年,他在老家的時候多,因為那里有歷史。他希望把歷史和現實貫通,呈現來路和去向。
讀書報:最早關注您的作品,是《潛伏期》《奸細》《最后一課》等中篇小說。這些集中關注教育的小說,各有側重,對教育改革進程中產生的系列問題都有深刻的反思。為何專注于這類題材的寫作?是否與個人經歷有關?
羅偉章:大學畢業后,我當過教師。那正是教育發生巨大變革的時期。我們一直被成功學鼓舞,到我教書時,追求“成功”已成為人們的某種本能,而成功的標準又極其單一,由此,教育的寬闊性被無限擠壓和切割。與此同時,教育部門和從業者都忙忙碌碌地與社會接軌,想方設法地賺錢。學生也跟著躁動,某些校園簡直就像個龐大的集市,鮮有學府氣。作為熟悉這個領域的寫作者,有義務呈現自己的感受、觀察和思考。
讀書報:能夠說說長篇小說《磨尖掐尖》是厚積薄發之作嗎?寫“教育小說”,您有怎樣獨特的感悟?
羅偉章:我想寫和要寫的,是成長,是倫理,是人與人的關系,是公德與私心的沖突,是價值觀的疑難和掙扎。這些東西自會“溢”出題材,讓更多的人觀照世相和打量自身。再就是我不回避——盡量不回避。在寫作中,即便是小說這樣的虛構藝術,“回避”也會成為自我過濾的方式,并因此使作品弱化力量、小化格局。我覺得,我們當下的許多寫作,包括我自己的寫作,格局太小了,好些作品無非是在人際關系的泥潭里打滾,最終鬧得自己也面目不清;那種躍出泥潭的清爽、開放、寂靜與孤傲,那種迎風而立和眺望云端的姿態,都難得一見。
從小說本身而論,《磨尖掐尖》并不是我喜歡的,我認為我的另幾個長篇都比它好。
讀書報:《聲音史》研討會上,評論家們對其多有贊譽。這部作品的選材并不十分新鮮,寫農村的空巢現象,寫到了鄉村生活和歷史變遷,但是您選擇了以聲音作為切入點,角度非常特別。能談談這部作品的創作緣起嗎?
羅偉章:我本人對聲音比較敏感,我覺得世上的許多情感,產生于聲音,你殺魚的時候,聽不到魚叫,你就以為魚不痛,也不怕死,你的各種感覺就比較遲鈍;殺豬殺狗就完全不同。我早就想以聲音為媒介寫一部小說。
讀書報:《聲音史》最近剛剛獲得“十月文學獎”,您如何評價這部作品的價值和意義?這部作品的寫作過程順利嗎?
羅偉章:如果我這部小說只是寫了農村的空巢化,我認為它就是失敗的。我當時的志向不止于此。我希望通過這部小說,讓某些東西“慢”下來,并從中尋求通向寧靜的道路。我想穿越物質的層面,向大自然的神性靠近一些。我認為這些才是重要的。僅僅印證,不是我的目的。寫作基本順利,只是寫得慢,修改花了很長時間。現在是越寫越慢。
讀書報:《空白之頁》2013年就發表了,為何三年后才推出單行本?
羅偉章:是的,這小說要2016年春節后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發表過后,我還放在那里,改來改去,但認真說起來,又沒作根本性的修改,許多時候是陷在一個詞語的表達上。我經常感嘆,覺得寫作的過程其實也是妥協的過程,你分明知道這個詞不好,想換一個,你想幾天幾夜,做夢都在為那個詞糾結,可就是換不了。這是相當苦惱的事情。后來我慢慢想通了,只要你是足夠認真的,你就得允許自己有這樣的妥協;即是說,有時候要體諒自己的無能。
讀書報:主人公孫康平的“英雄夢”,令人感慨萬端。但他是那個時代中的滄海一粟,他和惠君的愛情也是那個時代的獨特產物。很想知道您的目光為什么會轉向那一段歷史?
羅偉章:2012年,我出版了長篇小說《太陽底下》,是一部以重慶大轟炸為背景的作品,寫完這個小說后,我心里還硌得慌,需要完成另一部小說來釋放自己,于是從“太陽底下”溜走,鉆入一片陰影之中。《空白之頁》就是那片深長的陰影。可以這么說,《太陽底下》是從宏觀的角度書寫人心的廢墟,《空白之頁》是從微觀的角度探究廢墟是如何形成的。
讀書報:《空白之頁》中,劉湘率川軍出川作戰、驅吳拒陳等確有其事,您在寫作中是如何把握歷史的真實和虛構的關系?我想敘述中肯定有您自己的思考和判斷。
羅偉章:確有其事和事件背后的真實,是兩個概念。有時候,“真實”本身就是一個虛構的概念。作為寫作者,我認為被敘述才構成真實,虛構的目的,正是為了抵達真實。
讀書報:孫康平的“英雄夢”有幾次出現,但是很令人意外的一筆,是他在“紅牙碧串,妙舞輕歌”的得月樓里,腦海中居然會古怪地浮動著戰爭的幻影。而最后他的死亡,是“以完勝的英雄夢,去嘲笑死神,也把自己短暫的一生推向高潮,回歸、豐富和完成了自己的整體”。為什么會設置如此情境?
羅偉章:能做英雄夢的時代,要么波瀾壯闊,要么輝映著理想主義光芒,這都是超越物質層面的,于人生的更高意義而言是好的。然而生活要摧毀的目標,往往正是那些不能隨遇而安的人。夢和夢想的區別,是夢想可以一直存在,夢卻終會醒來。醒來就意味著夢的破滅。認輸是最便捷的道路,但認輸不等于心甘情愿。“不甘”,是人生中特別具有悲情的部分。孫康平就是這樣,他既沒認識到性格決定命運,更沒認識到命運還要選擇性格,同時也沒認識到,當他邁出第一步,就已經陷進了“裂縫”之中,而且拒絕他的追問。他在得月樓的思緒,以及臨終前對死神的蔑視,是以虛擬的英雄氣概,來凸顯現實世界的荒蕪。
讀書報:“這完全是陰差陽錯造成的‘裂縫’,孫康平是掉進了裂縫里。”這是小說中者光華的概括。寫“裂縫”中的人物,您覺得把握起來有何難度?
羅偉章:難度正在“裂縫”本身。那條裂縫不是齊整的,也不是靜止的,它扭曲,錯動,逼仄的時候讓你艱于呼吸,敞闊的時候讓你失去方向。世間沒有一條裂縫是“陰差陽錯”的,因此你得明辨裂縫的成因,它的偶然和必然。此外,裂縫本身帶有寓言的性質,你的所指和能指,究竟能開辟多大的空間?這些都是難度。
讀書報:陰陽先生和已經去世多年卻依然“參與”生活的“婆婆”,使小說籠罩著一種鬼魅之氣。他們的存在是必須的嗎?
羅偉章:只要你感覺到了鬼魅之氣,就證明他們的存在即便不是必須,也是需要的。那是這個作品的氣氛。再一方面,我想打開一面墻,包括陰陽之墻,為某種東西找到出口。小說中的人物活得太過憋屈,需要出口。此外我是比較有意識地向傳統文化和民間文化資源伸手。
寫作的過程中,我會盡量保持冷靜。我認為,即便是抒情性很強的作品,寫作者也要盡量保持冷靜,要跟你描寫的對象保持適當的距離;冷靜不是冷,要有熱度,但又不能過熱,否則很可能讓作品失去寬度,并因為公正的喪失而丟掉深度。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學術論壇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