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袁敏:無論厚重或淺顯,我都踩在生活的土地上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5年12月22日10:11 來源:文學報 傅小平“暖心教育讀本”《蒜頭的世界》出版
袁敏:無論厚重或淺顯,我都踩在生活的土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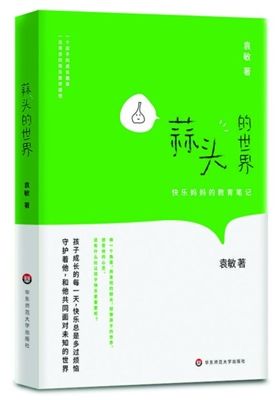
“故事是當年的,體悟是一路走來,回眸細想時慢慢產生的”
記者:我想對你有所了解的人,讀到《蒜頭的世界》都會感到驚訝,你怎么就沒有征兆地寫出了這樣一本兒童文學作品?這和之前的《重返1976》區別實在是太大了。
袁敏:我很高興你把這本書界定為兒童文學。其實,這本書出版社最初的定位是給家長看的,沒想到出版后孩子們也都很喜歡。中國作協兒童文學創委會主任高洪波看過此書后給我打過一個很長的電話,他也說,你明明寫的是有趣的兒童文學,版權頁上怎么是家庭教育?我以前從未寫過這樣的作品,之所以沒有征兆地寫了這樣一本書,是因為我從編輯出版《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作文選》開始,一直在關注中國的教育,有一些想說的東西總是在心里涌動,但我不知道該如何表達。
直到有一天,一位多年研究少兒教育心理學的朋友在聽我講述了我兒子小時候種種讓人哭笑不得的糗事后對我說,你兒子太有意思了,你為什么不把你和你兒子的故事寫下來呢?我一琢磨,對呀!我一直想表達的東西不正蘊含在我和兒子之間真實發生過的故事中間么?于是,我開始寫下一個個小故事。最初,這些故事在伍美珍主編的《陽光姐姐教作文》上連載,受到孩子們的歡迎,我信心大增,就一篇篇寫下來了。
記者:說起來,這兩本書也有共性,就是你總是能從一些細節里生發出生命的體悟,也因為這樣,雖說《蒜頭的世界》是有意為之的淺,但從這淺里,還是能讀出一些深的東西,這一點和《重返1976》是共通的。
袁敏:故事是當年的,體悟是一路走來,回眸細想時慢慢產生的。之所以會去回眸,回頭細想,是因為周圍總看到許許多多的母親在重復著我曾經有過的種種焦慮、困惑和抓狂,我終于意識到,那么多年過去了,我們的教育似乎還在原地踏步。我不是說中國的現行教育體制都不好,而是覺得我們學校的集體教育面對每一個孩子的個體生命時,常常不匹配。孩子們雖然上課在學校,而卻有一多半的時間在家里,許多父母總覺得把孩子送進學校,教育是老師的事情,家長只要管好孩子的衣食住行就可以了,殊不知孩子的智商、情商、財商,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其實更多的是在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中逐步形成的,父母若是忽略了家庭教育這一塊陣地,也許就是放棄了孩子一多半的人生。
記者:作為一個作家,同時也是一個出版人,在寫這本書之前,你對相關教育讀本會有一定的了解,你多半想著自己能寫出什么新的角度,能帶給這類圖書以什么新的質素。那么根據你的觀察,這類炙手可熱的圖書存在什么問題?
袁敏:你說的那些炙手可熱的家教類的書確實很久以來都是圖書市場上的寵兒,動輒上百萬甚至幾百萬的銷量不能不讓一個出版人心動。可憐天下父母心,誰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出類拔萃?那些“哈佛女孩”“耶魯男孩”的成功成才之路,誰不想借鑒一二?“好媽媽勝過好老師”的教育寶典,哪位家長都愿意從中取點真經。正因為此,眾多出版社蜂擁而上,各種家教類圖書鋪天蓋地。然而,越來越多的同質化的少兒和家教圖書折射出中國成功學的狹窄,這種狹窄弄得孩子很壓抑,弄得家長很焦慮。
記者:這本書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不是教父母如何讓孩子走向成功,而是教孩子學會享受快樂,而即使是要成功,也不能因為要追求成功而失去快樂。當然這么說,已經包含了對中國教育的批評。
袁敏:在我看來,出類拔萃的“哈佛女孩”“耶魯男孩”畢竟只是少數,大多數孩子都是普普通通的,但普通就不能成功嗎?不能成為鳳凰,為什么就不能做一只快樂的小鳥呢?
記者:在自序里,你寫到蒜頭是個非常普通的孩子,但我讀下來卻覺得這個孩子不普通,不說他身上有那么多古靈精怪的鬼點子,單單是他的財商就實在了得。你要說普通,只能說是在被當成重要衡量標準的學習成績上普通罷了。而另一個不普通在于,他成長的環境不普通。如此看來,套用羅丹的話來說,沒有一個孩子是普通的,我們缺少的只是發現他不普通的眼睛。
袁敏:我也很喜歡這句話:沒有一個孩子是普通的,我們缺少的只是發現他不普通的眼睛。我一直收藏著我兒子高一時的一張成績單,那上面物理、化學分別是29分和30分,不及格,這樣的考分當時真讓我汗顏。但我發現成績單上語文的班級平均考分是73.5,而兒子的考分是76,高出平均分,而“藝術”這一欄里是“優秀”。更讓我意外的是,在老師評語這一欄里寫著:“你知識面廣,多才多藝,積極參加班級、學校組織的各項活動,能力得到老師和同學的認可。”直到現在我都感謝這位老師,感謝她在一個物理、化學不及格的學生成績單上寫下了這樣的評語,它不僅讓一位母親面對偏科的孩子心生一絲欣慰,也讓一位考試成績不佳的學生保留了一份自信。
“我并沒有刻意選擇敘述的語言,提起筆寫下就是這種味道”
記者:題為《蒜頭的世界》,這本書實際上寫的是啦啦眼中的“蒜頭的世界”。而啦啦能深入到蒜頭的世界里去,很大程度上在于她能理解蒜頭的世界,會站在蒜頭的角度去看事情、想問題,她在面對蒜頭做出各類出格的事所保持的那份冷靜、克制,讓人印象尤其深刻。
袁敏: “冷靜、克制”在和孩子相處的過程中真的很重要,許多家長往往會在孩子犯錯誤或者學習成績不佳時不冷靜、不克制,沖動之下做出一些偏激的行為,其后果常常是兩敗俱傷。前段時間,浙江的媒體報道學校孩子自殺的事件有六七起,這真是一個驚人的數字。《蒜頭的世界》 中有一篇故事叫“尋找100棵大樹”,我兒子當時犯錯誤,老師把我叫到學校訓話,我也是一怒之下對兒子說了狠話,兒子當時也說要去死。幸虧我及時“冷靜”下來,克制自己,事情才有了拐彎。否則,后果可能也會不堪設想。可以想見,這樣的事情很可能就近在我們身旁。這種時候,家長一定要冷處理,給自己一個緩沖,給孩子一個過渡,等雙方都冷靜下來以后結果可能就完全不一樣了。
記者:作家寫孩子的書,一般都會寫到孩子與文學或圖書的淵源,但這書里似乎沒怎么寫到,不知道是不是遺漏了,還是你認為這部分并不能反映蒜頭的世界,把它給忽略了?換言之,我想進一步問的是,孩子的世界,是一個充滿可能性的世界,也是一個有著很多面向的世界,多半還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沒有寫進書里,那你在故事選材上,是怎么考慮的?
袁敏:書中有一篇 《四驅車風波》,講的是蒜頭在班上賣汽車的故事,小學四年級的蒜頭學著做生意掙了100多塊錢,被學生家長告到學校。高明的老師拿出兩堂作文課讓同學們在班上展開討論,她不對蒜頭賣汽車的行為做評判,卻指出:1.你賣汽車是經營行為,你無照經營,非法;2.你掙了錢,有盈利,應該交稅。你沒交稅,違法。之后,蒜頭的床頭居然出現了一本小書: 《中小企業100問》。我和孩子他爸都是文人,讀這種書肯定沒有我們的淵源,也和我們對他的人生設計大相徑庭。但他在生活中遇到事兒了,想要了解,根本不用我們指點,自己就去買來讀了。正如你所說,孩子的世界,是一個充滿可能的世界,也是一個有很多面向的世界,這個世界大人往往是不了解的。你可以嘗試去了解,但最好不要去干預或阻止。當孩子的興趣和父母的期望背道而馳時,你只能觀望,而不是扼殺。這種興趣也許是階段性的,也許是持之以恒,成為最終人生選擇的,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盡可能支持孩子做他想做的事情。
記者:這本書有個副標題, “快樂媽媽教育筆記”,其中的“快樂媽媽”這個理念是我特別看重的。就這本書里講述的故事來說,媽媽啦啦也有很多煩惱,要說她有不同之處,就在于她能把煩惱轉換為快樂。
袁敏:現在有許多父母對自己的孩子期望值太高了,常常讓孩子不堪重負。前段時間我去一所學校講座,互動交流時,一個女孩問我:我想當一個幼兒音樂老師,爸爸媽媽卻要我當居里夫人,我該怎么辦?我說你把自己的想法告訴過爸爸媽媽嗎?女孩搖頭。我問她,為什么不告訴呢?女孩說,我不敢,我怕他們生氣,說我沒志向。女孩說這話時,眼里全是眼淚。我當時真的很難受,這么懂事的一個女孩,為了不讓爸爸媽媽生氣,只好自己不快樂!我給她念了葡萄牙詩人費爾南多·佩索阿的一首詩,詩中這樣寫道:你不快樂的每一天都不是你的,你只是虛度了它。無論你怎么活,只要不快樂,你就沒有生活過。我問女孩,能把這幾句詩念給你的爸爸媽媽聽嗎?女孩說:能。我不知道女孩是否真的有勇氣把詩念給她的爸爸媽媽聽,但我很希望她的爸爸媽媽能注意到自己的女兒不快樂,了解她為什么不快樂!假如孩子不快樂,做父母的你能真的快樂嗎?
記者:寫這樣一本教育筆記看似容易,其實不容易。首先,作為一個成人,還原兒童經驗就很不容易。其次,作為一個成人作家,你得換一種孩子能接受,或說是大人孩子都能接受的語言來寫。還有,如果說這本書的敘述部分相對好寫,要寫好母子間的對話可就難了,要寫好對話,非得深諳兒童的心理才行。
袁敏:許多看過《重返1976》的讀者都說很難相信《蒜頭的世界》是出自同一個作者之手,《重返1976》 的語言風格沉郁、凝重,而《蒜頭的世界》的文筆幽默、俏皮,節奏快。其實,在寫作過程中我并沒有特別刻意地去選擇敘述的語言,好像提起筆來,自然而然地就流淌出現在這種味道的字句,書中許多啦啦和蒜頭的對話幾乎都是生活中的本來面目,我只是把它記錄下來了。這本書真正坐下來寫的時間很短,完成得很快,雖然都是兒子小時候的事情,時間似乎已經久遠,可是一旦寫起來,記憶清晰地撲面而來,好像還真沒有什么思路堵塞的時候。也許,發生在自己孩子身上的故事,都是拍攝在母親心上的底片吧,一翻印,一切都是那樣的清晰。
記者:我看有報道稱這本書是潤物細無聲的教育真經。說它“潤物細無聲”是沒什么錯的,“教育真經”卻是未必,因為這本書并非講的什么真經,即使有真經,那也是由故事生發出來的,這也正是現在很多教育讀本的通病,很多類似的書,都太急于傳授所謂“真經”了。
袁敏:我相信這個世界上就沒有什么教育真經,每一個生命的個體都需要有與其相匹配的不同的教育方式。《蒜頭的世界》也同樣,里面沒有什么教育寶典,只是一個尋常母親在育兒過程中的個人感悟。如果說想和讀者分享的,可能就是一種思維方式吧。
記者:你這么大跨度的寫作,讓讀者對你以后的寫作不由得多了一份期待。當然總的說來,你偏向于經驗性寫作,即使是寫的虛構作品,你也是有堅實的生活經驗打底的,而你的人生經驗可謂豐富,要把很多經歷,包括你父輩的經歷都寫出來是很可觀的,這樣就更可期待了。
袁敏:我的寫作常常在虛構與非虛構之間徘徊,無論厚重或淺顯,我的雙腳都踩在生活的土地上。我想,以后的寫作還是會延續自己的風格吧。上一輩跌宕起伏的經歷和故事肯定是我會深挖的礦藏,哥哥姐姐們的知青生涯是我一直在追尋的歷史,身邊的有關教育的話題依舊會是我關注的重點。至于計劃么,就先不透露了吧。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學術論壇
- 鐠侇噣顣介敍锟�鐠ф澘鎮滄稉鏍櫕閻ㄥ嫪鑵戦崶鐣岊潠楠炵粯鏋冪€涳拷
- 閸㈠顔曢敍锟�閸掓ɑ鍘涘▎锝冣偓鈧棅鈺傛緱閵嗏偓閸氭潙鍗�
- 閵嗘劒瀵岄弮銊b偓鎴窗缁楋拷73鐏炲﹪娲﹂弸婊冾殯8閺堬拷23閺冦儱婀紘搴℃禇閹活厽妾介妴鍌欒厬閸ユ垝缍旂€硅泛鍨幈鍫燁偩閸戭厼鈧喓顫栭獮璇茬毈鐠囨番鈧﹣绗佹担鎾扁偓瀣箯瀵版娓舵担鎶芥毐缁″洦鏅犳禍瀣殯閿涘矁绻栨稊鐔告Ц娴滄碍搴婃禍娲浕濞喡ゅ箯瀵版娲﹂弸婊冾殯閵嗗倽绻庨獮瀛樻降閿涘奔浜掗妴濠佺瑏娴f挶鈧璐熸禒锝堛€冮惃鍕厬閸ョ晫顫栭獮缁樻瀮鐎涳箒鎽ら崟鍐ㄥ絺鐏炴洩绱濋崷銊ユ禇閸愬懎顦诲鏇℃崳娴滃棔绱径姘愁嚢閼板懐娈戦崗铏暈閵嗭拷 [閻愮懓鍤潻娑樺弳]


網上期刊社
- 娴滅儤鐨弬鍥ь劅
- <鐠囨鍨�
- 濮樻垶妫岄弬鍥ь劅
- 娑擃厼娴楁担婊冾啀
- 鐏忓繗顕╅柅澶婂灁
- 闂€璺ㄧ槖鐏忓繗顕╅柅澶婂灁
- 娴f粌顔嶉弬鍥ㄦ喅閹讹拷
- 娑擃厼娴楅弽鈥虫疮閺傚洤顒�
- 娴f粌顔嶉崙铏瑰缁€锟�
- 娴f粌顔嶉柅姘愁唵


博 客
缁儳鍍甸崡姘瀮
- 閼规儳鍘犻幏婊冪毜: 鐠愮绻庢禍鐑樼毌 閸掓稐缍旈弴鏉戭樋閺囨潙銈介惃鍕稊閸濓拷
- 瀵娀娉ら弬锟�:閺冦儲婀伴幏鎺嶇瑝鐠併倗濮滈垾鏂衡偓鏃€鍨拹銉﹀灇閺堫剙銇婃担锟�
- 閻楀洭鈹堥敍姘卞閺堛劍鍨氶弸锟�
- 闂娾晝绶ㄩ弸妤嬬窗閺夊海鎲洪悳顖滄暏娑撱倓閲滅€涙鑸扮€硅鍨�
- 閺夈劍妾介弫蹇ョ窗濮圭喎鍝洪垾婊堢矋濞夈儲鍜曢垾婵嗙毈鐏忓繗顕╃化璇插灙閵嗕胶绮ㄩ弸鍕挤閸忚泛鐣�
- 闁厽鏋冮弬宀嬬窗鐠囧懎鎷婚敍宀冪箷閺勵垳顨㈢粋锟�
- 閸熷棝娓块敍姘冲壖缁愭繈鍣烽惃鍕槻


網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