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周宗奇:沒有“山藥蛋派”老作家,我也許成不了作家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5年09月24日10:11 來源:中華讀書報 魯大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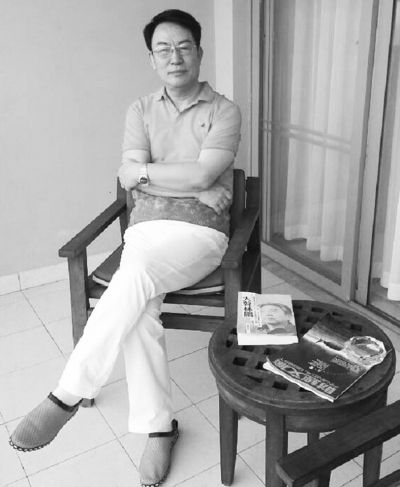 周宗奇
周宗奇20世紀的70年代,馬烽、西戎、胡正三位老先生來到臨汾,問文聯主席鄭懷禮有沒有發現“好苗子”。鄭懷禮說,霍礦有個娃寫的不錯。
這個“娃”就是周宗奇。40年過去了,周宗奇已年過古稀,他永遠忘不了三位老先生的幫助。是他們從煤礦把自己“挖”到山西省作家協會,1975年的春天,由此成為周宗奇生命的春天。
從上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已是“晉軍崛起”中骨干一員的周宗奇,把關注農民問題改為關注知識分子問題,把對人的生活現狀的描繪改為對其靈魂的掃描,把已然失重的小說形式改為批判色彩的紀實手法——在創作的旅途中,他始終沒有停止過探索。長篇小說《風塵烈女》、長篇歷史紀實小說《清代文字獄紀實》、長篇傳記小說《真偽人生》……在他洋洋數千萬字的背后,是廣泛、深入、扎實的采訪。在最近完成的“中國百位歷史文化名人傳記叢書”之《憂樂天下——范仲淹傳》的寫作中,他追尋傳主一生蹤跡,親歷9省、市29地實地采訪。山西作家周宗奇,書博會前夕接受本報專訪,吐露“好苗子”如何長成蒼天大樹。
讀書報:在霍縣礦務局辛置煤礦期間,您才26歲,寫出了《明天》《新房》《金鏈環》《一把火》《三遇楊堅》等20多篇中短篇小說。那個時期是怎樣的創作狀況?是在什么情況下寫作的?
周宗奇:多美呀26歲!我的26歲哪去了?就像《人證》中的那頂草帽,飛走了再也找不到,成了一個凄美傳說。說來可嘆,這一批早期作品是業余時間趴在床沿上寫出來的,屁股下是個小板凳,5平方米容身空間是一間俱樂部大倉庫的西南一角。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大學畢業后被打發到這座煤礦工作7年之久。這一段刻骨銘心的人生經歷,我在散文集《學灑脫齋夜話》中多有寫及,這里不提以免心酸。那時節身心傷累,前途迷茫,怎么辦?唯有寫作,既為打發孤獨憂傷,也是從小就有的愛好,一不小心就出產了這些中短篇小說。1973年,處女作《明天》在《山西日報》發表;《第一個師傅》(又名《金鏈環》)在《光明日報》發表;中篇小說《一把火》在《解放軍文藝》發表,并被翻譯成英、法文介紹至海外,還改編成蘇州評彈和小人書等文藝形式。一生的文脈就此開通了。
讀書報:《一把火》影響之大,甚至改變了您的命運。山西人民出版社召開全省“短篇小說學習班”(時稱“東陽筆會”),您作為重點培養對象應邀參加。筆會給您帶來了什么?
周宗奇:改變命運之說,不無道理。“東陽筆會”不光于我,于整個山西文壇來說,也是功不可沒,是一個不可忘卻的里程碑。40多年前,當作家協會還沒有恢復建制時,山西人民出版社有一個部門叫“文藝編輯室”,實際統領著全省的文學創作隊伍。從負責人劉江先生、關守耀先生,到周文、林有光、羅繼長、張仁健、常德順等具體干事諸位先生,為培養新時期作家盡職盡責,殫精竭慮。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從“文革”后期的1973年至1984年這10多年間,如果沒有“文藝編輯室”和上列這批承前啟后的重要人物,震撼全國文壇的所謂“晉軍崛起”就無從發生,新時期山西文學大省的地位就無從談起。這話不是我一個人說,作家張石山在其大著《穿越》中如是評論:“追溯歷史,文革結束后的山西文壇所以能夠兀立于中國文學之林、晉軍挺然崛起,文革期間的“東陽筆會”實在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文壇盛會。……東陽筆會,想不到聚會了那么多的文學愛好者。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后來成為支撐山西文壇的骨干力量。單憑記憶,我可以數出如下若干人的名字來。年齡二三十歲的,計有周宗奇,李銳,張石山,周山湖,崔巍,賀小虎,鄭惠泉,王紅羅,鄧建中,馬立忠,王巨臺等人,皆是年輕新銳,后來多數活躍在文壇。”
讀書報:作為“晉軍崛起”中的骨干一員,您愿意談談“晉軍”嗎?為什么當時會有這樣強大有實力的創作隊伍?
周宗奇:在中國當代文壇,“晉軍”和“晉軍崛起”的話題已覺不新鮮,各種論者熱鬧了30多年,哪容我拙喙再置。山西作家協會曾經擁有駐會專業作家十多名,我大致列出他們進入文壇時的“原始出處”,或者就能說明一點什么。以姓氏筆劃為序:王東滿、成一、張石山、李銳、麥天樞、鄭義、周宗奇、柯云路、鐘道新、趙瑜、韓石山、蔡潤田、燕治國、潞潞。這批人的共同點是:1、進入文壇時都因各種“文革賤民”子弟身份處于社會最底層,身陷逆境,日子很不好過,急需改變現狀。2、都具有異于常人的、程度不同的文學天賦。3、都受惠于改革開放大潮,即得“天時”之功也。周瑜抱怨老天說“既生瑜,何生亮”!我則要慶幸地說,老天真有眼,居然給山西弄來這么一批中青年作家!
讀書報:您的創作曾得到山西文學界馬烽、西戎、胡正等“山藥蛋派”老一代作家的賞識。您可否談談對他們的印象?
周宗奇:豈止是賞識,那叫恩重如山。是馬烽、西戎、胡正三位老先生親去臨汾,把我從該地區所屬煤礦挖到山西省作家協會的,多所倚重,12年中從小說編輯一路提拔到《山西文學》主編、作協常務副主席,不到40歲就成了體制中的副廳級干部,據說他們是要我來接班的。不光對我有恩,我們這一批作家均受惠非淺,對此,至今大家“供認不諱”。可是我們,尤其是我,辜負了他們的一片好心。以我為例,我難于茍同他們的政治理念和文學觀念。比如:馬烽先生說,宗奇你別忘了,是共產黨花錢辦刊物、養作家,這是事實吧?我則說,馬老師,沒有共產黨的國家不是也有作家嗎?據說活得也不差。至于圍繞“講話”內容所產生的種種文學分歧就更多了,關系就在這種誰也說服不了誰的、無休止的消磨中淡化了,直至那場風波驟起,我和我的中青年同道們幾乎“全軍覆沒”,他們也徹底對我和我們絕了望,心疼我們被整肅的同時,也多少有點幸災樂禍:你們不聽話,這是自作自受呀!
中國文化中的師道部分,始終存在一種難以破解的悖論,或者說是一種怪圈,就是:你要你師,還是你要真理?往往難倒后學。我就為此深深痛苦過,我愛父親般的山西老作家,可我又不想背叛自己的良知和追求。沒有“山藥蛋派”這些老作家,我也許成不了作家;但沒有對他們的反思和背離,我絕對得不到今天的創作自由與靈魂自由。我的選擇正確與否,天知道,我知道。
讀書報:1975年春天,您被調到剛剛成立的《汾水》(文革前叫《火花》,1982年改名《山西文學》至今)編輯部當小說編輯。從作者到編輯,是怎樣的心情?邊當編輯邊寫作,您在那段時期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老干事吳誠》由《小說選刊》轉載;《新麥》獲《汾水》短篇小說一等獎;《黃金心》由《小說月報》轉載;《古月劫》由《中篇小說選刊》轉載;《清涼的沙水河》被《作品與爭鳴》選載,獲1984年“趙樹理文學獎”,并由日本學者小林榮翻譯到日本;長篇小說《風塵烈女》由北方文藝出版社出版……您的創作幾乎都是噴發式的,似乎沒有“低潮”,什么原因?
周宗奇:什么“噴發式”呀,你是鼓勵我。我清醒著吶!一個作家成就大小高低,首先不在作品數量,質量第一;其次,與同在一個編輯部的李銳、張石山比,他們在創作路上已然遙遙領先,我已然是身處“低潮”了。這就不能不說到編輯之累。我成了刊物領導者之一,按我的天性,我不能對不起提拔我的老前輩,更不能對不起廣大基層作者,那種業余創作的艱難困苦我感同身受,所以我要把編務做到最好。但是,編刊與寫作矛盾之大且極難調和,有經歷者誰無體知?痛苦選擇之后,我毅然辭去了主編職務,專心文學創作。一時頗多震動,有一前輩老者親自登門勸告說:小周,可不敢孟浪,我30年才熬了個副主編呀。我生性中有一種決絕之氣,辭就辭了,了無后悔。當然,也有一種對創作前景的自信在。
讀書報:您的紀實寫作以《清代文字獄》開場,據說至今已出有5種版本,而且是計劃中的《中國文字獄》三部曲的第一部,整部書為10卷本,約350萬言,要把中國從古到今3000年文禍史,用文學語言書寫出來。這是一個填補中國文史空白的龐大工程。請問:是這樣的情況嗎?您為什么要做這件事?
周宗奇:用現代文學語言寫中國文字獄,寫得通俗易懂,專門奉獻給普通老百姓,從前似乎沒人干過。我有幸填此文史空白,或為天賜也。
不錯,我計劃中的《中國文字獄》分3部約350萬字:《清以前歷代文字獄》2卷約70萬字;《清代文字獄》3卷約80萬字;《現當代文字獄》5卷約200萬字。三部曲中,《清代文字獄》早已出版,先后由友誼出版公司、中國青年出版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另有兩種盜版書,所以說5種版本也不錯。《清以前歷代文字獄》正在出版運作中。《現當代文字獄》是重頭戲。可讓人沮喪的是,事情卻很難做下去,最主要的難題是相關檔案不解密,你無法見到第一手資料,尤其獄中資料秘藏不露,諱莫如深。無米之炊你怎么做?眼看書生老去,機會不來,你能把無情的現實怎么著?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學術論壇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