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wǎng)>>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劉慶邦:我們的國民性中有一種泥性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5年07月15日08:37 來源:中華讀書報 舒晉瑜我們的國民性中有一種泥性,也就是糾纏性,構(gòu)陷性。這種泥性一旦爆發(fā),會形成集體性的、無意識的人性惡,有著極強的攻擊性和破壞力。回顧過去遍地涌起的匪患,還有后來的多次所謂群眾運動,都與國民性中泥性的泛濫不無關系。
劉慶邦:我們的國民性中有一種泥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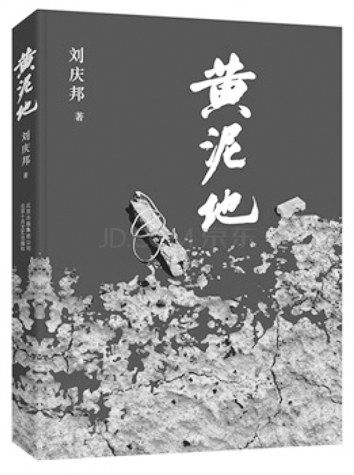 《黃泥地》,劉慶邦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29.80元
《黃泥地》,劉慶邦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29.80元“這里的泥巴起來得可真快,看著地還是原來的地,路還是原來的路,可房國春的雙腳一踏進去,覺得往下一陷,就陷落下去。稀泥自下而上漫上來,并包上來,先漫過鞋底,再漫過腳面,繼而把他的整個腳都包住了……”
劉慶邦的《黃泥地》自此開篇,那不動聲色的鉛字卻像無邊漫延的沼澤,扯住你的目光你的心,愈掙扎愈往下陷。是的,我們都來自黃泥地,都逃不脫這眷戀,這牽絆,這甩不掉的臟與累!作品的起筆很慢,越往后越緊張甚至于驚心動魄,主人公房國春的經(jīng)歷與奮爭,他周圍的看客的言行,很容易讓人想起魯迅。
或者可以說,《黃泥地》是一部向魯迅致敬的作品。
讀書報:作品開始進入比較松緩,越往后越好看,情節(jié)緊湊,高潮起伏。從寫作初就設定這樣的節(jié)奏嗎?
劉慶邦:事物的運行都有節(jié)奏,一般都是先慢后快,快到一定程度,再慢下來。這是自然規(guī)律。文學作品的節(jié)奏也是這樣,先是“轉(zhuǎn)軸撥弦三兩聲”,再是“鐵騎突出刀槍鳴”。如果一上來就緊鑼密鼓,進入快節(jié)奏,后面就不好寫了。
除了您說的看上去進入有些緩慢,開始出場的人物也比較多,情節(jié)的鋪排似乎也有些散漫。怎么說呢,這是整部作品的需要,也是我有意為之。它引而不發(fā),在為主要人物的出場營造氣氛,搭建舞臺。說得不好聽一點,是村里人集體性地為主要人物挖陷阱,把陷阱挖得頗有誘惑力,并極具隱蔽性,等待主要人物往里跳。從這個意義上說,開場出現(xiàn)的每一個人物、情節(jié)、細節(jié),甚至每一塊泥巴,都是有效的。有些看似閑筆,其實不可等閑視之。還有,小說的開始部分表面看好像有些輕松,內(nèi)里卻暗流涌動,殺機四伏,心弦是緊張的。
讀書報:故事發(fā)生在80年代,聽說是有原形的?為什么沉淀了這么多年?現(xiàn)在再寫,會不會覺得可能與當下脫節(jié)?
劉慶邦:不能不承認,這部長篇小說的一些人物的確有原型,不僅主要人物有原型,其他有的人物也有原型。小說的一個重要功能是塑造人物,特別是一部長篇小說,總得有幾個人物能給讀者留下印象。而要把人物寫得好,我們腦子里須裝有很多人物,供我們挑選。好比我們要釀酒,手里得有糧食才行。如果糧食不夠,一味摻假使水,再兌點酒精,造出來的只能是假酒。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腦子里儲存的沒有一些我們所熟悉的人物,寫起來就會捉襟見肘。不知別人怎樣,我個人的體會,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必須有生活中的原型作為支撐。如果沒有原型在我心目中活躍著,人物就很難立起來。也許我比較笨,對生活經(jīng)驗比較依賴,我已經(jīng)寫了好幾部長篇小說,每部小說的主要人物都有原型。
故事是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切入,時間的跨度將近二十年。我寫長篇都是向后看,是一種回憶的狀態(tài)。越是熟悉的事情,越不能急著寫,須放一放,沉淀一下。有句話說來也許顯得不夠厚道,我得等小說中的主要原型人物下世之后,才能動手寫這部小說。因為活著的人還是動態(tài)的,我們對其往往看不清楚。只有這個人死去了,蓋棺了,并埋進土里去了,我們才能把這個人稍稍看得清楚一些,這個人才會在我們腦子里活起來。與當下的生活是否脫節(jié),不是衡量小說成敗的標準。我們不必把小說綁在目前高速前行的列車上,“列車”它跑它的,我們慢慢寫我們的就是了。小說雖說是時代的產(chǎn)物,并不是時尚的產(chǎn)物,而是反潮流、反風氣的產(chǎn)物。小說不是新聞,不見得越新越好。小說是故事形態(tài),故者,往也,過去的事才稱得上故事。
讀書報:一個人的抗爭,想表達什么?
劉慶邦: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就是為抗爭而生,與環(huán)境、災難、邪惡、壓迫、剝削、歧視、非公平、非正義等等抗爭。在抗爭中成長,在抗爭中生存,在抗爭中發(fā)展。如果沒有抗爭,人類就走不到今天這一步,也不會有如今的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而抗爭意味著付出代價,甚至是付出犧牲,還常常以失敗告終。抗爭的教訓和預期,使多數(shù)人望而卻步,一些抗爭就變成了少數(shù)人的抗爭,或一個人的抗爭。這樣的抗爭當然更加艱難,更加嚴酷,它不僅需要奮不顧身、勇往直前的精神,還具有某種英雄主義的色彩。英雄幾乎都和悲劇結(jié)伴,但英雄主義仍不失積極意義。
讀書報:主人公房國春的經(jīng)歷,讓人覺得悲涼。各級政府官員的腐敗,似乎輕描淡寫,甚至順理成章,恰恰是這種“順理成章”,讓人覺得無奈和無望。寫作這類小說,稱之為官場小說也好、反腐題材的小說也好,您覺得難度在哪里?
劉慶邦:“直面中國基層腐敗”,這是書的編者概括出來的,并不是作者寫作的著力點,也不是作者要著重表現(xiàn)的主題。反腐敗當然很好,別人把反腐作為寫作題材,我也不反對,但我自己對寫反腐提不起興趣。我認為腐敗是由文化土壤決定的,歷朝歷代都不可避免。想起我年輕時在農(nóng)村搞高溫堆肥,就是把一些莊稼稈、青草和糞肥堆在一起,外面糊上泥巴,讓那些東西在里面發(fā)燒,發(fā)酵,腐爛,然后變成有機肥料。物質(zhì)土壤有催化腐敗的功能,文化土壤也是產(chǎn)生腐敗的溫床。腐敗表現(xiàn)出來的是分子,產(chǎn)生腐敗的文化土壤才是分母。不可否認,我們每個人都是文化土壤的一部分。要改變文化土壤的性質(zhì),不是短時間所能奏效。
我也從不寫官場小說,官場不能構(gòu)成我的審美對象。有人曾勸我寫官場小說,并主動愿意為我提供素材,被我拒絕了。看官場小說都讓我心生厭煩,我不可能去擺弄那玩意兒。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敏感點和關注點,我對下層普通民眾的生活更敏感一些,也更愿意在他們身上寄托我的審美理想。我對自己的寫作要求是,懷抱人道理想,投入自己的生命,以真誠的態(tài)度,寫人,寫人的豐富情感,寫人性的復雜性。只要寫好了人性,人性生成的背景,以及人性里所包含的社會性,自然會呈現(xiàn)出來。
讀書報:小說中還有一個人物,即《農(nóng)民日報》的房光東。作為本家,房光東處理房國春上訪一事,圓滑世故,還有些怯懦、冷酷。您如何看待他所代表的知識分子?
劉慶邦:實不相瞞,房光東身上有我自己的影子。我承認房國春代表的是正義的力量,也佩服他勇于挺身而出維護正義的勇氣,但我不會和他站在一邊,明確表示對他的支持。人情世故告訴我,一個從村里走出來的人,萬不可陷入村人之間的紛爭,一旦陷入就不可自拔,會造成世世代代的仇恨。房光東所選擇的立場,正是中國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在是非面前的抉擇,那就是中庸、自保和逃避。書中還有一位知識分子的形象,是曾經(jīng)被打成右派的高子明。高子明在村人的爭斗中,煽風點火,推波助瀾,發(fā)揮的是知識分子的智力優(yōu)勢。但他智力的發(fā)揮,是以自身的利益為出發(fā)點和落腳點。在書中,我借房國春的口對高子明進行了嚴肅的批評,也是對知識分子進行批評,房國春說:“你少在我面前耍小聰明,中國的很多事情就壞在你們這些愛耍小聰明的人手里。”
我愿意承認房光東身上有我的影子,是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意思。我對社會現(xiàn)實的所有批判,首先是對我自己的解剖,對我自己的批判。
讀書報:最無辜的人物是皇甫金蘭。作為一個善良而有涵養(yǎng)的女人,得不到丈夫和任何人的愛和同情,被宋建英掰斷手指,她的上吊是對丈夫、對社會、對一切的無望。為什么讓這樣一個好人死去?事實如此還是您有意設置?
劉慶邦:謝謝您注意到了皇甫金蘭這個人物,這個不起眼的人物,的確是我為之傾注了不少感情的人物。有人說整部小說沒有一個完美的人物,我說有的,皇甫金蘭就是一個無可挑剔的完美人物。她善良淳樸,任勞任怨,忍辱負重,是中國傳統(tǒng)女性的典型代表,在她身上集中體現(xiàn)了中華女性的所有美德。完美的人物往往容易受到傷害,正是這樣一位完美的人物,卻在絕望中結(jié)束了自己的生命。魯迅先生說過,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這個毀滅不是作者故意制造出來的,是社會現(xiàn)實的逼使。皇甫金蘭的自殺其實也是一種抗爭,是一種無聲的抗爭。只是這種抗爭容易被人們忽略罷了。
讀書報:房國春在泥地里回家的描寫令人動容。黃泥地是每個人離不開的土壤。它讓你眷戀,讓你無法自拔,但是很多時候也是甩不掉的牽絆。就像您在小說中所說“不動聲色的泥巴就像潛伏在地下的泥鬼一樣,伸手就把你的腳抱住”。
劉慶邦:魯迅先生的作品,致力于揭示和批判國民性中負面的東西,這是一種文化自覺,也是一種對國民高度負責的精神。我們向魯迅學習,對國民性中負面的東西也應當有清醒的認識。也許不少人都發(fā)現(xiàn)了,我們的國民性中有一種泥性,也就是糾纏性,構(gòu)陷性。這種泥性一旦爆發(fā),會形成集體性的、無意識的人性惡,有著極強的攻擊性和破壞力。回顧過去遍地涌起的匪患,還有后來的多次所謂群眾運動,都與國民性中泥性的泛濫不無關系。
以我們那里黏性極強的黃泥巴作為隱喻,并安排房國春在步步陷腳的泥巴地里摸爬滾打,讓他摔倒在泥巴地里,滾成了一頭“泥巴豬”,其寓意可想而知,說白了就不好了。因為任何隱喻都有方向性,也有局限性。
讀書報:在小說中,除了正面人物,宋建英是中國小說人物譜系是最獨特的一個。她的罵功被您寫得酣暢淋漓。您是怎么把握這個惡毒勢利的小人角色的?那些罵人的詞,是怎么想出來的?您對惡的表現(xiàn)何以會如此深刻?
劉慶邦:罵人也是一種文化,罵文化在我國源遠流長,功底深厚。我們那里有一種罵叫“罵大會”,是把罵人娛樂化了。慣于參加“罵大會”的人,三天不罵人就技癢,就著急,三天不挨罵也會受不了。罵人高手在民間,宋建英堪稱一位罵人高手的代表。有文章說柳青沒見過潑婦怎樣撒潑,故意把一盆水潑在潑婦身上,惹得潑婦把他罵了個狗血噴頭,才知道怎樣寫潑婦了。
我覺得這個辦法實在不可取。我生在農(nóng)村,在農(nóng)村長大,對農(nóng)村婦女罵人的技藝和語言比較熟悉。不過,我不能把那些罵人的話直接搬到書面上,那樣會顯得過于粗俗,不堪入目。我必須用敘述的語言,把宋建英罵人的話改造一下,轉(zhuǎn)換一下,起到刻畫人物形象的作用就可以了。
讀書報:宋建英找房國春罵戰(zhàn),村里人的圍觀,您把幾個特殊看客的心態(tài)描寫得入木三分,他們不是擔心打架,而是擔心打不起架來。這種看熱鬧的心態(tài)寫出了國民的劣根性。在寫作過程中,您對中國現(xiàn)實生活是否有新的思考?
劉慶邦:《黃泥地》里所描繪的村民對事件的圍觀,與魯迅所批判的國民的看客心理不同,它比看客的心理又進了一步,它不再是消極的看客心理,而是積極的看客心理;看客不再是冷漠的旁觀者,而是熱情的參與者;看客與爭斗的雙方不是無關,而是利益相關;這樣一來,看客不是害怕房國春和宋建英打起來,而是害怕他們打不起來。他們一旦打起來,看客們既可得到精神上的滿足,也可以獲得漁翁之利。這樣的看客更可怕。
讀書報:您的語言一向非常講究,在這部作品中,也許是情節(jié)掩蓋了語言,您覺得呢?
劉慶邦:您是說這部小說的語言不太講究嗎?不會呀,我一向重視小說的語言,對語言向來一絲不茍,哪里出語言,我的小說就往哪里走。只要語言好,小說就不會差到哪里去。現(xiàn)實中的故事五花八門,千奇百怪,我們的想象幾乎趕不上現(xiàn)實故事生產(chǎn)的步伐,我們只能在語言上下功夫,在語言上找齊。好的語言才是一個作家的看家本領。
網(wǎng)友評論
專 題


網(wǎng)上學術(shù)論壇


網(wǎng)上期刊社


博 客


網(wǎng)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