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花》2025年第2期 | 劉慶邦:不是鬧著玩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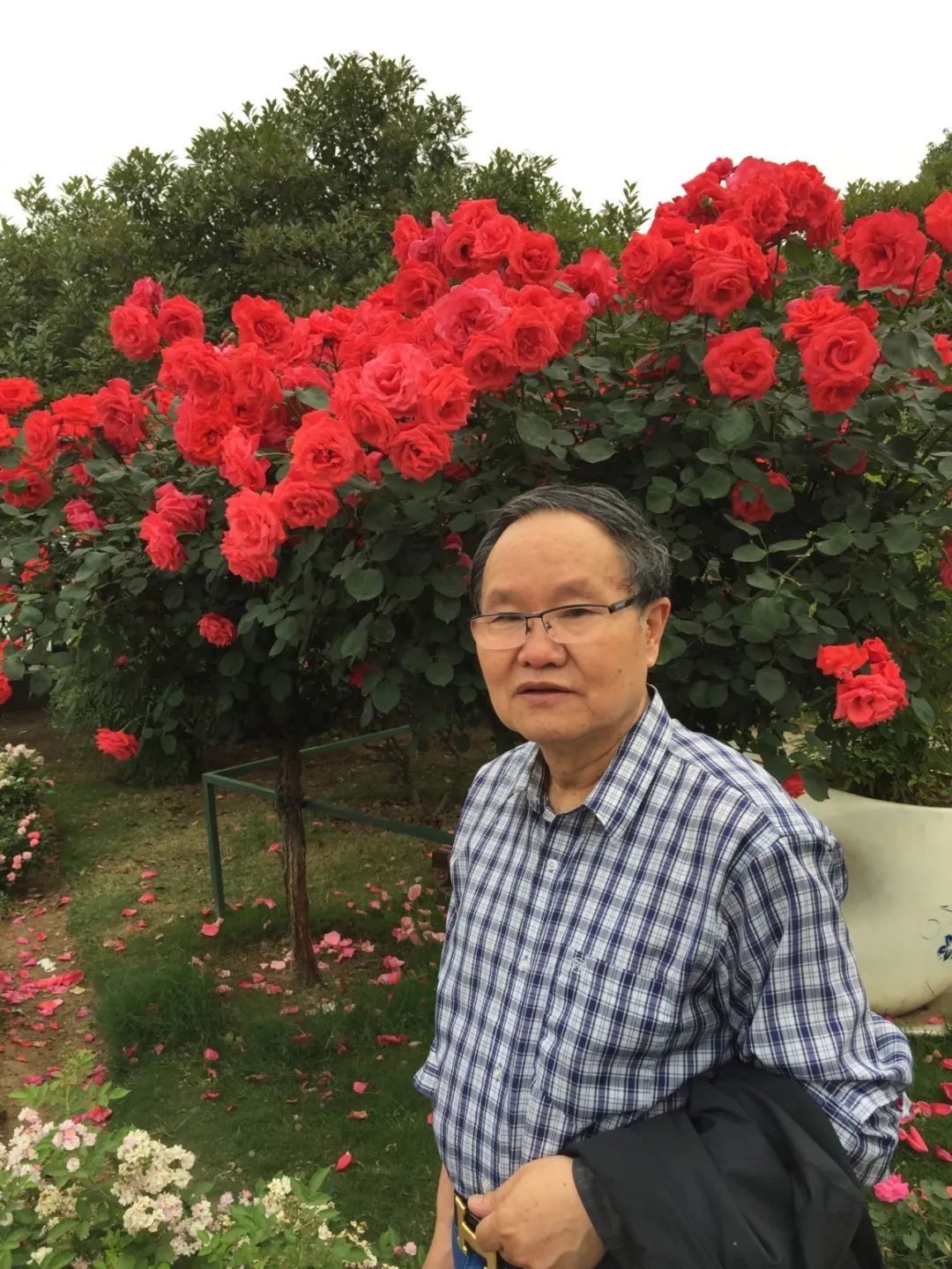
劉慶邦,1951年生于河南沈丘。著有長篇小說《斷層》《遠方詩意》《平原上的歌謠》《紅煤》《遍地月光》《黑白男女》《女工繪》《花燈調》等十四部,中短篇小說集、散文集《走窯漢》《梅妞放羊》《遍地白花》《響器》《黃花繡》《到處有道》等七十余部。《劉慶邦短篇小說編年》十二卷。短篇小說《鞋》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神木》《啞炮》獲第二屆和第四屆老舍文學獎。中篇小說《到城里去》和長篇小說《紅煤》分別獲第四屆、第五屆北京市文學藝術獎。長篇小說《遍地月光》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提名。長篇小說《黑白男女》獲首屆吳承恩長篇小說獎。長篇小說《家長》獲第二屆南丁文學獎。長篇散文《陪護母親日記》獲第二屆孫犁散文獎。曾獲北京市首屆德藝雙馨獎,首屆林斤瀾杰出短篇小說作家獎,第十屆冰心散文獎。獲《北京文學》獎十五次;《十月》文學獎七次;《小說月報》百花獎八次等。根據其小說《神木》改編的電影《盲井》獲第53屆柏林電影藝術節銀熊獎。1990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為中國煤礦作家協會名譽主席,北京作家協會原副主席,一級作家,北京市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屆政協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這個居民小區有一幫居民,先是球友,現在又變成了“驢友”。
小區公共衛生間南面有一塊空地,空地上支了三張綠色的乒乓球臺,男女乒乓球愛好者就自備球拍,在那里打將起來。單打時,他們有時男對男,有時女對女,也有時男對女;雙打時,他們打男雙,打女雙,也打混雙。他們打得乒乒乓乓,樂得笑語喧嘩,很是開心。那塊長方形的場地,四角打了鐵樁,用藍色的輕型鋼板遮擋起來。擋墻高約三米,只留東北角一個小鐵門可以進出,幾成封閉狀態。去衛生間“衛生”的人們從場地外面走過,只聞球聲,人聲,卻看不到人影。這樣一來,打球的場地就自成一統了,跟一個乒乓球俱樂部差不多。那幫越來越熟悉的球友,不但天天在“俱樂部”打球,有時一高興,還在里面烤開了肉串兒,喝開了啤酒。打乒乓球時,他們總是把敏感的小球推來擋去,不愿讓球在自己面前停住;吃肉串兒和喝啤酒時,他們就不再謙虛了,幾乎來者不拒。他們喝啤酒不用酒杯,直接舉著酒瓶說,來,走一個。他們吃肉串時,也把肉串舉起來,做得像喝酒一樣,也說走一個。他們以球結緣,以酒加油,打來打去,走來走去,弄得比球友還球友。
那,驢友又是怎么回事呢?
卻原來,那幫球友里不僅有本小區的人,還有別的小區的人;不僅有北京人,還有外地人。有一位貴州某公司駐京辦事處的副主任老周,也喜歡打球。他們的辦事處所租的房子就在小區里面,他去打球很方便。打球期間,老周禁不住向球友們夸耀,說他們貴州有全國最大的瀑布,黃果樹瀑布,有全國最大的溶洞,織金洞。還說,他們貴州有許多好吃的,小吃有腸旺面、羊肉粉等;大吃有花江狗肉,酸湯魚等。老周夸耀的次數多了,有一次吳老三就將他的軍說:您不要老饞我們的眼球,吊我們的胃口,可以請我們北京人民到你們貴州看一看嘛!老周滿口答應,可以呀,你們商量好,確定一個時間,我提前回去,在貴州恭候諸位。咱們丑話說在前頭,往返機票和住宿費你們自理。在貴州期間,我負責找車帶你們旅游,該看的著名景點,我保證讓你們都看到,該吃的美食,保證讓你們都吃到。球友們聚在一起打球容易,集體到外地旅游,就不那么容易了。他們把去貴州的話題一說再說,把出游的時間一拖再拖,直到兩年多之后,才終于商定,這年秋天的國慶節之后,錯過國慶節長假的旅游高峰,一塊兒到貴州走一趟。球友變驢友,以此為發端。
有人對驢友的說法不是很理解,認為旅游就是外出旅行和游覽,同行的人可以說成旅友,干嗎扯上四條腿的驢子呢?一說成驢友,大家不都變成驢子了嗎?這樣質疑著,他們就我看你,你看我。這一看不要緊,彼此在對方腦子里就幻化出一些驢子的形象,好像嘴巴也大了,耳朵也長了,讓人禁不住想樂。有人為驢子說好話,說驢子能爬山,能馱東西,吃得苦,耐得勞,要比人厲害,值得人類學習。還有人提前做了功課,說貴州簡稱黔,黔和驢是有聯系的,黔驢
是很有名的,赴黔當一回驢,是題中應有之義。他們一邊討論,一邊打哈哈,把哈哈打得像乒乓球一樣活蹦亂跳,仿佛已經享受到了驢友在一起的快樂。
不大高興得起來的有兩個人,一個是孫連棟,一個是喬新榮。他們生在北京,長在北京,卻從沒有出過北京。也就是說,他們從來沒有外出旅游過,從來沒有坐過飛機,更沒有去過離北京很遠的貴州。北京人手里現在有點兒閑錢了,外出旅游就成了一個熱門兒,好像只有走過幾個地方,才顯得手頭寬裕,有見識,跟上了時代的潮流。更重要的是,北京與全國是相對而言,北京是全國人民的北京,全國也是北京人的全國,作為一個北京人,如果不到全國各地走一走,就不像是真正的北京人了。而在所有的球友中,別的人都有著出京旅游的經歷,都能說出幾個值得吹牛的地方,就他們兩個搜腸刮肚,什么都說不出。既然老周熱情地向球友們發出了去貴州旅游的邀請,又有那么好的許諾,機會自然不可錯過。可是呢,孫連棟和喬新榮的表現不像別的球友那樣積極踴躍,雖說也表示會去,但他們的態度似乎有些猶豫,有些勉強。這又是為什么呢?主要原因有兩個。第一個原因,他們二人工資收入都不高,去一趟貴州,往返要買飛機票,每天住宿也要花錢,恐怕一個月的工資都不夠。這第一個原因是次要的,第二個原因才是主要的。正是第二個原因,構成了他們的心理障礙。與物質障礙相比,心理障礙似乎障得更高,礙得更實,更難以逾越。這是因為,他們前不久離了婚,正式辦理了離婚手續。雖然他們仍同居一室,仍在一個鍋里耍勺子,但他們的夫妻關系已不復存在了。他們離婚的事,球友們都知道,并且知道他們的夫妻感情并沒有破裂,離婚是出于無奈,可有離婚證書在那里證明著,當初的結婚證書已經成為了歷史。拿球友之間的關系來比喻,他們以前跟別的球友是球友,現在他們兩個人之間也是球友。別看孫連棟是男將,喬新榮是女將,在球技方面,喬新榮卻略勝一籌。他們兩個對打時,都是喬新榮讓著孫連棟一些,才偶爾能打成平手。打球的事好說,只拿著球拍子跟球干就是了,而外出旅游的事恐怕就不那么簡單了,一路走去,一天到晚在一起,他們不知道別人會怎么看待他們,會不會拿他們逗悶子。他們也不知道怎么樣對待自己,是跟以前一樣好呢,還是不一樣好呢,是不裝好呢?還是多少裝一點兒好呢?他們猶豫再三,經過再三商量,貴州還是要去。機會難得,不可錯失,這一次要是他們把好心的老周提供的機會錯過,恐怕這一輩子都沒有機會了。花錢的事要想得開,不可太心疼。錢就是用來花的,別人都舍得把錢花在旅游上,他們也不能太摳門兒。再說他們各人都有一份工作,每月都能掙到工資,利用年假把一部分錢花掉,回來再接著掙就是了。至于怎么處理他們之間的關系嘛,他們達成的共識是,外出這幾天,二人最好還是拉開適當的距離,不可表現得太親熱。親熱是兩個人私下的事,何必讓別人看見呢!外出期間暫時冷淡幾天,等回到北京再親熱就是了。
孫連棟是公交車司機,他每天所跑的固定線路,是從德勝門附近的車站到郊區昌平的一家溫泉城。一年四季,不管刮風下雨,他都是把黑色的車輪子當腿,照跑不誤。按他的說法,他閉上眼睛開車都不會走錯路。吳老三有點兒小瞧孫連棟,他說孫連棟簡直就像一頭拉磨的驢子,成天在一個磨道里轉悠,沒勁透了。
吳老三也是一名司機,他之所以在孫連棟面前有一些優越感,是因為他所在的公司是首汽集團。平日里,雖說他也開出租,也到處跑著拉活,但一到有重要會議時,他們公司的車就要應召為會議服務。服務期間,他穿上西裝,打上領帶,一下子就變得牛氣起來了。他把自己為自己豎大拇指的照片發在朋友圈里,附言是:看咱哥們兒!他給放在車前的停車牌也照了相,車牌上的黃字是廣場。他的留言是:天下廣場很多,天安門廣場全世界只有一個。
對于吳老三這樣的朋友圈,孫連棟從來不點贊。在他看來,吳老三和他,還是老舍筆下的駱駝祥子,只不過,他們手中用來勞動的家伙什兒變了,不牽駱駝了,不拉洋車了,變成了開汽車而已。你頭上又沒戴烏紗帽,身上又沒穿滾龍袍,屁股底下又沒坐八抬轎,有什么牛皮可吹的呢!
他們訂的航班,是早上七點多從首都機場第二航站樓登機,五點多就要到機場集合。從市區到機場有幾十公里,這段路至少也要留出一個鐘頭的時間量。這樣算下來,他們在凌晨三四點鐘就得起床。你看這事兒鬧的,平日的起居規律一下子給打破了,旅個游弄得跟過大年一樣。是呀是呀,大年每年都可以過一次,而去貴州旅游,是幾十年才遇上這一次,怎不讓人興奮呢!問題是每人都拉著旅行箱,有的人歲數不小了,公共交通的頭班車還沒有開始運行,分頭去機場可是不太方便哪。這時,吳老三站出來了,他說他找一個開中巴車的哥們兒,把大家往首都機場送一趟。他指定了一個時間,讓大家在乒乓球場地外面的路邊集合就行了。這好,這不錯,這可以。中巴車開進小區接大家,大家就不必為去機場的交通工具發愁了。到了機場,大家一個跟一個,也不用你找我,我找你了。
旅行團中有一個姓王的,是北京某事業單位機關辦公室的副主任。他家中養了一只虎背熊腰的巨型金毛犬,名字叫“泰森”。因泰森在小區里的名頭比他大,居民們就以泰森為主體,以他為附庸,把他叫成“泰森爸”或“泰森王”。泰森王天天都要在附近的環球貿易中心花園遛泰森,因此養成了早起的習慣。這天一大早,他提前二十分鐘就第一個來到了集合地點。天還黑著,路燈照不到的地方黑乎乎的。一只白貓從黑影里走出來,往后交錯蹬了蹬兩只后腿,走到了另一塊黑影里。天氣已經有些涼了,空氣里彌漫著秋天的氣息。趁著等人,他點燃一支煙,徑自抽起來。這個旅行團一共八個人,除了前面已經提到的四個人,還有兩位女士,和一對剛結婚的人。剛結婚的兩口子不是新人,是老人,男的七十出頭,女的六十不到,兩個都不是初婚,是再婚。與孫連棟和喬新榮相比,孫和喬是假離婚,而老郭和宋小琴是真結婚。老郭對宋小琴甚是喜歡,一會兒看不見小琴就急著找,喜歡得像一直在過蜜月一樣。他們的親密情況與孫連棟、喬新榮不敢親密的情況正好形成了對比,這個后面還會說到。
孫連棟和喬新榮走過來了,他們沒有并排走。喬新榮走在前面,孫連棟走在后面,二人手里各拉著一只帶萬向輪的旅行箱。喬新榮拉的旅行箱是大號,孫連棟拉的旅行箱是小號。他們所拉的旅行箱都有些舊,不像是新買的,像是借來的。
泰森王一眼就看出了問題,他對孫連棟說:小孫你這就不對了,你怎么讓喬新榮拉大箱子,你拉小箱子!
喬新榮先接過話,她說:沒事兒,箱子不沉,我拉得動。
這不是箱子沉不沉的問題,是一塊兒出門,男人必須照顧女人的問題。
孫連棟解釋說:我要替她拉大的,她不同意,堅持說自己的行李自己拉好一些。
她說不同意,你就當真了。女同志不同意的事兒多著呢,她們有時不過是假裝一下,你該干什么還得干。泰森王迎上前去,不由分說,把喬新榮手中的箱子提了過來,說:來,小孫不替你拉,我替你拉,讓他看看男人該怎么做。中巴車已經到位了,泰森王把喬新榮的大號旅行箱拉到車門口,就手把箱子提上了車。在把箱子往車上提時,他說:還說箱子不沉,我提著都夠沉的,里面不知道裝了多少金銀財寶。
喬新榮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說:泰森大哥笑話我,我哪里裝了什么金銀財寶,不過多帶了幾件替換的衣服。
行李箱都被放在了最后一排的座位上和座位前面的夾道里。最后一排還有一個空位,喬新榮就跟著自己的行李,自覺地坐在那個空位上。
孫連棟上車后,卻坐到了前排靠近車門那個單獨的位子上。
吳老三對孫連棟的態度不太好,他連連往后挑著手指對孫連棟說:往后坐,往后坐!
孫連棟還沒明白是怎么回事,吳老三又說:這是你應該坐的地方嗎!當司機的就是有這毛病,一上車就老是往前面打量。今天又不用你開車,你坐在前面干什么?!
孫連棟沒敢吭聲,起身到后面去了。最后一排已經沒有空位,他又不可能跟喬新榮坐在一起,他坐到倒數第二排的空座位上去了。
吳老三還沒完,他往后招著手對喬新榮說:小喬,喬新榮,你過來,你坐在這個座位上。
奇了怪了,把孫連棟攆開,卻讓她坐到那個靠前的座位上,這又是為什么?吳老三剛才對孫連棟那樣蠻橫的態度,已讓喬新榮有些不大好接受了,招罷孫連棟,吳老三又用命令的口氣招她,更讓她心生抵觸。盡管吳老三是優待她的意思,她也不想領情。她搖頭說:我不過去了,我就坐在這兒挺好的。
吳老三說:我說讓你過來,你就只管過來。今天在這個車上我說了算。
喬新榮心說:你算老幾,我干嗎非要聽你的?她仍坐著沒動,她心里想的是孫連棟,她要坐在后面陪著孫連棟。
局面有些僵住了。旅行還沒有正式開始,就像出現了僵局,這怎么辦?
打破僵局的是泰森王,他站起來說:咱們這個旅行團,要有一個團長。吳老三同志熱心為大家服務,我建議就由吳老三當這個團長,同意的請鼓掌。說罷他帶頭鼓起掌來。
誰沒鼓過掌呢?誰都會鼓掌。車廂里頓時響起了掌聲。連吳老三也在鼓掌,等于他自己也給自己投了一票。見別人都鼓了掌,孫連棟和喬新榮也跟大家一起鼓了掌。
泰森王宣布:好,全體鼓掌通過,吳團長正式走馬上任。
他接著說:喬新榮團員,你就聽從團長的指揮吧。
喬新榮如果再犯擰,再坐著不動,那就不好了,就是故意鬧別扭了。如果一開始就別別扭扭,恐怕后面的行程都不會愉快。眾目睽睽之下,喬新榮只得背著自己的小挎包,走到前面,坐在了孫連棟騰出來的位置上。她說:哎呀,太不好意思了,真讓人不好意思!坐下之后,她渾身都不自在,跟坐在針氈上差不多。她想,都是因為她與孫連棟假離婚,才鬧出了這些被動的狀況。倘若二人沒有“離婚”,還是名正言順的兩口子,她一定會和孫連棟光明正大地坐在一起,誰也別想對他們指手劃腳,誰也別想把他們分開。車開動了,趁人不注意,喬新榮回頭看了一眼孫連棟。她的意思是和孫連棟交流一下目光,給孫連棟一點安慰。目光沒交流成,因為孫連棟閉上了眼睛。中巴車開出了燈火通明的城區,在通向首都機場的快速路上疾馳,喬新榮無聲地嘆了一口氣。
在機場排隊領取登機牌和托運行李時,因孫連棟和喬新榮沒排在一起,兩個人的座位號就沒有挨在一起。而同行的老郭和宋小琴兩口子,不僅一起排隊,在領取登機牌時,老郭還特別聲明,宋小琴是他夫人,請工作人員把他倆的座位號挨在了一起。登機后,喬新榮才發現,她和泰森王的座位號挨在了一起,泰山王的座位號靠窗,她的座位號在三個座位號的中間。泰森王站起來在機艙里找孫連棟,他們的座位在過道的左側,孫連棟的座位在過道的右側,而且比較靠后,與他們的座位隔了三排。泰森王對孫連棟說:小孫,咱兩個換一下座位吧,你到前面來坐,跟小喬坐在一起。
孫連棟說:不用不用,您只管坐吧。
這不太合適吧?
沒什么不合適的。
孫連棟不跟泰森王換座位,吳老三卻說:你想換座位,咱倆換吧。
泰森王果斷拒絕,那不行。
你不是說我是團長嗎?
在車上你是團長,到飛機上就不是了。
你這不是搶班奪權嗎?你奪權奪得夠快的。
對某些人的權該奪就得及時奪,免得一朝權在手,就會產生別的想法。好了,老老實實坐下吧。
飛機在跑道上加速滑行時,由于機身震動得比較厲害,喬新榮顯得有些緊張,臉色都白了。要是孫連棟坐在她身邊,她一定會緊緊抓住孫連棟的手,以得到孫連棟的保護。此時坐在她旁邊的不是孫連棟,而是泰森王,她就不好意思向人家伸手了。沒辦法,她的兩只手只能緊緊抓住座位兩邊的扶手。
泰森王看出了喬新榮的緊張,問她:你是不是第一次坐飛機?
是。
你是不是有點害怕?
是。
放松心情,沒事的。誰第一次坐飛機都會緊張,坐的次數多了就好了。比起別的交通工具,飛機的安全系數是最高的。這會兒飛機正在穿破云層,向高處爬升,顛簸得比較厲害,等飛機飛到高空就平穩了。
謝謝您!我啥都不懂,心里一點兒底都沒有。
從小到大,從結婚到生孩子,喬新榮都是雙腳踩在地面上生活。她看見過鴿子在天上飛,燕子在天上飛,那是因為鳥們長有翅膀,所以才能飛到天上去。她只有頭發,連一根羽毛都沒有,怎么可能飛到天上去呢!人說大閨女坐轎頭一回,她是大媳婦坐飛機頭一回。當飛機飛到高空,她似乎有一種懸空的感覺,頭也空,心也空,手也空,腳也空,一點都不踏實。她不敢往窗外看,可眼角的余光還是看到了窗外的云層。那些云很白很白,恐怕比陽光下的白雪還要白。那些云也很厚,厚得重重疊疊,一點兒縫隙都不透。看到那些厚雪一樣的白云,喬新榮想到了冬天,身上似乎也有了寒意。她想回過頭看一眼孫連棟,又覺出座位的靠背比較高,就算回過頭,也看不到他。她要是站起來的話,應該能看到孫連棟,可系在小腹前的安全帶限制住了她,她站不起來。這都是假離婚造成的。倘若二人沒有離婚,他們就會像老郭和宋小琴一樣,自然而然地坐在一起,誰也別想把他們分開。要是坐在一起,他們會互相拉著手,互相照顧,并交流一下第一次坐飛機的感受。現在二人分坐在兩處,飛機在天上飛,他們跟天各一方差不多,誰也別想跟誰說話。誰都不能不承認,第一次坐飛機,會有恐懼心理,擔心飛機從天上掉下來,把自己摔死。喬新榮也難免有這樣的擔心,當飛機起飛的那一剎那,她的一顆心幾乎提到了嗓子眼。天哪,就算是摔死,也應該和孫連棟死在一塊,兩個人畢竟做了二十多年的夫妻啊!要是連死都不能死在一塊,真讓人不甘心哪!
還好,飛機什么事都沒出,按時平安順利地降落在貴陽龍洞堡國際機場。守信又守時的老周,已提前在機場的出口等候。旅行團的四男四女一從出口出來,老周就把他們接到一輛中巴車上,拉到了市里事先聯系好的酒店。到了酒店大廳的服務臺,他們須一一出示身份證,刷臉,方可入住。為了節省住宿費用,他們已提前商量好了,每個人都不住單間,每兩個人合住一個標間,也就是雙人間。八個人怎么分配呢?老郭和宋小琴當然合住一個房間。他們都知道,老郭存款多,退休工資高,老伴兒病逝后,經人介紹認識了宋小琴。宋小琴沒有了丈夫,退休金低,還要接濟孩子,經濟上比較拮據。而老郭一見宋小琴,個子高高的,皮膚白白的,性格靜靜的,很有風韻的樣子,一下子就鐘情上了。二人一結婚,老郭上來就給宋小琴的銀行卡上轉了五十萬元。宋小琴哪里見過這么多錢,感動得都快要哭了,連說不要不要。老郭說咱們成了兩口子,你就是我,我就是你,錢的事就不要客氣了,這些錢你先花著,不夠花我再給你。別人都說宋小琴遇上了貴人,宋小琴對自己的再婚也很滿意。一起出行,宋小琴把老郭照顧得很好,稱得上形影不離,有求必應。泰森王和吳老三住一個房間。衛女士和桂女士住一個房間。等以上三個房間入住手續辦理完了,孫連棟和喬新榮才上前去辦理。雖說他們辦理了離婚手續,但為了省錢,二人還是要住在一起。好在辦理入住手續時,酒店服務員只看身份證,不看結婚證,入住倒是不成問題。可不知為什么,當服務員安排他們住一個房間時,孫連棟和喬新榮還是有點兒心虛,像做了什么不正當的事情一樣。他們兩個之所以等到最后才辦手續,是想等其他人辦完手續離開他們再辦,以免服務員問他們是不是夫妻,他們不想當著熟人說假話。然而,東道主老周建議,等大家都辦完了入住手續,他再送大家一塊兒乘電梯上樓。所以,在孫連棟和喬新榮辦入住手續時,別的人都在一旁等著他們倆。這時,多嘴多舌的吳老三說了一句話,他對孫連棟說:小孫,你們兩個現在可是非法同居呀!
哪壺不開提哪壺,這話是敏感的。孫連棟聽見了吳老三說的話,他沒敢回頭看吳老三,更不敢接話。
衛女士知道這里不是鬧著玩的地方,她小聲對吳老三說:老三,你瞎說什么呢?
吳老三犯犟:怎么了?我瞎說了嗎?難道我說的不是實話嗎?
說實話也得分地方,也得看在哪里說。
吳老三不服:實話在哪里都可以說,我看這地方挺好。
衛女士也不是好惹的,她有些生氣了,質問吳老三說:你是什么意思嘛?你是要把他們兩個拆開,一人住一個房間嗎?要是一人住一個房間,住宿費你掏嗎?
吳老三嘁了一下,這才不說話了。
下午,老周還是派那輛中巴車,把旅行團的一行人拉到了離貴陽不太遠的著名的黃果樹瀑布。瀑布真高大,整個瀑布是從山頭上跌落下來的,沒有三千尺,也有三百尺,像是傾瀉而下的銀河。瀑布落在下面的深潭里轟轟作響,蓋住了人世間的所有聲音。這樣的轟鳴一點兒都不讓人覺得鬧,反而讓人覺得無比寧靜。瀑布真寬展,左邊是瀑布,右邊是瀑布,中間還是瀑布。那白布一樣密不透風的瀑布,似乎把整座青山都遮蓋了起來,白得月月復年年,地久天又長。這瀑布真神奇,后面有一條被瀑布遮蔽的山路,游人可以從小路上穿過。這樣一來,人們就可以在瀑布后面實現與瀑布的近距離接觸,既可以感受到瀑布散發的陣陣爽氣,又可以感受到瀑布在手上臉上飛珠濺玉。更為難得的是,由于瀑布的遮擋,游人像是走進了傳說中的龍宮,進入了另外一個世界。怪不得人們吃好了,穿好了,還不滿足,還要外出旅游,旅游就是好啊,有了旅游,才不枉在人世上走一遭啊!
飛流直下的巨大瀑布下面還有寬闊的水潭,水潭對面有近水的平臺,人們可以站在平臺上觀瀑,還可以站在平臺上以瀑布為背景照相。游人很多,照相的人也很多,無人不和瀑布合影,無人不“笑一笑”。老郭給宋小琴照,宋小琴給老郭照,夫妻互相照罷,還要請別人給他們照合影。孫連棟沒有和喬新榮走在一起,他和泰森王、吳老三一起觀景。喬新榮和衛姐、桂姐一塊兒活動。衛姐看出了孫連棟和喬新榮的不自然,也看出了他們內心的掙扎。對于兩個人假離婚的原因,衛姐知道一些。他們原本是一對相親相愛的好夫妻,只是由于生活所迫,出于無奈,才不得不辦理了離婚手續。衛姐對他們目前的處境很是同情,她主動給喬新榮照相,主動給孫連棟照相,還把孫連棟喊到喬新榮身邊,說給他們兩個照一張合影。
孫連棟和喬新榮是想合一個影,但他們在猶豫,也不好意思張口請別人給他們照合影。衛姐主動提出給他們照合影,二人都有些感動。孫連棟和喬新榮互相看了看,并看了看衛姐,站到了一起。
衛姐說:好,靠近一些,拉起手來,笑一笑,笑得自然一些。既然出來了,就好好玩,什么都不要多想。
孫連棟和喬新榮在衛姐的安排下,靠近了,拉手了,也笑了,但笑得有些勉強。
晚上回到酒店,吃過晚飯,洗過澡,孫連棟和喬新榮分別躺在兩張床上。孫連棟躺的是靠門口的那張床,喬新榮躺的是靠窗口的那張床。在他們北京的家里,只有一間房,房子里只有一張大床。雖說表面上離婚了,那是離給別人看的,實際上喬新榮是離婚不離家,兩個人每天還是同住一間房,同睡一張床,照樣過夫妻生活。說起來,他們離婚的原因很簡單,簡單得簡直不值一提。喬新榮作為紡織廠的下崗女工,在街道上找到了一份工作,每月可以掙將近兩千塊錢。忽一日,街道上的人通知她,這份工作不讓她繼續干了,要讓家庭平均收入達不到最低水平的人干。她丈夫是開公交車的司機,每月可以掙四千多塊錢工資。他們的女兒已嫁人,一切都不用他們負擔。把她丈夫的工資平均到兩個人頭上,已超過了最低收入水平。喬新榮一聽要辭退她,就有些著急,她很喜歡那份工作,也很喜歡那份工資。要是沒了工作,她每天干什么呢?要是沒了那份工資,收入一下子就少了一大塊,花錢就不那么方便了。這時有人給她出主意,讓她以夫妻感情破裂為由提出和丈夫離婚,并凈身出戶,那樣才有可能保住那份工作。于是,經過和孫連棟反復商量,他們真的辦理了離婚手續,并以離婚證為證明,保住了那份工作。喬新榮在床上四肢伸展了一下,說這床不錯,很軟乎。孫連棟說:怪不得大家都愿意出來旅游,旅游是挺好玩的。喬新榮說到,在瀑布那里照相的時候,吳老三想和她合一個影,她沒和他合。孫連棟說:不和他合影是對的,他以為咱倆是真的離婚了,就想打你的主意。你一定要離他遠點,千萬別讓他占到你的便宜。喬新榮說:看他色瞇瞇的那副德性,想瞎他的鼻子!孫連棟想到喬新榮的床上睡一會兒,喬新榮也想到孫連棟的床上睡一會兒。但他們都記著出來前說好的在外面暫不親熱的話,就沒有互相串床。
旅游起來,總是讓人覺得時間過得很慢,也很快。說慢,是因在北京時,呼嚕一天,呼嚕一天,沒留下什么痕跡,十天半個月就過去了。而出來旅游呢,新風景一處接一處,每天看的都是好風景。腦子里裝的風景一多,好像時間被拉長了,一天賽過好幾天。說很快,是說好風景還沒看夠呢,預定的旅游時間就要結束了。
這天晚上,老周做東請客,為大家送行。老周找了一家專門做酸湯魚的農家樂餐館,請北京的朋友們吃酸湯魚。酸湯柿紅色,微辣,味道渾厚,讓人一聞就滿口生津。魚是剛出水的烏江魚,下進滾湯里一煮,魚肉變白,白得像剝開的蒜瓣一樣。每人面前一只小碗,小碗里還有秘制的蘸料。一條幾斤重的烏江魚,很快就被八九雙烏木長筷子夾完了。人人都說,鮮美,好吃,夠意思!一條魚吃完,又下進沸騰的酸湯里一條。老周說:今天晚上大家放開吃,盡情地喝,來他個一醉方休。
老周說的盡情地喝,不是喝酸湯,是請大家喝酒,喝貴州當地產的醬香酒。老周稱大家為首都的朋友,他站起來向首都的朋友們敬酒。敬過三杯,他起身離座,給每個朋友一一敬酒。敬酒期間,他透露了一個消息,說他這次回來,就不再去北京上班了,因為他快要退休了。他一再感謝他在北京工作期間各位朋友對他的友好和關照。老周這樣說,也是跟大家說再見的意思。再見的話好說,能不能真的再見面就不一定了。見老周有些動感情,大家都動了感情。于是,所有“首都的朋友”都向貴州的朋友致謝敬酒,氣氛一下子沸騰起來,比鍋里的酸湯沸騰得還厲害。老郭說,他和夫人共同向老周敬酒。泰森王代表全團向老周敬酒,他敬老周一杯,自己喝兩杯。吳老三不甘示弱,他敬老周一杯,自己連喝三杯。
吳老三喝得有些多了,引發了后面的不愉快。他提出要和喬新榮喝一杯酒。
喬新榮不喝,她說她喝酒不行。
吳老三說:小孫跟你喝,你行,怎么到我這兒就不行了?
小孫是小孫,你是你。
這杯酒今天你一定要喝,不喝就是卷我的面子,就是看不起我。
喬新榮求救似的看著孫連棟。
孫連棟的臉也紅了,紅得像熟透的紅高粱。他對喬新榮說:不要搭理他!
吳老三不干了,他指著孫連棟說:我告訴你,你和喬新榮同居是非法的,我一個報警電話,警察就會來抓你。
有種你打電話呀,你讓警察來抓我呀!
我再告訴你,喬新榮以前是你的專車,她和你離了婚,現在就成了公共汽車。
孫連棟本人就是開公共汽車的,他懂得把一個女人說成公共汽車是啥意思。這話把孫連棟徹底惹翻了,他說:你老婆才是“公共汽車”呢,你找抽呢?
眼看兩個人要動手打起來,眾人上前,連吼帶拽,才制止了有可能發生的斗毆事件。
一場歡送晚宴就這樣不歡而散了。
回到酒店,孫連棟和喬新榮還是一人睡一張床。半夜里,孫連棟聽見喬新榮在嚶嚶地哭。
孫連棟也一直沒睡著,他說:哭什么哭,回到北京咱們就復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