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G.H.受難曲》:五個蟑螂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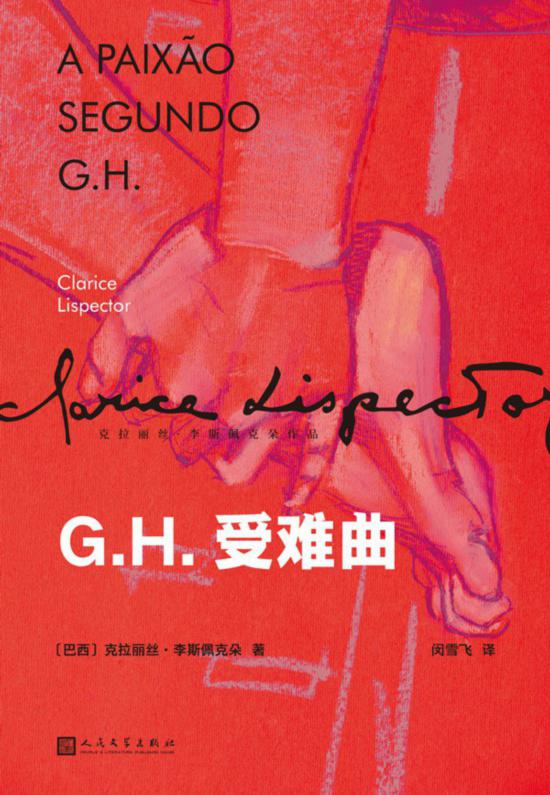
1964年,巴西作家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出版了《G.H.受難曲》,這是一部關于“蟑螂”的小說,以第一人稱“我”來展開敘述,是作家文學生涯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小說頗具神秘性,被視為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最難以解讀的作品。但是,如果參考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另一篇“蟑螂小說”《第五個故事》(收入《隱秘的幸福》小說集)的結構,那么這個故事也許可以擁有五種不同的讀解方式:
第一個故事:存在與虛無
G.H.是一位業余雕塑家,住在大樓頂層的豪華公寓里。她是小說的敘述者,也是書中人物。她并沒有透露真實姓名,而是自稱“G.H.”,即她名字的首字母。G.H.歸屬于那個可以將自己的名字刻在行李箱上的群體,這些字母是她中產階級光鮮亮麗生活的確鑿證明。她將行李箱存放于走廊盡頭的小房間里,那里是剛剛辭職的女傭的居所。為了維護中產階級典型生活的整飭與有序,G.H.決定整理這個房間,然而,在關上衣柜門的那一刻,她壓死了一只試圖逃出的蟑螂,“一只很老的蟑螂,仿佛從遠古而來”。這本是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卻成為了G.H.展開一場本體論體驗的契機。這場體驗令她原有的世界轟然倒塌,將她帶離日常生活的時間和空間坐標。
在對蟑螂的觀察中,G.H.感受到一種不可抗拒的召喚,渴望與她所看到的那只被壓扁的昆蟲產生原型認同:“蟑螂是純粹的誘惑。纖毛,纖毛顫動著發出召喚。我也一樣,我慢慢地化約成不可化約的我,我也一樣擁有成千上萬根顫動的纖毛,以這些纖毛,我在前行,我,原生動物,單純的蛋白質。”G.H.渴望超越物質的界限,卻不得不面對現實的殘酷。這種愿望與現實之間的矛盾使她不斷犧牲自己對“正常”生活的期望,追求更深層次的存在意義:“如何解釋我最大的恐懼正是關乎于:存在?然而并沒有另一條路。如何解釋我最大的恐懼正是活其所是?如何解釋我無法忍受觀看,只是因為生命并非如我所想,而是另一種樣子——仿佛我之前知道什么是生活一般!為什么觀看成了至大的無序?”這種劇烈而深刻的內心沖突,某種程度上,構成了一種現象學意義上的存在探索。
第二個故事:生與死,或世界的起源
G.H.殺死了一只蟑螂。然而,她發現,那只蟑螂,盡管從中部切斷,但依然活著。與這只雖瀕死但又堅強活著的昆蟲的對視造成了G.H.的痛苦:“面對這只沾染塵埃的生物,它在看著我。拿走我看到的東西:因為我以如此痛苦如此駭然如此無辜的局促看到了那一切,我看到的是生命在看著我。”G.H.的痛苦來自于她直面的并非僅僅是蟑螂,而是死亡本身,從而激起了她對生命脆弱性的反思,也是對人類命運的反思。
“蟑螂比我早了幾千年,也比恐龍早很多。”考慮到蟑螂攜帶的時間特性,或許可以說,G.H.殺死的不僅是一只蟑螂,而是線性歷史時間。凝視著這只存續遠比人類更久遠的物種,G.H.踏上了一場內心旅程,返回到數千年前:“幾百年又幾百年,我跌落進一片淤泥中——那片淤泥,不是已經干涸的淤泥,而是濕潤的依然鮮活的淤泥,那片淤泥中,以一種無可忍受的緩慢,我的同一性的根脈搖曳著。”G.H.希望去追溯的不僅是自身存在的本源,更是萬物的本源,即《星辰時刻》中言說的“前史之前尚有前史的前史”。
而且,蟑螂在遭受致命的一擊之下依然頑強地活著,G.H.因此意識到生命與死亡是一體的:“我的生命也同死亡一樣連綿不絕。生命太過連綿不絕,因此我們將它分為階段,其中一個階段我們稱之為死亡。”生命隱含著死亡,而死亡又內在于生命,物質具有生機勃勃的自我決定能力。蟑螂流出了那團白色的“生命物質”既代表了生命的延續,也象征著死亡的不可避免。G.H.無法抵御誘惑,在如受難一般的象征性儀式中,她吃下了這團物質,從此,生與死結合在一起,或者說,物質的消亡與精神的尋求之間建立了一種連接。而當死亡不是終結而是新生的起點之時,整個故事便成為了在毀滅中創造的場景,正如G.H.說:“恐懼將成為我的責任,直到完成變身,直到恐懼變成光亮。”
第三個故事:犧牲與拯救
G.H.殺死了一只蟑螂。這只蟑螂流出了白色的“生命物質”。蟑螂與這團“生命物質”的存在對于G.H.既是危險又是誘惑,引發了她強烈的恐懼與欲望,這種矛盾的情感充分體現于書名中的“Paix?o”(Passion)一詞中。這個詞具有雙重意義:既可以是人的激情,也可以是宗教中的受難,二者統一于巨大的痛苦中所蘊藏的巨大的喜悅。這樣,“吃下蟑螂”就變成了如同基督受難一般的犧牲與拯救的故事。實際上,這并非是克拉麗絲第一次“效法基督”。在短篇小說《效法玫瑰》(收入《家庭紐帶》)中,克拉麗絲已經書寫了一個以玫瑰為媒介的“效法基督”的故事。主人公勞拉在少女時代已經讀過了《效法基督》一書,但是其行為僅僅停留在機械地模仿外部強加的“善”,最終導致了她的精神崩潰。勞拉受到玫瑰誘惑,一心占有玫瑰,但是在對表面性完美的放棄中,最終以嚴酷的自我犧牲,實現了自我的救贖。
基督的受難以復活為終結,而G.H.的受難暗示了個人的蛻變與內在的重生。克拉麗絲將強調信仰與救贖整體性的基督受難故事轉化為G.H.的個體的心理探索,將一個線性的、有著明確的敘事結構與目的的故事轉化為更為碎片化和內省的個人思考與敘述。G.H.要踏上的是一段坎坷而痛苦的旅程,這場受難需要犧牲外在和表面,以便讓內在和本質浮現出來。作為最接近宇宙起源的物種,蟑螂是G.H.這場受難之旅中理想的伴侶和媒介。一個人吞下從被壓扁的昆蟲體內流出的白色物質是痛苦的,但G.H.必須克服這種行為造成的厭惡和惡心,因為超越痛苦是她獲得救贖與啟示的前提:“自身之中的救贖是指我將蟑螂的那團白色物質放入口中。”當她最終吃下這團白色物質之時,生命物質與神圣發生了共融,這是一個完全缺席與完全在場的時刻,個體的虛無化最終使其真正被吸納到“萬物”之中。
第四個故事:不潔之物
G.H.壓死了一只蟑螂。在克拉麗絲的定義中,蟑螂是一種“自然動物”。所謂自然動物,就是“既不是請來的也不是買來的動物”,這個定義下的動物主要為蟑螂和老鼠,顯然是兩種難以讓普通人產生好感的生物,或者說,兩種不可能融入人類價值體系的動物。對于克拉麗絲,與老鼠與蟑螂的接觸意味著“觸碰不潔之物,犯了禁忌”。這種對于不潔之物的敏感,顯然與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的猶太人身份有關。人類排斥“不潔之物”,而“不潔之物”也拒絕馴化,因此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生態,擾亂了人類與世界的秩序關系。從禁忌出發,克拉麗絲處理著人類無意或故意忽視的真實存在,意圖獲得出離人類中心主義的更大自由。
然而,克拉麗絲對于蟑螂和老鼠的關注,并非僅僅是倡導人類與動物和平共處的“后人類”主張,而且蘊含了對社會底層和被排斥個體的思考。在《星辰時刻》中,貧窮的瑪卡貝婭與老鼠形成了類比關系,共同居住在臟污的阿克雷大街,成為了敘述者羅德里格理想世界的對立面;而在G.H.的故事里,蟑螂代表被社會忽視或邊緣化的個體,有罪的“不潔之人”,是克拉麗絲必須面對的“他者”。
1964年,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發表了《米納斯人》(Mineirinho)一文,主人公是一個名叫若澤·米蘭達·羅薩的盜匪,因為出生于米納斯州,得了個“米納斯人”的諢名。“米納斯人”犯案累累:搶劫、襲警、三次越獄,傳說中有七條命,1962年5月1日凌晨,警察射出的十三發子彈結束了“米納斯人”罪惡的一生。
這讓克拉麗絲陷入了思考,即便是一個罪無可恕的盜匪,十三槍是不是也太過越界?她這樣寫道:“我聽到第一聲和第二聲槍響時感到安全的寬慰,第三聲時我警醒起來,第四聲讓我不安,第五聲和第六聲讓我感到羞恥,第七聲和第八聲讓我心跳加速充滿恐懼,第九聲和第十聲時我的嘴唇顫抖,第十一聲時我驚恐地呼喊上帝的名字,第十二聲時我呼喚我的兄弟。第十三聲殺死了我,因為我就是那個他者。因為我想成為那個他者。”
盡管克拉麗絲從未明言,但是,1962年發表的《第五個故事》,五次殺死蟑螂的故事,應該與“米納斯人”的十三次死亡有所關聯,或許正因為此,克拉麗絲將欲語還休的第五個故事命名為“萊布尼茨和波利尼西亞之愛的超驗性”。面對不潔之物與不潔之人,克拉麗絲依然希望給予他們一個愛的結局,殺戮的故事突轉為她為她所愛的母雞所寫的《愛的故事》(收于《隱秘的幸福》)。
書寫這只被壓扁的蟑螂之時,克拉麗絲/G.H.或許想到了黑皮膚的女仆,她居住在儲藏室中,那里是這座豪華公寓的貧民窟,她與蟑螂為伍,就像瑪卡貝婭居住于臟污的老鼠橫行的阿克雷大街上。在對蟑螂與“米納斯人”的同情和認同中,克拉麗絲/G.H.意識到自己的存在不僅僅是個體的,而是與他者的命運緊密相連。對他者的認同使她愿意承擔更多的痛苦和犧牲,心甘情愿地吃下那只骯臟的蟑螂。
第五個故事:語言與寂靜
業余雕塑家G.H.壓死了一只蟑螂。而在《第五個故事》中,克拉麗絲一度將死去的蟑螂命名為“雕像”。雕像是靜寂的,當克拉麗絲為她的女主角選擇“雕塑家”這個藝術身份之時,就已經決定了她會使用靜寂——而不是語言——去表達她的思想,更確切地說,不去表達她的思想。因此,這場受難也是語言層面的:“在這場找尋開始之時,我完全不知道哪一種語言將慢慢地向我顯現,以便有一天我能夠抵達君士坦丁堡。”在敘述過程中,她反復遭遇語言的局限性,盡管十分努力,卻發現根本無法完全傳達。當聲音一次次鎩羽,她“第一次聽到了自身的靜寂、其他人的靜寂和事物的靜寂,并接受它,作為可能的語言”。
G.H.的體驗超越于語言,人類語言無法完全描述,在與終極真實的偉大相遇時刻,在書寫的末尾,G.H.那宇宙間微不足道的“我”被傳送到無限的“萬物”,而她依然無法理解,依然不知道在講什么:“我永遠不會明白我要說什么。因為我如何說出而不讓詞語對我撒謊?我只能這樣羞澀地說出:生命就是我。生命就是我,我不知道我在說什么。因此,我愛。”
靜寂,或沉默,或對理解和語言的放棄,是G.H.精神冒險的終點,這場冒險從惡心開始,最終達到絕對的狂喜,無差別地指向虛無,“唯有通過我的語言的失敗,不可言說才能最終屬于我”。
(作者系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本書譯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