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潮”訪談丨楊天天:寫作是一座連結自我和現(xiàn)實世界的橋梁

《人民文學》“新浪潮”欄目自開設以來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現(xiàn)已成為雜志的品牌之一。此欄目的作者均系首次在《人民文學》發(fā)表作品。今年,中國作家網(wǎng)與《人民文學》雜志共同推出“新浪潮”作家觀察專題,作家訪談和相關視頻在中國作家網(wǎng)網(wǎng)站和各新媒體平臺、《人民文學》雜志各媒體平臺推出。繼第一期12位青年作家之后,自即日起,我們將陸續(xù)推出第二期12位作家:七堇年、 龔萬瑩、朱強、李知展、何榮、王姝蘄、傅煒如、葉燕蘭、李唐、楊天天、康雪、 吳清緣,敬請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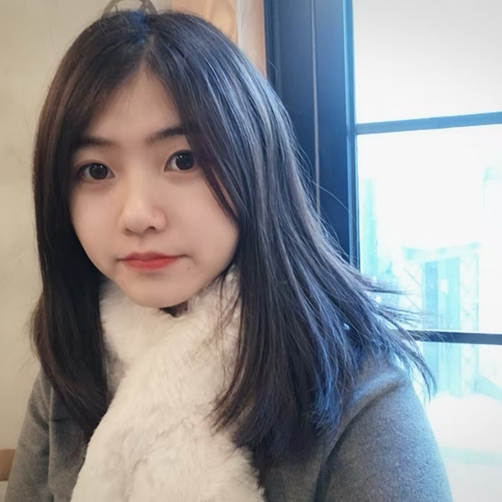
楊天天,1995年生于江蘇南通,江蘇省作家協(xié)會簽約作家,中國作協(xié)會員,揚州大學文學博士在讀。有小說發(fā)表于《人民文學》《青年文學》等。
楊天天是一名95后青年作家,近年來在許多重要純文學刊物上,發(fā)表了一系列中短篇文學作品,這些作品立足于女性視角,探討親情、愛情等多重關系,并且沿著歷史脈絡,勾勒出現(xiàn)實,也富有對未來的多重意象;她的作品節(jié)奏迅速,語言簡潔明快,頗有影像之感,情節(jié)中充滿了平靜下的波瀾,以及驟然的反轉(zhuǎn),較有吸引力,充滿時代感,好看,且優(yōu)美,贏得了眾多讀者的喜愛。
尹超:楊天天你好!感謝你接受我們的訪談。你是95后,近年來在《人民文學》《青年文學》《湖南文學》《山西文學》《廣州文藝》發(fā)表了一系列精彩的小說,成為受到文學界關注的一顆青年文學新星,在這里,想問問你,你是如何走上寫作這條道路的?其中有沒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
楊天天:我是18年左右開始寫小說的。雖然以前上高中的時候,偶爾會忙里偷閑寫一些現(xiàn)在看來不知所云的小故事,但是去構思一個邏輯、情節(jié)、結構完整的小說還是第一次。再后來,就一直不斷地寫下去了。我非常感謝在這個過程中給予支持和鼓勵的編輯老師們,我是一個很容易內(nèi)耗和自我懷疑的人,在我寫作初期,時常有老師鼓勵我說,你寫得很不錯,一定要堅持寫下去。這句話在當時對一個初次嘗試寫作的年輕人而言,具有莫大的力量,無論好壞,我就這樣寫到了現(xiàn)在。
就我個人而言,我是一個很抗拒暴露自我的人。因為從小性格內(nèi)向,所以每次需要自我介紹的場合,我都會特別緊張不安,尤其是念出自己名字的那一刻,總會有一種很別扭的感覺。寫作對我來說是一種釋放,如同一座連結著自我和現(xiàn)實世界的橋梁。它讓我逐漸意識到,我們其實可以擁有多種不同的表達方式,通過文字去袒露自己,會讓我覺得自在很多,就好像那些無法言說又渴望被聽到的聲音,終于有了一個落腳的地方。
尹超:你的創(chuàng)作,大多數(shù)是寫家庭,寫女性,寫親情的,寫上一輩,以及上一輩和自我之間的矛盾沖突,有很強的戲劇風格,節(jié)奏也很快,還有意想不到的反轉(zhuǎn),有時候讓人感覺很鄉(xiāng)土,有時候又有美劇的炫酷,其中伴隨著90年代特有的時代背景,所以呈現(xiàn)出一種新時代新文學的鄉(xiāng)土敘事之感,你覺得這個評價對嗎,你是如何平衡這些元素和風格的雜糅的呢?
楊天天:在我看來,每一種評價都是讀者在小說中讀到的對自身既往經(jīng)驗的投射,以及對現(xiàn)實生活的一種想象和理解。某種意義上,創(chuàng)作也是讀者和寫作者之間的一種雙向的互動。鄉(xiāng)土敘事是一個大的文學概念,我想要呈現(xiàn)的還是具體的人和事。比如《六月河流淌》講的是一個村莊的慢慢消逝,但是它在現(xiàn)實中映射的仍然是人的老去和離開。包括您所說的這些元素,其實并不是我刻意加上去的,很多時候是一種直覺,它來源于我熟悉的現(xiàn)實生活。記得有一次和奶奶打電話,聊到村里一個大家都叫他“小強”的老人前不久去世了,我當時很驚訝,因為印象中小強還算年輕。我奶奶說,你覺得他年輕,是因為從你記事起,就一直聽到大家叫他小強,你就總以為他還是以前的樣子,事實上他已經(jīng)八十多歲,早就不年輕了。末了她還說了一句很有文學性的話,小強打不死,可是卻悄悄老死了。那一剎那我心里有一種觸動,在我看來,這是一個生活和文學的界限模糊的時刻,這里面包含了很多動人的東西,包括想象、隱喻和超越現(xiàn)實的指認。很多時候,我首先要做的就是捕捉這樣的時刻,然后再不斷往里填充新的東西,讓它變得豐滿。
尹超:語言是作者創(chuàng)作的基石和標志,你的語言給人短促、干凈,又準確的感覺,呈現(xiàn)出獨有的語言特色,在創(chuàng)作中,你是如何形成這種語言風格的,你平時如何鍛煉自己的文學語言?
楊天天:我研究生讀的專業(yè)是漢語國際教育,除了需要具備語言學方面的知識之外,還需要有一定的教學經(jīng)驗積累。我在漢語教學的過程中,時常感到語言的傳遞者和接收者之間交流貫通的重要性,不管是母語還是教學用語,精準地傳達自己的想法,并且讓表達對象也能理解你的想法至關重要。就像喬姆斯基講的,語言是一個復雜的混沌,而我們要做的,就是從中提煉最核心的部分。
談回寫作,我在塑造人物、設計人物對話的時候,會格外重視她們所處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和生活經(jīng)歷。我很在意小說中人物語言是否真實這個問題,所以我會在寫作時先在心里默默演練一遍,想象我自己就是小說中的這個人物,代替她去參與對話,盡可能地安排適合她的語言。包括我自己去看一些權威作者的作品,如果他筆下的人物語言和這個人物本身不貼,那么不管他的情節(jié)設計地多么巧妙,在我心里都不會是一部非常完美的作品。我個人非常喜歡艾麗斯·沃克的小說,她筆下的視角轉(zhuǎn)換、人物對話都非常地恰到好處,有一種近乎蠻橫的原始力量,我在閱讀時會產(chǎn)生很強烈的共情感。
尹超:你的多部小說里,常以姥姥、母親、奶奶、妹妹等這些女性為主要角色,比如《鼠婦》《水蛭》《到海邊去》《六月河流淌》《淺命》《蝴蝶之眼》等等,女性的形象塑造完整,也特別,而且蘊含著多重的心理分析,但對男性角色的塑造較少,你認為這算是新女性文學的一種創(chuàng)作方式嗎?你對此有什么樣的看法?
楊天天:我個人覺得,女性文學其實沒有新舊之分。“女性文學”作為一個文學概念,最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出現(xiàn),在20世紀80年代重新浮出地表,一直走到今天,它被賦予的具體的時代意義和內(nèi)涵是不斷變化發(fā)展的。當然對這一概念的界定在學界存在有許多爭論,只能說它是一個不斷深化和明晰的過程。但有一點始終是確定的,不是所有女性作為主體的書寫,都可以被稱作是女性文學。
就我自身而言,我并不避諱,或者說否定“女性寫作者”這個身份,我不認為它是對我的一種限定或者標簽。相反,我把它看作我自身主體的一部分。過去女作家,比如簡·奧斯汀、瑪麗·雪萊以及瑪麗·安·尹萬斯,也就是我們熟知的喬治·艾略特,她們采用匿名或者化名的方式發(fā)表作品。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許多女性寫作者都曾在公開場合拒絕指認自己書寫中的性別姿態(tài),這其中既有她們?yōu)榱藬[脫一些刻板印象所做的努力,又隱含了對自己的性別意識的不安與否定。女性文學走到今天,我很珍惜和愛護女性作家這個身份,這也是我一直堅持用本名發(fā)表作品的原因,我有一種被看見的野心。但這并不代表我會在寫作中去刻意美化和迎合什么,相反,我更加注重去描繪一些脆弱的、易碎的東西。至于男性角色的敘述較少的問題,可能是因為我的小說更多時候側(cè)重于講述女性處境,所以有些讀者會有這樣的感覺。
尹超:你是如何來塑造小說里的人物角色的,她們在現(xiàn)實生活中有原型嗎?
楊天天:這個問題其實幾乎每一個寫作者,包括我自己,都會被問到。但事實上,在你準備構思一篇小說的那一刻,虛構就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在塑造人物的時候,肯定多多少少會有生活中熟悉的影子,那是我自己現(xiàn)實生活的一部分。而當我真正去書寫時,這些人物的個性特征、生活經(jīng)歷都會在作品中被整合、打散、再整合,所以說我的小說中某一個人物是取材于生活中特定的人,這種說法對這個人來講好像不是很公平。比如在《水蛭》中我寫了一個令人窒息的母親,在我的真實生活中,也的確存在許多控制欲很強的母親,但是沒有這么夸張的。我更多的時候還是在想象,想象這個人物的成長背景、心路歷程,以及發(fā)生在她身上的種種沖突和變化。
尹超:你在平時的生活中如何尋找創(chuàng)作靈感?你寫作的規(guī)律和計劃是怎樣的呢?另外,你的創(chuàng)作力旺盛,且有較強的綜合性,能把過去的生活,現(xiàn)在的生活,都寫得極為真實,貼切,到位,你是如何駕馭這些創(chuàng)作素材的呢?當遇到創(chuàng)作瓶頸的時候,你如何調(diào)整自己的狀態(tài)?
楊天天:我覺得是兩方面的積累吧,一方面是閱讀大量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一方面是調(diào)動本身的生活經(jīng)驗。一般在開始寫作之前,我會讀一兩部短篇小說集找找語感,然后再開始動筆。一旦開始寫作,我就會盡量一口氣寫完,然后把它放在一邊,靜置兩三個月甚至更久,然后再開始修改。那時候去看這篇小說,往往會有很多當時沒有的新的感覺。
當然,也會有遇到瓶頸,實在無法繼續(xù)的時候。我會允許自己放空幾天,完全不去想寫作的事,出去和朋友聚會,看一些和我要寫的東西無關的電影、書籍,或者去旅游,讓自己處于和創(chuàng)作時完全不同的環(huán)境中。其實我每次寫東西,都會處于非常矛盾的狀態(tài),一邊寫一邊自我懷疑,焦慮也是常有的事,我能做的就是盡量不讓這種焦慮占據(jù)我的全部。其實作者和她的作品之間是需要一些緣分和連結的,有時候可能你的構思、想法都很好,但就是沒辦法完成這篇小說,那就說明你還沒有做好足夠的準備去駕馭這個題材。我的文件夾里有許多完成了一半甚至更少的廢稿,我把它看作一種練習,或者說一種準備。
尹超:你是95后,但是在作品里描摹過去的事件時,會提到《射雕英雄傳》《天若有情》《獅子王》這些在你出生前的經(jīng)典作品,且鑲嵌得恰到好處,毫不違和,仿佛經(jīng)歷過一樣,你對過去時代的感受以及過去的作品的了解來自于哪里,如何將這樣的感受運用到作品當中?
楊天天:我成長于一個人口龐大的家族,盡管我自己是獨生女,但是卻有很多的表哥表姐、堂哥堂姐,我小時候就跟在他們的屁股后面,他們看什么,我就跟著看什么。他們中大部分都出生于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初,所以感興趣的東西都具有時代特征。像我在《淺命》里提到的電影《天若有情》,因為我有個姐姐是劉德華的忠實粉絲,所以劉德華的電影她都會看很多遍,還會拉著我們一起看。我自己腦海里也會有很多記憶碎片,這種碎片和埃萊娜·費蘭特所講的腦中的聲音不一樣,很多時候它是以畫面或者片段的形式存在我腦海中的。當我想要在寫作時用到它的時候,我就會像調(diào)取監(jiān)控畫面一樣把它抓取出來。
另外,有一個在我成長和寫作中影響都很大的人,就是我的爺爺。在我眼里他是一個活在過去的人,我小時候是在爺爺奶奶身邊長大的,每次吃飯爺爺都要和我講他父輩和祖輩的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祖父在家中遇到強盜打劫,被一槍打中肚子的故事。每當他講起這件事時,我的腦海中會像放電影一樣,浮現(xiàn)出一個和我爺爺一樣干瘦的老人,肚子上有個彈孔大小的洞,倒在血泊中的場景。后來在我十多歲時,爺爺?shù)昧税柶澓DY,也就是我們俗稱的老年癡呆,我在《六月河流淌》里也講了這個事情。這個病的一個典型癥狀就是當下的記憶會逐漸消失,和我們正常人相反,他的智力、記憶力、自控力、生活能力,都會隨著時間的流逝不斷減弱,像一個倒轉(zhuǎn)的時鐘,最后回到生命的原點。發(fā)病后,爺爺總是喜歡重復一些很久遠的事情,可能越是古老的記憶,在腦海中的溝壑越深,越難以忘記。爺爺離開后,我腦海里會反復調(diào)取他生病以前給我講過去的事情的場景,我慢慢意識到在爺爺回憶里和現(xiàn)實生活中的過去,以及我自己回憶和現(xiàn)實生活中的過去,它們在不斷被言說和標記的過程中,正在慢慢成為我人生中無法被分割的一部分。我想倘若有一個地方,能讓個人的意志不為外部條件轉(zhuǎn)移,能讓時間由流動變?yōu)橛篮悖蔷椭荒苁俏膶W世界。
尹超:現(xiàn)在不少年輕的寫作者似乎更愿意嘗試網(wǎng)絡文學、科幻文學、自媒體文學等創(chuàng)作路徑,你則堅守在傳統(tǒng)文學之中,你接下來的創(chuàng)作計劃是怎么樣的,是否會嘗試新的題材和風格呢?
楊天天:我個人認為,當下的青年作者們對現(xiàn)實的敏銳度很高,某種程度上,正是因為這種靈敏,使得他們看待和處理過去和當下的方式發(fā)生了一些變化。他們更傾向于打破傳統(tǒng)的寫作路徑,尋找一個更好的方法去串聯(lián)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比如我一直在關注的一些年輕的科幻寫作者,他們非常善于以一種超越現(xiàn)實、前瞻性的方式去處理歷史,繼而想象未來。
我是一個不喜歡做計劃的人,現(xiàn)階段的寫作重點依然是女性處境,關于這個主題其實還有很多未能講述的部分。我打算把它寫成一個系列,這個系列中的女性主體是每天從我們身邊經(jīng)過,卻沒有人會特別注意的,極其普通的女人。正因為普通,她們的人生經(jīng)歷顯得有些不值一提,甚至難以啟齒。我想通過這個系列的小說,去探討當下的普通女性一直難以向別人言說的困惑和隱痛,她們或多或少地感受到自己正被一些細碎的事物牽絆住,也因此渴望找到一個出口,找到一種和自我、和周圍和解的方式。但由于種種原因,她們沒辦法坦然地面對自己,只能被生活裹挾著向前。盡我最大的努力將這種狀態(tài)書寫并還原出來,是我現(xiàn)階段最想做的事情。
尹超:最后,想請你對比你年紀小的創(chuàng)作者們傳授一些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和心得體會,讓更多的年輕人也一起來“文學”吧!
楊天天:首先要寫下來,然后才是其他。一定要多閱讀、多積累,可以找一些自己喜愛的前輩作家的作品去學習,但不要在一味的模仿中迷失自我。寫作最重要的是講述自身,而不是復刻他人。無論你的個體經(jīng)驗在別人看來多么地微不足道,只要是你自己認為值得珍視和書寫的,就有存在的意義。最后,請永遠相信文字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