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磊:與艾蕪先生《南行記》的一份緣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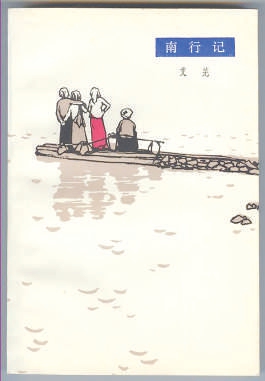
艾蕪《南行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
若不是《北京日報》的編輯老師問起,我幾乎已經忘記了這本深入心田的書籍。從年幼至年少,再到如今,每每炫耀地說起要高質量流浪這個話題時,那個向往又有點兒忐忑的想象中的旅途,它的起點,它的滋生,它的不停召喚,都起源于艾蕪先生的《南行記》。淺秋微雨,父親單位的圖書室清冷安靜,故紙堆特有的味道和校園里眼保健操播放的聲音很相稱。因為只有8個短篇,書冊很薄,擠壓在一堆“不起眼”里顯得更不起眼。不明白它為什么那么吸引我——一個10歲左右、認字還需要翻字典的孩子。以至于多年以后,我依然后悔當時應該采取“好借不還”的策略,把它留在身邊——新買的書冊,都不會有那種歲月沉淀的味道,而父親學校的圖書室已幾經翻新,這本書早已不在。
也許是里面每一篇的名字吸引了我:《人生哲學的一課》《山峽中》《松嶺上》《在茅草地》《洋官與雞》《我詛咒你那么一笑》《我們的友人》和《我的愛人》。每一篇簡單的題目下,都有精準且浪漫的文字——野蠻的山,咆哮的水,被世界拋卻的人們。它們組合起來,勾勒出一幅幅畫面:山中破廟里每個人在跳動火堆邊的臉龐,雞毛店里同榻的兄弟,低低垂頭的傣族姑娘。每一篇都在描寫苦難且充滿絕望:無家可歸、忍饑挨餓、窮困潦倒、饑寒交迫和生死未卜,偷竊、搶劫、行騙以及謀殺……但每一篇又充滿真實、神秘和浪漫。
工作后,有一次單獨去巫山出差。汽車行駛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霧氣中,以60公里的時速“蛇行”,一側是峭壁懸崖,一側是滔滔長江。看我神色緊張,司機說這條路他每天跑四次,這種天氣在巫山本地更是常見,他閉著眼睛都能開,讓我把心放在肚子里。一路上,我不時觀察著司機的眼睛。轉過高山,從海拔最高處下行,霧氣漸消,豁然間,一個村落如“世外桃源”般展現。遍地都是巫山脆李,果實累累,綠色無邊。我坐在農戶的堂屋里,對著一雙年輕的小夫妻。三人笑意盈盈,我吃著最新鮮的脆李,堂屋和吊腳樓之間是農戶祖父母的墳冢。一個老人蹲在土墻上抽煙,靦腆又認真地審視我。回來的路上,依然翻山越嶺,海拔漸高,霧氣漸濃,司機要帶我去摘野草莓,我卻有誤機的擔憂。在對視一眼之后,司機果斷向森林深處駛去。十分鐘不到,密林深處的一小片空地上,就像開了一個天井,陽光灑下來,鋪滿草地,野花野草間一顆顆粉白色的草莓穿梭跳躍——這里就像艾蕪先生描繪的“邊地”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先生對荒山野嶺充滿了深深的摯愛之情,對其間散發出的原始蠻力心醉神迷。我也跳躍——草莓不一定好吃,但突破藩籬的欣喜,許久沒有觸及的自然,沒有設定的隨心而為,是人生最銷魂的事。
所以,有人說艾蕪是“流浪文豪”——悲涼、苦澀又溫暖。艾蕪先生南行的緣由是逃婚——真是一個浪漫的起點。那年先生21歲,不能算作年少無畏了。雖然是為了逃避包辦婚姻——對方是屠戶的女兒。若從“野貓子”這個先生書中最明媚的角色來看,屠戶的女兒確實不是先生喜歡的類型。但《南行記》中不涉及愛情,卻有對女性的體恤和欣賞。若先生書中描寫的是一切弱小者被壓迫而掙扎起來的悲劇,那里面女性的發聲便是:“我還怕嗎?”“人應該像河一樣,流著,流著,不住地向前流著;像河一樣,歌著、唱著、笑著、歡樂著,勇敢地走在這條坎坷不平、充滿荊棘的路上。”這是《南行記》的詮釋,也是先生的人生寫照。
六年的南行,先生流浪到昆明,做過雜役;流浪到緬甸克欽山中,當過馬店伙計;漂泊在東南亞異國山野,與趕馬人、鴉片私販、偷馬賊朝夕相處;病倒在緬甸仰光街頭,為萬慧法師收留。以后,他當過報社校對、小學教師、報紙副刊編輯。幾經生死,一身灑脫的勇敢,化為一冊不羈的經典。
1990年拍攝的電視劇《南行記》僅有6集,艾蕪先生在劇中客串——飾演老年的自己,每集的開頭都是他坐在書房里與飾演青年時代自己的演員展開一段對話。鏡頭里先生抽著煙,坐在竹椅上,窗外細雨連綿,白紗窗簾微微擺動,先生瘦削的臉龐,在鏡頭里更加棱角分明,滿是滄桑——這就應該是他的模樣。
也許讓我們常含熱淚、相互體諒,以及對生命產生的更廣闊的悲憫尚在旅途中。我們不確定一條路要走多長,才能抵達遠方,但可以確定的是,一本經典能給所有善良和負重的人們送去安慰和生活的芬芳。
(作者為北京建筑大學建筑設計院風景園林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