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好一個人,就寫好了一個時代

李修文,湖北省作家協會主席、武漢市文聯主席、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著有《猛虎下山》《詩來見我》《致江東父老》《山河袈裟》《滴淚痣》《捆綁上天堂》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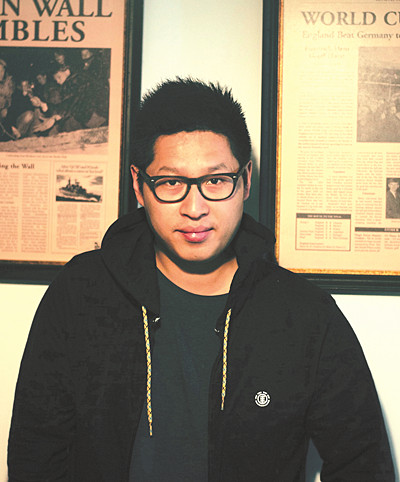
林東林,武漢文學院首屆簽約專業(yè)作家,著有《火腿》《出門》《燈光球場》《迎面而來》《三餐四季》《跟著詩人回家》等各類作品多部
把一個認識的人送到大家眼前
林東林:不僅僅是我,可能還有很多讀者和評論家也都會有同樣的疑問,你在寫完《滴淚痣》和《捆綁上天堂》那兩部長篇小說之后,很多年里一直沒再寫長篇,為什么?
李修文:其實寫長篇的愿望從沒斷過,不斷在寫,也在不斷廢棄,一直處在非常嚴重的自我懷疑中。這種自我懷疑,本質上是我一直想寫出真正具備某種時代特征的小說,對,我寫不出小說的原因很簡單,就是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寫出那些我在生活中認識的人,我喜歡的那些小說,都送來了一個個我們認識的自己,席方平、賈寶玉,到阿Q、孔乙己,一直到福貴,甚至孫少安、孫少平,而時代的樣貌和特征,往往就長在這些人身上。通過小說貢獻出來一個人物,把一個認識的人送到大家眼前,這是我的執(zhí)念,很長時間里我都覺得自己沒能力寫出來。問題出在哪?本質上還是一個作家如何認識他的時代和生活,如何和自己狹隘的美學為敵,再走向一個更加寬廣、復雜,更加泥沙俱下的人群和世界——讓寫作作為生活去自動呈現的結果,而不是畫地為牢之后再去苦思冥想的結果。當然,這只對我有效,對別的作家來說則可能不必如此。
林東林:時隔二十多年之久,現在為什么又會回過頭來寫長篇?是做好了內容和素材的準備,還是說感覺自己已經建立起來了這樣的能力,走出了當年的自我懷疑?
李修文:這一點我特別感謝寧浩導演。這些年里,他邀請我來做他的監(jiān)制,也跟他一起,為他簽下的年輕導演和編劇策劃電影項目,所以,我們總是在一起,去選景,去拍攝,去東游西蕩,我不斷聽他講他想拍的故事,他也不斷聽我講我想寫的故事——我給他講的故事,都不是作為劇本的故事,而是作為小說的故事,他一直都在鼓勵我重新成為一個小說家。甚至有好多次劇本討論會,當我們陷入困境,他總是跟我說,既然劇本不順利,你還不如把你想寫的小說寫出來。《猛虎下山》的故事,七八年前我就給他講過,當然只是個雛形,而且每次講得都不一樣,他一直勸我,趕緊寫出來。契機在于,當時為了一部電影選景,我們去了一趟貴州水城鋼鐵廠,鋼鐵廠背后有座山峰,寧浩走到哪都喜歡把手在眼前搭成一個框子,就像取景器一樣,透過取景器盯著山上的一座獨崖,他問我,在那兒趴著一只你要寫的老虎怎么樣?那一幕讓我非常震動,我一下子感受到了一種美學,類似黑澤明老電影式的裝置感。之前,我總模模糊糊覺得,既要寫下現實,又要寫出某種逸出現實的東西,經過寧浩的提醒,我突然覺得,工廠也好,獨崖也好,都是一座戲臺,一座讓無數人匆忙上場又竹籃打水的戲臺。
我還記得,鋼鐵廠的好多車間里都荒草叢生,時有野狗出沒,緊盯著我們這些不速之客,似乎還在聲討著當年:他們當年的主人,為什么全都遠走高飛,只剩下它們居留在此地,一天天變作了野狗?荒草叢里還散落著各種東西,我撿到過一張車票,明明是從水城去貴陽的,但為什么沒出發(fā)?當年的那些人可能無數次想遠走高飛,想離開這個囚禁之地,最后卻沒能成行。總之,我也沒想到,這個在我心里徘徊盤旋了很多年的故事,一下子就清晰了起來,就好像,我認識的那些人,一個個撥開荒草叢朝我走了過來。
林東林:《猛虎下山》這部長篇小說,以一個鋼鐵廠工人上山打虎、繼而又以身扮虎、最后甚至化身為虎的故事展開,在美學層面上,是不是也有一種對中國古典小說傳統的延續(xù)?
李修文:是的,你也知道,我受古典小說傳統影響甚大,單說人化虎的故事,唐宋傳奇里就有很多,蒲松齡更是寫了好幾個,這些故事一直裝在我的記憶之中,比如《汾上續(xù)談》里人化虎又生兒育女的那個故事,一直是我最喜歡的中國故事之一,我懷疑我自從想寫《猛虎下山》,這個故事從一開始就進入到了我的故事之中。我倒是常常想,在我們的古典小說傳統中,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的人化虎、人化鶴、人化孔雀、人化蝴蝶?無非是,這些人在現實里無處可去,作者但凡有一點憐憫之心,總要給他們找一個避風港、避難所,總要給無處可去的人一個去處,我甚至認為這種異化小說往往見證著一個作家的慈悲與公正,因為記錄龐大事件的史冊典籍里沒有給那些人去處。
林東林:他們一路被命運推擠著,進入到了某種絕境之中,想望門投止,不過根本就沒有人家,想望梅止渴,也沒有梅子,所以只有變身,化為老虎,化為蝴蝶,化為鶴,化為任何一種可以化成的動物或者植物。這可能也是一個循環(huán),不斷有這樣的人,他們身上不斷輪回著這樣的命運。
李修文:我就是在寫一種命運的重復,一代一代的人在這種命運的重復之中欲罷不能。所以,我希望自己不僅僅是在寫具體的某個時代,而是如前所說,將小說里的工廠和背后的群山當作一座戲臺,這座戲臺迎來了一代一代的劉豐收,他們一代一代地上山打虎,又一代一代地一無所獲。為什么我在小說中用了那么多短句子?也就是希望那些句子能像鼓點一樣敲起來,逼迫著每個人趕快撩起戲袍,匆忙上場,再去東奔西突和打斗翻轉,根本沒有時間喘息。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之中,劉豐收和他的打虎隊員們才一點點清晰起來,才讓我覺得,我是認得他們的。其實,寫這個小說最大的難度,還是如何盡可能真實地去面對自己,因為劉豐收就是我自己:多少時候,我們都是用謊言去對抗恐懼,又在謊言里左右為難?多少時候,我們的諂媚又將我們送上了一條難以回返之路?確實,在寫作《猛虎下山》的過程里,我有好多次,難以面對劉豐收這個人物,因為他就像是映照著我自己的一面鏡子。
林東林:《猛虎下山》里面的時間,大概對應到現實世界中的二十多年前,即上個世紀末和這個世紀初。你對那個時代和那個時代里的人,應該有著很切身的體會和認識,時過境遷,這部小說是對那個時代的一種還原和留痕么?
李修文:我最感興趣的,還是人的生命力——我們到底是依靠什么活下來的?我為什么去寫一個爐前工呢?因為爐前工在那個時代其實是一種大哥的形象,他們收入高,身體強健,他到廠里的浴池去洗澡,別人都要起身讓位,但他也要面對權力循環(huán),車間主任和廠長們來洗澡的時候,他也得乖乖起身,再讓位給他們;下崗時代到來之后,電工鉗工鍛工換個地方還能打工,但是爐前工則往往無處可去,尊嚴也好,驕傲也罷,只能隨著時代的向前一點點被磨損,所以生命力越強的人,往往在面臨時代轉折時,身上的傷口也最深。我在散文里寫過小時候見到的一個“關二爺”,在劇團里演關二爺的,義薄云天,急公好義,也下崗了,從那天起,他就換了個人一樣,失魂落魄,郁郁寡歡,不光是因為吃不上飯,而是他的義氣、他對別人的照顧全都在一夜之間沒了,這“關二爺”徹底地沒了自己的戰(zhàn)場。所以,寫《猛虎下山》的時候,我并沒有去描述和呼應一個時代的宏愿,而是老老實實通過書寫去認識那些從時代的縫隙里走出來的人,和他們一起,與那個年代艱難告別,甚至是無法告別。我記得,在水城鋼鐵廠,我跟寧浩邀請了很多當年的老工人喝酒,在他們身上,仍然還攜帶著那個時代賦予他們的強烈驕傲,那種驕傲是因為有多大權力嗎?不是,而是一種工人階級的驕傲,真是“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啊,所以我總是提醒自己:也許,寫好一個人就寫好了一個時代,寫出一個我們認識的人就能幫我們真正地感知到他所置身的時代。
時代的信使和時代情緒的翻譯者
林東林:在《猛虎下山》里面的那個時代,互聯網和手機還沒有廣為普及,每個人都是以一種直面相對和親身參與的方式與這個世界接觸,今天這個時代不一樣了,現在是一個信息時代、視頻時代,大家好像都躲在了手機或者電腦屏幕前面參與這個世界,我們的參與從動作參與變成了一種視覺的和心理上的參與,我們的經驗也變成了二手經驗,那么作家該怎么書寫這個時代?
李修文:我特別喜歡顧隨先生在評價陶淵明時的“身經”之說,所謂“身經”,就是自己動手,絕不旁觀。讓我們看看陶淵明的詩,“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你看看這些字詞中埋藏的動作就知道,他不是站在田埂上寫出來的,他是從貨真價實的農田里耕作完了再回到村里去的。寫作,在相當程度上就是生活本身,我們不過是我們所見之物的轉述者——多年前,我曾見過一個盲人,他告訴我,他并非和我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上,為了對付現世,他早早地在頭腦中給自己虛構了一個世界,絕大部分時候,他都生活在他所虛構的世界里。必須承認,我被他深深震動了,所以,在那篇叫做《三過榆林》的散文里,我決心越過所謂“真實”的邊界,去寫下他的顛倒黑白和指鹿為馬;我還見過一只猴子,好多年里,為了報答當年的救命恩人,每隔段時間,它便帶來食物,去喂養(yǎng)恩人去世之后留下的孤女,于我而言,當這樣的奇遇在眼前展開時,就是時代掀起了它的帷幔,時代也因為它們而顯露出更加真切的質地,更加具備了令人信賴的人格力量。所以,我自己的認識是:當我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人成為了情感共同體,時代便在哪里得以浮現,就好像,親身參與了“永貞革新”及其失敗,柳宗元的曠世孤寒才能穿越這么漫長的時間抵達今天的我們,我們也是在杜甫的際遇里,才對什么是“安史之亂”認識得更加深切。
林東林:時代變了,所以過去形成的一系列經驗也失效了,今天我們迎來了一系列新命題,對于作家來說,也必須及時觀照新的時代特征,通過寫作不斷建立起新的感受。
李修文:我自己作為一個寫作者,一直關注著一個持續(xù)的課題,那就是,我們的古典文學傳統如何在今天的生活里重新被激活,就像戲曲、話本、傳奇在當時的人們生活中所起到的那種作用,是否有可能被我們再一次認識到?我們說今天的生活碎片化,我倒是覺得,戲曲、話本和傳奇其實也是那個年代里碎片化的結果,但因為他們和俗世、和自己的生活貼得非常緊,人們通過它們看見了自己的存在,也就幫助他們更好地度過了他們的時代。你看《三言二拍》誕生的時代,《堂吉訶德》已經誕生了,當時全球范圍內的文學都是以個人為中心展開的敘事。歐洲不斷向外擴張,版圖不斷變化,強調海洋文明基礎上的英雄個人主義;在中國,正處于李自成那個年代、明朝將亡那個年代,越是戰(zhàn)亂頻仍,人們越是需要更多講述自己的故事來抵抗他們的幻滅之感,《三言二拍》里的很多人都沒有什么自控能力,我們不如將這些人物看作是一種自我嘲諷,所以,凌濛初和馮夢龍其實是那個時代的信使,是那個時代情緒準確的翻譯者,正是在這個基礎之上,他們成為了他們那個時代的“作家”。
林東林:所以,長篇小說的寫作,在今天這個時代也面臨著一個新的難題,怎樣去延續(xù)和對接傳統,又在這種延續(xù)和對接之中,形成長篇小說在今天這個時代的一種特質。
李修文:實際上,這恐怕不僅僅是一個如何對接傳統的問題,長篇小說在今天面臨著很大的文體挑戰(zhàn),就比如,那些大河式敘事的長篇小說就很難經得起考驗了——過去,我們的主人公要行進在漫長的旅途上,去對抗苦難,去經受時間,最終通過考驗,獲得正果,當然,也可能是落得個“白茫茫一片真干凈”,世界再一次向我們展示出他原本的威嚴和難以被克服。這有點像電影,過去有段時間,我們認為,“文學性”乃至“戲劇性”對于電影是重要的,但是,我們也許也該問一問,過度的“文學性”或“戲劇性”對于電影的主體性是不是一種干擾?一個我們目測起來特別嚴密的劇本,到底適合用舞臺劇還是電影去呈現它?電影之所以是電影而不是話劇,是因為它有個普遍的現代心理學基礎在打底,在這個基礎之上,許多類型化橋段的運用,反而能召喚更多的人心,于是,所謂的類型化,似乎反倒建立了一種更廣泛的完整性。我們的時代當然是波瀾壯闊的,但這種波瀾壯闊并不像從前一樣,自上而下的線性發(fā)展著,而是不斷地碎裂:時間在碎裂,處境也在碎裂,也許,我們的長篇小說也要發(fā)生碎裂,再在碎裂中去鏈接散文和詩歌,去鏈接戲劇和電影,等等,以更加有效地去建設長篇小說在今天的主體性。
林東林:像不少作家一樣,今年年初,你的身份也發(fā)生了改變,從一位專業(yè)作家成為一位大學教授。你是從1999年開始做專業(yè)作家的,算起來至今有25年了,為什么會發(fā)生這種身份上的改變?
李修文:其實,就是想要和更多的年輕人打交道。這些年,除了做一個專業(yè)作家,我還擔任了不少影視項目的監(jiān)制或總策劃,其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和年輕編劇、導演一起討論他們的創(chuàng)意和劇本,本質上,我認為這和我去大學跟學生們討論創(chuàng)作是一樣的。這些年,在和這些年輕編劇、導演討論的過程中,我自己深受他們的觸動和啟發(fā),就像我之前擔任武漢大學駐校作家時,在和同學們的討論課上,他們的好多觀念和角度都讓我常常暗自驚詫,所以我想,也許是時候讓自己跑上一條自己之前并不熟悉的跑道了。另外,我也需要某種自我建構:閱讀的建構、知識體系的建構,乃至人格的建構。
重新找到講述世界和人群的快樂
林東林:你最初就是寫小說,《滴淚痣》《捆綁上天堂》,還有一系列中短篇小說,后來進入影視行業(yè),有十多年沒有寫小說,這十多年的經歷為你帶來了什么?
李修文:老實說,成為影視行業(yè)的一個什么人物對我沒有吸引力。我只希望自己好好做一個作家,對,我曾經是一個編劇,但我必須得承認,我是一個失敗的編劇,我寫過很多劇本,最后拍出來的不過十之一二,是什么支撐我呢?其實還是文學——我一直在寫那些我心目中想寫下的東西,比如《山河袈裟》里的很多篇,也沒發(fā)表過,我就是自己寫給自己看。甚至后來寫《詩來見我》,無非是做影視的時候老是動蕩,今天在這里明天在那里,往往今天把合同簽錯了,明天劇組又沒了,但是,也是在那樣的顛沛流離中,我感受到了古人走過的道路、寫下的詩句,他們遭遇的人間草木、飛沙走石和我遇到的一模一樣,我行走在他們行走過的道路上,那些古老的情感和際遇又換了一種面目和模樣重新來到我身上——當它們成為我的生活本身時,我突然意識到,我只要寫下它們就好。對你說起的十多年,我懷有深深的感激:文學不僅沒有從我的生活中消失,相反,我越來越相信它之于我生命的重要。
林東林:但是后來,你沒有去寫原來在寫的小說,而是寫了一系列散文,《山河袈裟》《詩來見我》《致江東父老》,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從一位小說家、編劇,成為了一位散文作家,為什么會寫那一系列散文作品?
李修文:一點兒都不矯情地講,就是出自內心的生命需要,總覺得還是要寫下來點兒什么才能將此刻度過去,才能證明文學仍然在我的生活里。我寫散文時,起心動念都特別簡單:就是把自己見識過的一個個人寫出來,把自己難以忘記的那些瞬間寫出來,像《青見甘見》,其實就是記錄了我和葉舟兩個人浪游青海甘肅的整個過程而已,但是我知道,這趟浪游,對于寫不出東西的我重新找到自己信賴的字詞,是無比重要的,這不過是一種直覺,也許,散文就是一種靠直覺引領的文體吧?有一年,為了給《瘋狂的外星人》做前期采訪,我去了陜北的佳縣,突然看見一群盲人聚在一起唱山曲,唱花兒,一打聽才知道,那些年,幾乎全西北的盲人都會在三月三那一天趕往黃河邊聚會,他們?yōu)榱耸裁矗繜o非是為了證明吾道不孤,證明你的存在可以鼓舞我的存在。所以,當他們湊在一起,一個個不要命地唱起來,我?guī)缀鯗I下,也一直想把他們寫下來,但是,一直到今天也沒寫成,因為我覺得我的文字幾乎無力去匹配我所目睹到的那些近于奇跡般的時刻,可他們仍然時時被我想起,從這個意義上說,或許,我一直都在寫著他們。
林東林:他們讓你見識到了一種完全不同卻又情意相通的天地人間。當然,這同時也提出了一個問題,今天,好多人將自己物質化了,精致化了,把自己弄到一個精巧細致的螺螄殼之中,躲在舒適區(qū)和同溫層之中,抱團取暖,或者自己給自己取暖,不愿意從象牙塔里走出來,不愿意從辦公室里走出來,不愿意從工作室里走出來,走到一個更加廣大的世界和天地里去,走到一種與之前不同的異質生活里去。
李修文:你說得對,文學界也好,影視界也好,好多人都有工作室,那種文創(chuàng)園里的工作室,但我一直對此稍有懷疑,我覺得,一個創(chuàng)作者,恐怕還是得不停地為自己創(chuàng)造盡可能嶄新的生活,而不是嶄新的工作室。很長時間里,我都懷疑自己再也寫不出什么東西來了,幸虧有人叫我去做編劇,編劇沒有做成什么樣子,倒是攢了一肚子的苦水——今天見縣長,明天見國企領導,今天被人從劇組踢了出去,明天又和欠了錢的劇組一起被扣留了,可能也正是如此,祁連山和戈壁灘來到了我的筆下,各種犄角旮旯和站在其中的人也跟我遇見了,也許,個人美學也好,生命底色也罷,就此便發(fā)生了變化;所以我覺得,你所說的“異質生活”,可能其實是一種再正常不過的生活,就像潯陽江頭之于白居易,永州柳州之于柳宗元,但它們在今天尤其需要我們去創(chuàng)造,像柳青那樣的作家,舍棄了北京的生活和戶口回到老家去生活,這不是體驗生活,這是在為自己重新創(chuàng)造生活。
林東林:你以一個散文作家的身份重新歸來,寫出了一系列極具個人色彩和辨識度的作品,但是怎么沒有繼續(xù)寫下去了?還是說,你覺得要在散文和小說之間穿梭游移?
李修文:散文當然還是要寫下去的,對于散文,我的理解可能很狹隘:散文的背后,就是各種各樣的“我”,許多時候,寫散文的那個我,就是私設公堂的我和獨斷專行的我。以一座法庭為例,無論你是原告、被告、書記員、法官,只要你寫下自己的感受,那就是一篇散文,因為它背后都有一個強大的自我;而小說,更像一座完整的法庭,需要各種各樣的聲音,甚至需要“我”的消失,許多優(yōu)秀的小說里都充滿了爭辯,不爭辯,就沒有公正,所以為什么小說如此重要?我覺得它實際上是映射我們個人生活的一座法庭。如前所說,許多時候,一個作家寫什么,在于他為自己創(chuàng)造了什么樣的生活,寫《山河袈裟》和《致江東父老》時的我,背靠在一個我所踏足過的世界上,并因此而獲得了某種充沛之力,如果我還要繼續(xù)寫散文,我便要召回從前的那個“我”,去曠野,去我篤定的道路上,去我投下了情意的人群里,我隨時準備這樣做。
林東林:近幾年,你密集地寫了一系列小說,新近又完成了一本小說集,其中的一些故事你也跟我和朋友們分享過,目前的狀態(tài),是對自己當年那個小說家身份的尋找和接續(xù)嗎?
李修文:從生命體驗上講,我也覺得很神奇,好多年之后,忽然又開始寫小說了,而且每天都想寫,每天都寫一點,但說實話,對于把小說寫成什么樣子,我也并沒什么特別的指望,畢竟能寫這件事就足以讓我覺得非常振奮了。回過頭來,我還是要感謝寧浩,感謝《猛虎下山》,寫作《猛虎下山》的過程中,好多中短篇故事便找上我來了,它們其實都是過去十幾年里我無數次想要寫出來的故事,寫完《猛虎下山》,像是閉塞的感官被喚醒,再一次打開了,我才空前地信任著這些故事,因為我知道,就像寫散文時一樣,我只要成為一個我所見之物的轉述者就好了。當然,寫作的過程里,還是困難重重,不斷琢磨、修改或者放棄,但是現階段,寫小說的隱秘快樂遠遠大過了我去寫別的文體,就像我在一篇創(chuàng)作談里寫到過的:“好好做一個說書人吧,年復一年,用講述去理解時間,去理解命運,去理解人們在時間與命運中的流轉和忍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