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埃爾諾:用寫作逃離小鎮,最終還是回來了
每年春節返鄉之時,總是最能攪動回鄉之人的思緒。在大城市生活多年,家鄉小城已經在記憶中逐漸陌生化,回到故鄉,其實我們已經格格不入了。當初因為怎樣的信念而離開?小城的生活經歷如何影響和塑造了我們?
回望故鄉,就是回望自己的過去,思考是什么使你成為現在的你。
伊沃托,一個籍籍無名的法國小鎮,只有福樓拜在書信中提到過,“這是全世界最丑陋的城市。看過伊沃托,死也無憾。”而對于作家安妮·埃爾諾來說,這里是她的故鄉,是她的經驗之地。

當埃爾諾在2012年回到故鄉時,她已經是個著名作家,盡管距離她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還有10年。“從某個私密而深刻的角度來看,伊沃托是世界上唯一一座我去不了的城市。”在《我的青春之城:回到伊沃托》里,埃爾諾說自己無法返回伊沃托,但伊沃托是她夢想的起始之地,寫作的經驗之地,承載了她的回憶和野心。
《我的青春之城:回到伊沃托》是埃爾諾的非虛構作品,收錄了她在伊沃托發表的演講、照片資料、日記節選、和友人的通信等。書中埃爾諾向讀者坦陳自己如何依靠閱讀、求學和夢想,脫離原本的小商販家庭,進入布爾喬亞階層,成為一名作家。這種“向高處降級者”所蘊含的,是跨越階層帶來的生命之重,但也正是這種“重”讓她成為如今的埃爾諾。

埃爾諾并非出生在伊沃托,她是在5歲時和父母從其他地方搬遷過來的,她還記得,坐在搬家的卡車上,眼前是一個到處殘垣斷壁、百廢待新的城市。這就是二戰后的法國,每個人都忙忙碌碌,充滿希望,埃爾諾的父母同樣如此,他們計劃在小鎮上開一個咖啡館,相信憑借自己的勤勞和才智可以過上富足的生活。
這家賴以為生的咖啡館其實很小,兼賣日用生活品,做的都是街坊生意,那些熟客都有自己的綽號,每個人的八卦在顧客之間流傳、發酵。年幼的埃爾諾浸淫其中,有了講述故事的沖動。
童年時期的埃爾諾是幸福的,她是家中獨女,父母盡自己的全力給她提供了最好的生活。可等到上學后,她漸漸意識到了階級的區別,還有貧富差距。首先是家庭住址,她家住在所謂的“街區”,也就是魚龍混雜的地方,每次去市中心都會說“我去城里”或者“我去伊沃托”,她意識到似乎有堵無形的墻橫亙在她的家和市中心之間,踏入那片不屬于她的土地時,她需要穿上體面的衣服,表現得舉止得體。之后,是家里的陳設。埃爾諾在作文里寫道,她最喜歡她家的廚房,但這是她根據時尚雜志臆想出來的夢中廚房。廚房寬敞、溫馨、廚具擺放得錯落有致,甚至還有個閱讀角。但她提到了塑料桌布,卻讓夢境露出了馬腳,一般有錢人家是不用塑料桌布的,只有窮人為了圖方便才用。她家真實的廚房只是樓梯下方的空當,甚至沒有洗碗槽,只能在盆里洗餐具。
但最大的沖擊源于某個氣味——消毒水的氣味。那原本是一個稀松平常的日子,所有學生坐在教室里等待上課,突然有個女生尖叫起來:“誰用了消毒水!難聞死了!”埃爾諾下意識地把自己的手縮進了袖子,她中午在家里用消毒水洗過手。她突然明白了,原來消毒水在不同階層代表著不同的含義,在她生活的街區,消毒水意味著衛生、健康,而在富人家里,這刺鼻的味道只會和女傭畫上等號。
她是學校里的優等生,她最喜歡上語文課,她要用一種近乎外語的法語來寫作,因為她日常生活中的法語充滿了俗語和方言,并非是那個用詞嚴謹、語法規范的法語。她如饑似渴地閱讀書籍,《魔鬼附身》這樣的書名聽著就大逆不道,薩岡的青春小說幫助她想象那個小資的美好世界,就像她后來在小說中寫道:“我以浪漫的方式經歷著青春叛逆,就好像我的父母屬于布爾喬亞階層。”
埃爾諾想要上大學,想要離開這個小鎮,想要有份受人尊敬的工作,老師或者作家,總而言之,她想要遠離原生家庭了,她成為了她階級的“叛徒”,或者如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所說,一個“向高處降級者”。
埃爾諾把克洛代爾的詩句貼在墻上,仿佛一條與撒旦的協約:“是的,我相信自己不是平白無故來到這世上,我身上有某種這個世界不可或缺的東西。”她有野心,有欲望,她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盡管她這個階層的父母也搞不清楚大學專業和職業規劃的關系。他們只是質樸地相信:讀到大學,就有燦爛前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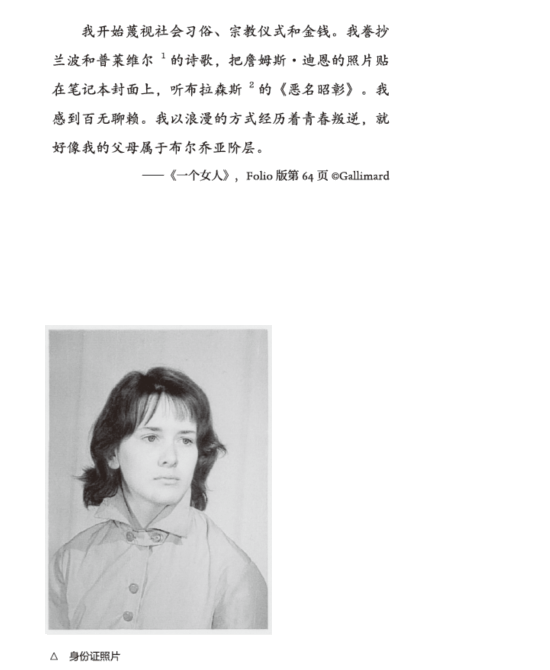
埃爾諾在讀大學時把第一份稿子投給了門檻出版社,遭到了無情拒絕,她在日記中也流露出灰心喪氣,但她后來也承認,因為那時受到新小說風潮的影響,她的第一個手稿只是寫了一個追趕潮流的東西,并非是她自身情感的流露。之后,她經歷了父親去世,時隔多年回到家鄉,看到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人和物,她決定要用平實的語言來記錄她出身的工人階層,替這些被統治階級發生,“為我的族群復仇”。
也正是在寫作過程中,埃爾諾實現了和父母、和原生家庭的和解,她慢慢可以正視很多她之前羞于提起的事情,那些會讓她感到刺痛的事,她可以心平氣和地描寫貧窮、偏見、掙扎。最終,埃爾諾在寫作中完成了自我蛻變和成長。最終,她鼓起了勇氣,以作家的身份回到故鄉伊沃托,講述她寫作的欲望和沖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