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喬伊斯研究專家的約瑟夫·坎貝爾
作為神話學家的約瑟夫·坎貝爾在中國已經廣為人知,作為喬學家的約瑟夫·坎貝爾在國際喬伊斯研究者中其實有著同樣的知名度。不僅因為他第一個對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真正天書級別的作品《芬尼根的守靈夜》做了從頭至尾的解讀,而且也因為他一生對喬伊斯作品所做的神話哲學研究,使喬伊斯筆下20世紀初的都柏林現實社會,呈現出整個人類文化的普遍規律,為喬伊斯的愛好者們打開了一扇通往終極意義的大門。
坎貝爾在喬伊斯研究史上的觀點和貢獻主要體現在兩部書中:一本是他與亨利·莫頓·羅賓遜合著的《解讀〈芬尼根的守靈夜〉》,這本書第一個給出了《芬尼根的守靈夜》的整體框架;另一本是由他40多年的喬伊斯研究論述編輯而成的《解讀喬伊斯的藝術》,這本書由埃德蒙·L.愛潑斯坦博士按照主題模式做了整理,從而既具有了專著的系統性和整體性,又打破了專著的時間局限,包含了坎貝爾隨著對喬伊斯和對神話學的認識日益深入,而獲得的最新領悟。
坎貝爾雖然出生在紐約,但他的祖父是從愛爾蘭梅奧郡移民來的地地道道的愛爾蘭天主教徒,因此雖然生活在美國,坎貝爾成長中的愛爾蘭天主教環境卻讓他對喬伊斯描繪的天主教都柏林社會有感同身受的理解。這或許也是為什么23歲到巴黎學習中世紀語言學、古法語和普羅旺斯語時,坎貝爾會被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靈夜》(部分章節)深深吸引,最終改變了自己的職業生涯。不過,坎貝爾不是停留在喬伊斯筆下的20世紀初的都柏林現實世界,他敏銳地注意到了喬伊斯高密度的語言里包含的神話內容,以及這些神話敘述所揭示的當下當地行為中潛含的從古至今人類共有的行為模式。從這一點說,喬伊斯與坎貝爾可以說是互相成就的。
一方面,可以說是喬伊斯啟發了坎貝爾的神話學基本思想。坎貝爾在代表作《千面英雄》中用monomyth(單一神話)來指稱書中描寫的英雄從出發到歸來的冒險之旅,而這個詞正取自喬伊斯的《芬尼根的守靈夜》,即第三卷第四章中的“還有他的單一神話”,喬伊斯這里的單一神話指的就是主人公HCE從被審判、死亡到復活的英雄循環之旅。此外,《千面英雄》的第二部分把研究的對象從英雄人物的命運轉向了“宇宙演化周期”,而這也正是《芬尼根的守靈夜》在敘述上的與眾不同之處;到了《芬尼根的守靈夜》,喬伊斯突破了傳統文學對個人命運的關注和書寫,從更開闊的視角將人類的遭遇與宇宙的循環結合在一起。這些相似之處表明,很可能是坎貝爾在《千面英雄》出版五年前對《芬尼根的守靈夜》的詳細解讀,影響了他的神話學思想。
另一方面,坎貝爾的解讀同樣推動了對喬伊斯的理解。雖然今天一些研究者認為坎貝爾和羅賓遜的解讀犧牲了喬伊斯在書中放入的更加豐富的含義和具有后現代特征的敘述風格,而且也有誤讀,但是在《芬尼根的守靈夜》剛剛出版的幾年,那時讀者雖然憑著直覺,覺得“某個聞所未聞、不同尋常的事情正在喬伊斯的新小說中進入語言、歷史、時間、空間和因果關系”,但是卻無法讀懂,更別說理解這部天書了,用當年一個評論者的話說,“有些時候,這些新詞表明是把兩個或更多含義用更聰明經濟的方式融合。而在大多數時間,它們始終無法理解,作者的意圖完全無法捉摸”。在一片哀鴻中,坎貝爾卻只用了5年,就不僅勾勒出了全書的主要輪廓,而且對其中一些文化的尤其是神話的用典做出了深入的解讀,從而一下就把對《芬尼根的守靈夜》的理解推進到了神話哲學的高度。要知道,對該書詞語的其他系統破譯要等到20世紀60年代才開始,《〈芬尼根的守靈夜〉注釋》要一直等到1982年才問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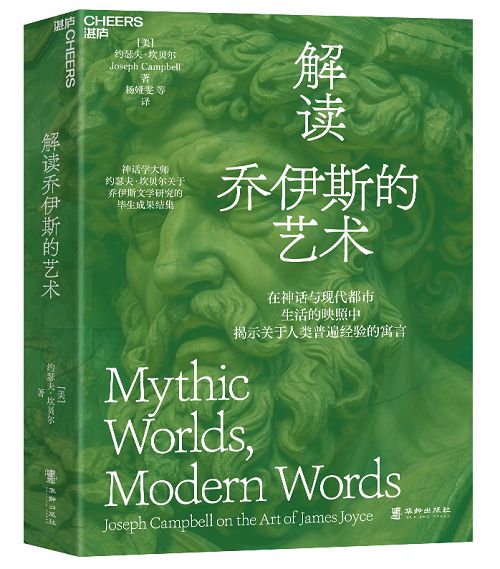
當然,作為神話學家,坎貝爾最擅長也最具啟示的是他對喬伊斯作品所做的神話原型批評,而且這層解讀對于理解喬伊斯至關重要。喬伊斯筆下年輕的主人公代達勒斯與古希臘天才工匠代達勒斯的對應,《尤利西斯》與荷馬史詩《奧德賽》的對應,都是喬伊斯作品中最明顯的神話內容。《尤利西斯》出版不久,英國詩人艾略特就以詩人的敏銳看到了喬伊斯作品中存在的這種“雙層面”(two plane),稱“喬伊斯先生對《奧德賽》的平行使用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它所具有的是科學發現的重要性。之前沒有其他人把一部小說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在使用神話,使當下與古代之間達成持續的并行方面,喬伊斯先生探索著一種其他人必須在后面奮起直追的方法”。如果說艾略特指出了喬伊斯作品中神話內容的重要性,那么正是坎貝爾用細致的文本分析和淵博的神話知識,指出了喬伊斯三部長篇中在什么地方放入了什么樣的神話,以及這些神話思想具有的心理學和文化學的內涵和深度。
因此,約瑟夫·坎貝爾的《解讀喬伊斯的藝術》和《解讀〈芬尼根的守靈夜〉》的中譯本同時出版,對無論神話學的愛好者還是喬伊斯的愛好者來說,都是一次知識的饗宴。喬伊斯和托馬斯·曼被坎貝爾視為承載著當代神話學的兩大重要作家,而神話學是打開喬伊斯思想寶庫的一把不可或缺的鑰匙。坎貝爾在書中既深入淺出,又娓娓道來的語言,使得這一豐盛的知識饗宴變得如拾地芥而又回味無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