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2023年第2期|馬可:這個(gè)春天(節(jié)選)
推薦語
這個(gè)短篇小說寫的是兩個(gè)孤苦女性的晚年人生及她們之間相濡以沫的深厚情誼。大昭喪夫喪子孤身一人,和已有家室的男人蘇寧保持了多年的婚外關(guān)系,但在絕癥來襲時(shí),她所能依靠的,還是那個(gè)終身未婚跟養(yǎng)女關(guān)系疏離的好友和生。兩個(gè)孤獨(dú)的畸零人,抱團(tuán)成就了血緣之外人間難得的親情和溫暖。小說舒緩平靜哀而不傷,頗有韻味,也頗見功力。
這個(gè)春天
□馬 可
醫(yī)院的過道上全是消毒藥水味,想必是剛有人用帶有藥水的拖把拖過地,和生從過道上走過的時(shí)候這樣想著。珞彤工作的這家醫(yī)院是專科醫(yī)院,平時(shí)住院的人不多,和生每次來,都見走道上空蕩蕩的。和生之所以不喜歡這里,就是因?yàn)樗帐幨帯_@種空蕩蕩讓人心里不踏實(shí),它和那些讓人感到踏實(shí)的醫(yī)院不一樣,那些醫(yī)院像菜市場似的,人流像潮水一樣涌動(dòng),但在這家醫(yī)院的過道上卻幾乎見不到一個(gè)人。有一次和生問珞彤:“這里有病人嗎?”珞彤笑笑說當(dāng)然有了。那時(shí)候珞彤才剛到醫(yī)院上班,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她不是和生的親生女兒,是和生撿來的棄嬰。二
十六年前,和生把珞彤抱回去的時(shí)候,只是覺得她可憐,還沒想到要收養(yǎng)她。珞彤當(dāng)時(shí)就被扔在和生的房子外面,那天天氣特別冷,剛下過大雪,雪花像棉花一樣落在樹杈上。珞彤已經(jīng)凍得哭不出聲,臉紫了,眼睛鼻子擰到了一塊兒。和生把她抱回去,心想可能活不成了。
“即使是一只小貓,我也會(huì)收養(yǎng)的,”和生說,“更何況這是個(gè)人。”
和生這話是對大昭說的,她的意思是,她不是因?yàn)闆]結(jié)婚怕寂寞才想養(yǎng)珞彤,而是覺得珞彤應(yīng)該有人照料。
“她真是命大啊,”大昭撇著嘴說,“你說會(huì)不會(huì)是誰未婚生子啊,養(yǎng)不了才放在這里的。”大昭一說話表情就特別豐富,鼻子眼睛都動(dòng)起來。
這倒是有可能的,和生想,珞彤身體方面沒什么問題,拋棄她的人應(yīng)該不是因?yàn)樗胁〔艗仐壦摹?/p>
星期一和生去見珞彤,是為了把自己的決定告訴她。和生以為她會(huì)反對,以她的性格,不反對至少也會(huì)板下臉來哼一聲,但珞彤這次只是抿抿嘴,什么也沒有說。珞彤嘴唇上方有個(gè)白色月牙樣的疤痕,是小時(shí)候和生帶她去鄉(xiāng)下時(shí)被一頭羊頂了留下的,從那以后珞彤就變得不愛說話,和生也因?yàn)樘澢匪裁词露柬樦_^了這么多年,那個(gè)疤痕都幾乎看不出來了,她涂上遮瑕霜,就一點(diǎn)痕跡都沒有了。但這天她沒化妝,那個(gè)疤痕就在暗處閃了一下。她垂著眼瞼,一眼都沒看和生。“如果你已經(jīng)決定了,”她說,“那你就這么做好了。”
自大昭病后,珞彤一次也沒去看過大昭。珞彤認(rèn)為,大昭只是和生的朋友,和她關(guān)系不大。不過在珞彤還沒有離開家獨(dú)自生活之前,每到過年過節(jié),大昭都會(huì)來和生家和她們母女相聚。那多半是因?yàn)樘K寧要在家陪簡珍和兒子,抽不出空來陪大昭。大昭一來,珞彤一般都不怎么說話,有時(shí)還會(huì)對大昭翻白眼。大昭在和生家住的那兩年,珞彤住在學(xué)校,連周末也很少回家。
大昭是和生的好朋友,以前她們一起在保險(xiǎn)公司上班。大昭的丈夫和兒子先后都死于一種罕見的遺傳性心臟病,為了給他們治病,大昭把房子給賣了,沒地方住,才搬到和生家。和生覺得后來她之所以又搬了出去,是為了蘇寧。她已經(jīng)和蘇寧好了一年多了,應(yīng)該有個(gè)單獨(dú)的地方用來約會(huì)。大昭說不是,她搬走只是不想再麻煩和生。“你恐怕也應(yīng)該考慮一下自己的個(gè)人問題了。”大昭說。和生沒什么個(gè)人問題要考慮,她不是沒想過結(jié)婚,上學(xué)的時(shí)候喜歡過班里的兩個(gè)男生,畢業(yè)后也喜歡過一兩個(gè)人,后來又有一個(gè)同事喜歡她,但她都沒和這些人發(fā)展出不同尋常的關(guān)系。
“你不想跟我去看看她嗎?”這時(shí)和生又問。
“我要值夜班。”珞彤說。
“你就跟我去看她一眼又怎么了?”
與珞彤的冷淡相反,每次大昭一提到珞彤,就夸她安靜、懂事,“不用大人操心”“你養(yǎng)她養(yǎng)對了”。
珞彤走了兩步又折了回來,什么也沒說,只管往和生手里塞錢,說:“這是五百塊,你替我買水果給大昭,就算我看過她了。”
和生想,她和大昭缺的不止這五百。
星期六還是個(gè)大晴天,到星期天天氣就變了,小雨淅淅瀝瀝下了一整天,連屋子里都潮乎乎的。她們現(xiàn)在住的房子,是和生早幾年開服裝店時(shí)買下的。那時(shí)生意比現(xiàn)在好做得多,和生還用心地把房子裝修了一下,雖說只是兩間臥室一個(gè)客廳,住起來卻非常舒適。客廳里有一張長沙發(fā)和一張?zhí)梢危梢问翘倬幍模芗?xì)膩,不像竹的那么粗糙。大昭沒來之前,和生喜歡躺在上面打盹,大昭來了之后,就把躺椅霸占了,躺在上面看電視,不過通常把電視的聲音開得很小,除非遇到自己特別想看的電視節(jié)目。
大昭說她想吃羊肉火鍋,用火鍋來驅(qū)驅(qū)寒氣,和生就出去買羊肉。和生并不喜歡春天吃羊肉,可一想到大昭能這樣高高興興吃羊肉的日子沒有多少,就不管她說什么,都不反對了,一切都按大昭說的辦就行。她把羊肉買回來,把冰箱里的魚、白菜、豆腐、土豆、毛肚、番茄拿出來洗干凈,煮成一鍋,最后又把電磁爐搬到桌上,和大昭兩個(gè)人對著鍋涮羊肉。
大昭的鼻尖很快就冒出汗來,臉也變得紅潤了,可這不過是回光返照,和生想著,雖然她希望大昭的健康狀況,沒有醫(yī)生說的那么糟糕,但事實(shí)就是這樣。她想起以前她們一道在辦公室上班的時(shí)候,大昭坐在她對面,經(jīng)常會(huì)拿出隨身帶著的化妝鏡察看自己的臉。她一邊檢查臉上有沒有長出新的皺紋,一邊和和生聊天。“這里又是一顆。”她會(huì)說,“這是青春痘,可我已經(jīng)不青春了呀。”如果兩樣都沒有,她就開始說毛孔粗大,需要買化妝品來收縮毛孔。
大昭比和生小兩歲,皮膚比和生嫩白,也比和生會(huì)化妝,兩個(gè)人在一起的時(shí)候,她更引人注目。和生通常只梳一個(gè)發(fā)式,她的頭發(fā)剪到耳垂下面,她的臉又長又尖,鼻尖又瘦又薄,讓一開始見到她的人,會(huì)以為她為人尖刻,但其實(shí)她人很好。大昭要比她圓潤得多,經(jīng)常變換發(fā)型,頭發(fā)一會(huì)兒燙卷,一會(huì)兒拉直,每天都要化妝,整張臉看起來就像一個(gè)粉紅的蘋果。
一直都是這樣,大昭喜歡把自己收拾得體體面面,和生卻不修邊幅。現(xiàn)在卻完全不一樣,倒是和生要更注重顏面問題了。和生覺得,再怎么樣,一個(gè)人的變化也不該那么大,雖然生了病。但醫(yī)生說大昭現(xiàn)在還沒有到最嚴(yán)重的時(shí)候,“再過幾個(gè)月,那會(huì)更不一樣”。
還能怎么樣呢?和生生氣地想,難道還會(huì)變得和骷髏差不多嗎?現(xiàn)在的大昭已經(jīng)完全沒形了,體重降了那么多,以前最胖的時(shí)候,她的體重可是將近七十公斤,現(xiàn)在連五十公斤都不到。以前的衣服不能再穿了,束之高閣,重新買了新的來。那是些窄小的,以前連想都不敢想的衣服。“我以前就想有現(xiàn)在的體重,”大昭說,“可總也瘦不下來。現(xiàn)在倒好了,我可以穿以前不能穿的衣服了。”那些衣服不怎么樣,大昭是想自己也穿不了多久,不用買得太好。
和生把涮好的羊肉全都放在漏勺里,等湯都濾完才放進(jìn)大昭的碗,她自己的碗,就只放了芝麻醬。芝麻醬是她唯一喜歡的調(diào)味品,她不喜歡吃大蒜,也不愛吃辣椒,以前大昭特別能吃辣,現(xiàn)在在和生的勸說下不吃了。
大昭吃了一點(diǎn)就飽,她說:“我只吃了豆腐,還吃了番茄。肉吃了一片,我怕不消化。”
“你應(yīng)該再吃點(diǎn)生菜,”和生說,“煮在湯里的很好吃。”
“我吃了。”大昭說。她站起身到沙發(fā)上坐下,打開電視機(jī)看體育節(jié)目。
“我最近越來越能吃。”和生說,“我就老是覺得餓。”
“你干活太多,干了兩個(gè)人的活。”大昭嘴上說著,眼睛卻沒有離開電視屏幕。
自從生病之后,大昭就自動(dòng)跟蘇寧分了手。他們來往已經(jīng)將近十年了,蘇寧一直沒有跟簡珍離婚,和生不知道是簡珍不愿意離,還是蘇寧就從來沒想過要和簡珍離。大昭從來不向和生透露實(shí)際情況,每次和生只要一提,她就用別的話來搪塞。和生覺得這是大昭自己的私事,也不好過問。和生認(rèn)識簡珍,只是從來沒和她說過話。“她總來店里買糕點(diǎn),每次買得還不少,”林達(dá)說,“她可是我的大主顧。”
那是和生為了湊齊這筆錢,去找林達(dá)借三萬元時(shí)的事。她沒想到林達(dá)會(huì)一口答應(yīng)下來,趕緊說以后慢慢還他。“還不還無所謂。”林達(dá)笑著。但和生覺得林達(dá)說的只是客氣話,男人一般都會(huì)這樣說,以顯示男子氣概,如果不這樣說,好像就會(huì)顯得太小氣,但和生知道,做生意的,哪有不在乎錢的?“三萬塊也只是我面包店一個(gè)月的租金。”林達(dá)安慰她,“你不要把這事放在心上。”不過回去的路上和生想,肯定是要慢慢把林達(dá)的錢還上的。
蘇寧在二十年前就開了一家汽車修理廠,經(jīng)營得還不錯(cuò),他和簡珍一人有一輛車,還有一套大公寓。那套公寓離和生經(jīng)常去的超市不遠(yuǎn),和生有時(shí)候會(huì)在超市見到他和簡珍。就在不久前,和生還遇到過他們,兩次都見到他們的購物推車上堆滿食物,當(dāng)然還有其他日用品。兩次都是蘇寧推車,簡珍走在旁邊。
第一次碰面的時(shí)候,和生還能和他們聊上幾句。簡珍談到了大昭。“有你照顧她就好了,”她拉著和生的手,很親熱的樣子,好像她們很熟,“她能有你這樣的朋友,肯定很欣慰。我一直想著去看看她,總是忙,抽不開身。看看下周有沒有空,要是有空的話就去看看她。”說完她扭頭望著蘇寧,“我們下周有空嗎?老蘇。”蘇寧沒有馬上接茬兒,可能是因?yàn)榭吹剿荒樋嘞啵^了一會(huì)兒才說:“有的。”他們當(dāng)然沒有來看大昭,不過和生認(rèn)為,大昭也不想他們來看她。一個(gè)人和和生待著,是大昭現(xiàn)在唯一的想法。所以再在超市碰見蘇寧和簡珍時(shí),和生就沒跟他們說話,遠(yuǎn)遠(yuǎn)地點(diǎn)了點(diǎn)頭就走了。
和生去了汽車修理廠,她想找蘇寧問問,如果要買二手車的話,應(yīng)該買什么樣的車。和生去的時(shí)候,只有蘇寧一個(gè)人在。簡珍在廠房二樓布置了一間茶室招待客戶,順便賣些茶葉,周末的時(shí)候,她通常會(huì)留在家,陪從大學(xué)城回來的女兒。
蘇寧比大昭大三歲,算起來剛好五十,看模樣卻像四十不到。他頭發(fā)濃密,方方的下頜,給人固執(zhí)陰郁的印象。他帶和生去廠房轉(zhuǎn)了一圈,指給她看哪些車是適合的。
“如果走的路遠(yuǎn),這樣的車比較合適,”他指著一輛越野車說,“車廂寬大,底盤又高,只有這種車才便于作長途旅行。是四輪驅(qū)動(dòng)的,輪胎摩擦力又強(qiáng),防滑,排氣管還高,馬力也很大,上坡不吃力。”
和生知道,這樣的車不便宜,即便她和大昭所有的錢加在一起,再加上從林達(dá)那里借的錢,大概也夠不上買這樣一輛。
蘇寧想想又說:“還不能買太舊的,要是太舊,萬一路上出了故障就麻煩了。你會(huì)修車嗎?”
和生說不會(huì)。
“那就不能買太舊的。”停停,他又問,“你有駕駛證嗎?”
和生說有。
“但你平時(shí)很少開,對吧?很多人都有駕駛證,但平時(shí)很少開車。”
要是簡珍在,說不定是不會(huì)贊成讓幾乎沒開過車的和生碰車的,蘇寧卻說先找臺車讓和生練練。“先在廠區(qū)里開,如果開得還行,我們就到馬路上。”蘇寧說。和生戰(zhàn)戰(zhàn)兢兢上了車,打著火,在廠區(qū)的空地上開起來,蘇寧就一直在一旁指點(diǎn)。和生剛開始還不習(xí)慣,但一小時(shí)后就不再磕磕絆絆了。“你學(xué)得很快。”蘇寧鼓勵(lì)她,“我們?nèi)ヂ飞祥_。你要是不會(huì)錯(cuò)車、讓車,等于還是不會(huì)開。”
和生考駕照的時(shí)候,都有教練在旁,她確實(shí)沒一個(gè)人真正在公路上開過。這次她一上路盡管只是把車開在慢車道,但只要從后視鏡一看到有車跟上來,就開始頭暈。
“沒那么可怕,”蘇寧說,“他們不會(huì)故意來撞你,你開你的就行。”
車好不容易開出城的時(shí)候,和生手上全是汗。
“有我在旁邊,你怕什么?”蘇寧讓她膽子大一點(diǎn),“你不要這樣死死抱著方向盤不放,要把方向盤看成工具,而不是什么要抓住不放的東西。”
和生愣了一下,很想說:“大昭可沒有要抓住你不放。”但最終還是把這句話咽回去。他沒有那么討厭,至少?zèng)]有她之前想的那樣討厭。
路邊的河溝已經(jīng)起了綠意,田里更是綠絨絨的。已經(jīng)是春天了,兩邊的梧桐樹上已經(jīng)長出了新芽,還有河邊的柳樹,葉子也已經(jīng)長大了。風(fēng)吹過來的時(shí)候,和生感覺心曠神怡,她想,在這之前她怎么沒有注意到?自大昭病后,她就一直在照顧她,連服裝店也暫時(shí)關(guān)門了,只在家和醫(yī)院兩個(gè)點(diǎn)之間跑,可能就是這樣,這些事讓她太緊張了。
“我們別再往前開了,”蘇寧說,“再往前就要出昆明了。”
“出昆明還早,”和生嘴上說,卻還是把車停住,“我的腿為了踩剎車都已經(jīng)發(fā)抖了。”
“不用緊張,沒事。”
過去十年,大昭每個(gè)星期都在等蘇寧。星期六對她來說就是節(jié)日。如果說前面五天,她就像死了一樣,那么到星期六她又活了過來。應(yīng)該說到星期五,她就已經(jīng)有活過來的跡象。她開始興奮,想著為即將到來的蘇寧做什么好吃的。到了星期天,那種鮮活勁還沒有散去,和蘇寧一整天的相處,讓她精神愉快,但從周二又不行了,她開始焦慮,害怕自己某些方面讓蘇寧失望,他再也不會(huì)來了,這種焦慮在周四達(dá)到頂點(diǎn)。一般來說,那天晚上蘇寧會(huì)打來電話,說周六會(huì)過來,只有到那個(gè)時(shí)候,她才放松下來,開始憧憬著即將來到的周末。
和生認(rèn)為大昭的生活就是一個(gè)可憐的循環(huán)。“她完全把自己交給別人做主了。”她對珞彤說。珞彤對大昭的事一點(diǎn)興趣都沒有,她才開始談戀愛,男朋友是她的大學(xué)同學(xué)。和生見過那個(gè)人一次,算有禮貌,只是太自大了。和生沒把自己對那個(gè)人的看法告訴珞彤,他們已經(jīng)約定畢業(yè)后就結(jié)婚。處于幸福中的珞彤,對他人的痛苦置若罔聞,就像它們根本不存在,和生怎么能指望她理解大昭?
和生自己也理解不了。她只知道,大昭生活中的不幸把她擊垮了,誰給她一點(diǎn)溫暖,她便停在那里。她對什么都不在乎。她和蘇寧的關(guān)系維持了十年,蘇寧和簡珍都沒有要分開的跡象,她也不著急。“他只是下不了決心。”大昭說。大昭說這話的時(shí)候皺著眉,像小學(xué)生一樣啃著指甲。她一有煩心事或焦慮就咬指甲。“他就是心軟。”啃完指甲后她接著說。
得知罹患癌癥后,她倒是抱著和生哭了一場,眼睛腫得像兩個(gè)魚泡似的。“沒事的,這真的沒什么。”和生只能安慰她。和生也想哭,她恨自己除了這句話外,再也找不到別的詞。
和生從醫(yī)院回家,大昭正在曬被子,她們曬衣服都是在陽臺外面的防盜籠,和生在那里拴了一根繩子,衣服和被子都可以掛在上面。“天氣已經(jīng)熱了,這么厚的被子用不上了。”大昭從陽臺進(jìn)來時(shí)說,“我明天再洗一下衣服,把該打包的打包起來。”
“你不用那么累。”和生說。
“這用不了多少力氣的。”大昭笑笑。
和生洗青菜的時(shí)候,大昭就在一旁切香腸。大昭刀功好,又有耐心,能把香腸片切得很薄,她把香腸整齊地?cái)偲皆诒P子底上的時(shí)候,和生去廚柜取酒。她在那里放了三瓶酒,兩瓶紅的,一瓶白的,回來的時(shí)候她故作歡快地對大昭說:“我們喝酒吧。”她覺得她們應(yīng)該高興,雖然可能買不了那么好的二手車,差一些的總是能買,這并不影響她們的計(jì)劃。于是她邊說邊晃著手里的酒瓶,好像那是一面勝利的旗幟。大昭已經(jīng)把香腸切好了,走到桌邊,望著和生說:“只要一輛舊車就行。”
“當(dāng)然,沒問題。”和生把酒瓶放在桌上,騰出手來拍了拍大昭。
“要是她半路上死了怎么辦?”珞彤問過和生。
“那我就把她埋了。”
……
(全文詳見《江南》2023年第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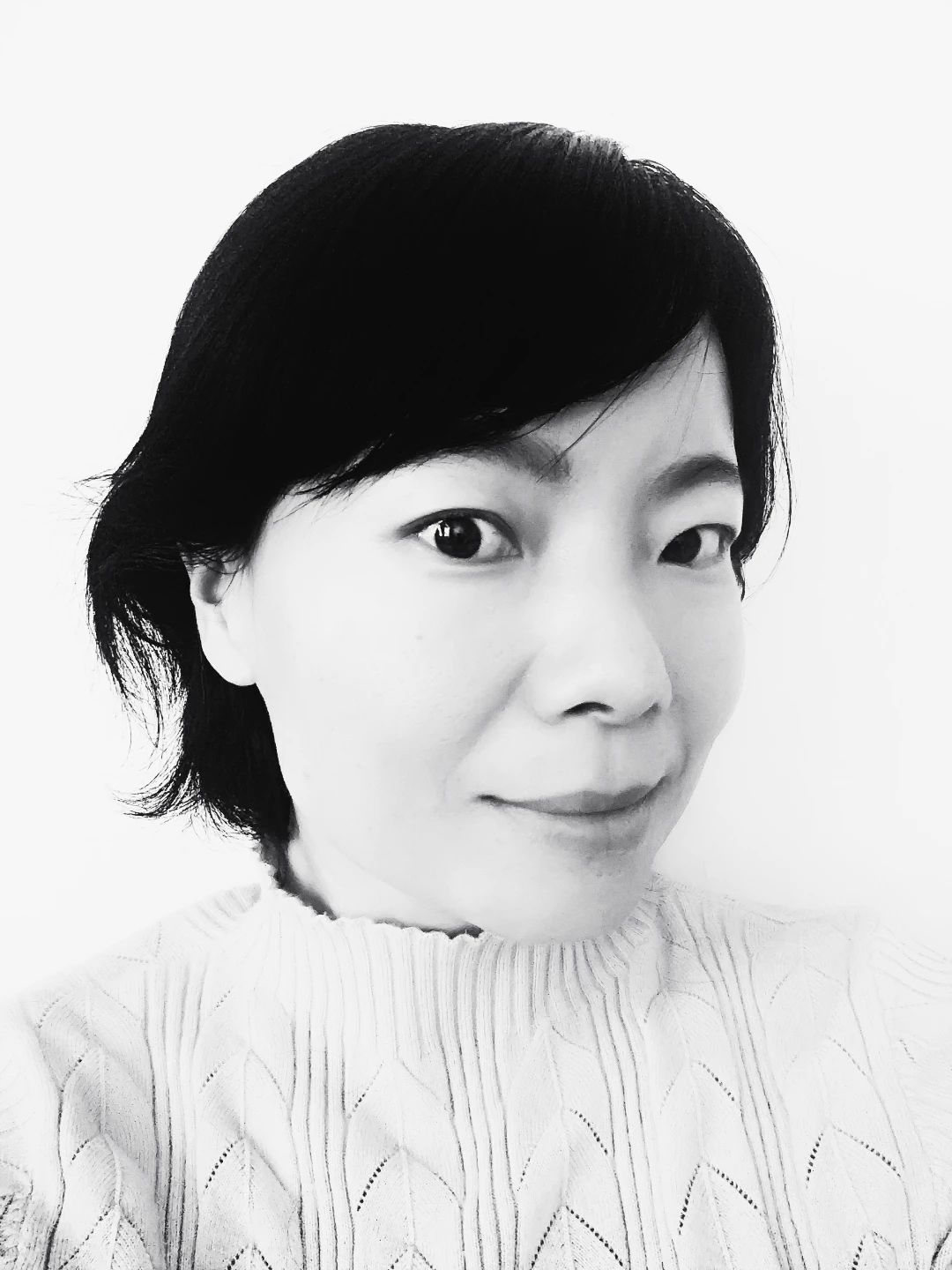
馬可,云南昆明人,大益文學(xué)院編輯。在《滇池》《邊疆文學(xué)》《江南》《野草》《四川文學(xué)》《香港文學(xué)》《北京文學(xué)》《上海文學(xué)》《十月》等刊物上發(fā)表有小說詩歌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