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增杰:略論現代文學史料研究中的幾個問題 ——劉增杰先生訪談錄

劉增杰,1934年5月生,1952年考入河南大學國文系,195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6年大學畢業后,留校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1959年,到北京大學進研班學習一年,師從著名現代文學史家王瑤先生。曾擔任河南大學中文系現代語文教研室主任、中文系副主任、中文系主任、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學院名譽院長,榮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河南省優秀專家、河南省高校師資培訓工作先進工作者、河南省優秀研究生導師等稱號。
劉增杰先生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研究、解放區文學研究等方面皆有開拓性貢獻,影響深遠。主要著作有《魯迅與河南》《中國解放區文學史》《中國近現代文學思潮史》《文學的潮汐》《戰火中的繆斯》《云起云飛——20世紀中國文學思潮研究透視》《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發現與闡釋——現代文學史料知見錄》等,主編有《抗日戰爭時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文學運動資料》(三冊)《師陀研究資料》《師陀全集》(五卷八冊)《師陀全集補編》等。
劉先生于2022年12月29日在南京因病去世。
Q
郝魁鋒:劉老師,很高興你就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的建設問題接受我的采訪。我知道,你在中國解放區文學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學術工作。在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研究領域也投入了不少精力。據我初步統計,三十多年來,你除發表了一批史料研究論文外,還出版過多種史料研究著作,編校過多種史料集。這些論文和著作,在現代文學史料研究中,引起過讀者和研究者的思考與興趣。我想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最初你是怎樣開始注意現代文學史料研究的呢?
劉增杰:說來話長。我對史料研究產生興趣的時間可以追溯到1978年年底。那時候,國內逐漸涌動起了為紀念魯迅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的魯迅研究熱潮。研究熱點往往誘發學術欲望。起初我不知所措,不知道自己能夠做點什么。不久就找到了選題。在此之前,我在河南大學圖書館,曾經讀過20世紀初年日本東京出版的《豫報》和《河南》。河南省留日學生在東京創辦的這兩種刊物思想激進,堅持反封建的愛國立場,吸引了魯迅、周作人等在刊物上發表了一批產生過影響的文章。
記得讀到1906-1908年出版的這兩個刊物,以及1925年在魯迅支持下開封創辦的《豫報副刊》時,我的情緒激動,第一次了解了魯迅對河南作家和中原人民的關心和牽掛,但當時還沒有產生寫作的沖動。待到再找出來重讀時,眼前突然一亮。心想:為了避免研究中的雷同、重復,我何不選取地域文化的視角,寫一點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呢?邊讀邊寫,在兩年多的時間里,我接連寫了二十幾篇魯迅與河南相關的短文來,部分文章分別發表在《奔流》、《莽原》等刊物上。
當時,我對《豫報》第一期刊出的魯迅早期著作《中國礦產志》的出版廣告和《中國礦產全圖》的出版廣告的作者是誰,產生了疑問。經過初步分析,我認為應是魯迅所寫,但我對辨析、考證方法相當陌生,心里不踏實。于是就將《〈豫報〉所刊魯迅早期著作的兩個廣告》短文,唐突地寄給了魯迅研究家唐弢先生,請他幫助做一下判斷。在此之前,我只知道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的叔父尹達(原名劉燿)和唐弢先生都住在社會科學院家屬院。叔父曾向唐弢先生介紹過我,請他對我的學習給予指導。我在信上向唐先生介紹過自己的情況,唐先生給我回過短信,對我怎樣學習現代文學提出過一些建議。但我們并沒有見過面。這次唐弢先生收到短文后,并沒有給我回信,他把短文的題目改成《有關魯迅早期著作的兩個廣告》,寄給剛剛創刊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已出了第1輯)。料想不到,短文很快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2輯刊出。文章的發表給我的史料研究帶來了新的推動力。
Q
郝魁鋒:聽說,你的魯迅與河南研究、現代文學史料研究,得到過任訪秋先生、王瑤先生的指導,具體情況怎樣?
劉增杰:在寫作過程中,我不止一次地向任訪秋先生匯報過自己在河南以及赴北京搜集有關資料的情況,在北京等地訪問曹靖華、劉峴等作家的收獲。任先生每次都叮囑我:史料的搜集、整理,一定要不拘大小,一網打盡,最后再做出獨立的判斷。當時,研究進展順利。河南人民出版社已經和我簽約,決定出版《魯迅與河南》這個小冊子,曹靖華先生題寫了書名,木刻家劉峴先生設計了封面。我邀請任先生寫序,他也高興地應允了。先生在序言中說:“增杰同志寫的《魯迅與河南》這部書,對史實詳加稽考,對事理深入分析,平實審慎,細大不捐。”序言上業師的囑托是對我從事史料研究提出的基本要求,讓我終生受益。《魯迅與河南》按計劃于1981年8月出版。

《魯迅與河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在撰寫《魯迅與河南》書稿的同時,197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持的中國現代文學資料征集活動在全國范圍內展開。由六十多所高等學校、研究機構的三四百名研究者參與,十七家出版機構同時組織出版的龐大機器,在文學所的統一協調下開始運轉。1980年9月初,主持單位邀請相關出版社編輯和高校、研究機構的代表,在安徽黃山召開了現代文學資料會議,具體討論了編輯三種叢書的原則與任務。三種叢書即:甲種:《中國現代文學運動·論爭·社團資料叢書》;乙種:《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研究資料叢書》;丙種:《中國現代文學書刊資料叢書》。落實編選任務的時候,討論到《中國現代文學運動·論爭·社團資料叢書》中的《抗日戰爭時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文學運動資料》一書時,會場冷了場。大家你看我,我看他,卻沒有人站出來認領任務。會場里不時還能夠聽到有人小聲地議論:戰爭環境下,資料丟失太嚴重,搞起來困難……片刻沉寂后,會議主持人之一的王瑤先生,突然抬起頭來,微笑著望了望我說:“劉增杰,你們單位人多,承擔起來怎么樣?”我那時已經答應了承下編《師陀研究資料》等作家研究資料的任務,卻對從事解放區文學資料編選沒有思想準備。聽到了王先生的問話,我支支吾吾,講了一些對研究對象不熟悉等理由進行婉拒。沒想到,針對我列舉的理由,王先生竟逐條做了“反駁”。他說,對研究對象不熟悉,不是理由。你下點功夫不就熟悉了么?還說,編選史料的學術價值,主要是看編選者的認真程度,學術見識的高低。王先生雄辯滔滔。他一邊陳述自己的理由,一邊詼諧地哈哈笑著,好像等待著我應答時出現新的漏洞,再來將我一軍。會場上的氣氛頓時活躍起來。顯然,大家都被王先生機智的論辯方式征服了。當時我自知不是與先生論辯的對手。心想,自己又被聘為乙種叢書編委,應該服從工作大局,就爽快地接受任務了。王先生和我論辯時直言直語,隨意而親切,顯然是源于二十多年前我們之間的師生關系。1959年8月到1960年7月,我在北京大學中文系進修班讀書的時候,王先生給我們班講了一年現代文學課。這段師生之誼,此后一直保持著。我很尊重先生的為人和學術見識,現在還珍藏著一厚本當年的聽課筆記。解放區文學史料的征集、編選任務,就這樣落實到了我和教研室幾位老師肩上。三卷本《抗日戰爭時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文學運動資料》編好后,經過王瑤先生、徐迺翔先生審定,1983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面世。
應該說,我的史料研究,經歷了一個從半勉強到自覺的過程。我在實踐中所逐漸獲得的一些感悟、收獲,受惠于幾位學術前輩的關愛。他們強大的人格力量,獻身學術的精神,對我們這一代人的指點、呵護,深深地影響著我們前進的腳步。
Q
郝魁鋒:學術前輩對你們那一代學人的幫助、愛護、培養本身,就是中國現代文學寶貴傳統的組成部分,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研究者的幸運。在這里,你能不能根據自己史料研究的實踐,從宏觀上梳理一下現代文學史料研究的發展脈絡?
劉增杰:你提出的問題的確重要。百年來的現代文學史料(從晚清民初直到21世紀初年),各個階段的研究,呈現為一種既有內在聯系又各有所異的復雜研究景觀。
我的感受是:研究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從晚清民初到20世紀30年代,為史料研究的第一個階段。這一階段,30年代的史料研究成果豐碩。突出特點是:由學術界領軍人物親自出馬,以高屋建瓴的學術視野,采取作品編選、創作評論與史料整理三者并重的方式開展工作。研究的突出成果是十卷本《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出版。
20世紀30年代至80年代是史料研究的第二個階段。研究成績以80年代最為突出,特點是痛定思痛之后的反思。由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主持的中國現代文史資料征集活動及其出版的三種史料叢書(約80種)就是這一階段史料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表面看來,這只是一次史料征集活動,它的背后卻隱藏著深刻的學術動機。這既是對持續十年之久的文化專制主義的根本性反叛,也是恢復現代文學研究活力的決定性步驟。還應該看到,這次史料征集活動,不僅對現代文學史料研究起到了推動作用,而且還繼續發酵,對整個新文學史料建設產生過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現代文學資料三種叢書出版過程中,由多批學者組成的研究隊伍,還先后出版了《中國近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中國解放區文學史料叢書》。應教學之需,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現代文學教研室聯合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中的《文學運動史料選》也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該書第一版就印了10萬套。這從一側面,說明了當時史料研究的廣度及其產生的巨大影響。
20世紀90年代以后二十年的史料研究為第三階段。這一階段的史料研究,既沒有大規模的、有組織的史料征集活動,也沒有輿論的集中造勢,它已經沉潛為日常學術建設的一部分。知識產權出版社以《中國文學史資料全編·現代卷》的形式,集中出版了上個世紀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主持的三種叢書中大部分史料,但也只能稱為第二階段史料研究的余波;或者說,是對第三階段研究的銜接、配合。
這一階段史料的發掘、整理與闡釋,并不轟轟烈烈,多是個體活動或少數志同道合者的聯合,但研究極具深度,甚至稱得上是百年史料研究的精彩總結。我在《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里專門開列書目,對以新一代學者為主在這一時期所取得的史料研究成果,作了贊許性的介紹,可以參看。

《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
中西書局2012年版
Q
郝魁鋒:《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人物篇,向讀者介紹了許多研究家和他們的著作。你在這里可否給我們推薦一些學術特色鮮明的史料學論著?或者說,介紹幾部(篇)帶有經典性的研究著作?
劉增杰:在閱讀過程中,的確有許多著作讓我愛不釋手,印象深刻。有閱讀興趣的朋友,不妨讀一讀以下幾部(篇)著作。不過,這并不是通常所說的經典重讀。就現代文學史料研究而言,時間時刻在調整著,或者說在顛覆著已有著作的評價與地位。我只是主張讀幾部有個人見解的書,有思想力的書,甚至看來有某些偏激片面卻言之成理的書。
梁啟超是從古典文學史料學研究走向現代文學史料學研究的關鍵性人物。單就中國近現代文學史料研究而論,他在“五四”之后完成的《清代學術概論》(1920年)、《中國歷史研究法》(1921年)等,系統地對清代學術研究的成績與問題進行了總結,在學術思想上與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研究直接銜接,血脈相通。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對清代學者整理舊學成績的十項總體性評論,他所主張的以科學的眼光對研究對象的“重估”,他對史料研究面臨諸種困境的警示,等等,都給讀者帶來了深刻影響。梁啟超以無所不及,無所不窺的學術視野,使他在文學歷史轉向時刻握有關鍵性的玄機。他的研究不僅向過往追溯,而且向著未來延伸,文字中蒸騰著過渡時代高格調的文化氣息。梁啟超是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研究當之無愧的先行者。
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最初刊于1923年《申報》50周年紀念刊。胡適在日譯本《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的序中說:“我的目的只是要記載五十年新舊文學過渡時期的短歷史。”“過渡時期”是現代文學史料研究首先碰到的一個大問題,關鍵問題。《胡適全集》里研究新文學的文字極多,有時間不妨多看一些,但至少要翻一翻中華書局1993年版《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一書中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的現代文學史料研究,比起他的古典文學史料研究來不免顯得有些薄弱,但他的研究仍具有首創的意義。作為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倡導者和實踐者,胡適以放眼全局的學術視野,在新文學運動發生二十年之際明智地提出,因為中國新文學運動發生的“時間太逼近了,我們的記載與論斷都免不了帶著一點主觀情感的成分,不容易得著客觀的、嚴格的史的記錄……一個文學運動的歷史的估價,必須包括它的出產品的估價。”他強調,沒有足夠的時間積淀,只能進行初步的史料整理,而不能寫出信史。胡適期望,在漫長而復雜的文學生態下,史料研究者應保持著獨立姿態和批評立場。正是堅持著這一基本原則,魯迅的經典小說,才獲得了胡適經典性的評論。
魯迅的史料研究實踐豐富、深刻。他早年在寂寞中從事整理的《古小說鉤沉》、《小說舊文鈔》,顯示出了魯迅史料研究中的真功夫。他的史料研究的鮮明特點是:以批判性思維審視歷史與現實,始終保持著史料研究鮮明的現實品格。魯迅特別強調保存史料與搶救史料的現實迫切性,并且身體力行。比如,為了保存隨時可能流失的史料,他在雜文集里,通常采用如下方式保存史料。在《而已集》、《花邊文學》中采用“附錄”的方法將對方的文字錄入自己的雜文之后備查;在《偽自由書》、《準風月談》、《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中采用“備考”或“附記”、“后記”的方式保存史料;《且介亭雜文末編》(許廣平在魯迅逝世后編定)則又采取了“立此存照”的方式保存史料。魯迅的現代文學史料研究本身是一部大書,我們無法僅僅開列出一部書來搪塞。還是請讀者通過對《魯迅全集》瀏覽性的閱讀實踐,自己來作出智慧的選擇吧。
阿英是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研究的一位自覺的開拓者。阿英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卷是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建設中出現的第一部具有完整意義的史料著作。把現代文學史料分為總史、會社史料、作家小傳、史料特輯、創作編目、翻譯編目、雜志編目及索引等類別,是阿英史料研究的首創,影響深遠。阿英自覺地將近代文學史料研究和現代文學史料研究打通,形成了兩者相互融合、滲透的研究格局。阿英所確立的貴今賤古的史料觀,他對現代文學史料不斷被毀棄現象進行的持續性揭露等,確立了一個立體的史料研究空間。阿英創作與史料研究并重的學術實踐,對后來者留下的啟示多多。
唐弢在現代文學史料研究中有著突出的貢獻。人們熟知,他對魯迅作品的輯佚成績蜚然。收藏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唐弢藏書有雜志1.67萬件,圖書2.63萬件。正如舒乙所說,一冊《唐弢藏書目錄》是“一座天然的紀念碑”。我在這里更愿意推薦的,則是他的《晦庵書話》(1962年北京出版社印行,1980年10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書話中不僅收藏有豐富的史料,還濃縮了唐弢的書話觀。他在1980年版《晦庵書話》中說:“光有資料卻不等于書話”,“書話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點事實,一點掌故,一點觀點,一點抒情的氣息,它給人以知識,也給人以藝術的享受”。之前,唐弢還說過類似的話:“通過《書話》,我曾嘗試過怎樣從浩如煙海的材料里捕捉使人感到興趣的東西,也嘗試過怎樣將頭緒紛繁的事實用簡練的幾筆表達出來。”這兩段論述啟示我們:史料研究并非全部是沉悶的整理、介紹。史料研究的天地廣闊,它同樣需要《晦庵書話》這類讀來興味盎然的文字的滋潤。
王瑤先生是從治漢魏六朝文學改為中國現代文學教學與研究的。得天獨厚的知識結構,使我們看到了他以豐富史料為基礎對現代文學闡釋的精彩。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是一種無聲的宣示:文學史寫作必須以堅實的史料為基礎。許多研究者都對這部書在史料學建設上的突出貢獻做出過中肯的評論。早在1950年,詩人臧克家就看出了“查原始材料,讀原著,出己見”是這部文學史的鮮明特點。嚴家炎也說:“《中國新文學史稿》是我國第一部史料豐富、體系完備的現代文學史著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奠立了最早的基石”,“在研究資料把握上,有人說他是‘竭澤而漁’,那就是說,他要力求做到占有所有的有關材料,在此基礎上形成創見”(《先驅者的足跡——王瑤學術思想研究論文集》第1、2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臧克家、嚴家炎的文字,確系對王瑤研究個性的準確概括。王瑤還明確主張,現代文學研究要借鑒古典文學研究的方法,指出:“在古典文學研究中,我們有一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鑒別文獻材料的學問,版本、目錄、辨偽、輯佚,都是研究者必須掌握或進行的工作,其實這些工作在現代文學的研究中同樣存在,不過還沒有引起人們應有的重視罷了。”對前輩研究現代文學的歷史經驗,王瑤也十分重視。他特別看重朱自清講授《中國新文學研究》表述自己的看法和評價的時候說的“先從敘述事實根據開始”的歷史經驗。王瑤四十年的現代文學、現代文學史料學研究的成績及其所經歷的曲折,是迄今為止較完備的研究遺產,值得認真思考與研究。
嚴家炎治學嚴謹,1980年代初期,唐弢對他的研究就做過切實的評論。唐弢說,嚴家炎對丁玲小說《在醫院中》的重新評價,對艾青發言《現實不容歪曲》的具體分析,揭示蕭軍刊登在《文化報》上“社評”和“獻詞的真實意義”,這些,都“充分顯示了一個史學工作者的職業道德”(唐弢:《求實集·序》,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求實集》是一本有生命力的書。三十年后重讀,仍然可以讀出作者的人格精神。比如,他反復強調,研究者要讀第一手的原始資料,占有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在研究原始的作品和史料上下苦功夫。用他形象的說法叫做:“啃別人吃過的饃是沒有多大意思的”。嚴家炎特別推崇研究者學術研究中的獨立思考。他多次申明:“學術研究應該是獨立的,除了服從歷史事實這位上帝之外,它不應該服從任何人。”嚴家炎對現代文學研究中的重大問題,常能發前人所未發,率先進行學術清理。
嚴家炎也是建設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熱心倡導者。只要讀一讀他對樊駿《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一文的極高評價,就可以看出他對這項工作的重視程度了。嚴家炎說:“《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是把這項工作當作‘宏大的系統工程’來闡述的,全文長達八萬多字,更是現代文學史料學這個分支學科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它不但是對過去幾十年文學史料工作的一個綜合考察,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極好的建議,具有相當的實用價值和可操作性。可以說,這八萬字是作者經過長期積累,查閱了至少一二百萬字的各種材料才寫成的,照我個人看來,實在可以規定為現當代文學研究生的必讀篇目和新文學史料學課程的必讀教材。”當他看到我在上海中西書局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時,嚴家炎在《一點感想》一文中作了熱情的鼓勵性評價,飽含著他對史料學研究新的期待。
如嚴家炎所說,樊駿對現代文學史料學建設作出的貢獻最多。《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是迄今為止百年來篇幅最長的史料學研究論文。樊駿自己說,這篇探討現代文學史料工作得失的文章,寫了兩年,自己得以“從容地把想法寫出來,實在是少有的痛快”。論文分六個部分,回顧了現代文學史料研究的坎坷道路,新時期十年史料研究的進展,闡釋了進一步發掘新的史料類型的現實意義,提出了鑒別史料與提高史料研究者的學術修養的迫切性,呼吁搶救史料與觀念更新等。樊駿當時發出的強化史料研究的呼吁,在國內許多高校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名稱各異的史料學講座或課程紛紛開設,刊物上圍繞建立史料學問題的研究論文明顯增多。樊駿的文章里,他的人品、文品和歷史精神,總是和諧地統一于一個內在的結構之中,文字中有著含而不露的思想光芒,隱而不顯的理性內核,是一代研究者為創建史料學留下的精神記錄。樊駿的史料學研究實踐,具有某種恒久的示范意義。
人們當然不會忘記朱金順先生的獨特勞作。他的《新文學資料引論》,是在高等學校開設史料學專題課的第一部教材(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86年版)。如他自己所說,資料學在整個研究工作中,唱配角而不唱主角,類似邊緣學科,它為一切史論制造論據,提供佐證,雖然這是材料的爬梳、考辨工作,卻有它獨立的價值。他“愿做為引玉之磚而拋出”。從幾十年來史料學研究的實踐看,《新文學資料引論》的確具有首創之功。
Q
郝魁鋒:你對新一代史料研究者的學術成果有何評價?可以向讀者推薦幾部他們的著作么?
劉增杰:我平時很關注新一代史料研究者的學術成果,到手必看。他們代表著史料學研究的未來。他們不走老路,視野開闊,連老一代研究者也能夠從他們青春的活力中汲取力量。他們的研究不隨時潮仰俯,有著出手不凡的創獲,進行著富有新意的學術清點。他們重視利用網絡,但是,更靠閱讀紙質材料實現著自己的學術構想。這里只能做掛一漏萬的舉例性介紹。時間是他們研究成果最終的裁決者。在史料研究中能夠耐得住寂寞的人,可能就是歷史最后青睞的人。
陳子善的現代文學史料研究成績蜚然,他的多部著作都在讀者中產生過反響。他研究史料,不是板起面孔寫“嚴肅”的大文,而是以小見大,在自己發掘的史料海洋里自由地穿行。他曾經不無自得地敘述過自己研究的特點:“它們發掘了一些重要作家的佚文,考訂了一些鮮為人知的文壇史實,解決或部分解決了現當代文學史上的一些懸案或疑案。說得學術一點,它們是現當代文學史料學的微觀研究和實證研究的一些實例。書里雖然沒有多少理論上的闡發,但我對現當代文學史的思考已蘊含其中矣。我想,這就夠了。”“我想,這就夠了”,寫得從容淡定,謙虛而自信,余味無窮。讀者從他多種著作中任選一種讀一讀,都可以讀出特有的陳子善味。
上海另一位重視史料研究的學者是陳思和。讀到不久前他和王德威共同主編的《史料與闡釋》(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6月版),我不禁脫口而出:“這是一部智慧之書!”書名沒有張揚,甚至沒有給讀者帶來吸引眼球的驚喜,但“史料與闡釋”五個字含義深長。當前,提高現當代文學學科研究學術質量的關鍵所在,不就是在堅實史料基礎上進行深入闡釋么?《史料與闡釋》的欄目分為“文獻”、“資料”、“論述”三個部分,中心是對2008年去世的三位“胡風冤案”受難者的紀念。“文獻”、“資料”中包含著當事人的一批極具歷史價值的信件、日記以及在壓力下的自我檢查等,讀后令人扼腕嘆息。《史料與闡釋》把史料與闡釋有機地結合到了一起,這種更具個性化的表述方式自有其生命力。
解志熙的《考文敘事錄——中國現代文學文獻校讀論叢》(中華書局2009年版)值得一讀。解志熙舍得在閱讀上下苦功夫,他的閱讀范圍相當廣博,由今溯古,進而由文學而歷史而哲學。《考文敘事錄》對那些目前研究相對薄弱的作家和作品選取獨特視角,寫出了洋洋灑灑,讓人耳目一新的考證文字。對古典文學研究著作的解讀,他沒有隔行的陌生。像他評論業師的長文《古典文學現代研究的重要創獲——任訪秋先生文學史遺著三種校讀記》,就寫得極見功力。他堅持客觀、公正的學術立場,指出:先生的中國文學史研究,把握“中國文學史發展大勢和關鍵環節”,“他的文學史洞見,不僅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學史論著中穎然秀出,即使在今天那些寫來越來越繁的文學史著作中也甚為罕見,所以今天讀來仍然讓人深深感佩其以少總多,啟人神智的力度與美感”。解志熙并不為尊者諱,為老師諱。在評論先生的《中國小品文發展史》時,他就對先生“拔高小品,貶抑古文乃至駢文的態度”提出了商榷。解志熙感受力敏銳,語言融通、周詳、機智、厚重,謙恭禮讓又自尊自強,值得人們注目與期待。
在現當代文學史料研究中,另一位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李怡。他在《歷史的“散佚”與當代的“新考據研究”——史料建設之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意義》中說:“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歷程中,還發生了不斷的人為損毀事件,最顯著的至少就有三次:國共兩黨的軍事斗爭與文化斗爭,日本侵華戰爭,‘文革’的浩劫。國民黨對異端思想與革命文學的鎮壓,我們也同樣不易見到其他政治立場的文學作品,乃至張愛玲的作品對許多研究者而言也是并不完整的。日本侵略導致了中國文化整體板塊的破碎,在風雨飄搖的歲月,許多的文學現象幾乎就處于自生自滅之中,其意義根本就來不及在文學史家那里得以衡定,隨著一代歷史見證人的紛紛謝世,隨著‘抗戰土印紙’在時間的磨蝕下隨風而逝,我們曾經有過的歷史之鏈也將永遠殘缺,更不用說‘文革’了,一切文化的遺產都進入了清算之列,政治家不斷通過對文化遺產的銷毀來鞏固自己的合法性,這樣以‘焚書坑儒’的方式維護政治利益的思路可以追溯到秦始皇時代,但卻并沒有因為‘文革’的結束就宣告終止。文化保存制度的欠缺和人為的有組織的破壞是導致中國現代文學史料散佚的最大原因。”(《學習與探索》2004年第1期)。李怡一方面義正辭嚴地向讀者指出史料遭遇到三次損毀的現實;另一方面,他又擴大研究視野,積極從事文化與史料建設。他近年主編的《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22冊,臺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出版),就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其中,李怡、謝君蘭、黃菊編的《民國憲政、法制與現代文學》(上、中、下),就是一個新領域的開拓。
Q
郝魁鋒:劉老師站在歷史的高度,對百年來有影響的史料學著作,作了簡要而富有個性的評說,對我很有啟發。我注意到,這些年來,學術界對你的史料研究也發表過不少評論文字。比如,你的論文《脆弱的軟肋——略論現代文學研究的文獻問題》,在《文學評論》2006年第6期發表的同時,《編后記》就寫了如下一大段評論:“我們曾多次指出:在古典文學研究由史料的整理向史料的解釋大膽挺進的同時,現代文學(也許也應包括‘十七年’的文學)研究應該由史料的解釋向史料的整理小心地回溯。——現代文學研究中史料文獻問題愈來愈成為這個學科生命的泉源所在,離開了真實可信的史料文獻:史料的匱缺、誤解、曲解、割裂、藏匿、毀棄、纂改、變造等,現代文學研究的實證性將遭異變,歷史本質將被閹割,她的科學價值便不復存在,學科生命也隨之窒息。劉增杰的文章希望大家認真讀一讀,其中文獻自身的史學力度與作者忠愨的學術良知令我們震撼,也令我們信服了今天的現代文學研究運作機制中史料的核心地位。”我知道,這篇論文當時就獲得了2003至2007年度《文學評論》優秀論文獎。去年,文章又獲得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第三屆王瑤學術獎二等獎。張中良在評獎語中指出,論文“勇于直面這一‘脆弱的軟肋’,透過對文獻匱乏、史實舛誤,任意刪改等常見弊端的梳理,指出問題的普遍性與嚴重性,并對軟肋的成因做出深入的分析。論文的重要意義在于提醒現代文學界,失去文獻學基礎的所謂學術,很難獲得旺盛而長久的生命力。”希望你能夠結合研究實際,談談自己在史料研究中的心得體會,經驗教訓。
劉增杰:在現代文學史料研究中,我的確做了較長時間的努力。至于這些年來所受到的一些肯定,都不過是學界朋友的鼓勵。應該承認,在學術理念上,我和《編后記》作者張中良先生是心心相印的。我在史料研究中,比較關注研究中存在的薄弱環節,我把它比作“脆弱的軟肋”。“軟肋”中突出的一個表現,是一些自恃權威、名人的人,他們有時并不依據事實說話,或奉命對學術問題妄下結論,或以個人好惡亂下斷語。每讀到他們的這些文字時,就想據理爭論,但又舉筆不定:一會兒自我安慰,我堂堂正正說理,靠事實辨析問題有何妨礙;一會兒又躊躕不安,嘆息一聲,放下筆來。寫《脆弱的軟肋》一文時,學術良知戰勝了心理怯懦。如文中指出:在文藝批評中,郭沫若不顧事實對朱光潛作簡單的政治裁決,“不僅在當時不能說服被批判者和讀者,甚至還會在被批判者乃至整個學術研究者的心理上留下長長的陰影。”根據當時的大量事實,我批駁了茅盾對抗戰文藝主要毛病是右傾的觀點。指出這是“理論上的蒼白”。文章對于涉及政治敏感的王實味問題,通過學術考察,也理直氣壯地做出了自己的結論。認為,對復雜的文學歷史現場,用符合研究主體或符合主流話語的價值判斷進行簡單化的裁決,不僅會造成批評的淺層化,甚至還會造成重大失誤。又說,史料研究中存在的這一類問題,不是枝節性的問題,不是在個別問題上的偏激,而是涉及全局的方向性問題。
我的史料研究,特別是涉及解放區文學的研究,前些年的經歷還是曲曲折折的。某些非學術的壓力,讓我有口難辯,承受著心靈的熬煎。幾年以后,自己還是忍受不了這不公正的責難,趁著撰寫《遲到的探詢》的《前記》的機會,就做出了雖還溫和但也帶有點火氣的抗辯。我說,人們在研究中,“對于解放區當時有不同意見的爭論、作品,或歷史已經證明處置失當的問題,卻總是較少涉及。對于解放區文學發展中所經歷過的若干曲折,似乎引以為羞,或有意遮蔽,或避而遠之。而殊不知:曲折是生命,曲折是生命的豐富。沒有曲折的生命無法享受人生。文學亦然。正是文學發展中的曲折,才構成了文學的真正壯麗。對解放區文學真正的理解,體現于建立嚴肅的歷史意識,確立史家的公正與自信,而不是對于某些前進中的缺陷諱莫如深。前幾年,由我主編,趙明、文金先生參與部分撰稿的《中國解放區文學史》出版后,曾經有位好心的先生把書中凡是講到局限與不足的地方,全部細心摘出,開列清單,巧妙編排,煌煌數千言,以期證明該書錯誤的嚴重。誠然,書中我寫的那部分書稿肯定是有不少缺點的,甚至也可能有錯誤。我過去、現在、將來都歡迎展開討論和爭鳴。但是,上述作法我是不敢茍同的。斷章取義、羅織罪狀;或聽風是雨,滿目‘敵情’。把真知斥為異端,把不同見解誣為謬論,毒化學術討論空氣,必欲置論敵于死地而后快,等等。此種文風,曾經使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學術研究,付出了血的代價。學術研究就是學術研究。研究者的心思用在非學術上,以圖從批判、否定別人的學術成果中撈取學術以外的收獲,則會把我們的整個研究工作扭曲。”
史料研究質量提高的另一個重要環節,是對自己研究中出現的差錯、教訓,及時進行反思與清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中的《后記》里,我用較大的篇幅,回顧了自己研究中出現過的失誤:史料研究的實踐繼續讓我碰壁。《魯迅與河南》出版不久,根據《中國現代文學運動·論爭·社團資料叢書》編委會的統一規劃,我們就開始進行解放區文學史料的調查、搜集、整理工作。史料征集完成后,終于獲準出版。當得知書的清樣已經印出,我隨即向責編寫信,要求校讀清樣。不料,好心的編輯來信說,“不用了,來往郵寄書稿,太費時間。”我開始耐心地等待著。等待是一種急切的期待夾雜著甜蜜的幸福感。我的心頭涌動著即將獲得豐收的特有興奮。書果然很快寄來了。封面設計簡潔大方,厚厚的三大冊史料集擺到了案頭。待打開細看,我的心驟然一驚:書的校對實在粗糙,一些不該出錯的字竟印錯了,甚至個別小標題也出現了差錯。我再次嘗到了自己釀造的,卻又怎么也喝不下去的苦酒。……經歷了多次丟面子的難堪,我開始回過頭去檢點自己的起步:不注重對史實的核查,不顧及具體語境對研究對象亂下斷語,輕視校對工作,等等,都是我從事史料工作的致命傷。這些沉重的生命記憶,終于讓我懂得了什么叫做史料研究中的謹慎、認真。
其實,最近又發現,連在《后記》中做了檢討的這本史料學,出版后也還是發現了新的錯誤。我真切地理解到:史料研究絕不僅僅屬于技術、技藝層面。對于研究者來說,史料研究是大修煉、大思考。糾正研究中的差錯,并非能夠一勞永逸,這甚至是研究者需要終生正視的現實課題。
Q
郝魁鋒:劉老師:你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前言》告訴我們:“本書原想討論的一項內容,還包括史料學的理論研究,試圖對百年來出現的某些影響較大的問題做出理論的闡釋。”后來書的結構有所改變,能夠做一些說明么?
劉增杰:的確像你說的那樣,自己總想把史料與闡釋的關系說得更明白一些。我在《前言》中說,史料、數據本身就是一種言說,它的背后也許代表了許多不必直說或不宜直說的觀點的闡釋。在史實面前把研究推向理論層面,古老的實證研究將會煥發出新的生命力,沖破一切先驗的妄說,使研究處于學術的前沿。我的愿望美好,可惜功力不夠。同時,目前許多文獻史料尚未解密。在史料殘缺的情景下形成嚴謹的觀點還為時尚早。因此,我的史料研究沒有建立體系的奢望,不追求認知體系的完整,只能對自己感受到的問題提供若干史實。原來計劃的理論篇壓縮到了第十章,敲了敲邊鼓,說了幾句皮毛的話。好在,陳思和先生出版的《史料與闡釋》的《卷頭語》告訴我們,他們欄目中的“論述”部分,“不僅僅是對史料的深度闡釋,也包含本學科各種文學理論以及文學現象的探討”,我期待他們在理論探討中獲得新的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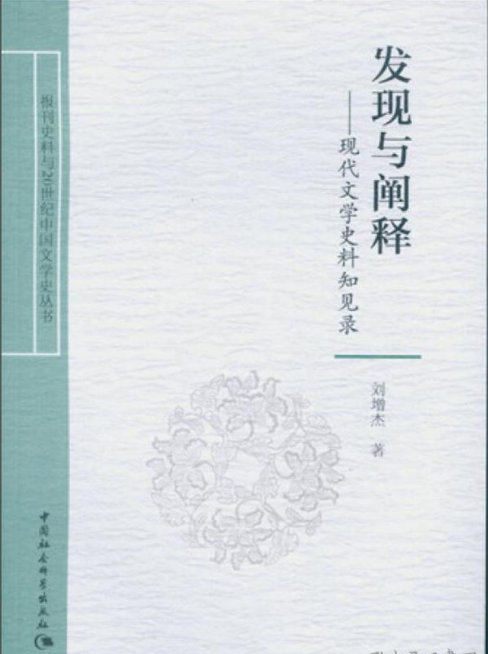
《發現與闡釋》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
事實上,理論上的探討學界正在展開。我看到,錢理群、董健分別對一些文學現象的解讀,就是出色的理論研究成果。錢理群告誡,對過去經常發生的極端化的研究思路,應有一種預防性的清醒。他說:“過去我們的研究不斷地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就跟我們對自己所要倡導的研究思路與方法的有限性、局限性、盲點缺乏清醒的認識有關。……在學術論爭中,一方面,每一方都必然要堅持自己的意見的合理性,即所謂據理力爭,另一方面也要尊重對方的意見,要善于從對方的不同意見中發現其某些合理的因素,從對方對自己的詰難中警覺自身可能存在的盲點或陷阱。這里最要防止的是,就是絕對化的極端思想,即認定自己絕對正確,對方絕對謬誤,為了與對方‘劃清界限’,不惜將自己的觀點推向極端,其結果必然是自己觀點中原有的合理性在極端的推演中喪失殆盡,從而走向反面。在這方面過去我們是有許多教訓的。因此,今天,當我們在‘重新發動’某種學術思路、潮流的時候,重提這些教訓,或許可以使我們保持某種必要的清醒。”(《對現代文學文獻問題的幾點意見》,《河南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董健對二元對立思維模式更有一針見血的理論辨析:“‘簡單化的、直線的兩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已經使我們的學術受害匪淺。要神化魯迅,就必把胡適妖魔化,或者反之。為了沖破‘魯郭茅’的評價格局,便非把沈從文、張愛玲、錢鍾書抬得更高不行。這種非此即彼的視角,叫人辨不清歷史的真實色彩。很少有人從綜合的文化效應上,從人與文學之現代化總趨勢上,去研究魯迅與胡適的共同價值及其在今天的意義。如魯迅主張改造貫為人奴而麻木不仁的‘國民性,張大‘個性之尊’,呼喚‘人國’之建立;胡適則鼓吹健康的‘個人主義’,這在人的現代性追求上是一致的。”(《總序》,見朱壽桐:《中國現代社團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6頁)
一旦這些精卓的見識得到進一步深化,帶有暴力色彩的學術話語將會逐漸消隱,史料學研究藏匿的隱蔽秩序將會得到進一步呈現。
Q
郝魁鋒:臺灣學者黃一農曾說過,“網絡的發展不僅是一個信息革命,實際上也是一場社會革命,它改變的不僅是理科,也包括文科的研究方式”。網絡作為目前研究者獲取史料的重要渠道之一,您如何看待網絡資源中的史料文獻對現代文學研究的價值意義?
劉增杰:史料的范疇會隨著時代記載歷史手段的變化而不斷發生變化,從早期的甲骨文、竹帛、紙張再到圖片、影像及電腦網絡數字化技術,一直處于不斷的豐富和發展之中。現代文學史料學本身即是以搜集、研究、編輯、運用現代文學史料為任務,因此對網絡資源中的現代文學史料予以關注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在此前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我曾提到“文獻管理體制的落后以及傳統文獻整理,研究方法和手段無法適應現代文化變革需求”是現代文學史料建設長期滯后的原因之一。而網絡自身具有的開放性、高效性、自由性等特點,為研究者獲取史料提供了諸多便利。網絡作為現代文學史料新載體的出現,正體現了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隨著網絡的發展和普及,網絡資源中的現代文學史料已經在較大程度上影響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進展。但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其所帶來的不良影響,如對網絡資源中的史料不加考辨鑒別隨意引用而導致的史實訛誤、利用網絡的便利進行學術造假等。
Q
郝魁鋒:目前,許多現代文學研究者正在利用各種網絡數據庫搜集史料從事學術研究。您認為通過網絡這一新媒介獲取的現代文學史料存在哪些問題?應該如何解決?
劉增杰:網絡資源中的現代文學史料首先就存在一個可信度問題。雖然大量史料經過數字化技術處理后以掃描或影印的方式呈現了出來,給人以原版原貌的印象,但經數字化處理過的電子文本或許并不是按原版掃描,或者即使是原版掃描,在此過程中也會發生錯排、遺漏等種種意外。譬如我們看到的很多網絡版現代文學報刊就沒有將報刊中縫里的一些文學廣告再現出來,因此處理過的網絡版本依然存在問題。再有就是網絡資源中的很多報紙期刊影印本都存在缺刊漏刊現象,如果研究者僅僅借助網絡資源進行學術研究,就會陷入獲取史料不完整的狀況。這就要求我們研究者必須嚴肅地看待網絡資源中的現代文學史料,意識到通過網絡獲取的史料代替不了對傳統紙質報刊的閱讀。網絡的興起,不是紙質的潰敗,它代替不了艱苦的閱讀與思考。網絡時代的學術研究應該加強研究者自身的學術道德修養,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精神去做學問、搞研究,這樣才能拿得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史料學研究成果。
Q
郝魁鋒:最后還想提出一個問題:老師對當前研究者的精神狀態有怎樣的評價?
劉增杰:就研究者的感情基調而言,據我的觀察和自己的切身感受來說,史料研究者的心態還是有某些憂郁的。史料的數量太多、太雜,鋪天蓋地,需要人們長期地凝神靜思,坐冷板凳。研究時刻考驗著研究者的忍耐力。他們面對的,還有不時飄來的對史料研究者不屑一顧的閑言冷語。同時,對發掘出來的史料進行闡釋,往往更難,路也更為漫長。但是,從總體實踐來看,史料研究者應是最終的成功者。他們的研究雖苦,但心不發虛。研究中每一次新的發現,都可能使他們的憂郁轉化為喜悅,暢快地發出鮮活的學術新聲。當然,每個人的路并不相同,冷暖自知。在我的內心里,一直對史料研究同行懷有深度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