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創傷書寫”(1936—1941年)
原標題:“失貞”以后怎樣——論丁玲的“創傷書寫”(1936—1941年)

1933年《生活畫報》第廿七號報道丁玲被捕消息時所刊的照片,下書“最近失蹤之女作家丁玲女士”
1933年5月,丁玲遭國民黨特務機關逮捕,并被押解到南京。軟禁三年后,1936年9月,在馮雪峰的安排下,丁玲由南京逃到上海,隨后離開上海經由西安轉赴陜北。同年11月,丁玲到達當時黨中央的所在地保安。從1933年丁玲被捕起,有關丁玲“變節”“轉向”的謠言便開始流傳。1936年丁玲到延安后,即有人對她的南京經歷提出質疑。南京三年的經歷成為丁玲一生都繞不開的歷史問題。她非同尋常的存活經驗始終難以被納入強調“忠烈”的革命話語之中,因此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失貞”的問題常常是一個無法繞開的“坎”。
延續了“反右”運動中論者對小說人物貞貞與丁玲歷史問題之互文性的關注,日本學者高畠穰在《丁玲轉向考》中認為,丁玲創作于1937年8月的獨幕劇《重逢》“是丁玲三年監禁生活的感受和體驗,揭示了活著的人們內在的危機的秘密。換句話說,在自己的心中建起一道深淵,并與其相對峙,作家一面凝視著它,一面寫出了不放棄正義而試圖生存下去的精神的軌跡。丁玲撰寫這部作品,也許免去了試圖轉向或已經轉向的人們的或多或少必須背負的腐蝕作用”[1]。藍棣之也曾在丁玲及其創作的人物之關系上做過精彩的癥候式分析。他認為,在1958年《文藝報》組織的“再批判”中被認為是“毒草”的一批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記》《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和《“三八節”有感》,是丁玲的“自敘傳、血淚書和懺悔錄”[2]。
本文即是在上述層面展開的嘗試。在《松子》《一顆未出膛的槍彈》《新的信念》和《我在霞村的時候》等文本中,都隱含了對“失貞”現象的共性敘事。這是作者丁玲在創作時揮之不去的個人歷史問題,也是小說人物在故事中面臨的困境。“現實”與“幻象”的同構使得這些文本具有高度的癥候性。在不同時期對“失貞”問題的鏡像式書寫中,我們可以發現丁玲在強調“忠烈”的革命話語面前所進行的自我辯白、自我證成和自我斗爭。
一 難以言說的“渣滓”
短篇小說《松子》寫于1936年3月,發表在1936年4月《大公報·文藝》第130期,初收《意外集》。本文集收錄了作者被囚后寫就的五篇文章,對此,丁玲在不同場合下有不同的解釋。1936年10月到達西安后,丁玲在《〈意外集〉自序》中表示,這幾篇文章是在“極不安和極焦躁中”勉強寫成的,“簡直不愿看第二次”,“匯集起來不過作為我自己的一個紀念”。《松子》“是那末充滿著一片陰暗的氣氛”。《意外集》“不是一個好的收獲,卻無疑的只是一點意外的渣滓”[3]。多年以后,在1980年給趙家璧的復信中,丁玲卻說“我對于那幾篇文章沒有什么感情”,一再強調“完全是為了稿費勉強湊成的”,并且將《松子》和《團聚》歸入《奔》的創作路徑之中[4]。兩相對照,丁玲在1980年的說法淡化了《意外集》與她創作時的情感共鳴。
有趣的是,在1936年5月致葉圣陶的信中,丁玲的說法與上述又有所不同,《松子》的寫作之于丁玲有積極主動的意義:“我什么都不愿意說,不希望向任何人解釋,只愿時間快點過去,歷史證明我并非一個有罪的人就夠了。三年過去了,我隔絕著一切,我用力冷靜我自己,然而不知為什么卻又忍不住給《文藝》寫了那一點小東西(即《松子》——引者注)。而且還在預備寫下去,你不以為我寫得太早了或者太遲了嗎?”[5]此處丁玲對《松子》的說法顯然不是1936年10月宣稱的“勉強”寫成,更不是1980年所說的“沒有什么感情”,恰恰相反,丁玲其實對《松子》的創作有“忍不住”的感情。1984年7月完稿的回憶錄《魍魎世界》中的說法也印證了這一點:“我反復思忖,如果我不放出信息,我自己不主動,黨怎能知道我正在南京盼星星,盼月亮等著她的援救呢?我想,第一步便是要寫文章。我本來是寫文章的,是作家,只能透過自己的文章,發出信號。”[6]到寫作《魍魎世界》之時,丁玲口中《松子》的創作動機更加具體了——這是向黨發出的求救信號。1936年蕭乾收到《松子》后的反應也可佐證上述“言志”的說法。在和魯迅的談話中,蕭乾以《松子》為證據,不同意魯迅認為丁玲“完了”的看法,認為《松子》“毫不含糊地表明,她的思想并沒改變”[7]。
自從1936年年初收入《意外集》之后,近半個世紀以來丁玲沒有將《松子》編入自己的任何一個選本。直到198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丁玲小說選》之時,曾經的“渣滓”和“充滿著一片陰暗的氣氛”的《松子》以“還是沿著小說《奔》的道路前進”[8]的理由被編入。事實上,《松子》和丁玲在“左聯”前期以《水》《奔》為代表的“政治化”小說有著很大的不同。比如,小說中階級斗爭的設定并不典型:松子偷西瓜偷的不是地主惡霸家的;松子并未遭到地主惡霸及其走狗的欺凌,卻險些被同為無產者的打鐵學徒強奸[9]。
丁玲的丈夫陳明曾明確談到《意外集》之于丁玲個人遭遇的獨特含義:“限于當時的處境,《意外集》中的各篇可能都不是佳作。但在那特殊情況下,作者在這些作品中流露的思想、感情卻是值得深挖,并和她前后的作品相聯系、比較,這也是研究丁玲作品、創作道路的一個方面。”[10]有研究者注意到《松子》的關注點“不再是以理性化的分析去鼓吹階級斗爭、傳達意識形態說教,而是‘人’的生存困境本身”[11]。某種意義上,《松子》反映的更是丁玲自身的生存困境。

丁玲《意外集》(1936)封面。注:右下角的圖畫描繪的應是《松子》中的場景:松子母親抱著妹妹小三子,揚手準備打瑟縮著的松子
小說講述了一個“流丐”家庭中小男孩松子的“罪與罰”的故事:松子因為饑餓去偷西瓜吃而一時沒有照顧好妹妹,結果妹妹小三子走上岔路被狼吃掉。自己也沒偷成瓜,在瓜地里反而差點被打鐵的黑小子強奸。當受盡屈辱的松子忍著痛即將回到家時,卻因聽見父母的厲聲責難,害怕父母的暴力而不敢現身,最終悄然沒入無止境的黑暗之中。
在丁玲的小說序列里,《松子》或許是一個最“黑暗”的故事。全篇充斥著饑餓、冷漠、死亡、雞奸和暴力,籠罩在徹頭徹尾的黑暗之中——連試圖強奸松子的鐵匠學徒也是一個“黑”小子!家庭在其中不僅不是庇護所,反而是恐怖的壓抑性力量。耐人尋味的是,此前丁玲的小說基本不處理親子關系式的家庭矛盾。正是從《松子》開始,丁玲第一次觸及黑暗的親子關系,而且寫得如此絕望。正如范雪所指出的那樣,這是一個“窮人家里人們互相怨恨,進一步家破人亡”[12]的故事。故事矛盾更多指向了家庭內部的怨恨,而非階級仇恨。
小說中父母的出現總是伴隨著暴力和責難。小三子從搖籃里跌出來,松子挨打;小三子落水了,松子將其撈起后并無大礙,自己卻差點被打死;小弟弟小毛被載重汽車壓壞了腦殼,松子被父親無聲地狠狠打了一頓,連小三子也被父親踢了幾腳;即使小三子和母親都吃著松子偷來的東西,母親還是罵松子不成材,總有一天要被抓到警察廳里去打死;最后,小三子被狼吃了。這一次,父親很可能將松子打死,這也直接導致了松子不敢歸家、只得沒入黑暗中的結局。父母在小說中純然是懲罰性的暴力權威化身,松子與父母沒有任何心靈交流的可能。有意味的是,在小說開頭,當松子唯一一次帶有依戀感地主動去“看”父母的時候,出現了頗具夢境色彩的一幕:黃昏陰暗的天際下,當松子“回頭去看了一下坐在窯門口的媽和爹”[13]時,他們卻不見了。
可以說,松子一家根本不像正常的家庭,其中看不到任何的愛,只有怨恨、恐怖和暴力。面對松子父母的責難與暴力,無論是敘述者還是小說人物松子都始終處于“失語”的狀態之中。日本學者野澤俊敬敏銳地指出了松子與丁玲早期小說主人公在“苦悶孤獨”上的不同。“莎菲”們“由于自我意識的覺醒,他們才幻想、幻滅、痛恨,從而陷入虛無、頹廢、自暴自棄”。而松子并沒有這種自我意識的覺醒,更談不上“幻想”與“幻滅”,他只有“壓抑狀態下動物般的求生愿望”[14]。
在弗洛伊德看來,宗教和文明的起因在于一種成功引發個體罪疚感的壓抑性結構:“社會以同謀罪中的共犯關系為基礎;宗教以帶有悔恨的罪惡感為基礎;而道德的基礎則一部分是社會的迫切需要,一部分是為罪惡感所要求的贖罪行為。”[15]實際上,《松子》的故事展現的正是一個引發罪疚的壓抑性結構。表面上看,妹妹是因為松子一時疏忽而被狼吃掉的,但細究起來卻頗為可疑,整個故事更像一道“讖語”的應驗,其中敘述者精心“設計”了松子的受罪。首先,敘述者明確提到松子母親每次罵松子的結語總是“小毛被你弄死了,我知道你一定還不夠,有一天小三子又會死在你手上的”[16]。故事后來的發展正好應驗了母親的話。此外,種種跡象表明,松子仿佛是故意要使自己獲罪。比如,在離開妹妹去偷西瓜之前,松子便嚇唬妹妹,廟里的大狗會吃掉她;又如,松子明知前天小妞子剛被吃,卻依然選擇丟下妹妹;再如,松子曾告訴妹妹自己會目送她去窯里躲起來,但后來他根本沒有這么做。
丁玲曾在《〈意外集〉自序》里談到自己“寫時特別審慎著‘技術’”[17],陳明在注釋里解釋為“這里是指在敵人的耳目下,不讓敵人從作品中揣摸到作者的意愿和動向,不是通常說的表現技巧”[18]。然而袁良駿對此卻有另一番理解。他認為“技術”指的是情節安排的技巧。《松子》和《團聚》等像是“‘無巧不成書’的舊文藝”,“因為太巧,反而削弱了感人的力量”,是丁玲一貫作風的倒退,而丁玲以前的作品不是以情節取勝的[19]。實際上,在1931年5月的創作談《我的自白》中,丁玲自己明確表示過,反對“由幻想寫出來的東西”[20]。
從上文分析來看,《松子》中種種“巧合”的敘事結構或許正是丁玲無意識的體現。我們可以將《松子》讀成一個作者在“極不安和極焦慮”中創作的原罪式故事,即作者“無意識”地選擇了“家庭”作為一種壓抑性的、便于引發罪疚的敘事框架;與此同時,作者設計出“過失犯”松子,讓松子在懲罰性權威的“教唆”下完成“無意識”的犯罪。
當自己普遍被外界認為“失貞”但卻又準備再次投身革命之時,丁玲復出的第一篇小說《松子》高度癥候性地表現出了她內心的矛盾情感。一方面,她強調自己的受難,希望將自己的幸存經驗界定為一場自己無法抗爭的苦難從而獲得救贖的機會;另一方面,對于如何呈現自己的受難,對于如何把自己的故事講入革命話語中,丁玲卻始終面臨“失語”的難題,對自己究竟能否獲得救贖抱有很深的疑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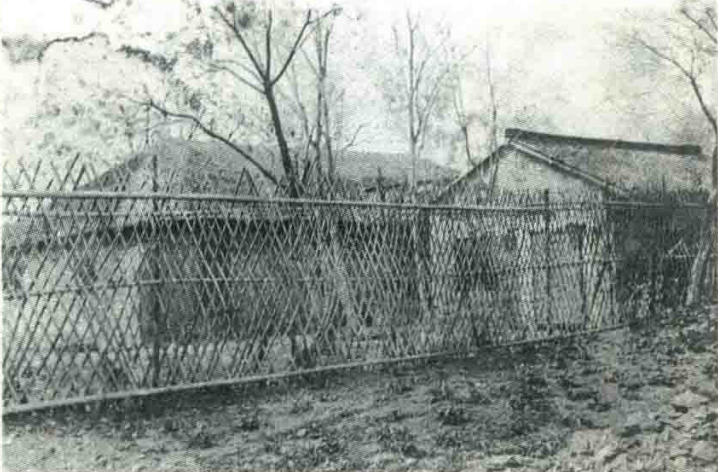
南京苜蓿園丁玲囚禁處
事實上,在南京的三年里,丁玲長期處于一種“失語”的狀態之中。在謠言四起而丁玲自身表現也十分曖昧的情況下,她即便找到了同志,也無法交流,因為她很難得到同志的認可與信任。1934年,丁玲與張天翼在南京夫子廟偶遇,然而隨后雙方的會面并不愉快。丁玲在《魍魎世界》中回憶了自己當時的感受:“我在敵人面前是受盡折磨的,但在朋友面前,忍受著這樣的冷淡,卻是第一次。”[21]“從此,一天到晚我重又浸泡在失望里,隱隱地難受。我不理解張天翼,只覺得自己是被遺忘的。”[22]
小說中還有一個情節值得我們注意,即黑小子想要雞奸松子。如果松子愿意的話,他就允許松子把西瓜偷走。其實,這一幕是小說故事的旁支,大可以不寫;要寫,也可以寫其他種類的欺凌方式。但丁玲偏偏寫了性暴力,寫了一個此前從未寫過的“失貞”情節,而這類情節在她后面的小說中還將不斷上演。
萬幸的是,松子畢竟并非“故意”致死了自己的妹妹,也沒有因為饑餓和暴力脅迫而“失貞”,這也是丁玲始終堅持的立場——自己從始至終并沒有真的背叛黨,寫條子只是受敵人誘騙,是為了逃出生天以求繼續為黨效力的權宜之計。但丁玲非同尋常的存活經歷卻注定無法見容于革命話語,丁玲這段遭遇和心曲只能以“渣滓”“剩余”的方式存在。正是從《松子》開始,被符號系統閹割的“失貞”問題驅動了丁玲的欲望,暗中策劃、影響著她的創作。
當松子受盡屈辱,從瓜地往家里走時,小說中有這么一段描寫,或許反映的正是丁玲當時的心聲:
他的難受的饑餓跑走了,代替的是更其難受的許多肉體上的疼痛,和一種被欺侮而又無告的凄傷。他用頭枕著草,草已被露水濕透,草上的一顆螢火蟲,無力的亮著那微弱的小燈,在前面飛去了,飛到無止境的黑暗里去了。他也有一點想哭,可是沒有眼淚。他覺他需要一點什么,他說不出來,他卻鼓著勇氣又拖著沉重的腳步,忍著痛,一跛一跛的走上崗去,是朝著有著窯的那方。[23]
二 被懸置的死亡
1937年4月,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周刊創刊。應博古之約,丁玲為創刊號寫了《一顆沒有出鏜的槍彈》[24](即《一顆未出膛的槍彈》,以下簡稱《槍彈》),這是丁玲到陜北后所作的第一篇小說。丁玲本人非常重視這篇小說,她到陜北后出版的第一個小說散文集即名為《一顆未出膛的槍彈》。小說后來又被收入《我在霞村的時候》《丁玲選集》等多個集子。1956年,丁玲將其改寫成《一個小紅軍的故事》,由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單行本。
小說的政治意涵受到了普遍的關注。有論者指出《槍彈》是一篇“主題先行、具有很強的政治說教色彩”的作品,是對《八一宣言》的圖解[25]。更有論者進一步認為,小說為了政治功利以至于犧牲了人物真實與生活真實,小紅軍在生死關頭說出的“用刀殺我”以省下子彈抗擊日寇是“一種政治功利性的虛假而拙劣的演繹”[26]。
我們固然可以認為,丁玲的創作受到了當時高漲的政治熱情的驅使,但我們也不能忽略另一種可能性,即“失貞”問題對其創作的影響。有論者指出,丁玲受制于“囚徒生活留下的陰影”,“清醒的階級責任感更使她不敢放肆地寫作,以至于使得有著獻禮意味的《一顆未出膛的槍彈》《重逢》都只顯出幾條干巴巴的筋,幾乎僅存一個概念的框架”[27]。
事實上,丁玲到陜北后曾經打算寫一本關于南京三年幽禁生活的書。但據說后來因為顧及統一戰線的利益,最終放棄了出版的計劃[28]。在接受訪談時,丁玲雖然不愿意多談自己南京三年的經歷,有趣的是,她卻一再強調女性在革命事業中的忠烈,甚至不惜因此貶斥男性:“她說:‘在磨難中的中國女性的英雄主義,甚至比男同志們更堅定。在黨的記錄中,指出了許多男同志在監禁和磨難之后自己認了罪;但是女黨員們呢,不管遭遇著怎樣的痛楚和羞辱,終不肯自認其罪名。許多女同志已死在刑房中,更有許多在刀槍之下被處決了。’她追述到幾年以前在‘湖南的清共’中,被湖南省主席何鍵處死的女性比男性為更多。”[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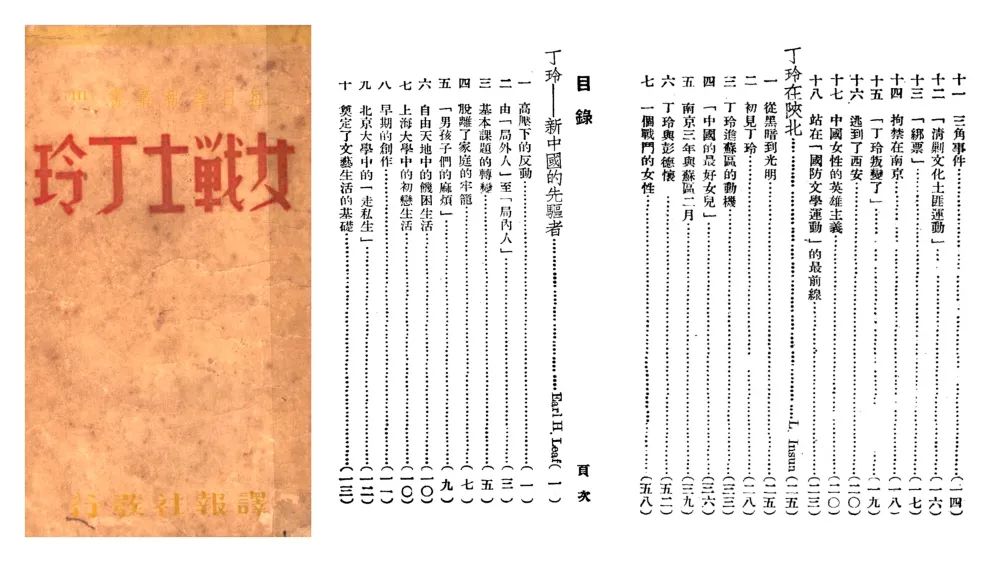
《女戰士丁玲》,每日譯報社1938年版
丁玲一開始決意要寫卻沒寫,一方面可以解釋為是顧及統一戰線的利益,但另一部分原因或許是她不愿寫,不敢寫,也不會寫,她難以把自己的遭遇講入強調“忠烈”的革命故事里去。某種程度上,她為革命女性所鳴的不平應該也是為自己而鳴的。令人驚訝的是,盡管丁玲這般強調女同志的忠烈,自己卻從未寫過一個女烈士的故事,也沒有寫過一個以烈士為主角的故事。在《槍彈》中,小紅軍可能的壯烈犧牲被高度戲劇性的情節抹去了。小說實際上懸置了“失貞”困境下“生還是死”的問題,選擇帶來的真正后果并沒有發生。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指出小說與丁玲的遭遇在情節結構上的相似之處:“掉隊→行將被東北軍士兵雞奸,如果失貞可保性命無虞→選擇反抗從而保住貞潔”的結構對應的是“丁玲落入魔窟與同志失聯→面臨敵人誘騙→不屈服從而保住貞潔”的故事。不同的是,小紅軍的反抗以極其戲劇化的儀式收場——他被舉起來了,敵人被感化了!顯然,這是丁玲在過去無法做到的事情。作者用政策話語替代性地實現了自己的欲望。
在1937年6月應博古之約創作的另一篇小說《東村事件》中,我們也能看到一個有關“失貞”的情節。為了救佃戶陳得祿的父親,陳家人選擇以做工的名義逼迫童養媳七七去趙老爺家,致使七七被趙老爺奸污霸占。然而,陳得祿在與七七私會時,他并不理會七七“失貞”的緣由,反而對七七施暴。
對于七七的“失貞”問題,敘述者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態度——“這是不能責備七七的,七七只是一個十五歲的少女,她沒有抵抗的力量,當她被關在一個籠子里的時候”[30]。顯然,敘述者并不認為失貞的七七應當去做一個“烈女”。有趣的是,在小說開頭,陳得祿的母親曾去見過七七,“說她只會哭,咒罵他,說她總有一天要上吊,否則就跳水”[31]。但到了結尾處,敘述者并沒有給出七七自盡的可能性——“他(陳得祿——引者注)想著一個人,不知道是趁機會跑丟了,還是又正被人拷打著”[32]。
可以說,這與丁玲之前關于女性死烈的敘述是矛盾的,但與她自己的遭遇卻是相符的。這正如符杰祥指出的那樣,“丁玲文學與人生世界中的烈女/烈士認知”,“其所訴求的‘忠貞氣節’與傳統女德、革命政治”之間,存在著“相糾纏的壓抑、變形、扭曲、揚棄等系列問題”。“圍繞‘死之歌’所纏繞的‘不死’心結,也許才是丁玲表達‘忠貞’的最大心結”[33]。
由此,處理“失貞”問題更大的困難其實發生在,假如“不死”,“失貞”回來之后怎樣?在1939年春創作的《淚眼模糊中之信念》與1940年秋冬創作的《我在霞村的時候》中,這個問題以兩種極其不同的方式得到了回應。
三 奇詭的歸來
《淚眼模糊中之信念》[34](即《新的信念》)創作于1939年春,同年9月16日發表在《文藝戰線》第1卷第4號上。小說寫的是一個失貞茍活的老太婆在歸來后宣說自己苦難遭遇的故事。在敵人的羞辱面前,陳老太婆沒有像自己的孫子一樣拼死反抗,沒有如自己孫女一般在失貞后死去,也沒有像她對一個姑娘提供的建議那樣咬舌自盡,而是順從鬼子從而茍活了下來。期間她不僅在“敬老會”里幫鬼子做事,還和一個中國老頭子被迫在鬼子的觀看下發生了性關系[35]。從故事發展來看,老太婆失貞之后健在的代價則是,她必須以一種歇斯底里式的施虐和受虐的方式向家人和村民反復宣說她的殘酷遭遇。這是小說中最令人感到震驚與費解的地方。
對于老太婆的癲狂之舉,小說中有這么一段解釋:“這并不愛饒舌的老太婆,在她說話所起的效果中,她感到一絲安慰,在這里她得著同情、同感,覺得她的仇恨也在別人身上生長,因此她忘了畏葸。”[36]然而,作品沒有從根源上交代老太婆為何會對自己的受害經驗有如此特異的態度。從最初家人和村民的反應來看,老太婆根本就是“瘋”了。
有論者認為,老太婆的講述雖然被設定為對受害的瘋狂式反應,但她從一開始就有積極、主動的目標,而且有堅定的意志去貫徹,老太婆對家人和村民實際上承擔起了一個“啟蒙者”的角色[37]。“被強暴的女性身體”的隱喻是“女性可以成為民族/革命主體的手段”[38]。在這種解讀方式下,需要注意的是,小說從“癲狂故事”到“啟蒙故事”的轉變其實發生在三兒子從游擊隊帶回的“打日本”的話語進入之后。當老太婆最愛的三兒子從游擊隊上回來之時,老太婆感到“不需要在兒子跟前訴苦”,因為沒什么用處[39]。此后,老太婆的殘酷宣講即有了理性的目的——訴完苦后,用“打日本”的英雄故事激勵大家,并且動員大家參軍。隨著公家人的介入,她的話不再是瘋人瘋語,而是婦女會也在宣講的“道理”。針對老太婆的歇斯底里癥,民族革命話語似有一種神奇的藥效。當“失貞”的老太婆能夠將她被強暴的生理體驗講入一個抗戰動員的故事里時,她便不再瘋癲而成為了一個抗日的主體。
馮雪峰在為《丁玲文集》撰寫的后記中這樣談到他理解的老太婆形象:“從莎菲到《新的信念》中的陳老太婆和《霞村》中的貞貞,這兩種對象的不同,是兩個世界的不同,并非作者用同一個主觀可以同樣去打入的;作者必須在新的對象的世界中生活很久,并用這新的世界的意識和所謂心靈,才能走得進去。作者并且必須擁有這個世界及其意識和心靈,才能夠把這世界和人物,塑成使人心驚肉跳的形象。”[40]在馮雪峰看來,丁玲能夠走進老太婆和貞貞的“意識和心靈”,而且是“在新的對象的世界中生活很久”的,他讀出了老太婆和貞貞與丁玲經歷的互文。實際上,創作《新的信念》之時,丁玲正在馬列學院學習。在1938年,中央黨校校長康生在一次會上曾言,丁玲沒有資格到黨校來,因為她在南京自首過[41]。盡管丁玲聲稱自己是1940年才從羅蘭口中得知康生對她的懷疑,但王增如和李向東認為,“即便果真如此,她在馬列學院也會感覺到這種氛圍”[42]。

陳明、丁玲及蔣祖林、蔣祖慧在延安
對于老太婆在失貞茍活后發生的施虐/受虐行為,我們或許可以參考齊澤克對受虐狂做出的闡釋:“性受虐狂使我們面對作為‘虛構’秩序的符號秩序的悖論:在我們所戴的面具中,在我們所玩的游戲中,在我們所遵從的‘虛構’中,存在著的真理比隱藏在面具背后的要多。”“暴力的實在正好爆發于性受虐狂的歇斯底里狀態——當主體拒絕他的他者快感的對象-手段的角色時,當他震驚于存在的前景在他者的眼中被還原為對象a時,為了逃出這種僵局,他求助于行為的通道,針對他者的‘非理性的’暴力。”[43]
置身于民間倫理的環境里,老太婆難以找到她失貞茍活的合法性。她只能通過施虐和受虐般的苦難宣說,在抗戰動員的主人能指中獲得意義,取得在革命倫理中的崇高地位。事實上,老太婆瘋癲行為的倫理正當性是回溯性地建構起來的。從故事的發展來看,她施虐是因為被施虐對象需要受虐,他們在未來召喚著她的“語言暴力”,以獲得抗日民族精神的覺醒。這也就是齊澤克所說的,“對施于受害者的殘酷行為的效果的理解(或誤解)反作用地使傷害行為合法化了”[44]。在丁玲最后的遺作《死之歌》里,我們也可以看到類似的意義生成結構:“但是后來,時間隔久了,我慢慢地體會出來了,我還是不應該死。死,可以說明我的不屈,但不能把事實真相公諸于世,不能把我心里的歷程告訴人們。因此,我想我不能死,我要活下去!”[45]
小說還有一個耐人尋味的轉變,即老太婆一開始在兒子面前宣說會感到羞恥痛苦,但到后來卻越來越放肆。最后當兒子們全都來會場聽她的宣說時,她內心涌動起“似乎是羞慚,實際還是得意”[46]的感覺。在精神分析的視野里,受虐對于主體而言不一定是痛苦而也可能是快樂的。“受虐狂主體認為,想象一位他深深依戀的人無意識地傷害了他,他將因某些罪行而錯怪他(或實行了某些類似于錯誤的責怪行為),這是件非常令人高興的事。這種快樂是因為他想象到了未來情景,即他所愛的人無意識地傷害了他,他將會對自己的不公正的責怪而感到深深的內疚。”[47]與此同時,“受虐者的真實目的并不在于為大對體提供原樂,而是令其焦慮。也就是說,盡管受虐者心甘情愿地忍受大對體的折磨,盡管受虐者要對大對體畢恭畢敬,使自己處于被奴役的狀態,但真正制定規則的是他自己。結果呢,盡管看上去是他勇于獻身,把自己當成了供大對體享受原樂的工具,但實際上,他向大對體披露了自己的欲望,這導致了大對體的焦慮”[48]。然而,這種欲望并不光明,小說必須借助其正式的故事線把這種不堪的欲望加以升華。
四 穿越幻象
《我在霞村的時候》大約創作于1940年秋冬之際,也就是延安中央組織部對丁玲的南京歷史作出審查結論的前后。1941年6月20日,小說發表在《中國文化》第2卷第1期。20世紀80年代以來,評論界主要有“啟蒙主義”“女性主義”“革命主題”的三種解讀方式。然而,無論做何種解讀,我們勢必都要面對陸耀東和張光年(華夫)文章中對小說情節真實性提出的質疑。在20世紀50年代的“再批判”中,評論家認為貞貞替黨做情報工作的情節根本就是捏造的,因為貞貞“并沒有半點革命者應該具有的認識和覺悟,她并不熱愛祖國,也不懂得愛黨,愛人民,對敵人也沒有刻骨的仇恨”[49],黨不可能“委托一個毫無民族氣節、毫無政治覺悟的不可靠的人物來做這個工作”[50]。然而,有趣的是,此前馮雪峰卻認為“她(貞貞——引者注)過去和現在的一切都是真實的”[51]。
丁玲曾多次表示小說的創作是基于一個她聽來的故事。其中,細節最豐富的故事版本見于1952年4月24日丁玲所做的一次創作談:“‘人要活下去,要斗爭下去!’但在我思想上又覺得必須要犧牲一些東西,才能得到成功。譬如我寫《我在霞村的時候》,就有這樣一個思想。其中的主人公雖然沒有其人,不過我卻曾聽到過這樣一個新聞。有一次,我看到一個同志要到醫院里去,他告訴我說,是去看一個剛從前方回來的女人,那個女人曾被日本人強奸了,而她卻給我們做了許多的工作,把病養好了以后,又派她到前方去做她原來的工作。她是恨透了日本人的,但她為了工作,為了勝利,結果還是忍痛去了。我當時聽了,覺得非常感動,也非常難過,我想,她真是一個品質崇高的人,她不僅身體被損害了,精神也受了損害,雖然當時有許多人不能同情她,但是她有崇高的理想,她要活下去,黨在同情她,在支持她。這個人物一直是在我的腦子里活著,醞釀著的,最后終于把她寫了出來,起初是以第三人稱寫的,后來改用了第一人稱。”[52]
這一故事樣本也在1940年8月19日蕭軍的日記中出現:“一個在河北被日本擄去的中年女人,她是個共產黨員,日本兵奸污她,把她擄到太原,她與八路軍取得聯絡,做了很多的有利工作,后來不能待了,逃出來,黨把她接到延安來養病——淋病。”[53]
如果我們可以認為,蕭軍日記里記載的故事是丁玲小說所依據的本事的話[54],不難發現,在小說、蕭軍的記錄和丁玲的回憶之間存在著非常關鍵的不同點。首先,在蕭軍的故事里,這個婦女是一個中年女性黨員,最初可能是她主動與八路軍取得的聯絡。然而,在小說中,這個女人的黨員身份被抹去了,而且變成了未婚青年。其次,相較于1952年的講述,小說中這個女人對日本人鮮明的仇恨也被抹去,取而代之的是對其痛苦遭遇的淡漠態度。如此一來,貞貞不惜犧牲自己的身體從而為黨做情報工作的動機便十分可疑。這與《新的信念》里的蠻橫地不斷宣講自己苦難的老太婆,與《重逢》中嚴詞拒絕男同志的建議——通過“失貞”以成為“桃色間諜”的白蘭是多么不同!最后,當這個女人進入小說中時,她變得異常“倔強”,不肯接受任何人的規勸,以至于后來被指認為“復仇的女神”[55]。
有研究者敏銳地指出:“這種執拗和直面現實的態度無論對于落后的村民還是對于先進的青年,乃至對于革命組織都帶著一種挑釁的意味。因為它挑戰各個立場、認識基礎上的對‘受害’、‘反抗’、‘斗爭’、‘生存’的規范性看法。”[56]實際上,與其說貞貞“不是向敵人復仇,而是向人民群眾復仇”[57],毋寧說貞貞反抗的是整個符號秩序本身。
從小說一開始,面對民間倫理的律令,貞貞始終堅持了一種決絕的反抗性姿態。很大程度上,她的悲劇根源便在于她的這種反抗性姿態。因為反抗包辦婚姻,跑到天主教堂的她恰好被日軍擄去。歸來后,家人要求她和她曾經愛過的男人結婚,她卻做出對所有人來說都不可理喻的拒絕,并且拒絕解釋她的拒絕,以至于無法繼續待在霞村。不僅如此,她對馬同志和阿桂對她遭遇的探詢也顯示出拒絕的姿態。某種程度上,村里負責工作的馬同志和從政治部出發與“我”同行的宣傳科女同志阿桂或許可以視作當時政治倫理的代言人。也就是說,馬同志和阿桂的看法很可能代表的就是貞貞去了延安之后將要面臨的審視。然而,貞貞也以沉默平靜的姿態,拒絕了兩位同志在“看”她的時候,流露出的一種獵奇式的和政治功利性的眼光。在小說結尾貞貞甚至拒絕了“我”對她的憐憫——當“我”勸貞貞聽娘的話嫁給夏大寶時,貞貞卻告訴“我”她也要離開霞村去延安了。

1941年,丁玲在延安
有意味的是,我們在丁玲1942年3月創作的《“三八節”有感》也能看到這種決絕的姿態:
下吃苦的決心,堅持到底。生為現代的有覺悟的女人,就要有認定犧牲一切薔薇色的溫柔的夢幻。幸福是暴風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彈琴,花前吟詩。假如沒有最大的決心,一定會在中途停歇下來。不悲苦,即墮落。而這種支持下去的力量卻必須在“有恒”中來養成。沒有大的抱負的人是難于有這種不貪便宜,不圖舒服的堅忍的。而這種抱負只有真真為人類,而非為己的人才會有。[58]
面對女同志的婚戀困境,丁玲開出的藥方是要女同胞“堅持到底”,“犧牲一切薔薇色的溫柔的夢幻”。這讓人不禁想起拉康的箴言——“涉及欲望不讓步”。拉康認為,人有兩種死亡,一次是生物性的死亡,一次是符號性的死亡,而安提戈涅進入了介于兩次死亡之間的空間,即她的符號性死亡先于她的實際死亡。安提戈涅獲得永恒安寧和救贖的方式,是以歇斯底里式的要求懸置和顛覆整個人世間的符號秩序,不對欲望讓步,穿越為我們欲望提供坐標的幻象,因而無法被馴服和教化。在安提戈涅身上,齊澤克辨認出了死亡驅力的要求對于意識形態秩序的解構性與顛覆性[59]。
可以說,貞貞“不可理喻”的徹底的反抗性姿態正是在安提戈涅式“穿越幻象”行動的維度上才能得到充分理解。她的行動在民間倫理和民族革命話語之中都難以找到位置。象征界中她已然“死亡”,但她卻依然堅持自己的行動,并拒絕加以解釋,這引發了人們因無法弄清其想法而產生的難以忍受的焦慮。與此同時,“穿越幻象”也意味著“認同征兆”,即在“過度”中發現社會制度的必然產物以及有關自身的真相[60]。正如顏海平所指出的那樣:“丁玲故事示意著的真實變革,只有在參與者們掙脫他們自己亦在其中的‘歷史常態’結構關系及其強制邏輯,超越他們自身以植根其中的‘正常’現狀及其界定慣勢的情形下,才會發生,才能發生。”[61]
經受了組織審查和流言蜚語,看到了延安的“封建色彩”和官僚主義,有了種種復雜經驗的丁玲,對自身遭遇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從1940年到1942年春“整風”開始之前,丁玲創作了大量的作品,主要包括:小說《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和《夜》,雜文《開會之于魯迅》《我們需要雜文》和《“三八節”有感》,散文《風雨中憶蕭紅》。這些作品由前期的“歌頌”轉向“暴露”,更加注重對革命隊伍中消極現象的揭露和針砭。貞貞“穿越幻象”的行動暴露了話語結構中的空隙。象征秩序的吊詭之處在于,混雜有“封建色彩”的革命話語被放置在比人的解放更高的位置之上。但仍需要指出的是,貞貞的這種革命性解放姿態并非出自“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人生哲學”,而是體現了蘊含于左翼文化邏輯中的“不斷革命”的激情[62]。
然而,“穿越幻象”之后,生命將喪失立足之地。實際上,“主體生命的一致性就是建立在想象性認同上的。主體一旦‘知情太多’,一旦過于接近無意識之真(unconscious truth),他的自我(ego)就會土崩瓦解”[63]。盡管丁玲看到了革命話語中的復雜和難以自圓之處,但她卻無法提供擺脫這種困境的道路,她會發現自己身處在不堪忍受的空白之中,從而必將再次陷入難以自拔的僵局。因此,創作于1941年的《在醫院中》注定成為一個丁玲無論如何都難以完成的成長故事。
注釋:
[1]轉引自小林二男:《丁玲在日本》,《丁玲研究在國外》,孫瑞珍、王中忱編,第378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藍棣之:《現代文學經典:癥候式分析》,第14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
[3][17][18]丁玲:《〈意外集〉自序》,《丁玲全集》第9卷,第25頁,第25頁,第25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8]丁玲:《致趙家璧》,《丁玲全集》第12卷,第137—138頁,第137—138頁。
[5]丁玲:《致葉圣陶》,《丁玲全集》第12卷,第16頁。
[6][21][22]丁玲:《魍魎世界》,《丁玲全集》第10卷,第75頁,第62頁,第63頁。
[7]安危:《魯迅同斯諾談話整理稿》,《新文學史料》1987年第3期。
[9]參見宋建元:《丁玲評傳》,第221頁,陜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0]彭淑芬:《試論丁玲創作道路的重要特色》編者注,《湖南教育學院院刊》1983年第1期。
[11][25]秦林芳:《丁玲評傳》,第121頁,第140—141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12]范雪:《誰能照顧人——丁玲延安時期(1936—1941)對人與制度關系的探索》,《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1年第1期。
[13][16][23]丁玲:《松子》,《大公報·文藝》第130期,1936年4月19日。
[14]野澤俊敬:《〈意外集〉的世界》,《丁玲研究在國外》,第249—250頁。
[15]弗洛伊德:《圖騰與禁忌》,邵迎生譯,第103頁,長春出版社2010 年版。
[19]參見袁良駿:《丁玲研究五十年》,第55—56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20]丁玲:《我的自白》,《丁玲全集》第7卷,第2頁。
[24]丁玲:《一顆沒有出鏜的槍彈》,《解放》周刊第1卷第1期,1937年4月24日。
[26]劉思謙:《丁玲與左翼文學》,《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11期。
[27]聶國心:《論丁玲創作的情感歷程》,《江西社會科學》1999年第2期。
[28]參見朱正明:《丁玲在陜北》,《女戰士丁玲》,第45—46頁,每日譯報出版社1938年12月版。
[29]里夫(Earl H·Leaf):《丁玲——新中國的先驅者》,《女戰士丁玲》,第21頁。
[30][31][32]丁玲:《東村事件》,《解放》周刊1937年第1卷第5—9期。
[33]符杰祥:《“忠貞”的悖論:丁玲的烈女/烈士認同與革命時代的性別政治》,《學術月刊》2019年第7期。
[34][36][39][46]丁玲:《淚眼模糊中之信念》,《文藝戰線》1939年第1卷4號,1939年9月16日。
[35]這一情節在《丁玲全集》的版本中遭到刪除。
[37]參見程凱:《重讀〈新的信念〉與〈我在霞村的時候〉》,《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6期。
[38]吳曉佳:《“被強暴的女性”:丁玲有關性別與革命的敘事和隱喻——再解讀〈我在霞村的時候〉及〈新的信念〉》,《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
[40][51]馮雪峰:《從〈夢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記》,《丁玲研究資料》,袁良駿編,第254頁,第254頁,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年版。
[41]參見王增如、李向東:《丁玲年譜長編》,第146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2]李向東、王增如:《丁玲傳》,第205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5年版。
[43][44]斯拉沃熱·齊澤克:《快感大轉移——婦女和因果性六論》,胡大平等譯,第116頁,第117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5]丁玲:《死之歌》,《丁玲全集》第6卷,第322頁。
[47]斯拉沃熱·齊澤克:《敏感的主體——政治本體論的缺席中心》,應奇等譯,第323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8]斯拉沃熱·齊澤克:《歡迎來到實在界這個大荒漠》,季廣茂譯,第22頁,譯林出版社2015年版。
[49]陸耀東:《評“我在霞村的時候”》,《再批判》,第96頁,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50][55][57]華夫:《丁玲的“復仇女神”——評“我在霞村的時候”》,《再批判》,第87頁,第89頁,第86頁。
[52]丁玲:《關于自己的創作過程》,轉引自《丁玲傳》,第245頁。
[53]蕭軍:《蕭軍日記(1940)》,《新文學史料》2007年第3期。
[54]有論者認為蕭軍所記錄之事即是丁玲小說的本事。詳見李明彥:《一類故事的兩種寫法——〈我在霞村的時候〉與〈金寶娘〉的互文閱讀》,《文藝爭鳴》2015年第12期。
[56]程凱:《重讀〈新的信念〉與〈我在霞村的時候〉》,《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6期。
[58]丁玲:《“三八節”有感》,《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第98期,1942年3月9日。
[59][60]參見斯拉沃熱·齊澤克《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季廣茂譯,第188—194頁,第178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版。
[61]顏海平:《中國現代女性作家與中國革命,1905—1948》,第339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62]李楊:《“右”與“左”的辯證:再談打開“延安文藝”的正確方式》,《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2017年第8期。
[63]斯拉沃熱·齊澤克:《斜目而視:透過通俗文化看拉康》,季廣茂譯,第78頁,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