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圖書史中貼近人類的情感與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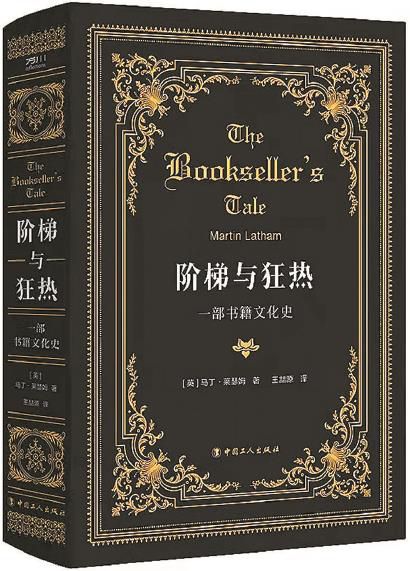
關(guān)于圖書的文史,之前我看過(guò)翁貝托·艾柯所著《植物的記憶與藏書樂》,因?yàn)榘卤救吮闶遣貢遥运麑?duì)圖書的進(jìn)化史很是熟悉。在這部作品中,艾柯將人類的閱讀和記憶分為兩個(gè)時(shí)代。一個(gè)是礦物時(shí)代,就是人類將經(jīng)歷過(guò)的事情刻在石頭上,給后世的人作一個(gè)提醒。這就是至今保留在世界上的巖畫或石窟中的壁畫。而自從人類發(fā)明用植物制作紙張,人類的記憶便可以記錄在紙上,而紙更易保存。艾柯將這種記憶稱為“植物的記憶”。正因?yàn)橛辛酥参锏挠洃洝獔D書,人類的進(jìn)化便越來(lái)越快。因?yàn)椋淮嘶钪慕?jīng)驗(yàn)得以記錄,那么,后世的人們可以避免重復(fù)上代人犯下的錯(cuò)誤。
在相當(dāng)長(zhǎng)的時(shí)間里,女性是被禁止讀書的
與艾柯相比較,英國(guó)書商馬丁·萊瑟姆的《階梯與狂熱》更偏向于圖書的佚事,讀來(lái)非常有趣味。
比如,萊瑟姆用很大篇幅來(lái)敘述讀書所帶來(lái)的情感震顫,比如很多人讀書時(shí)痛哭的故事。狄更斯給他的弟媳寫信時(shí)說(shuō),有人在讀他的《董貝父子》時(shí)大哭起來(lái),毫不掩飾,激動(dòng)得渾身發(fā)抖。塞繆爾·理查森的書信體小說(shuō)《克拉麗莎》出版以后,更是看哭了數(shù)萬(wàn)讀者。1852年,一位年老的蘇格蘭醫(yī)生給作者理查森寫信說(shuō),讀他的這部小說(shuō)哭得吃不了飯。而偉大的托爾斯泰竟然也有讀書時(shí)讀哭的時(shí)候,他是讀普希金詩(shī)的時(shí)候被感動(dòng)了,哭得像嬰兒一樣。
這種讓自己的情感沉浸在某種閱讀時(shí)光里的感受,只有在某一個(gè)特殊的環(huán)境里,一個(gè)深情的讀者才能獲得如此深刻而美妙的體驗(yàn)。
如今,世界范圍內(nèi)的女性讀者到書店的架子上翻開一本書閱讀,便可以進(jìn)入一個(gè)人的思想世界,這已是司空見慣。然而,翻開《階梯與狂熱》這部關(guān)于圖書文化史的書,便可知道,我們所能看到的印刷品書籍,在相當(dāng)長(zhǎng)的時(shí)間里,只能被男性閱讀;女性是被禁止讀書的。
《階梯與狂熱》中,有一段文字記錄了女性閱讀的困境:
15世紀(jì)的波蘭對(duì)閱讀書籍的女性抱有更大的敵意。15世紀(jì)80年代,克拉科夫的一名女性為了進(jìn)入大學(xué)偽裝成男性。在整個(gè)課程學(xué)習(xí)過(guò)程中,她一直女扮男裝,不僅取得了優(yōu)異的成績(jī),而且以具備高度責(zé)任心聞名,但就在畢業(yè)前夕,一名士兵識(shí)破了她的偽裝,她因此被告上法庭。
《階梯與狂熱》還用大量筆墨寫了中國(guó)的圖書故事。有一個(gè)小插曲很有意思,作者寫到,唐代詩(shī)人柳宗元讀韓愈的詩(shī)時(shí),每每先用玫瑰水洗手,而后再閱讀。此類如野史一般的細(xì)節(jié),讀來(lái)讓人著迷。看到此處,真想問(wèn)一句作者,這些歷史的片斷到底源自哪里?
一個(gè)小道士賣掉了敦煌莫高窟藏經(jīng)洞里的半數(shù)藏書
在《階梯與狂熱》中,萊瑟姆用一個(gè)完整的章節(jié)寫了道士王圓箓,這位在中國(guó)歷史上非常不起眼的小道士,幾乎是中國(guó)最大的文物販賣者。他一個(gè)人賣掉了敦煌莫高窟藏經(jīng)洞里的半數(shù)藏書。
萊瑟姆筆下的王道士,在1890年代是乞討者。一天,王道士來(lái)到莫高窟,非常喜歡這個(gè)地方。萊瑟士這樣寫王道士的選擇:
王道士參觀這里時(shí),這些寺廟狀態(tài)不佳,因此他自愿獻(xiàn)身成為這里的保護(hù)者。他清除了一些石窟里填滿的沙漠沙子,修復(fù)壁畫,甚至委托別人繪制新壁畫。他常常用盡布施與乞討,但現(xiàn)在這些錢財(cái)只有一個(gè)用途——石窟。
這段文字至少說(shuō)明,在沒有發(fā)現(xiàn)藏經(jīng)洞的前期,王道士是敦煌石窟的保護(hù)者。直到有一天,王道士在修復(fù)一幅壁畫時(shí),發(fā)現(xiàn)壁畫的后面應(yīng)該是空的。萊瑟姆寫道:
他破墻而入,在他那盞小油燈的昏暗光線下,他看到另一個(gè)約2.7米見方的山洞,里面堆著約3米高的卷軸。這項(xiàng)考古發(fā)現(xiàn)與霍華德·卡特進(jìn)入圖坦卡蒙陵墓不相上下:這些卷軸可以追溯到4世紀(jì)到11世紀(jì)。王道士多次試圖引起當(dāng)?shù)毓賳T對(duì)這個(gè)藏經(jīng)洞的興趣,但他們興致缺缺,只是讓他看守石窟。
王道士最初出現(xiàn)在中國(guó)大陸的流行文字中,是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余秋雨對(duì)王道士是痛心疾首的。然而,歷史的真實(shí)情況是,王道士并不懂得這個(gè)藏經(jīng)洞中書的價(jià)值。他一直在向當(dāng)?shù)氐难瞄T匯報(bào)這件事情,結(jié)果,他一次次地去,步行幾十幾百公里,卻一次次地被打發(fā)回來(lái)。最好笑的是,王道士趕著毛驢,冒著被沙漠中的狼吃掉的危險(xiǎn),行程800多里找到時(shí)任安肅兵備道的道臺(tái)廷棟。這位廷棟大人瀏覽了一番,最后得出結(jié)論:經(jīng)卷上的字不如他的書法好。
這才有了王道士向斯坦因和伯希和等人出賣經(jīng)書的事情。
斯坦因從王道士手里買走了《金剛經(jīng)》的刻板印刷的版本,這一下讓全世界知道了,是中國(guó)最早發(fā)明了印刷術(shù)。《金剛經(jīng)》除了讓王道士出名以外,還讓唐代一位叫王玠的刻字工匠出了名。因?yàn)椋谒固挂蛸?gòu)買的《金剛經(jīng)》印刷版上,竟然留有王玠的名字,“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咸通是唐懿宗李漼的年號(hào),這差不多是向世界宣告,至少在唐或者更早期,中國(guó)已經(jīng)有了刻版印刷的技術(shù)。
萊瑟姆筆下的中國(guó)早期印刷的佛經(jīng)特別有意思的是,每一本佛經(jīng)印刷前都有人許愿。在萊瑟姆的筆下,贊助印刷佛經(jīng)的中國(guó)人有這樣的愿望:
一卷是一個(gè)農(nóng)民為他的牛許愿獲得更好的轉(zhuǎn)世,另一卷是一位女性希望逃離荒蕪沙漠回到國(guó)都,還有一卷是一名官員為了升官……
一部中國(guó)人的精神生活簡(jiǎn)史
與《階梯與狂熱》這部圖書野史相對(duì)照,我近期剛好閱讀了《中國(guó)書業(yè)史》(上下)兩卷本。打開目錄,我直奔唐代的中國(guó)書業(yè)史。與萊瑟姆的書寫相對(duì)應(yīng)的是,《中國(guó)書業(yè)史》不僅有考證,還有更為細(xì)節(jié)的舉例。
在唐代,中國(guó)的鄉(xiāng)村識(shí)字教材,是《千字文》。《中國(guó)書業(yè)史》這樣寫道:
唐代女詩(shī)人薛濤居于成都浣花溪,與客人飲酒,行《千字文》令。在敦煌石室藏有許多從唐代至五代的《千字文》寫本,僅被外國(guó)人斯坦因、伯希和劫至西方的就達(dá)31種。
《中國(guó)書業(yè)史》雖是關(guān)于圖書出版的正史,然而,這部作品中的引文也非常有趣。
比如唐代開書店很有名的徐文遠(yuǎn)是河南洛陽(yáng)人,徐文遠(yuǎn)和他的哥哥徐文林在長(zhǎng)安城開了一個(gè)書店。一邊開書店,徐文遠(yuǎn)還一邊開設(shè)學(xué)館講學(xué)。徐文遠(yuǎn)教出來(lái)的有名的學(xué)生李密,后來(lái)造反成為農(nóng)民起義的領(lǐng)袖。
唐代的中國(guó),因?yàn)榛实劾钍烂裣矚g書法,所以,書店大多代售書法作品。這就要求書店老板有一定的鑒賞能力。在《中國(guó)書業(yè)史》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唐代人李綽著《尚書故實(shí)》載:“京師書肆孫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鑒書畫,精于品目,豪家所寶,多經(jīng)其手,真?zhèn)螣o(wú)所逃焉。”這條史實(shí)可以使我們對(duì)唐代書肆的情況有進(jìn)一步了解。第一,孫盈辦的這家書肆,經(jīng)營(yíng)有方,遠(yuǎn)近聞名;第二,這家書肆不僅賣書,也賣名家書法字帖、字畫和名畫家的畫卷;第三,這些書畫多出自前朝名家手筆,價(jià)格很高,十分珍貴,有人就加以臨摹仿制,以假充真騙取買主的錢財(cái),書肆經(jīng)營(yíng)這類書畫精品必須是行家里手……
從這一段文字來(lái)看,唐代的書店和現(xiàn)在的書店形態(tài)幾乎一樣,只是更多了一些古玩字畫,就像是民國(guó)時(shí)期的舊書店。
如果說(shuō),《階梯與狂熱》是一部輕松的關(guān)于圖書的奇趣博物館,那么,《中國(guó)書業(yè)史》差不多是中國(guó)人的精神生活簡(jiǎn)史。在手機(jī)資訊過(guò)度供給的當(dāng)下,我們更需要安靜地閱讀紙質(zhì)圖書的時(shí)間,而《階梯與狂熱》和《中國(guó)書業(yè)史》中所介紹的圖書目錄,足以支撐我們很長(zhǎng)時(shí)間的閱讀。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從這樣的圖書中找到更多的書目來(lá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