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語殷殷——論舒群抗戰創作中的認同書寫
在馳名中國現代文壇的“東北作家群”當中,最受學術界乃至文化界關注的當屬蕭紅、蕭軍、端木蕻良、駱賓基。這一方面是其文學成就使然,另一方面也和他們之間富有傳奇色彩的感情糾葛以及凝聚其中的知識分子心靈史有關。但在傳記和影視反復聚焦的這幾位作家之外,“東北作家群”的其他成員亦不乏值得稱道的創作與人生。這其中,舒群便是一位早年獲譽、史有令名,而其創作成就和意義卻沒有得到充分認識的作家。
1913年9月20日,舒群誕生于黑龍江省阿城縣(今哈爾濱市阿城區),本名李書堂,筆名黑人、舒群。[1]李姓這個姓氏看似普通,背后卻隱藏著整個家族顛沛流離的苦難歷史。李家本是吃“鐵桿莊稼”的鑲黃旗人,隨清軍入關后定居關內,世代從軍,舒群的祖父便是一名駐防山東青州的軍官。衰敗的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炮聲中轟然坍塌后,各地旗人頓失護持,不僅沒有了旱澇保收的口糧,還不得不面對“驅除韃虜”“反滿興漢”的革命動員點燃的怒火。在朝不保夕的惶恐中,祖父決定舉家逃亡,回歸千里之外的白山黑水。一家人雖然歷盡千辛萬苦回到了滿族的發祥地,卻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老姑被賣,祖父慘死途中,連血脈所系的滿姓,也因逃亡時刻意的隱姓埋名而湮沒于歷史之中。
在舒群的幼年,一家人為了糊口輾轉于阿城、一面坡、哈爾濱之間。不過,雖然舒群家境貧寒,他的成長環境卻并不像內陸僻壤那樣閉塞。晚清以降,東北邊地既有漢、滿、蒙等多個民族雜居,又被俄、日等列強染指,是一個社會狀況復雜、文化異常多元的交匯之地。沙俄所修筑的中東鐵路,意在侵吞東北,客觀上卻也繁榮了東北經濟,沖擊、改變著當地風習。這些不可替代的人生經驗和文化視野,加之“九·一八”事變后舒群投身抗日斗爭、參與第三國際情報工作而奔走于北滿各地的耳聞目睹,為其抗戰書寫提供了異常豐富的素材。他根據自己的成長經歷和東北淪陷后的痛切體驗寫下的一系列小說,生動地呈現了東北各個族群在歷史轉折中的錯綜關系和復雜心態,在白雪黑土之上描繪出色彩斑斕的認同景觀,以文學的方式詮釋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作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一部分的國際廣度和歷史深度。
一、旗幟·慶典·語文:民族國家認同的豐富圖景
舒群小說處女作《沒有祖國的孩子》發表后,評論家普遍注意到,小說中的國旗是匯聚認同的焦點。周立波有如下評論:
孩子們看見中國的旗子換上了“滿洲國”國旗的時候,他們對祖國的舊旗感到了無限愛惜和懷念,竟撲到儲藏室的玻璃窗上去看那丟在角落里的旗子。這種情緒像本能一樣的自然,而又很使人感慨。[2]
梅雨、周揚等人也紛紛指出,舒群對國旗意象有著巧妙的運用。[3]事實上,舒群的多篇小說都將國旗作為推進情節的抓手和引發高潮的關鍵。國旗是國家的象征,它的消失意味著國家淪亡:“這城的旗桿,失去了祖國的旗子,我……我失去了一切的自由。”[4]取而代之的是侵略者的旗幟,“紅色旗面的中間,縫補著一個白色的圓球”[5]。這面旗幟不僅飛舞在東北的大城小鎮,還深入到鄉間:“孩子們拾著樹枝,/赤著足,破了衣,/我問孩子,孩子默語,/遙指遠山的日本旗。”[6]傀儡政權“滿洲國”的“國旗”,“在地圖與萬國旗中,我們從來也沒有見過”[7],也在刺刀的庇護下粉墨登場:
在十八的那天,在公園里搭好了幾所華麗的席棚,一邊懸滿著燈彩,一間高搭著講臺,四角垂著新樣的旗子:四分之三是黃布,四分之一是紅藍白黑四色。中間高懸著萬國旗,那里沒有祖國的旗子,全數都是新樣的代替了。[8]
認同的碰撞和爭奪,很自然地圍繞國旗展開。小說《肖苓》中,曾經要求學生牢記“讀書救國”的張訓育員,在敵軍到來之前忙不迭地燒毀國旗,引起了學生的不滿:
我們的眼睛全集中在一處——七八丈長的旗桿頂點象有一塊模糊的彩霞飄落下來。
突然有幾面國旗丟向火中去,肖苓立刻搶了一面,她用手擺動著,叫著:
“中國不亡!中國不亡!”
這叫聲仿佛沖裂了我們每個人的每個毛孔,落著一滴一滴的鮮血。[9]
更為激烈的斗爭,發生在短兵相接的軍事領域。《松花江上的支流》講述的便是不甘心為虎作倀的愛國軍人奮起反抗的故事。哈爾濱淪陷時,江星軍艦隨整個江防艦隊,未發一槍一炮就投降了。“它的無能的懦弱的主人,也讓它不幸地隨著主人做了俘虜,以最大的恥辱,恥辱了它,艦尾失去了國籍,——艦尾空留一條不懸旗子的旗桿,寂寞地伴著兩條赤裸的繩段。”[10]以馬平為代表的眾多水兵反對投降,要求抗戰,艦長卻一味貪戀權位,甘當日寇走狗,并嚴厲地責罰“破壞軍紀”的艦員。然而,人心自有向背,投敵者為了表白忠心而舉行的“隆重的升旗禮”最終變成無情的諷刺:
集合的軍號響了。一切的艦員,都在甲板上排成隊伍。因為江星軍艦沒有裝置禮炮,以二十一發的紙炮行了海軍最高的軍禮,歡迎著艦長陪來的一個敵人。然后艦長命令升旗:紅,藍,白,黑,黃,五色合成的旗面,慢慢地飄起。任著艦長隨伴那個敵人如何地鼓掌,聽來也只有他們兩人單調的響聲。十幾人合奏的軍樂,也并不象從前一樣響亮,仿佛所有的樂器,都漸瘖啞了,而且,錯亂著節奏,不相調諧,有的人,只有裝做著奏樂的姿勢,卻聽不見他的樂器的音響,有的人,繼續地奏響著,也許他在擔心樂聲中斷下來,有的人……所以艦長以一種嚴責的眼色傳給他們。于是,他們響亮地奏了一段,然而從狂歡的樂譜卻轉為悲哀的葬曲了,仿佛不是在祝賀著一種典禮,而是在曠大的墓場,哀悼著千萬的死者,或是,憑吊著祖國的亡魂。[11]
效忠“滿洲國”的江防艦隊被派去鎮壓松花江兩岸的吉林救國軍,用引以為自豪的炮火殺害自己的同胞。馬平等人終于無法忍受這種恥辱,聯合其他水兵發動起義,處決了附逆求榮的艦長和敵人派來的“指導官”。艦隊的其他軍艦聞訊趕來,江星軍艦不幸未能逃脫追擊,受創累累,行將沉沒。決心與艦同亡的水兵們,在生命的最后時刻用再一次的升旗禮洗雪了恥辱——
馬平從廚房取來了那面已經失了形色的國旗,舉行著升旗禮。
軍號響著,國旗爬至旗桿頂點的時候,江水已經浸沒甲板四尺以上,只讓一列人頭留在水面,同聲地喊了最后的一句:“中國萬歲!”[12]
從城市到鄉村,從學校到軍營,中國人用鮮血和生命捍衛著侵略者企圖消滅的國旗。這正說明,中國人不再“只知有家,不知有國”,而具有了民族國家意識,高度認同國家的象征符號——國旗。訴諸大眾情感的象征,也就是“紀念日以及應該留存于記憶中的時代,公共場所以及紀念碑式的道具,音樂及歌曲,旗幟、裝飾品、雕像、制服等藝術的設計,故事與歷史,精心策劃的儀式,以及伴隨著行進、演說、音樂等的大眾示威行為”[13],對于民族國家的構建和鞏固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從1862年中國的第一面國旗黃龍旗投入使用開始,經過數十年的國家建設,雖然實質性的國家能力尚有諸多欠缺,形式上的象征體系卻已漸趨完備,并內化于國民認同。對于“九·一八事變”發生時的東北民眾來說,幾年前的“東北易幟”僅僅意味著政權在中國內部的易手,五色旗與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所號召的民族國家認同一脈相承,是以懸掛了沒幾年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被廢棄時,孩子們懷念這面旗幟的情緒“像本能一樣的自然”,而試圖分裂中國、營造“滿洲認同”的偽滿國旗則遭到冷遇。[14]

舒群
既有的象征符號系統嚴重地阻礙著“心的征服”,侵略者和傀儡政權必然視之為眼中釘肉中刺,用各種手段予以拔除。“滿洲國”不僅大力推廣“五族共和滿地黃”的“國旗”,還編寫了新的“國歌”,強迫學生們學唱。但無論是肖苓將“人民三千萬,無苦無憂”的歌詞唱成“人民三千萬,如豬如狗”,還是《孤兒》中的烈士遺孤小村憤然直言“誰還念亡國奴的書!”,都顯示了東北青少年對殖民奴化教育的反感和抵抗。同樣,廣大東北人民視“九·一八”為恥辱日,“滿洲國”卻在這一天大肆慶祝,試圖將其強行改造成“紀念建國”的節慶。《做人》反映了亡國的人們對這場丑劇的普遍抵制。一家報社被分配了五張慶祝典禮的入場券,除三個外勤記者之外還余下兩份,
社長拖著那兩份送到每個人面前的時候,每個人都是推開他的手說:
“社長一個人帶著兩份去吧!”
“那還不如讓我死吧!”
……
社長想了許久,說:
“叫兩個印刷工人去吧!”
可是印刷工人卻說:
“我們工人不是人嗎?”[15]
顯然,工人所說的“人”,并不是指自然的生物人,而是有其民族國家認同的社會人。無論工人與編輯、記者在經濟、社會地位和文化程度上有怎樣的差異,他們同樣具有中國認同,而這種認同是其人格、尊嚴與良心的一部分。參加慶典,同樣會讓他們的人格遭受侮辱。與之呼應,小說的標題《做人》號召,不要做一個茍且偷生、人格殘損的奴隸,而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反抗奴役,追求自由。
和有形的象征相比,無形的語言更是認同的天然載體,其份量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這個方面,舒群貢獻了相當精彩的《沙漠中的火花》,其獨特之處在于將目光投向了同樣遭受日寇欺凌的蒙古族同胞。日軍侵占內蒙后,貼出蒙文告示,宣稱“順天安民”“想造東亞樂土”,于是“注意建設,招募工人”。貧苦的蒙人阿虎太和朋友薩達爾圖為了糊口應募做工。他們很快發現,侵略者為了遂行殖民統治,做了精心的準備:
“到這里來報名!”“小狼”喊著。
他說的是蒙古話,由于字音的準確,聲調的熟練,使不看見他的人,絕不會想到他是在說著異族的話。
……
……他又從帳篷里喚出八個人參加進來。他說:
“這里有幾個中國人,也是同你們一樣的工人。他們跟我們的軍隊太久了,比你們能多知道一些,要聽他們的話才好。總之,你們大家好好在一起做,有事不妨大家商量。”[16]
“小狼”的話隱藏著許多玄機。首先,殖民者會說被殖民者的語言,而且字正腔圓,這并非文化“親善”所致,彰顯的是“狼”的野心和耐心。其次,蒙人不是中國人,這既是“小狼”的言下之意,也是日本政學兩界長期以來基于本國的侵略企圖反復論述的觀點。最后,“是同你們一樣的工人”,但“要聽他們的話才好”,不外乎利用民族矛盾“分而治之”的殖民手段。但詭譎之處尚有更深一層:
這幾個中國人,沒有一個穿中國衣服的。他們上身是雜色的西裝,下身全是一色的馬褲。雖是短小的肢體,卻異常的高傲。每天指示著蒙人的工作。有時一同談起話來也很和氣,意思是常想問出蒙人的內心話來。[17]

《舒群文集》,舒群 著,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9
這些衣著舉止異樣頗多、兢兢業業為寇前驅的“中國人”,引起了阿虎太的懷疑。當他和一個名叫“趙德”的“中國人”被派去刷洗墻上的“天下為公”標語、重新涂色時,一場唇槍舌劍的對決終于發生:
……他的豬毛刷剛觸到“天下為公”的“天”字上,又停下來問:
“這是什么字?”
“天——”
趙德搖起頭來。他匆忙地追問著:
“這是中國字,你怎么不認識?和我一樣?”
“你說的……中國話怎么太好呢?”
趙德是用蒙古語問的。同時,無意中也引起他蒙古語的回答:
“哼!我以前在中國地方多少年啦。這里也是有許多中國人住,我常和他們有來往。他們以為我是中國人呢!”他望望趙德又說:“你說的蒙古話太壞,我們差不多都聽不懂!”
“我能聽懂你們的。”
“我們都說中國話吧!”
“說蒙古話吧!”
“你說的不好!”阿虎太改用中國話說。
“啊啊!”
“我擦掉這中國字,你心不難受嗎?”
趙德不回答,臉上也沒露任何的感覺。所以阿虎太輕蔑地說:
“你這樣的中國人啊!可是我倒痛快!”
他一下就把“天”字抹去了一半,眼角與嘴角全笑得裂開了;可是他望見哨兵又失意地收攏起來。
趙德憤憤地回答他幾句中國話;那比他說的更不熟練。[18]
這一幕多少有些滑稽:“中國人”非要用蒙古話交談,“蒙人”卻建議兩人都說中國話。不過,如果說中國人不識中國字還可辯稱自己是文盲,中國人講中國話還不如久居“中國地方”的蒙人,這就越發蹊蹺。最可能的情況是,“趙德”及其同伙其實是冒牌的中國人,他們的蒙古話和中國話都是為了臥底而學的。這種可能性不久之后便被證實,因為趙德等“中國人”飲酒作樂時用阿虎太完全不懂的語言高談闊論。看似粗豪愚魯的阿虎太,就這樣通過關鍵性的身份標識——語言,洞悉了敵人的奸詐。
身份認同固然系于象征和語言,卻又每時每刻體現在人的行動當中。當帝國主義的鐵蹄踐踏中國的土地時,許多不曾受過良好教育、也不能游走于不同的語言文化之間的民眾,訥于言而勇于行,和肖苓、馬平、阿虎太一樣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事跡。在舒群的筆下,涌現了與借宿的游擊隊員兄妹相稱并隨游擊隊逃亡的農家少女(《農家姑娘》)、為了掩護抗日戰士慘遭日軍奸殺的蒙古姑娘(《蒙古之夜》)、臨終前在孩子的手腕上寫下力透皮肉的“東北好男兒 馬革裹尸歸”的母親(《嬰兒》)、被強征入日軍輜重隊后拼死逃脫的東北青年(《血的短曲之五》)、不堪暴虐與敵人同歸于盡的馬車夫(《奴隸與主人》)等人物群像。而在《青年》《老兵》等另一些作品中,一些人心安理得地茍且事敵,另一些人則逐漸擺脫了麻木、頹唐和彷徨,走上堅決抵抗的道路,兩相映襯,益發彰顯了人民在戰爭中的偉大覺醒。覺醒了的、熱愛自己的大好河山的人民,不再甘于壓迫和奴役:“那一切的一切,都是自由地生長,自由地存在;雖然有滅絕的時候,也都是自由地滅絕!”[19]
二、《沒有祖國的孩子》中的繁復心曲
《沒有祖國的孩子》寫于獄中,1936年發表于《文學》六卷五期,既是舒群的成名之作,也是他最負盛名的作品。小說所弘揚的愛國情懷和國際主義精神,一直為評論家和研究者所稱道。然而,舒群在這篇“真實同誠實”的小說中寄寓了較為復雜的情感,論者對此缺乏足夠細致的考察。若要完整聆聽回蕩在小說中的心聲,我們必須以“深入廣出”的方式,在較長時段的舒群創作和生活中尋找進入文本深層的線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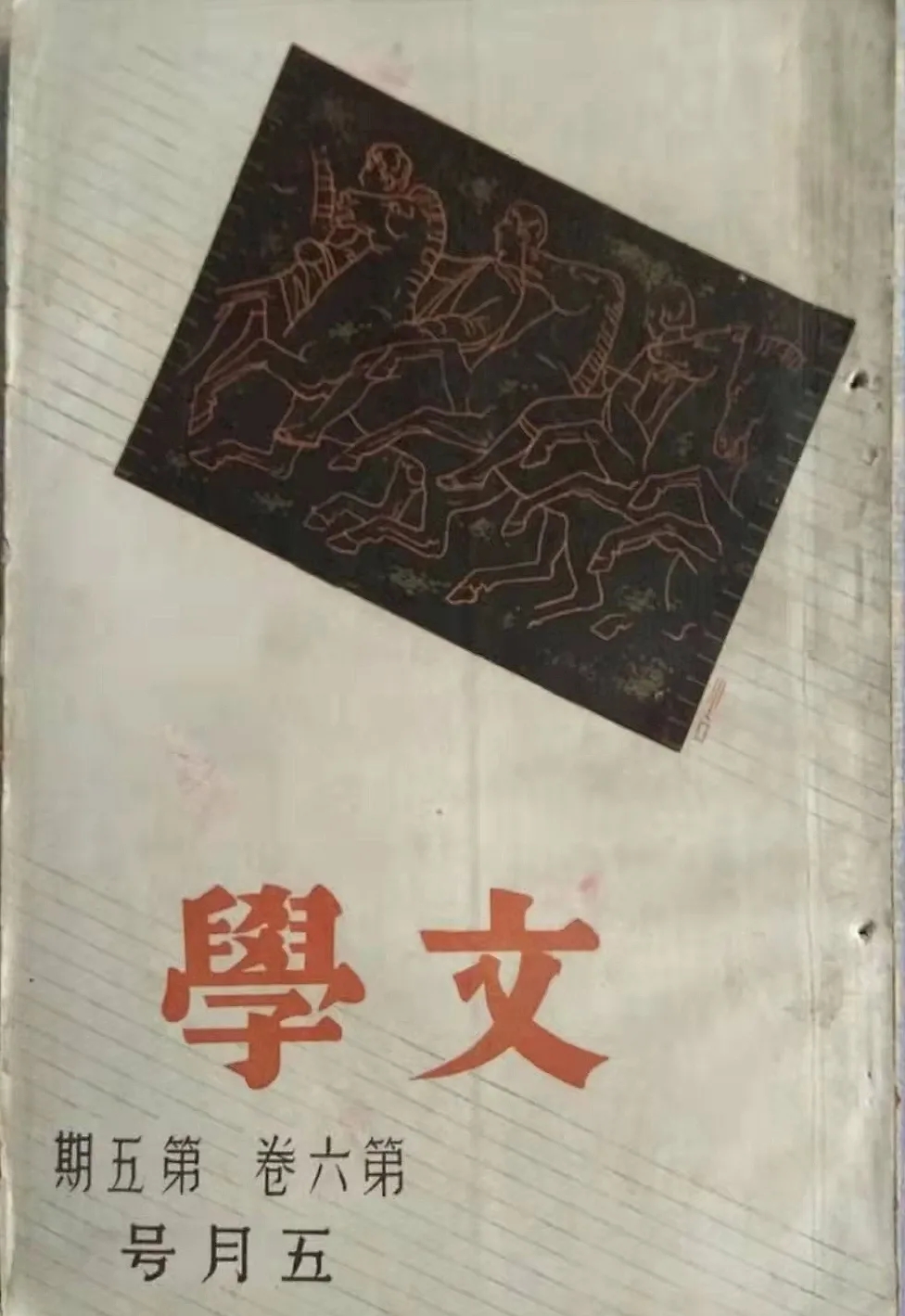
《文學》六卷五期,1936
小說中的蘇聯少年果里沙無疑是一個頗具爭議的人物形象。他一出場,就表現出種族主義傾向:“果里沙總是用手指比劃著自己的臉,果里的臉。意思是讓果里看看自己的臉和他的臉,在血統上是多么不同啊。”[20]對于流落異國的果里,果里沙毫無同情之心,也不相信朝鮮還有安重根這樣視死如歸的志士,屢次出言譏刺、當面羞辱。在他的口中,果里和其他朝鮮人都像老鼠一樣懦弱,朝鮮正是因此而亡國的。果里沙不僅不愿意和果里做朋友,還想盡各種辦法橫加欺侮,“罵他,向他身上拋小石頭,伸出小拇指比量他……”[21]但在得知果里用“我”的刀殺死了日本兵之后,剛剛還在嘲諷他的果里沙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
“好樣的,好樣的,”果里沙抱住果里又說:“這才是我的好朋友!”
果里搬到宿舍來,除去蘇多瓦贈給他的毛毯之外,再什么都沒有。果里沙把自己所有的東西分給他一半,并且,在販賣部內給他買了牙刷,牙膏,襪子,毛巾,小手帕……費用全寫在自己的消費簿上。[22]
此前的輕蔑態度非常僵硬,此刻的轉變又顯得過于戲劇性,無怪乎批評者認為,“果里沙的性格,也強調得失當”。[23]這個人物的原型,是舒群就讀于中東鐵路蘇聯子弟中學時的朋友。在舒群寫于1950年的回憶少年時代的小說《童話》中,“我”和果里沙(文中名為“哥里沙”)親密無間,還在清明節一同種下了象征著友誼的榆樹。多年后,“我”重回故里,看到果里沙曾經居住的院子成了廢墟,榆樹卻已經枝葉成蔭,遂有“木猶如此,人何以堪”的感慨。在這篇小說中,果里沙完全把“我”這個中國同學當作兄弟看待,絲毫沒有高人一等的傲氣。再看另一篇自傳性小說《我的女教師》中的相關情節,果里沙也只是在“我”剛到蘇聯子弟中學念書時,惡作劇搶走了“我”的帽子,很快也就聽從老師的教訓而改變了態度:“從此,同學們再沒有一個人,耍笑過我;而且,哥里沙對我,表現的更好。”[24]這樣一位金蘭之交,為什么在《沒有祖國的孩子》中如此面目可憎呢?舒群在塑造果里沙形象時“過火”,是僅僅因為寫作技巧上不夠圓熟,還是有什么別的原因?
為了準確把握這一人物形象的內涵,讓我們把目光投向這篇小說的文本和現實之間的“顛倒”。在真實的歷史中,舒群逡巡于校門之外,藉由果里的幫助和女教師的關照而幸運地入學;在小說中,這個情節卻被改寫為,在蘇俄學校念書的“我”(果瓦列夫)給予朝鮮孩子果里同情和友誼,而女教師蘇多瓦最終接納了果里。小說家的處女作往往具有自敘傳的性質,《沒有祖國的孩子》亦取材于舒群自己的經歷,但對人物關系和形象做了重要調整,將被侮辱和被損害而堅貞不屈,終于奮起反抗的果里置于敘事中心。顯然,這樣的設置并非隨意為之,而是舒群出于表達需要而采用的寫法,這與他在“紅俄學校”的所學所思有著密切關聯。舒群曾短暫就讀的中東鐵路蘇聯子弟十一中學,是中東鐵路管理方為蘇聯僑民和鐵路員工的子女設立的學校。對于舒群來說,師生主體是蘇聯人、教學語言為俄語、課程內容秉承蘇聯本位的這所學校,跡近異國。在這里的學習生活,賦予他前所未有的視野。菲律賓民族主義者何塞·黎薩(José Lizal)在其小說名著《不許犯我》的開頭描述了主人公的心靈受到沖擊的時刻:長期旅居歐洲之后,他返回了1880年代的殖民地馬尼拉。當他在馬車中觀望窗外的植物園時,發現自己處于“倒轉的望遠鏡的末端”。“這些園圃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地隱沒到它們在歐洲的姐妹園子的意象當中去了。他不再能夠實際平常地體會它們,而只能近在咫尺同時又遠在天邊地看著它們。”[25]和黎薩相似,在“紅俄學校”浸淫過的舒群也不再能夠用“自然”的眼光去看待周遭的人和事,但這番“留學”經歷帶來的“比較的幽靈”于他不是或主要不是民族主義意識,而是國際主義精神。在“幽靈”的纏繞下,作者下意識地將小說中的自我置于審視的位置,而在特定政治視野中的人物形象并不是紀實性的,往往承載著類型化的政治意識投射,果里沙刻板乃至畸形的性格與這一寫作取向有重要關聯。[26]
藉由國際主義視角,人物形象呈現為類型化的二分。“我”叫果里同去看電影時,守門的中國人蔑稱果里為“窮高麗棒子”,堅持不許他進去,并以教訓“我”的口吻說:“你和他做朋友,有什么出息?”對朝鮮流亡者的輕蔑乃至厭惡在當時的中國東北普遍存在,原因是日本殖民侵略的受害連帶感未能超越現實中的民族隔閡而成長為清晰的共情。與之相對,因為電影院門衛侮辱果里而憤怒、寒心、羞愧,“一夜沒有安靜地睡”的“我”,已經建立了足以明辨是非的國際認同。同樣,在蘇聯人群體中,給予果里慷慨饋贈,接納他入學的女教師蘇多瓦,也和狂妄自大、視果里為“老鼠一樣”的亡國奴而加以欺凌的果里沙形成鮮明對比。果里沙的民族沙文主義或魯迅所謂“獸性愛國”面目,或許的確取材于舒群所熟悉的那個蘇聯少年,但更應該說是近代以來不斷覬覦、反復染指中國東北的俄國形象之化身。[27]他最后認可果里(而非朝鮮人),并不意味著思想上的升華,更像是崇拜強力者對勇士的敬佩和承認。
果里沙這個人物,一方面和從一開始對果里平等以待并時時維護的“我”恰成反對,映照出后者本于人道情感和自身經驗對被殖民者苦難的感同身受,另一方面與“那異國的旗子,那異國的兵”共同構成了理解小說的必要背景,即復數的強權存在。不難注意到,中國人“我”和朝鮮人果里各自的母語姓名都沒有出現,兩人在中國的土地上始終以俄文名互相稱呼,使用俄語交談,“仿佛忘記了我們是異國的人”。[28]雖然小說中三位少年在果里沙改弦更張之后結為“不可離散”的伙伴,評論者也矚目于“三個不同國籍的孩子的真誠友情”[29],筆者細讀全篇后卻認為,“我”和果里的友誼才是作者念茲在茲、深情傾注的敘事焦點。小說點出了放牛為生的果里對朋友的誠摯:“他天天會給我們送來許多新鮮的趣味;并且,我們房里一瓶一瓶的,紅色與黃色的野花,全是他給我拾來的。”[30]果里沙不屑與之為伍,并刺痛了果里的民族自尊心,導致他從此辟易,再不從“我”和果里沙的宿舍門前經過。“我”憤恨于果里沙的傲慢,“總想找著機會,再和果里好起來”。這種情誼源于共通的受害經驗——果里是朝鮮抗日烈士的遺腹子,其父被殺害于櫻花盛開的時節。果里父親壯烈犧牲的一幕,敘事者“我”因為果里的講述迅急甚至錯亂而“沒有完全明白”,隱含作者的態度卻昭然若揭。早在1933年發表的一首詩作中,舒群便寫道,“飄落了南國的櫻花,/長茂了塞上的荒草,/它們曾幾度開凋,/把我的童顏逼老。”[31]櫻花是日本的國花,爛漫時節如緋云絳雪,美不勝收,但在淪為殖民地的朝鮮和中國東北,它卻是不言自明的侵略者象征。事實上,“我”的視角,融合了多年后的革命者舒群回眸往昔的目光,這使得“我”的所見所思雖以少年口吻道來,內里情感卻敏銳、深沉。小說中,“我”對果里以至朝鮮流亡者的同情,正是在“淪陷時刻”的震驚和恥辱中升華,并在作者舒群流亡關內而懷念故土、身陷縲紲而向往自由的心靈狀態中達于深切。
發表稍早于《沒有祖國的孩子》、同樣書寫了“淪陷時刻”的《鄰家》,則用更加戲劇性的手法,揭示了中朝人民共同的命運。小說中,中國人對待朝鮮流亡者的態度再次涇渭分明。“我”的房東是一位高麗老太婆,她的三個兒子都因為從事獨立運動被日本人抓去判了重刑,只能靠轉租住房和女兒賣淫維持生計。“我”和房東發展出了母子般的真摯感情,“有時,我病了,她照顧著我,象我的母親。同時,我照顧著她,也是盡了我所有的好心。”我的朋友均平卻蔑稱房東和她的女兒為“窮高麗”,并說她們不配坐柳樹下的長凳,應該坐在后面的一塊大石頭上,因為“那才是亡國奴坐的地方!”故事以精彩的一筆收束:當均平再次呵斥“窮高麗”,讓老太婆“滾開”,坐到那塊大石頭上,
她向他伸出了食指低聲說:
“現在也該你去坐了。”
那天,恰好是“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天。[32]
正如果里憤怒地擲向電影院門衛的那句“好小子,慢慢地見!”讓“我”覺得為自己復了仇,高麗老太婆對均平的反唇相譏在舒群筆下同樣充滿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快意。國際主義的“幽靈”,讓舒群筆下的敘事者比一般的中國人更能在受壓迫民族身上看到自己的命運,進而由同病相憐而同仇敵愾,以彼之敵對為己之仇讎。果里借“我”的刀手刃“魔鬼”,正是戮力同心的寫照。真實歷史中的舒群離開蘇聯子弟學校時,其他同學只是揮手告別,果里卻送給他一滴眼淚——他們之間,有著更多的羈絆,有著被殖民者的相互慰藉,有著來自一個富強國度的果里沙乃至蘇多瓦所不能充分理解的深刻認同。《沒有祖國的孩子》的第一版話劇改編中,蘇聯人物被完全隱去,固然與論者分析的時勢因素有關,亦不排除話劇試圖回避小說中對于蘇聯并非純然正面的感受,盡管那更符合舒群的原初生命體驗。[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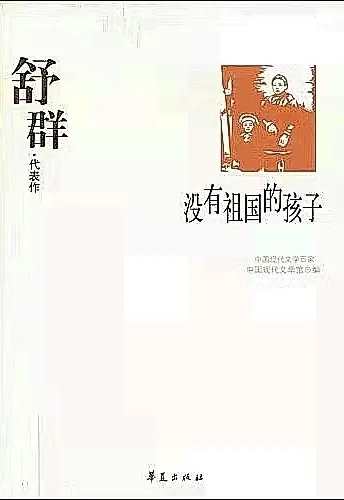
《沒有祖國的孩子》,舒群 著,華夏出版社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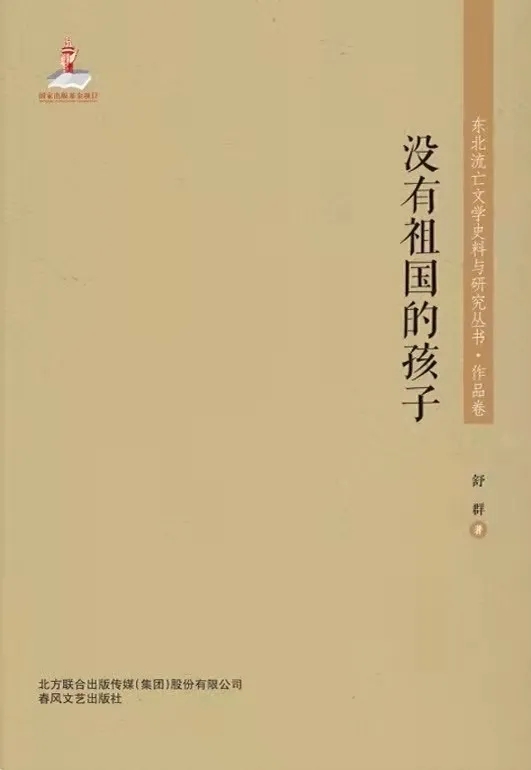
《沒有祖國的孩子》,舒群 著,春風文藝出版社2019
三、全世界受苦的人
舒群對朝鮮流亡者的同情始終如一。除了上文提到的兩篇小說,稍后創作的《血的短曲之八》和《海的彼岸》中也出現了令人難忘的朝鮮人形象。前者描繪了一個飽受凌辱的朝鮮慰安婦,她被中國軍隊解救后“仿佛更記起了而且渴望著她的祖國、故鄉、家庭,人類圣潔的感情依托的所在;她痛苦得打起自己的頭來,不惜打到粉碎”,幾欲獨自一人踏上危險的歸途。[34]后者是舒群的又一名篇。朝鮮抗日志士在風雨中告別老母,渡海亡命中國,從此兩人天各一方。十年后,時日無多的母親為了見兒子最后一面,來到上海。兒子深夜潛入母親下榻的旅館,母子悲歡交集,卻因鷹犬環伺,只能在黑暗中握手低語,終未燃燈相見。心有不甘的母親囑咐兒子,明天早晨在窗下走過,讓她看一看。兒子遵命而行,第二天卻沒能見到母親,原來她已在黎明溘然長逝。
這兩篇作品發表時,舒群身在桂林,受李克農指派擔任八路軍桂林辦事處與駐七星巖的朝鮮義勇隊的聯絡工作,還曾參演金昌滿編導、金煒主演的三幕話劇《朝鮮的女兒》和朝鮮歌劇《阿里郎》。他的創作靈感,除了早年的記憶,大概也得益于這時和朝鮮愛國者們建立的戰友情。遭受殖民侵略的共同體驗以及人道關懷,使得中國現代文學中不乏描寫朝鮮流亡者的篇章,對舒群影響很大的“沒見過面的第一個文學老師”[35]蔣光慈即有《鴨綠江上》傳世。但無論是由赴日途經朝鮮的短暫經驗敷演出《牧羊哀話》的郭沫若,還是借留學生聯床夜話轉述朝鮮人黍離之悲的蔣光慈,又或是偶識朝鮮鄰人而感慨良多的臺靜農,對亡國之民綿長苦難的體會都不如舒群深切。與果里朝夕相處、患難與共的經歷,使他在抗戰創作中對朝鮮人民的悲慘遭遇念念不忘,再三著墨。
朝鮮淪為日本殖民地后,為數甚多的朝鮮人或不愿屈服,或迫于生計,紛紛遠走中國東北,故除舒群之外,李輝英、蕭軍、蕭紅、羅烽、端木蕻良、駱賓基等東北作家都曾下筆描摹在華朝鮮人。舒群的殊異之處,如前文所述,乃在于自覺的國際主義意識帶來的寬廣視野,這使他的觀照更為廣闊。青年舒群曾用筆名“黑人”發表作品,一方面是因為膚色黝黑的他被朋友戲稱“老黑”,更主要的在于他認為身處社會底層的自己與國外飽受欺壓的黑人實堪比擬。[36]這樣的階級意識,由小說《獨身漢》可得印證。黑人琴師貝特技藝精湛,卻孤苦伶仃,浪跡世界。貝特來哈爾濱演出時,欽佩貝特琴藝的美國姑娘維兒斯經“我”的介紹與貝特墜入愛河,最終卻因母親對黑人的種族歧視,未能和貝特比翼雙飛。舒群再次用少年的眼耳和口吻,記錄了受壓迫者的艱辛、憤懣和身為“一萬二千五百萬中的一個”[37]而與生俱來的彷徨無助,以及彼人哀苦無告的悲歌:
然后,他就從伏爾加船夫曲的中間唱起來了:
“——世界誰聽吾歌聲,祈禱上蒼,誰能救我們,我在呼喚自由與平等。”
這時候,我看他的臉。他的手,他的腳,沒有一處不是在憤抖的突變中。[38]
作為現代文學史上罕見的黑人題材小說,《獨身漢》對貝特以及全世界的黑人表達了深深的同情,具有鮮明的進步意義;而舒群發表于1934年的一首詩作,則讓我們聽到了《獨身漢》的弦外之音:
黑人呵,你們沒家沒國,
家國呵,已被白人侵奪,
你們都是流浪在天涯,
生活在主人的腳下。[39]
舒群的白俄題材小說《無國籍的人們》,同樣具有不容忽視的意義。十月革命后,大批反抗或逃避紅色政權的白俄流亡到中國,成為哈爾濱、上海等城市的社會和文化生活中的醒目存在,也催生了中國作家的白俄書寫。《無國籍的人們》取材于舒群在青島獄中的真實經歷,因而與《沒有祖國的孩子》有一定的互文關系。這篇小說中同樣有一個名叫果里的孩子,但不是朝鮮人,而是白俄。他和同伴逃離上海,奔向祖國,卻因沒買船票被扣留在青島。如果我們以作者舒群的行跡為參照,可以發現朝鮮少年果里和白俄少年果里的去向恰成反對:前者逃票離開哈爾濱南下,后者用同樣的方式北上,都在相向而行的交匯點青島陷入魔掌。他們的南北殊途源于兩個國家的不同命運,然而他們對祖國的情感卻又十分相似。
小說中一共有四個白俄人物,除了果里和同伴,還有一對由于作奸犯科被投入監獄的白俄夫婦。舒群很善于塑造同一族群中存在差異乃至對立的人物形象,白俄丈夫穆果夫寧便是一例。相對于懵懂地向往祖國的少年們,穆果夫寧對蘇聯抱有頑固而強烈的敵意。他承認普希金是“我們最偉大的文學家”,卻怒斥高爾基為“叛徒”“混蛋”,叮囑果里“你應該記住斯大林是強盜”,并給孩子們講故事,“或是校正他們的思想,阻止他們往祖國去”。[40]單純從左翼角度來看,這樣的白俄無疑是應予批判的反動分子,但小說非但未對穆果夫寧的立場置評,還以敘事者“我”的視角,充滿同情地描繪他的憔悴容顏,呈現他的悲愴歌聲。裊裊哀音,令“我”心有戚戚,“使我記起了一些悲哀的記憶”,以至于常常和穆果夫寧親如舊友般打招呼。考慮到“我”在很大程度上是舒群本人的化身,這里表現出的情感傾向并不尋常。有研究者指出,《無國籍的人們》遵從左翼文學“奔向蘇聯”的敘事模式,卻又不囿于特定階級立場,對白俄群體寄予普遍的同情,這源于舒群背井離鄉、“同為天涯淪落人”的個人經歷以及由此產生的家國情懷。[41]這是較為貼切的分析。需要補充的是,有別于大部分左翼作家,舒群早有與“紅俄”并肩戰斗的切身經驗:
一九二七年,我和哥里沙同學的時候,一面坡的學生,大致分為兩派。一派是:戴著櫻花帽徽的日本學生,戴著大鷹(記不十分清楚了)帽徽的白俄學生,也許還有些教會學校的中國學生,和日本學校的朝鮮學生;另一派是:戴著紅黃藍白黑五角星帽徽的中國學生,戴著鐮刀斧頭帽徽的蘇聯學生,戴著櫻花帽徽的朝鮮學生。在放假的日子,這兩派學生,自然而然地列開由八九人到八九十人的兩條戰線。……一旦開戰,手巾旌旗蔽空,嘴里鑼鼓齊鳴,吶喊助威,殺聲四起,棍子石子,飛來飛去。[42]
在一面坡的各國學生富有象征意味的沖突中,舒群堅定地和蘇聯學生站在一起,與白俄學生為敵。數年后,舒群和朋友傅天飛在哈爾濱觀看關于十月革命的電影《最后的命令》時,紅俄觀眾和白俄觀眾打斗起來,兩人“理所當然地站在紅俄一邊,還負了一點小傷”。[43]對于舒群而言,“擁護蘇聯”并不是教條的組織要求,而是少年時代受惠于蘇聯女教師悉心教導的感恩和景仰使然,因而他早在加入左聯之前就坦然地寫下了《歌頌著莫斯科》等憧憬蘇聯的詩作。但所有這些對于蘇聯的好感和與白俄針鋒相對的記憶,都不曾凝固為臧否人物的刻板標準;相反,舒群在書寫穆夫果寧這個白俄形象時,雖觸及其政治偏見,主要還是視之為類同于果里、貝特以及自我的失落祖國、飄零四方的受苦之人。究其根由,舒群的“認識裝置”是一種既有階級意識、民族自覺而又不失人道本色的國際主義,與殖民和流亡經驗造就的情感結構相結合,乃有創作中放眼四海、感同身受的博大胸襟。
四、結語
規模空前的抗戰既是一場慘烈悲壯的反侵略戰爭,也是廣大中國人民在戰火中冶煉民族國家認同,并進而生發國際意識、與身受法西斯暴虐的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歷史進程。在這一進程中,身處三重邊緣(即身為旗人后裔而處邊緣族群、家境貧寒而處邊緣階層、成長于東北而處邊緣地域)的舒群,對于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侵略,比關內作家更早地產生了切膚之痛和沉郁之思。[44]在這個意義上,“邊緣”并不等同于“落后”,反而因為包容了族裔文化的錯落混雜、承載著多方勢力的明暗競逐、涵育出生命意志的山呼海嘯,而具有更加豐沛的文化政治潛能。

《舒群年譜》,史建國、王科 編著,作家出版社2013-9
舒群既沒有巴金、郭沫若、蔣光慈等人負笈海外的經歷,也不曾像艾蕪那樣遠走異邦,但他的小說卻藉由真實而又廣闊的社會圖景和人物群像,真切自然地實現了人道關懷、民族情結和國際主義的融會貫通,獨具一格,卓然一家。在彰顯不同人物的身份認同時,舒群善于運用國旗等象征符號,而這種創作手法與其情感傾向和斗爭意志一樣,不是理論的驅使和理念的外化,而是來自真實的生活,來自舒群混跡于販夫走卒的童年記憶、求學于紅俄學校的少年往事、游走于冰城街巷的青年身影,來自東北淪亡后舒群身負秘密使命奔走在廣袤的黑土地上的見聞以及周旋于三教九流之間的歷練。四戰之地、歷史巨變所成就的舒群抗戰創作,盡管有些篇章行文簡疏,總體而論修辭特色不夠突出,卻始終充盈著對國家和民族遭際的整體感受和體驗,以及推己及人、心意相通的感喟。王富仁先生在論述東北作家群時認為:“中國新文化、中國新文學現代發展的最主要的表現形式是社會意識、民族意識和人類意識的增強,在整個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在整個社會發展和人類共同命運的基礎上感受人生、表現人生恰恰是中國新文學現代性的主要標志。”[45]據此觀之,舒群不僅可與聲名更盛的幾位東北作家同列,還在書寫人類共同苦難、擁抱世界人民的實踐中,悄然達致甚或超前的文學品格,時值今日對我們的世界認知和想象仍有良多啟發。
注釋:
[1]本文參考的舒群生平材料主要有:史建國、王科編著:《舒群年譜》,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董興泉編:《舒群研究資料》,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方朔:《回憶舒群叔叔的幾段往事》,《文史精華》2013年第10期。
[2]立波:《一九三六年的回顧》,上海《光明》第2卷第2期(1936年12月25日)。
[3]梅雨:《創作月評》,《文學界》創刊號(1936年6月5日);周揚:《關于國防文學:略評徐行先生的國防文學反對論》,《文學界》創刊號(1936年6月5日)。
[4]舒群:《舒群文集》(第二卷),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3年,第48頁。
[5]舒群:《舒群文集》(第一卷),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年,第40頁。
[6]舒群:《舒群集》,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17頁。
[7]舒群:《舒群文集》(第一卷),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年,第22頁。
[8]舒群:《舒群文集》(第一卷),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年,第73頁。
[9]舒群:《舒群文集》(第一卷),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年,第103-104頁。
[10]舒群:《舒群文集》(第一卷),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年,第345-346頁。
[11]舒群:《舒群文集》(第一卷),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年,第348-349頁。
[12]舒群:《舒群文集》(第一卷),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年,第361頁。
[13]Charles Edward Merriam, Political Power: Its Composition and Incidence, New York & London: Whittlesey House, 1934, p. 105. 轉引自小野寺史郎:《國旗·國歌·國慶:近代中國的國族主義與國家象征》,周俊宇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8-9頁。
[14]關于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對五色旗的承繼以及東北民眾為抵抗日本侵略而主動要求易幟的情況,參見小野寺史郎:《國旗·國歌·國慶:近代中國的國族主義與國家象征》,周俊宇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55-177頁。
[15]舒群:《舒群文集》(第一卷),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年,第74頁。
[16]舒群:《舒群文集》(第一卷),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年,第31-32頁
[17]舒群:《舒群文集》(第一卷),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年,第32頁。
[18]舒群:《舒群文集》(第一卷),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年,第38-39頁。
[19]舒群:《舒群文集》(第一卷),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年,第362-363頁。
[20]舒群:《舒群文集》(第一卷),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年,第5頁。
[21]舒群:《舒群文集》(第一卷),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年,第17頁。
[22]舒群:《舒群文集》(第一卷),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年,第21頁。
[23]梅雨:《創作月評》,《文學界》創刊號(1936年6月5日)。
[24]舒群:《我的女教師》,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6頁。當然,我們應注意到1950年代初“中蘇友好”這一寫作背景,但縱觀舒群文學生涯可知,他對蘇聯的敬意是一以貫之的,其作品中的蘇聯人物形象基本都是積極正面的。
[25]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比較的幽靈:民族主義、東南亞與世界》,甘會斌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年,第3頁。
[26]正如柳書琴所言,“每位少年代表的形象,都是集體性的,民族國家式的。他們的身世是民族現況的縮影,年齡與貧富反映著民族國家成立的先后或有無,彼此的互動模式及人際關系則是東北亞現實或未來國際關系的隱喻”。《“滿洲他者”寓言網絡中的新朝鮮人形象:以舒群<沒有祖國的孩子>為中心》,《韓中言語文化研究》第21輯(2009年11月)。
[27]舒群幼子李霄明先生于2018年9月8日接受筆者采訪時認為,舒群曾經就讀的中東鐵路子弟學校,雖然管理人員和教師有蘇聯背景和進步傾向,學生里面卻有不少沙俄時期鐵路員工子弟,情況比較復雜。而且,當時的俄國人瞧不起中國人,這一點并不會因為政權的更迭而發生根本改變。可與李霄明觀點相參照的是,蘇聯因中東鐵路問題與東北當局發生沖突時,曾對部分鐵路員工的沙文主義思想有所檢討并采取相關措施,如教育員工“中東鐵路是中國人的鐵路”,并“解除那些以搞沙文主義而臭名昭著的負責人的職務”。薛銜天、金東吉:《民國時期中蘇關系史:1917-1949》(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第216頁。
[28]柳書琴認為,言說受限的舒群使用了“替身書寫”的策略,通過批判“次要他者”蘇聯人對“底層他者”朝鮮人的輕侮,間接表達了作為“底層他者”鏡像的自我對于“主要他者”日本侵略者的憤怒。因此,少年形象的“片面化”,乃出于“隱喻經營上的必要”。參見柳書琴:《“滿洲他者”寓言網絡中的新朝鮮人形象:以舒群<沒有祖國的孩子>為中心》,《韓中言語文化研究》第21輯(2009年11月)。
[29]千里草、劉鳳艷:《堅實的腳步——論舒群早期的小說創作》,董興泉編:《舒群研究資料》,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第230頁。
[30]舒群:《舒群文集》(第一卷),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年,第8頁。
[31]董興泉:《舒群的革命文藝活動及其創作》,董興泉編:《舒群研究資料》,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第200頁。
[32]舒群:《舒群文集》(第一卷),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年,第122頁。
[33]關于《沒有祖國的孩子》的話劇改編,參見馮昊:《他者視角中的“九一八”國難敘事——〈沒有祖國的孩子〉三個文本的比較研究》,《民族文學研究》2020年第6期。
[34]舒群:《舒群文集》(第二卷),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3年,第45頁。
[35]董興泉編:《舒群研究資料》,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第13頁。
[36]方朔:《回憶舒群叔叔的幾段往事》,《文史精華》2013年第10期。
[37]舒群原注:黑人的總數,約計非美二洲及非洲的雜種,共有一萬二千五百萬。
[38]舒群:《舒群文集》(第一卷),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年,第84-85頁。初刊《今代文藝》1936年第1期,收入《沒有祖國的孩子》(生活書店,1936年)一書時,改為“法國姑娘維兒斯”,《文集》保留了此處改動,今據初刊本和上下文恢復。
[39]舒群:《舒群集》,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48頁。
[40]舒群:《舒群文集》(第一卷),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年,第307-308頁。
[41]楊慧:《隱秘的書寫——1930年代中國東北流亡作家的白俄敘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年第3期。
[42]舒群:《我的女教師》,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3頁。
[43]舒群:《早年的影——憶天飛 念抗聯烈士》,董興泉編:《舒群研究資料》,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第70頁。
[44]汪暉認為,東北作家群的獨特性在于“雙重的邊緣性,即東北在中國文化和區域關系中的邊緣性和被迫失去家鄉而流亡關內的邊緣性”。《竦聽荒雞偏闃寂》,《讀書》2018年第8期。具體來看,舒群出身寒微,家境在東北作家群中幾乎是最差的,而這與其家族早先因滿族身份而流離失所有很大關系,所以舒群的邊緣地位和底層意識尤為突出,成為其創作的底色。據前引筆者對李霄明先生的采訪,舒群對滿族感情深厚,但因民國時期社會對滿人有偏見而刻意淡化和壓制這種感情,直到晚年其民族意識才有所復蘇,但仍很謹慎。這種與創作心態直接相關的隱秘民族身份/認同,在討論舒群作品時不應忽視。例如,小說中“我”的中國姓名的缺失,便和舒群家族在離亂中失落滿姓的往事構成某種微妙的對應。
[45]王富仁:《三十年代左翼文學·東北作家群·端木蕻良(之四)》,《文藝爭鳴》200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