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爾律治試圖幫助華茲華斯寫出對時代更有現實意義的詩歌
一七九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的下午,華茲華斯、多蘿茜和柯爾律治開始了短途的徒步旅行,沿著布里斯托海峽南岸漫步。在這次旅行中,還有隨后的幾個月里,柯爾律治作為詩人面臨的一些心理問題被暫時擱置轉移,或派上不曾預料的絕妙用場。
柯爾律治和華茲華斯此前計劃合寫一首詩賣給某個雜志,用以支付這次旅行的開銷。合作雙方的興趣有了交匯點。這首詩得是一首民謠,是華茲華斯鐘情的簡單而傳統的形式。但是為了取悅柯爾律治,它也要包含探索的主題。關于這點,柯爾律治想到了鄰居約翰·克魯克香克告訴他的一個夢境,有“船的骨架,上面還有一些人”。他也在重新考量社會的棄兒:那些因考慮不周或犯下無心之過的罪人,像流浪的猶太人(the Wandering Jew),相傳耶穌在受難的路上,遭受一位猶太人的嘲弄,于是這位猶太人被詛咒在塵世行走,直到耶穌再次降臨。該傳說從十三世紀開始在歐洲傳播,逐漸有了不同的版本,各版本中猶太人的性格和輕慢行為有所不同,文學作品里比比皆是。他當然對這些人感興趣,但是要想為他們辯護是不可能的,起碼這時不能。“流浪的該隱”該隱(Cain)是《舊約》中亞當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園后生下的兒子,出于嫉妒殺死了弟弟亞伯,因此被上帝流放。社會棄兒的原型,則是更好的主題。罪責是理所當然的,不會涉及任何道德問題。柯爾律治提議以此作為合作的主題,華茲華斯不感興趣。他自己靜心一想也索然無味。這個主題能寫出什么呢?該隱確實犯有謀殺罪。減輕罪行的戲劇是不可能的,至少對于柯爾律治來說不行,盡管后來拜倫能夠寫出。他們一笑了之,放棄了這個主題。然而華茲華斯當時在讀謝爾沃克的《航行記》——喬治·謝爾沃克(George Shelvocke, 1675—1742),曾是英國皇家海軍軍官,在1723年根據自己的經歷寫了一部《經由大南海環球航行記》(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by Way of the Great South Sea),書中提及他的一位船長在南美洲南端的合恩角附近射殺了一只信天翁,里面提到信天翁是一種能帶來好運的大鳥,能從南極飛來停在船上;有個人殺死了一只信天翁,從而招致了這地區守護神的報復。
他們一起沿著海岸漫步時,想出了關于民謠的計劃,如能完成便可連同華茲華斯的其他詩歌一起發表(這對柯爾律治而言既是保證又是激勵)。柯爾律治對這個想法興趣濃厚,想象豐饒。華茲華斯后來說,他覺得自己要是貢獻部分詩句會顯得冒昧唐突,索性退出“一項我只能成為累贅的任務”。他們結束旅行回到家時,柯爾律治對這主題更加癡迷。他感覺華茲華斯和多蘿茜的眼睛都在盯著他,便持續寫作了幾周,專心致志的程度在他的作家生涯里堪稱罕見。這種專心直到二十年后才再次出現——他在絕望之中逼迫自己寫出了《文學生涯》。
柯爾律治這次的處境,以其特有的方式似曾相識,總體而言又絕然不同:與他以往的寫作方式不同,與他通常認為自己該用的方式不同,也與華茲華斯不同。他發現自己在寫詩方面完全無法和華茲華斯媲美,這也帶來一種樂趣: 詩歌這塊天地就可以完全交由華茲華斯,柯爾律治只在一旁充當哲學助手和總體的勉勵者。他想幫助鼓勵華茲華斯寫出對時代更有現實意義的詩歌:這種詩使用通俗的語言,熟悉的形象和質樸的情感,深思而熟慮(與柯爾律治的沖動不同),而且最重要的是(這里柯爾律治感到自己最欠缺的)結合了道德端正和個體自信。
柯爾律治鼓勵華茲華斯,幫助他找到進一步澄清自我的理由,也為他們之間著名的分工奠定了基礎——他自己將扮演次要角色。結果是柯爾律治寫出了《老舟子吟》《克麗斯特貝爾》和《忽必烈汗》,它們的主題、旨趣、風格乃至整體構思,幾乎都是華茲華斯的對立面,也與他自己此前的詩風迥異。如果說柯爾律治急于扮演次要或者更專業的搭檔,似乎為自身制造了局限,但同時對他也是真正的松綁。他天性易被泛濫的同情所累,在相互沖突的抉擇面前容易猶豫不決。對于這樣的個性,任何形式的局限都有一種優勢。這種特殊形式的局限成果尤其斐然,哪怕只是短期效應。醞釀每行詩時,不用顧忌道德或宗教審查,技術性要求(有關情節、氣氛、主旨、韻律)變得至關重要。他習慣要去證明作者的個人善意,這點即便沒被麻痹,也變得明顯無關,直至他寫到《克麗斯特貝爾》中途。
如果說他拋開了一度如影相隨的些許拘謹,部分是因為他尋求道德基礎的過程中出現了心理轉換。仁慈的姿態不必用力寫進詩里,現在能以另一種形式出現:柯爾律治通過抹殺自我、提供專業而有限的幫助,協助一位受尊敬的朋友。此外還有新奇的誘惑,他發現自己寫作《老舟子吟》進展迅速,然后一鼓作氣開始了《克麗斯特貝爾》。他得以宣泄,也是因為這種新穎、專業的模式刻意疏離而具象征性。柯爾律治為百年之后的詩人示范了象征如何能帶來釋放感。在此過程中,他動用了分量驚人的內在儲備。他突然獲得了表達能力,詞語和意象凝練雋永,富有樂感,這些使他如今能夠躋身主要英國詩人之列。
這時發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暗示柯爾律治的創作能量如何被長期壓抑,他的其他詩歌也未能將其釋放。他的閱讀量無與倫比,只有一小部分被發掘并充分利用(我們談到他的閱讀時要記住,他此時不過二十幾歲,年近三十)。對這個主題的詳細闡釋要看最偉大的文學偵探研究,約翰·列文斯頓·洛斯的《仙那度之路》(1927),洛斯主要關注的是《老舟子吟》和《忽必烈汗》。亞瑟·H.內瑟科特在《特里耶梅因之路》中用同樣的方法分析了《克麗斯特貝爾》,它堪稱文學研究的一座豐碑。在長度相當的任何其他詩作中,人們從未發現如此廣泛的閱讀被突然釋放。在完成《仙那度之路》之前的十五年和之后的二十年,洛斯試圖以同樣的手法分析其他詩人(他自己的閱讀在二十世紀也是無與倫比,涵蓋了自希臘和希伯來以來的所有主要文學)。但是這位最偉大的文學偵探經常承認,他找不到類似的例子。《仙那度之路》出版四十年來學者們的集體努力也證明了這點。艾略特的《荒原》偶爾被提起作為有趣的參照,但是并無真正可比性,因為那里使用的文學呼應和典故是刻意的手段。只憑這點而言,柯爾律治的這三首詩也堪稱奇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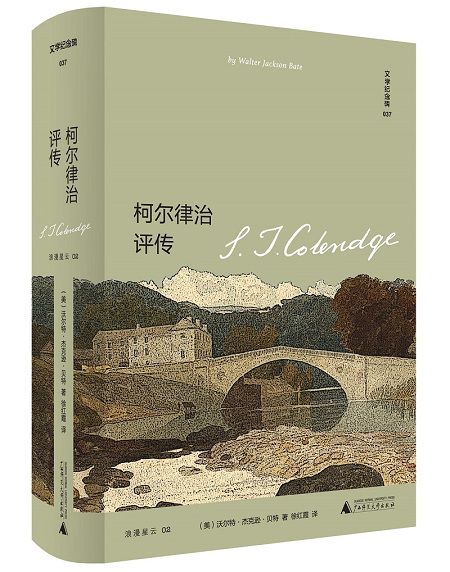
《柯爾律治評傳》,[美]沃爾特·杰克遜·貝特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0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