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與石黑一雄在小說中對日本侵華戰爭的反思
石黑一雄在《浮世畫家》中講述過這么一件事:二戰結束后,一家日本公司的總裁自殺謝罪,敘述者“我”和朋友三宅就此事討論起來。三宅說:“我們總裁似乎覺得要為我們在戰爭中所做的一些事情負責。兩個元老已經被美國人開除了,但總裁顯然覺得這還不夠。他的行動是代表我們向戰爭中遇害的家庭謝罪。”
因為總裁的自殺,“公司上下如釋重負。”他們“現在覺得可以忘記過去的罪行,展望未來了。”諷刺的是,“有許多應該以死謝罪的人卻貪生怕死,不敢面對自己的責任。結果反倒是我們總裁那樣的人慨然赴死。許多人又恢復到他們在戰爭中的位置。其中一些比戰爭罪犯好不了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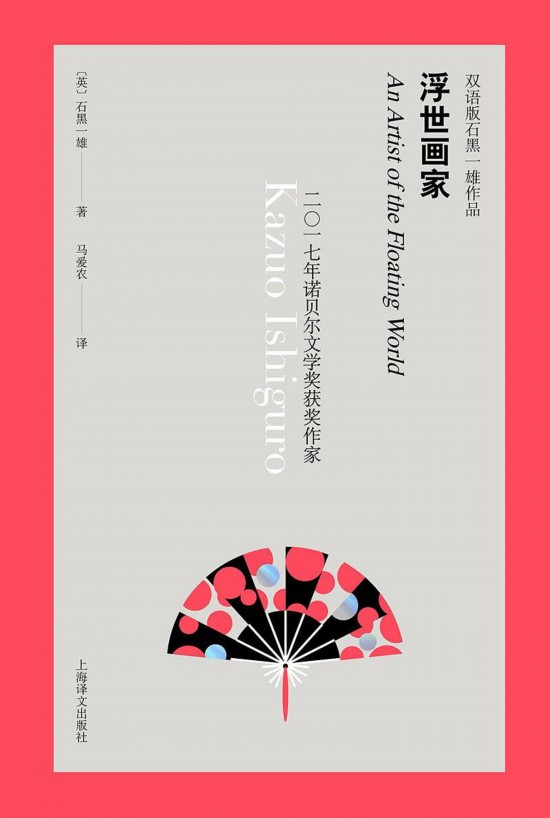
這是一個曖昧的悲劇。試想一下,當總裁自殺的消息傳出后,公司的其他高管和員工是什么心情呢?悲傷是表層,但透過石黑一雄的敘述,悲傷里還有一絲慶幸,因為在他們眼里:總裁的死猶如一個象征,是集體對過去罪行的交代。好像總裁一死,集體的罪責就洗清似的,其他人都能因此赦免,面向未來。如此就出現了一種心理——參與到戰爭的人們倘若失敗,就希望有人代表他們去死。而他們將很樂意地進行哀悼。那么,這種懺悔是否嚴肅呢?其中是否存在偽善、僥幸的成分?
恐怕,追問其是否嚴肅是自討苦吃,馬克思在《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中指出:“嚴肅是肉體為掩蓋靈魂缺陷而做出的一種虛偽姿態。如果嚴肅不應當適合這個定義,如果嚴肅的意思應當是注重實際的嚴肅態度,那么這整個規定就會失去意義。因為我把可笑的事物看成是可笑的,這就是對它采取嚴肅的態度;對不謙遜仍然采取謙遜的態度,這也就是精神的最大的不謙遜。”在馬克思看來,與其嚴肅,不如“認真”,不必強調一個人的言行舉止是嚴肅還是輕薄,應當直擊它的實質,那個真的部分。是什么,便指出什么。而在《浮世畫家》所描繪的這個場景中,與其說公司的領導、員工們深感自己在戰爭中負的責任,不如說他們希望有一個象征物,好讓自己與過去劃清界限,從殘酷真實的歷史中脫逃,好活在自己的安穩之中。顯然,總裁之死成為了這個象征物。真正懺悔的人死了,歷史依然被生者規避。
在《浮世畫家》中,這樣的懺悔并不少見,這是一本直面二戰創傷的小說,石黑一雄在小說里主要處理兩個問題:經歷且參與二戰的人該如何自處;戰后的日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第一個問題反映在主人公小野身上。他在戰時通過作畫推崇軍國主義,成為社會紅人。戰后卻因軍國主義的清算浪潮而倍感自責。他曾相信自己的國家做著正確的事,而他作為國家一員,理所應當為國家盡自己的一份力,但戰爭的失敗和日本政府所犯下的累累罪行讓他無法視而不見,這一矛盾成為小說的張力來源之一,而石黑一雄在日后也重復了這種“荒謬”,《長日留痕》中的英國管家就是例子。1949年,當小野先生拜訪故人佐藤博士時,他說:“當時我是憑著堅定的信念做事的。我滿心相信我是在為我的同胞們謀福利。可是您看到了,我現在坦然承認我錯了。 ”
而第二個問題則貫穿整部小說。宮本武藏、美國的牛仔、烏龜象征著不同的價值選擇,畫家小野在與朋友松田的對話中,也在思索這個問題。松田說:“事實上,在這樣的時期,當周圍人民越來越窮,孩子們越來越饑餓、病弱,一個畫家躲在象牙塔里精益求精地畫藝伎是遠遠不夠的。我們落在貪婪的商人和軟弱的政客手上,這樣的人會讓貧困日益加劇。除非,我們新生的一代采取行動。但我不是政治家,我關心的是藝術,是你這樣的畫家。有才華的畫家,還沒有被你那個封閉的小世界永遠地蒙蔽雙眼。”
無獨有偶,在村上春樹的小說《刺殺騎士團長》中,戰后成長的主人公同樣對二戰進行了追溯。村上春樹以畫、洞穴、騎士團長為線索,展現出一位老年畫家與記憶傷痕的博弈。懺悔再次成為重點所在。
《刺殺騎士團長》的故事可以這樣梗概:主人公“我”是一位36歲的職業肖像畫家,他遭遇婚姻危機,心情低落之下決定離家出走,寄居好友父親的老宅,也就是《刺殺騎士團長》作者雨田具彥的舊畫室。主人公后來發現這部畫作,繼而遭遇一系列撲朔迷離的事件,神奇地進入洞穴,在歷史、現實與幻境之間,回顧了自己和畫家生命中的重要事件,進行了一次意念上的時空穿梭,最終實現精神救贖。
在這一連串事件中,圍繞著“老畫家”的故事尤其值得注意。“老畫家”的故事集中出現在小說第二部分,騎士團長告訴“我”:老畫家的一個弟弟曾參與中日戰爭,他曾被迫砍掉三名俘虜的腦袋,這讓他從戰線撤回國內后卻羞愧自殺。而老畫家則在維也納參加過一次針對納粹的暗殺行動,畫中的騎士團長,原型可能正是這次行動中的某位納粹軍官。通過老畫家之子的描述,我們發現:老畫家是一個把自由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人,他同法西斯和軍國主義格格不入。老畫家一直因為弟弟因戰爭中的死亡而耿耿于懷,更為自己的茍且偷生感到內疚,他一生最后的心愿,就是再現“刺殺騎士團長”的場景,彌補他沒有刺死那位納粹軍官的遺憾。他將自己無法完成的刺殺納粹軍官的心愿寄托在畫里,將自己生命的救贖托付于“刺殺騎士團長”這一行動。
因此,我們就不難理解小說為何夾雜了對“南京大屠殺”的討論。盡管南京大屠殺的部分在小說中只占十幾頁的篇幅,但這部分內容絕非可有可無。村上春樹借人物之口問的:“有人說中國人死亡數字是四十萬,有人說是十萬。可是四十萬人和十萬人的區別到底在哪里呢?”這句話直指日本右翼政府的軟肋,后者一直有意在報告中減少南京大屠殺的傷亡數字,可是,即便是死10萬人,難得就不是屠殺了么?他們犯下的罪行就可以被諒解嗎?顯然,日本當局的說辭經不起推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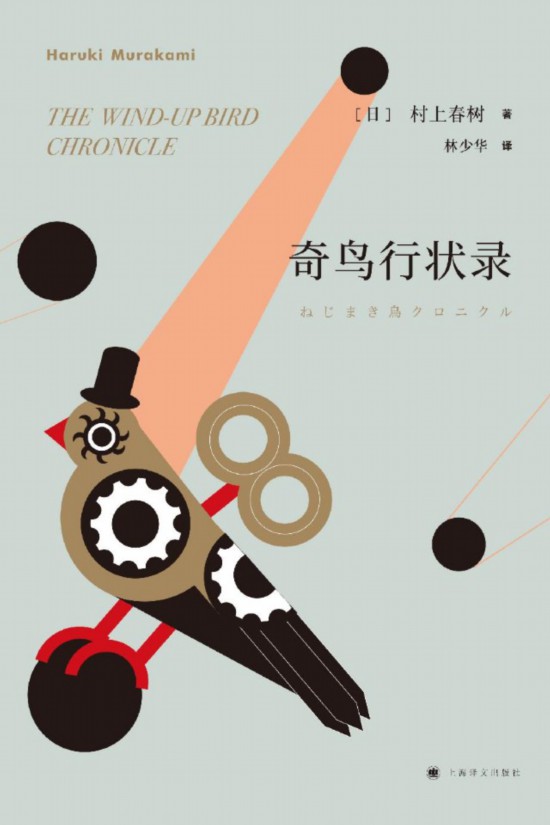
村上春樹是一位堅定的反戰派,從《奇鳥行狀錄》到《刺殺騎士團長》,他都對日本右翼以正義之名發起的戰爭展開過批評。在《刺殺騎士團長》中,村上借戰后成長的主人公對老年畫家的追尋,揭開了二戰對個體及民族造成的心靈負擔。和藝術家宮崎駿類似,村上并沒有回避自己的國家在歷史上的污點記錄,他在作品中主動“舊事重提”,為的不只是和部分日本人的虛無史觀作斗爭,也是要追溯日本人近代以來的精神史。從昭和男兒的熱血沸騰,到太陽族的反叛傳統,再到九十年代經濟危機后相對平緩的“低欲望社會”,大和民族的狀態變化絕非一日而就,其背后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村上寫過去,也是在和今天做比較,低欲望的、輕飄飄的新日本世代常常被人批判,可是那個熱血沸騰的日本,真的就值得舊夢重溫嗎?村上警惕的是:在那片熱血之中,翻滾的往往是不可遏制的民族主義之血。
所以在長篇散文《扔貓,關于父親我想說的話》中,村上再度提起侵華舊事,通過書寫父親如何被強征入伍、參與中日戰爭,表現出戰爭對個體造成的不可磨滅的創傷。文中提及,“我”的父親被分配到福知山步兵第二十連隊,“作為輜重兵,被這樣送到了血雨腥風的中國大陸戰場”,“這個時候,在中國大陸,殺人的事情被認為是習以為常的,命令新兵和預備兵去處死抓捕的中國士兵非常常見……殺害毫無抵抗能力的俘虜,當然是違反國際法和不人道的行為。可是,在當時的日本軍隊中根本沒有人對此有所考慮。父親說,從1938年開始到1939年,作為新兵的自己剛剛來到中國大陸,一個下級士兵即使被強迫做很多殺害俘虜的行為,也完全不是奇怪的事。父親后來回憶說,士兵開始是用槍上的刺刀殺死俘虜,后來是用軍刀殘殺。”(村上春樹:《扔貓,關于父親我想說的話》)
村上的父親曾切身感受到戰爭的殘酷,在村上的童年里,父親經常去參拜佛像,面對一個小玻璃盒子念經,“他說,你知道我是為了誰念經么?我是為了很多此前戰爭中的死難者。這些在戰爭中死去的人是的我的戰友,還有作為‘敵方’死去的中國士兵”。村上坦言:“用軍刀砍掉人腦袋的殘忍情景毫無疑問強烈刺痛了我幼小的心靈。”
通過這篇文章,村上重申了自己的反戰立場。更進一步,他希望探討在戰爭年代,國家機器如何煽動意識形態,并采用強制手段造就一幕幕殺戮,使民眾成為冰冷的殺人工具。當悲劇發生后,當事人試圖通過曖昧的態度來逃避歷史責任,以看似中立的觀點模糊是非,但恰恰是這種曖昧,導致暴行的重復成為可能。
相比起村上,石黑一雄在《浮世畫家》里對二戰時期的日本軍政府進行了更為辛辣的諷刺,這在小說人物池田的話里可見一斑。池田說:“壯烈犧牲似乎沒完沒了……我們中學同年畢業的半數同學都壯烈犧牲了。都是為了愚蠢的事業,但他們永遠不會知道這點。”“當初派健二他們去英勇赴死的那些人,如今在哪里呢?他們照樣活得好好的,跟以前沒什么兩樣。許多人在美國人面前表現乖巧,甚至比以前更得意,但實際上就是他們把我們引入了災難。到頭來,我們還要為健二他們傷心。我就是為此感到生氣。勇敢的青年為愚蠢的事業丟掉性命,真正的罪犯卻仍然活在我們中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