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與史料——論現代文學出版史研究
中國現代出版以1843年墨海書館采用鉛印設備發端,現代文學遲至1915年《青年雜志》創刊起源,二者之間有著長達70余年的時差,但彼此之間相互選擇,相互影響,甚至存在著以自身力量改變對方演進軌跡的共振關系。因此,從文學史研究角度梳理、檢討并展望出版史研究的發展系譜具有了正當性。我認為,此研究譜系的關鍵詞經歷了從“啟蒙”到“生意”的轉變,如今二者合流已蔚為風潮,而為了突破高度范式化所隱藏的危機,走到了應重新整合“政治”的路口。另一方面,史料作為推動研究轉型的動力之一,它的運用與解讀同樣引發了闡釋話語的重心調整,史料及其引發的問題亦值得爬梳。
自1990年代起,隨著對“純文學”觀念的祛魅,愈來愈多研究者從非文學的外部因素入手解讀現代文學。在這一根本性的轉向里,王曉明、陳思和與錢理群三位學者先后撰文為現代文學出版史研究確立基調。

《青年雜志》
1991年,王曉明發表《一份雜志和一個“社團”——論“五·四”文學傳統》,指出“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不但注意到‘五·四’那一代作家的創作,更注意到“五·四”時期的報刊雜志和文學社團,注意到由它們所共同構成的文學運行機制,注意到與這個機制共生的一系列無形的文學規范,……如果把這一切都看成“五·四”文學傳統的組成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文學史就會出現新的解釋[1]。1993年,陳思和發表《試論現代出版與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提出“現代出版業已經成為知識分子以思想文化為陣地,實現自身價值的重要途徑。”[2]。在王曉明、陳思和方向性的主張后,錢理群將之具體化。1996年,錢理群發表《我所設想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大綱》[3],提出應該運用文學社會學的方法,“有計劃地逐步開展20世紀文學市場的研究,推出一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出版文化叢書》。第一批研究對象確定為商務印書館(含其主辦雜志,下同),泰東書局,北新書局,開明書店,現代書局,良友圖書出版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等。”[4]
仔細辨析,三位的設想之間略有差異,王曉明意在文化生產體制的追問,陳思和指向知識分子崗位意識思索,錢理群的目標是審視文學的現代化。不過更值得重視的是他們之間的共性,20世紀80年代思想解放的勢能遭遇挫折,1990年代開始面對市場化的挑戰,作為回應,王曉明、陳思和兩位于1993年發起了著名的“人文精神大討論”。與之互為表里,他們擬想的計劃是為大寫的“文學”服務,內核則在顯影“文化啟蒙主義”。
以此為起點,涌現了一大批開創性成果。其中,劉納的《創造社與泰東圖書局》、楊揚的《商務印書館:民間出版業的興衰》與葉彤的碩士學位論文《新文學傳播中的開明書店》[5]堪稱典范。
劉納在《創造社與泰東圖書局》的“前言”中坦陳:“我從王曉明的《一份雜志和一個社團——重識“五四”文學傳統》得到很多啟發。”[6]她視出版機構是造就文學界“勢力”之一種,以極具藝術感的筆觸描述了創造社與泰東圖書局之間的關系演變史。劉著呈現給讀者的不是作家與出版商之間親密無間的合作,而是充滿了彼此算計的相互妥協,文學史現象也不再是審美的表述,而是各方人士的利益角力。稍顯遺憾的是,劉著偏重創造社,史料大多來自創造社諸君的回憶及作品,致使泰東圖書局淪為負面色彩的配角。這與彼時史料不健全有相當關系,根本原因是文學的外部研究,始終是“文學的”外部研究,研究者心存文學與出版的主從關系執念。
楊揚的《商務印書館:民間出版業的興衰》,本書是國內較早的以出版社史為目標的研究著作。本書的特點在于以“民間”為線,刪繁就簡,通過還原各時期代表性事件,為讀者敘述商務印書館1949年前的風雨歷程。正如陳思和的評價:“完整地描述了商務印書館在20世紀上半葉的興衰史,同時也折射了現代知識分子如何從廟堂里的士大夫群中走出來,在民間確定了新的工作崗位和價值崗位。”[7]需要指出的是,“民間”提供了一條清晰的脈絡,但過于理想的劃分,使得本書筆墨集中于以張元濟、王云五為代表的商務高層,既沒有關注外界風云變幻,也沒有注目普通商務員工,這本書敘寫的商務史僅僅是高層史,且只能到1949年為止,因為“民間”的單一視角無法為商務印書館1949年后的巨變提供解釋。
葉彤的學位論文由錢理群指導,文章論證了開明書店以青年為目標讀者群,通過教材出版將新文學運動的實績點滴滲透給下一代,為新文學培養了大批合格的鑒賞者和后來者,書店自身也成為新文學傳播的主要力量[8]。本文觀點新穎,考梳精彩,啟發了相當一批后繼者。如今看來,不足之處在于論點略顯拔高。首先,選編新文學作品入教材,不止于開明書店,而是新文化成為主導話語后,各家出版社都予以執行的共識。其次,對編輯而言,編選作品是為國文教學服務,夏丏尊、葉圣陶在《文心》中借人物王先生之口說出如下觀點:“國文教材應該是‘歷代文學作品選粹’一類的東西。”[9]意即教材中的白話文與語體文二者之間并不存在特別的價值高低。最后,在民國時期,教科書業務是綜合出版社的主要經濟支柱,開明書店創辦人章錫琛說過教科書“做一季,吃半年”[10],因此拋開經濟因素談教科書存在片面性。

開明書店
此時期成果價值不可否認,必須看到它們的目的都是以“出版”來求證“文學”,“出版”自身的復雜面相未得到有效展現,更可惜的是,它們都默認并共享了文學啟蒙的預設,對其缺少應有的警醒,以致在某些“啟蒙”被過度消耗的論著中,出現了研究對象雖有不同,但框架相似、邏輯一致、結論無異的高度同質化現象。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起,中國社會進入全面市場化的結構轉型,知識分子亦有自己的因應。“思想淡出,學問凸顯”,人文學術逐步與宏大敘事脫嵌,專業研究更強調自身的主體性。對出版史研究而言,還有一個刺激性因素是美國歷史學家羅伯特·達恩頓《啟蒙運動的生意》的出版。方法論上,達恩頓基于瑞士納沙泰爾印刷公司的50000封信,輔之以其他文獻,采用歷史敘事與分析行為模式并重的形式,實現“英國的經驗主義和法國對寬廣的社會史的關注結合”,他“通過追蹤一部書(即狄德羅的《百科全書》——引者注)的生命周期揭示啟蒙運動的出版方式”,得出結論“啟蒙運動存在于別處。它首先存在于哲學家的沉思中,其次則存在于出版商的投機中”[11],《啟蒙運動的生意》為重新思考出版與文化的關系指明了新方向。綜上,此時期文學出版史研究開始了立足于“出版”的研究,討論“出版”如何“生意”成為了重要的突破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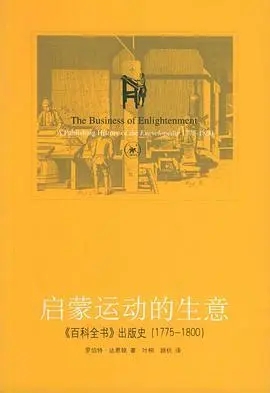
《啟蒙運動的生意》
在諸多著述中,有三本值得一提。李家駒在《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一書中,采用專題的形式,論析出版社在文化實體與出版企業之間的張力與平衡[12]。李著超越一般出版社研究流于空疏思想撰述的地方在于,作者任職于商務印書館,他充分利用出版社各種檔案,特別是《百年書目》光碟來進行多重檢索、排列和統,繪制出版社的經濟數據——如其在第四章“書籍出版:商務產量統計”和第五章“迎合與塑造:近代圖書市場”中呈現給讀者的,通過詳實數字揭示了商務印書館作為贏利性出版企業的面目。
與李著的深描不同,劉震的《左翼文學運動的興起與上海新書業(1928—1930)》,通過考察“革命文學”論爭引發的“報刊之戰”以及早期普羅小說的暢銷流行,論證“左翼文學運動的興起在它成為一個文學現象之前,也可以說首先是個出版現象。”[13]賦予“出版”更為主動的位置,顛倒了傳統的文學與出版二元關系認識裝置。
王飛仙的《期刊、出版與社會文化變遷——五四前后的商務印書館與〈學生雜志〉》,此書“研究期刊、出版、言論以及五四前后社會文化變遷間,密切而復雜的關系”,“注意商務的營利取向對《學生雜志》傳播的新文化所發生的影響”,其論點在第二章“商務投入‘新文化’市場”和第三章“作為商品的‘新文化’”中得到了闡釋[14]。略顯遺憾的是,由于作者掌握的史料不足,其余各章仍依期刊編輯思想史及欄目考察的循規設計。
以“啟蒙”與“生意”為關鍵詞的兩種研究思路存在內部差異,具有理論敏感度的學者彌合了不同范式之間的縫隙。2000年以后,布迪厄的書籍在國內得到大力譯介, 其理論體系中的習性、資本、場域三個基本概念——特別是從資本細分的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為“啟蒙”與“生意”之間的通約打開了空間[15]。荷蘭學者賀麥曉最早將布迪厄的理論運用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他1996年在《讀書》發表《布狄厄的文學社會學思想》。1998年又在《學人》發表《二十年代中國“文學場”》,運用布氏理論解析二十年代中國文學場,并提出中國文學中的集體性、師生關系無法為該理論所涵蓋[16]。專著《文體問題:現代中國的文學社團和文學雜志(1911—1937)》于2016年正式翻譯為中文,賀麥曉借鑒布迪厄的文學場理論,并復雜化“文體”的內涵與外延—“不僅僅是語言,形式和內容的聚合物,而且也是生活方式、組織方式(像在社團中)和發表方式(像在雜志中)的聚合物”—替代了布迪厄的“習性”,為讀者描繪了1911—1937年復雜多元的文學生態地圖[17]。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于2003年引入到國內,該書對“出版”有極高的重視,“印刷資本主義使得迅速增加的越來越多的人得以用深刻的新方式對他們自身進行思考,并將他們自身與他人關聯起來。”進而“資本主義、印刷科技與人類語言宿命的多樣性這三者的重合,使得一個新形式的想象的共同體成為可能”[18]。其理論在日本學者藤井省三《魯迅〈故鄉〉閱讀史》中得到精彩運用,該書2002年翻譯出版,在國內引起了廣泛討論。作為閱讀史研究的典范,《魯迅〈故鄉〉閱讀史》在分析北洋政府、南京國民政府、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期四個時段均質化讀者群的形成問題上用力尤勤,豐富了文學出版史研究[19]。
在國內,姜濤的《“新詩集”與中國新詩的發生》極為突出。該書對“新詩集”的出版、流布和閱讀狀態做出了富有說服力的歷史描述,在此基礎上討論了在新的傳播空間,新詩的功能、形象與讀者的關系、新詩場域的構成以及相應的閱讀程式的塑造[20],《“新詩集”與中國新詩的發生》是由出版討論文學問題的創獲。
“啟蒙”與“生意”作為“告別革命”的演繹,如今已是絕大多數學人之間的公約數,展望未來的文學出版史研究,激活“政治”的語義分析能量——“政治”可以為“革命”或“戰爭”同義替換——是可以預見的趨勢。不可否認“去政治化”研究思路的貢獻,但2010年前后,面對中國社會急劇轉型所帶來的陣痛,過于自足的研究越益暴露其不及物性和缺少現實對話能力,已引發了新生代學人的反省,正視并重新錨定“政治”在中國歷史中應有的坐標,成為了人文學科不約而同的新動向,文學出版史研究不能亦無法自外于此。
首先,“政治”,作為20世紀中國的底色,形塑了知識分子的情感結構,因此只有從“政治”出發才能深刻把握與分析中國知識分子的內在特征與外顯行為。不過,作為前提的是,這不是簡單地回歸到以“政治”為唯一面相的比附研究,即它并不是1949-1970年代主流階級政治話語的復歸,這里的“政治”已同“文化”“心理”“身份”“社會”“制度”等構成互文空間,自身的內涵與外延都極大拓展,更具包容度。
其次,出版人的制度想象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安排。中國出版人有基于自身經驗而萌生的現代規劃,陸費逵分析過彼時出版業的弊病所在:“我國習慣,對于出版業和印刷業,向來界限不分。”[21]對此,夏丏尊提出設立聯合書店統籌發行,各出版社專營出版的“新途徑”[22],胡愈之更有“出版”“印刷”“發行”三者分立的類似表達[23],他們所提構想雖然略顯粗略,但當他們寶貴的本土思考為中國共產黨所吸納,將其與蘇聯模式相融合,就發展出了1949年后的中國現代出版體制。基于上述歷史事實,需要作出合理的解釋。
最后,“政治”應作為搭建出版史研究的基石之一。以五四后興起的以發行新文學新文化新思想書籍為目的“新書業”為例,其公會宣言首段如下:
自五四運動以來,我國文化驟更一新面目。一般學子之知識欲,突焉亢進。顧以國內出版界之幼稚,與出版物之稀少,致識者咸報知識饑荒之嘆。邇者國民革命成功,政府對于促進文化,不遺余力,一般社會,遂群知出版事業關系文化前途之重要。多數著作家,感于時代之需求,往往投身出版界,努力于出版事業之經營。
由其描述中“文化”“革命”“經營”用詞的關聯可見,“新書業”既是“啟蒙”的,亦是“政治”的,還是“生意”的。質言之,只有統攝“啟蒙”“生意”“政治”三位于一體,才能明辨中國現代文學出版史的內在理路。
總之,正如林春的分析:“中國革命之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方案可以在社會(主義)——國家民族——發展框架中來分析。這一框架在根本上既解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凝聚力和政治共識的維持,也解釋了其斷裂。民族主義意味著國家統一、主權完整、獨立自主,社會主義代表著平等和社會正義,發展主義意味著對于落后的克服——對應著國家尊嚴、社會主義雄心和經濟動力。”[25]作為知識分子的中國出版人,1949年后絕大多數選擇留在大陸,投入新型國家的建設之中,根源是他們的國族觀念、現代想象、行業規劃高度內在于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方案,這體現了從文化認同到政治認同的接榫,因此討論“政治”是中國現代出版史研究的必然之義。
必須承認,現今僅有為數不多的年輕學人于此進行嘗試。青年學者范雪的博士論文圍繞延安的文學和出版展開,重構了1949年后建立的文學生產體制前史。在她業已發表的以生活書店為對象的《出版延安的“知識”與“政治”——延安與生活書店的戰時交往史》與《抗戰時期生活書店的制度選擇》兩文中,拋棄了舊有的預設,細致地論析了抗戰時期生活書店與中國共產黨各種層面的互動,為學界深入討論提供了有力個案[26]。
自1990年起,大量出版史料得到系統整理與出版,對史料的類型側重和意義解讀,與關鍵詞位移合力促成了范式更替。在史料日益豐富之際,有兩個方面必須予以注意:一是史料的等級序列,一是史料的效用界限。
不同類型的史料之間存在等級[27],此處的等級是就可信度而言。法國歷史學家馬克·布洛克把史料區分為兩類,一類是有意留下的敘述性資料,一類是非刻意留下的文獻,前者“是唯一能夠提供具有一定連續性的時代框架的史料”,而后者因能“彌補敘述資料的空缺,或者來檢驗后者的真實性;它還可使我們的研究遠離比無知或不確定更為致命的危險:這就是不可救藥的僵硬化的危險。”所以“歷史研究在其發展過程中給予了越來越多的信任。”[28]照此論述,回憶錄、新聞、廣告、書信、日記、檔案等存在相應等級,在征引時應有所區別。要強調的是,基于主觀性程度的分類只是較為粗略的做法,每種史料都有其特殊的位置,理想的研究狀態應該是盡可能多地占用不同類型的史料,在眾聲喧嘩中拼貼出歷史的斑斕色彩。
與等級互為因果的是史料的效用界限,即必須留意史料的適用性。如出版人的回憶錄日記書信,它們為研究者提供了觀察出版社運營非常重要的內部上層視角,但執筆人的立場與情感,要求我們在參引時必須有所甄別。相比于主觀性較強的書信日記,看似客觀記錄的出版社文檔、政府部門解密檔案等史料更需保持警惕。
我曾整理發表了《開明書店1938—1952年版稅版權表》,此表為細察民國出版實況提供了證據,但不能僅憑表中數字來簡單反推彼時作家實際的稿酬收益,以此論證作家的經濟境況。試以作家沈從文為例,《開明書店1938—1952年版稅版權表》登記有他的兩本書,分別為1940年11月25日簽訂的《沈從文著作集》和1948年3月27日簽訂的《長河》,兩書都是15%的版稅,作家待遇維持不變,但如果將物價更迭、幣值變化、乃至簽約與支付的時間差等外在因素納入在內,實際作家收入不升反降。只有在這樣的對照下,才能理解沈從文對此的抱怨:
今年,開明書店才結算版稅給我,我拿的是法幣三百六十元,因為是照偽幣計算的。算起來要十八年的版稅才能買自己著的一本書,有人說章錫琛的對付著作者的手段太毒辣了,戰時開明書店總店是開設于大后方的,并不是售的偽幣,上海書店雖然是售的偽幣,那不過一部分吧了,何以要照偽幣折算呢?總之,章氏著作家而一為商人,精括至此,當然是商人本色,但這些我也不在乎,只要我的書出在那兒有讀者就行了。
政策文件的使用同樣需謹慎。在文學研究界,洪子誠最早提出了系統研究“文學體制”的設想,他以“一體化”概念來定義50—70年代文學的生產方式與組織方式,認為其時“存在一個高度組織化的文學世界。對文學生產的各個環節加以統一的規范、管理,是國家這一時期思想文化治理的自覺制度,并產生了客觀的成效。”[30]后起不少學者承繼此史觀而展開相應探討,其中包括不少對1949后私營出版業改造、新型國有出版社建立的考察。但此類撰述中,存在機械理解“一體化”,過于強調制度與政策的剛性,忽略了其中人情倫理的差異空間,導致把繁復的進程簡單化,輕易地得出研究結論的情況。因此,“一體化”固然起源于政策文件的頒布實施,但探查著力點不應只停留在政策細則本身,同樣要考證在個案落實過程中所存在的不同位差。
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提出“史學之進步有兩特征”,即“客觀的資料之整理”與“主觀的觀念之革新”,陳寅恪亦有類似表述:“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究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32]“啟蒙”“生意”“政治”作為文學出版史研究的三個關鍵詞,它們之間并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其中有替代、往復、交疊。史料的發掘與使用亦復如此。從學術史的角度看,二者背后折射了不同代際學人的成長。在終極意義上,文學出版史研究,既不能僅僅是“文學”的,也不全然是“出版”的,應該成為超越專業畛域的視野,燭照出不同學科之間的盲區,以精細地描繪歷史跳動的節奏。
注釋:
[1]王曉明:《一份雜志和一個“社團”——論“五·四”文學傳統》,《今天》,1991年第3—4期。后以《一份雜志和一個“社團”——重識“五·四”文學傳統》為名刪改發表于《上海文學》1993年第4期。
[2]陳思和:《試論現代出版與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復旦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
[3]《我所設想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大綱》發表于《河北師范學院學報》1996年第3期,后以《我的中國現代文學大綱》為名,以更為詳盡的篇幅發表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7年第1期。
[4]錢理群:《我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大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7年第1期。
[5]碩士論文以同名摘要發表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9年第1期,署名“葉桐”。
[6]劉納:《前言》,見《創造社與泰東圖書局》,廣西: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頁。
[7]陳思和:《序》,見楊揚:《商務印書館:民間出版業的興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頁。
[8]葉桐:《新文學傳播中的開明書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9年第1期。
[9]夏丏尊、葉圣陶:《文心(讀寫的故事)》,《中學生》第38號,1933年10月1日。
[10]章錫琛:《教科書與開明書店》,《開明通訊》,1950年第1期。
[11](美)羅伯特·達恩頓:《啟蒙運動的生意》,葉桐,顧杭譯,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第1頁,第3頁。
[12]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
[13]劉震:《左翼文學運動的興起與上海新書業(1928—1930)》,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第9頁。
[4]王飛仙:《期刊、出版與文化變遷——五四前后的商務印書館與〈學生雜志〉》,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4年,第3頁,第11頁。
[15](法)布迪厄:《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劉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
[16]賀麥曉:《二十年代中國“文學場”》,《學人》第13輯,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
[17](英)賀麥曉:《文體問題:現代中國的文學社團和文學雜志(1911—1937)》,陳太勝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
[18](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吳叡人譯,2005年,第33頁,第45頁。
[19](日)藤井省三:《魯迅<故鄉>閱讀史:近代中國的文學空間》,董炳月譯,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
[20]姜濤:《“新詩集”與中國新詩的發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2頁。
[21]陸費逵:《六十年來中國之出版業與印刷業》,《申報月刊》第1卷第1期,1932年7月15日。
[22]夏丏尊:《中國書業的新途徑》,《大公報》,1945年12月17日。
[23]《周揚對胡愈之關于出版問題之意見致中共中央電》,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第1卷,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年,第48頁。
[24]《新書業公會宣言》,《開明》第1卷第8期,1929年2月10日。
[25]Lin Chu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Durham: Duke University,2006) ,P60, 轉引自朱羽:《社會主義與“自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5—16頁。
[26]范雪:《出版延安的“知識”與“政治”——延安與生活書店的戰時交往史》,《文學評論》,2016年第5期。《抗戰時期生活書店的制度選擇》,《文藝研究》,2017年第7期。
[27]詳盡討論參見王秀濤:《當代文學史料的等級問題》,《文藝爭鳴》,2020年第1期。
[28](法)馬克·布洛克:《歷史學家的技藝》,黃艷紅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71—73頁。
[29]徐公:《沈從文大罵開明書店》,《快活林》,1946年第34期。
[30]洪子誠:《當代文學的“一體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第3期。
[31]梁啟超:《自序》,《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2頁。
[32]陳寅恪:《陳垣敦煌劫余錄序》,《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26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