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學術史視野中的“述學文體”

陳平原教授的新著《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即將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在這篇文章中,作者追述這項課題發端與展開的經過,勾勒出二十多年來學術史研究的軌跡,從中也可見出作者對學術選擇與人生體驗和時代變革之間關系的深入思考。某種意義上,這篇關于作者本人學術史研究歷程的自述文字,本身亦可作為學術史來讀。
一
與唐宋詩文或上古史研究不同,“現代中國研究”往往與當下的思想文化潮流,乃至政治局勢相互激蕩,好處是問題意識突出,缺陷則容易陷入古今循環論證。當初選擇這個題目,確實別有幽懷,日后在推進過程中,騰挪趨避,更是得失寸心知。如今到了收官階段,正準備撰寫序言,收拾無比雜亂的書房時,竟然發現好幾篇早年文章手稿,其中有兩則讓我感慨萬端。
初刊《東方》創刊號(一九九三年十月)的《當代中國人文學者的命運及其選擇》,其中這段話,已經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了,至今重讀,仍讓我熱血沸騰:
我曾經試圖用最簡潔的語言描述這一學術思路:在政治與學術之間,注重學術;在官學與私學之間,張揚私學;在俗文化與雅文化之間,堅持雅文化。三句大白話中,隱含著一代讀書人艱辛的選擇。三者之間互有聯系,但并非邏輯推演;很大程度仍是對于當代中國文化挑戰的一種“回應”—一種無可奈何但仍不乏進取之心的“回應”。
只有明白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社會及學界的狀態,才能體會其中的憋屈與悲壯。不知道為何這份手稿居然能存留下來,當初文章完稿后,一般都是直接送編輯部或印刷廠,極少有重抄或復印留底的。
更不可思議的是《章太炎與中國私學傳統》,此文初刊《學人》第二輯(一九九二年七月),后入王曉明主編《批評空間的拓展: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東方出版中心一九九八年版)等,那是我比較得意的長文之一。文章寫在廣播電視出版社每頁五百格的大稿紙上,總共五十九頁,書寫瀟灑,偶有涂抹,幾乎可作紀念品收藏。更重要的是,此文最后兩段,既是史學論斷,也隱含著我當年的心境:
章太炎對中國私學傳統的推崇,在學術精神上是力主自由探索“互標新義”,反對朝廷的定于一尊與學子的曲學干祿;而在具體操作層面,則是借書院、學會等民間教育機制,來傳國故繼絕學,進而弘揚中國文化。
民間講學涉及經濟、政治等一系列問題,并非一句“學術自由”就能解決。章太炎一生堅持私人講學,多次拒絕進入大學當教授,有其明確的學術追求。至于章氏私人講學所面臨的困境、所取得的實績,以及借此建立學派設想之實現等相關問題,只能留待專文論述;這里只是突出章太炎對中國私學傳統的體認與繼承。
手稿及刊本所署寫作時間,都是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五日;可我清楚地記得,此文應寫在《在政治與學術之間—論胡適的學術取向》(撰于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九日,刊《學人》第一輯,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之后。翻查日記,終于發現“立字為據”也不一定可靠—此文一九九一年十一月開筆,完稿于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五日。當初大概是忙暈了,題寫時間時,忘記已經“天增歲月人增壽”。
一九九一年對我來說是個十分關鍵的年份。元旦那天,寫下《〈千古文人俠客夢〉后記》,為完成一部突發奇想的小書而得意洋洋;半年后撰寫“校畢補記”,則感嘆喜愛劍俠的父親去世,“再度燈下涂鴉,不禁悲從中來”。接到父親病危的電話,我正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學,急忙趕回潮州。病床前,母親稱已無力回天,父親彌留之際,多說好聽的,讓他寬心上路。日后多次回想當時的情景,埋怨自己不該絮絮叨叨,但又真的不知道該做什么好。
父親的英年早逝,對我是個巨大打擊,但也促使我迅速成熟。這個世界上,最關心也最牽掛我的人走了,以后一切都只能自己做主。因機緣湊合,在日本“國際友誼學術基金會”(籌)及江蘇文藝出版社的支持下,我與王守常、汪暉合作主編的《學人》在這一年十一月問世。事后想來,以當時的輿論環境,《學人》能夠破土而出,實在是個奇跡。起碼開創了民間辦刊的新路徑,也算是實踐了章太炎的私學理念—起碼我自己是這么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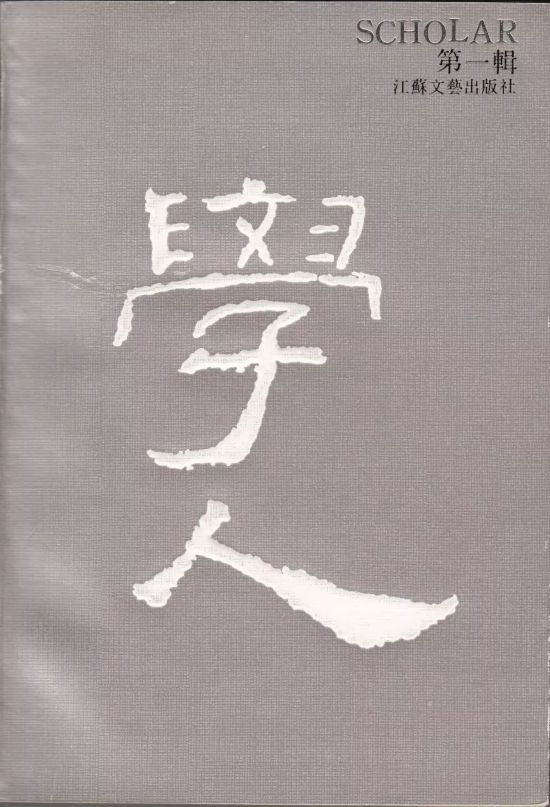
《學人》第一輯,江蘇文藝出版社,1991年
我在《學人》第一輯上,除了《學術史研究隨想》,還有一篇專業論文《在政治與學術之間—論胡適的學術取向》。單看題目,不難明白當初我的困惑與抉擇。可我更懷念的是同年四月撰寫,因各種緣故壓了兩年才刊出的《學者的人間情懷》(《讀書》一九九三年五期),此文當初引起不小的爭議,日后被別人收入多部選集中。這回翻箱倒柜,特別希望能找到此文稿,可惜沒能如愿。
對于我來說,一九九一年是重要的轉捩點,如此巨變,既是人生體驗,也是學問境界。當年發表大小十二文,談武俠的屬于前一年的積累,說學術史的,方才是剛剛開啟的新天地,而《在政治與學術之間—論胡適的學術取向》《在專家與通人之間—論胡適的學術取向》《章太炎與中國私學傳統》三文,日后收入《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因這三篇論文(加上那則《學者的人間情懷》)與我日后的人生選擇及學術道路密切相關,我對自家的學術史“三部曲”十分在意。
二
在撰于一九九一年六月的《學術史研究隨想》中,我曾這么談論學術史研究:
在我看來,這既是一項研究計劃,更是一種自我訓練。在探討前輩學人的學術足跡及功過得失時,其實也是在選擇某種學術傳統和學術規范,并確定自己的學術路向。能不能寫出像樣的學術史著作,這無關緊要,關鍵是在這一研究過程中,親手“觸摸”到那個被稱為“學術傳統”的東西。……也就是說,在學術流派的形成、概念術語的衍變、學科的崛起、方法的更新以及名著的產生等之外,還必須考察作為治學主體的學者之人格。“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固然值得大力褒揚,可由于特殊思想背景造成的學者落寞的神色、徘徊的身影以及一代學術的困惑與失落,同樣也很值得研究。這種研究,不乏思想史意義。
話雖這么說,作為職業讀書人,自我訓練之外,還是希望能寫出稍微像樣點的學術史著作。二十多年來,從最開始的“學人精神”(《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初版),到“學科體制”(《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一年初版),再到眼下的“述學文體”(《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終于完成自成一格的現代中國學術史“三部曲”。只是如此環環相扣,并非一開始就成竹在胸,而是在漫長的探索過程中逐漸調整而成的。
在九十年代初討論晚清及“五四”兩代讀書人如何在求是與致用、官學與私學、學術與政治、專家與通人的夾縫中掙扎與前行,當然是有感而發。不過,《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更有價值的是以章、胡為中心說開去,討論經學子學方法之爭、晚清志士的游俠心態、現代中國的“魏晉風度”與“六朝散文”,以及現代中國學者的自我陳述等。而其中談論胡適的文學史研究,促使我從個人著述轉向學科體制,于是有了《作為學科的文學史》。
二〇一六年增訂版《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加了個副題“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及境界”,主旨更為顯豁。全書共十二章,大致分為三塊,分別討論學科建立與學術思潮、學人及其著述、若干專業領域的成績與拓展的可能性。第一至第四章從課程、教師、教材、課堂入手,討論百年來中國大學里以文學史為中心展開的文學教育,分析其利弊得失。第五至第八章談論具體的文學史家。第九至第十二章牽涉小說史、散文史、戲劇史和現代文學四個專業領域,屬于典型的學術史思考。其中《“文學”如何“教育”—關于“文學課堂”的追懷、重構與闡釋》一章,自認為頗多新意:從“聲音”角度探索文學教育的方法與途徑,與《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中關于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的思考路徑相通。

《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增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
十幾年前,我曾為北大中文系研究生開設“現代中國學術”專題課,開場白整理成《“學術文”的研習與追摹》(初刊《云夢學刊》二〇〇七年第一期)。那門課共挑了十五個研究對象,每人選三文,既是歷史文獻,也是學術文章,要求學生閱讀時兼及“學問”和“文章”兩個不同的維度,且特別提醒:
學問千差萬別,文章更無一定之規。“學術文”的標準,到底該如何確立?唐人劉知幾講,治史學的,應具備三本領:才、學、識。清人章學誠又添加了一項“史德”。史才、史學、史識、史德,四者該如何搭配,歷來各家說法不一。我想補充兩點:第一,選題及研究中“壓在紙背的心情”;第二,寫作時貫穿全篇的文氣。
此處提及的“學術文”,用的是老北大的課程名稱,轉化成我的研究課題,便是“述學文體”。
三
談論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與傳統中國的文體學、目錄學以及西方的修辭學等有關系,但又不全然是。我最關心的,其實是在中外新舊文化激烈碰撞的時代,中國學者如何建立“表達”的立場、方式與邊界。
《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共八章,個案部分,除了已完成的五章,原本還選了陳垣、陳寅恪、馮友蘭、錢穆、朱自清、顧頡剛、俞平伯、鄭振鐸、李澤厚、余英時十位,都是述學方面的高手,值得再三推敲;可說著說著,越來越往修辭學方向走,這可不是我的愿望。于是當機立斷,就此打住,因為,單就“述學文體”這個話題而言,前五個案例已經足夠精彩,再多說就是具體的技術分析了。五個案例中,談論章太炎那一章最薄弱,因最初是為整理本《國故論衡》做導讀,筆墨不免拘謹。好在關于章太炎的思想、學問及文章,此前我在《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中多有涉及,讀者也可參考《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初版)的第四章《學問該如何表述—以〈章太炎的白話文〉為中心》。
借如何“引經據典”來討論晚清以降“述學文體”的變革,是個有趣的入口。原本設想的章節還有《教科書、專著與劄記—著作成何體統》《雜志、學報與副刊—學問怎樣發表》《標點、段落與文氣—文章如何呈現》,為此我還做了許多理論及資料準備,最終沒能完成,固然很可惜,但以目前中國學界的狀態,能將此類題目經營得風生水起的大有人在。
相對來說,我更看好從演說角度切入,討論近現代中國文章的變革。此舉可以上掛下聯,縱橫馳騁,自認為頗具創見。這里牽涉聲音與文字、文言與白話、大學與社會、論著與雜文等,可以說牽一發而動全身。實際上,本書好多個案都涉及此話題,只是立場及趣味不同而已。
需要多說幾句的,是關于著作的想象。清儒章學誠《文史通義》以及今人余嘉錫《古書通例》都曾講到著述體例,但不及以下三位痛切精辟。王國維刊于一九一四年的《二牖軒隨錄》中有一則“古今最大著述”:
余嘗數古今最大著述,不過五六種。漢則司馬遷之《史記》,許慎之《說文解字》,六朝則酈道元之《水經注》,唐則杜佑之《通典》,宋則沈括之《夢溪筆談》,皆一空倚傍,自創新體。后人著書,不過賡續之,摹擬之,注釋之,改正之而已。
吳汝綸在《天演論序》中提到,古今之文大體可以分為“集錄之書”和“自著之言”:“集錄者篇各為義,不相統貫,原于《詩》《書》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干,枝葉扶疏,原于《易》《春秋》者也。”漢代多自著之書,唐宋以后則多集錄之文,“獨近世所傳西人書,率皆一干而眾枝”,這點很令人羨慕。胡適也曾列舉自古以來若干“成體系”的著作,如《文心雕龍》《史通》《通典》《文史通義》《國故論衡》等,給予特殊表彰,稱之為學術著述的極則。這里的“最大著述”“自著之言”,以及“成體系”,與傳統中國的四部分類沒關系,乃中國學者面對西潮沖擊的自我反省與價值重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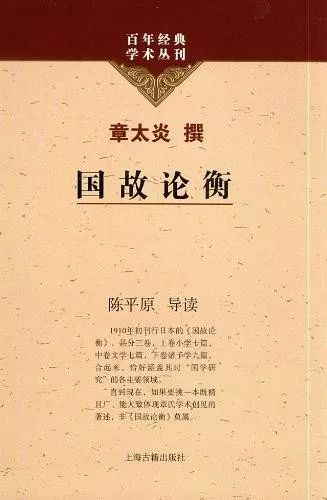
章太炎《國故論衡》,陳平原導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晚清以降,在中國學界,這種“一干而眾枝”的著述形式逐漸興起,而傳統的“文集之文”相對衰落。這牽涉近代中國的知識轉型,以及新的表達方式的確立。但著作的定義并非一成不變,完全可以百舸爭流。針對世人抱憾陳寅恪沒能撰寫“中國通史”,我曾撰《學者的幽懷與著述的體例—關于〈陳寅恪集·書信集〉》(《讀書》二〇〇二年第一期),對此略有辨析:
陳先生無疑是很講“通識”的史家,無論講課或者著述,其眼光從不為一時一地一民族一文化所限。可假如從著述體例考慮,撰寫“通史”又恰好不是其著意經營的目標。還不是晚年雙目失明或精力不濟,而是其研究及著述深受歐洲漢學以及傳統中國學術的影響,以專深的論文,而不以系統的著作為主要工作方式。
身處大變革時代,學者到底該如何思考、表述與立說,前輩們做了許多艱辛而有效的探索,初步勾勒了若干可行的通路,讓后來者有所依傍。但所有探索,即便十分成功的,也都只是范例,而不是定律。
四
當初《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出版,學界反響極佳,背后有一代人的心路歷程,這點以后很難復制。雖然此書獲教育部頒發的第三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二〇〇三年),算是人文學著作所能得到的最高褒獎;《作為學科的文學史》也不遜色,先后獲得多個獎項,但我自己知道,后者雖學術上更為嫻熟,也更多創獲,仍只能在專業圈子里博得掌聲,很難為知識界(更不要說公眾)所激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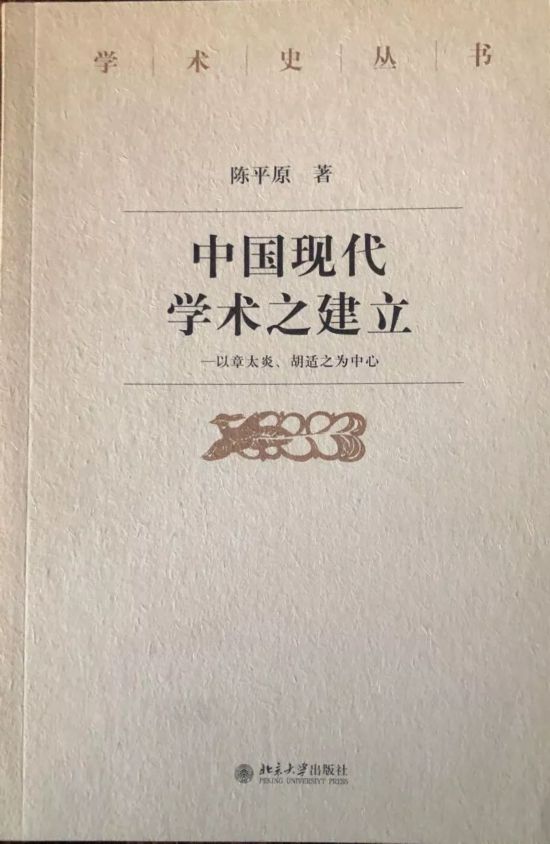
《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如今談論“述學文體”,這個話題更專深,要想引起公眾的興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至于學界,那就很難說了。二〇〇六年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一日在香港城市大學舉辦“現代性與二十世紀中國美術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作為特邀的“門外漢”,我做了《關于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的專題發言(錄音整理稿初刊宋曉霞主編的《“自覺”與中國的現代性》,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居然大獲好評。我稱現代性是一種思想體系,一種思維方式,一種生活方式,同時,也是一種表述方式。而我理解的“表述”,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表述,文學家的表述,還有學者的表述—后者最容易被忽視,在我看來卻最值得關注。這里所說的基本定型且意蘊宏深的“述學文體”,包括學科邊界的確立、教科書的編纂、論文與專著的分野、標點符號的意義、演說與文章之關系,還有如何引經據典等。
照道理說,既然不乏知音,那就該擱置其他雜務,取狂飆突進姿態才是。可實際上,本書總共八章,七章撰寫于二〇〇六年底前(各文撰寫及發表狀態參見本書《后記》)。為什么?除了精力分散外,就是懸的過高,而又力所不逮。論題再三推敲,資料也積累了不少,甚至還在北大研究生課堂上講過,但不敢貿然下筆。過于矜持的結果,就是眼看許多后起之秀翩然起舞,異彩紛呈,很多重要話題已經不需要我努力發掘了。這才想起胡適為何被人嘲笑“半部書”先生,就因當初沒能一鼓作氣,故再而衰,三而竭。
另外,還有一個緣故,就因《有聲的中國》那一章頗多心得,越寫越高興,其學術延長線上,浮現出“聲音”的生產、傳播與復原,而不再是“述學文體”了。深恐尾大不掉,沖淡了本書主旨,于是壯士斷腕,只保留以“講演”為“文章”者。
二十多年前,初闖此領域,那時意氣風發,以為路子走對了,持之以恒,總能做出大成績。可如今奉獻給讀者的,也就只有這區區三書。好在我的學術史研究,是與文學史、教育史研究結伴而行;三者成果無法疊加,但相互映照,多少也是一種精神支撐。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四日初稿,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改定于京西圓明園花園
(《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陳平原著,北京大學出版社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