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生的金智英》:走出性別對立的陰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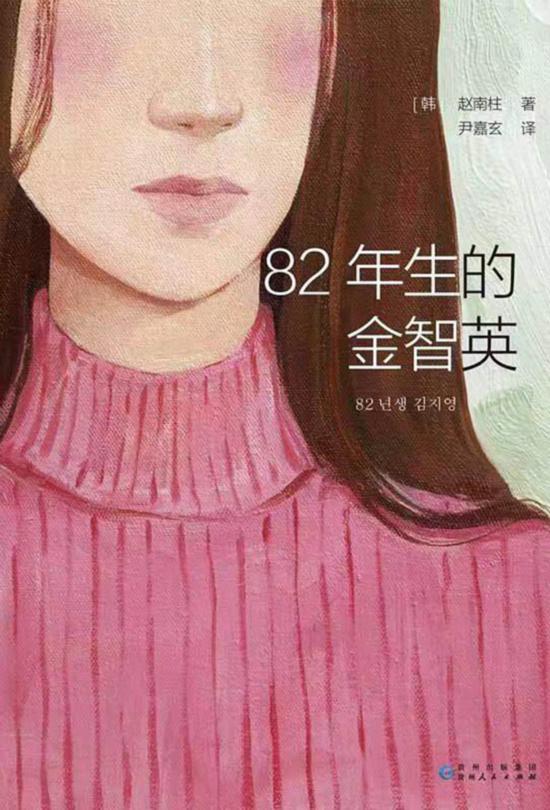
《82年生的金智英》需要男性讀者嗎?
“經濟不景氣,高物價,惡劣的職場環境……其實人生中的各種苦難,誰都會面臨,無關性別,只是許多人不愿承認這點”,雖然這是韓國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作者趙南柱說的,但它藏在書中深處(簡體中文版145頁,以下引用頁數均指簡體版),不像書尾“作者的話”那樣顯眼易找(中文版還特意拎出來印在目錄前):“由衷期盼世上每一個女兒,都可以懷抱更遠大、更無限的夢想。”——很顯然,這是一本獻給女性讀者的書。韓文版出版社宣傳語也稱這是一本韓國三十多歲女性的生活報告書。2018年,韓國女性平均結婚年齡為三十點四歲,因此可以更準確地說,這是獻給已婚女性的。
然而,附錄的女性主義研究學者金高蓮珠在作品解析最后說,“希望閱讀這本書的讀者朋友們一起思考,尋找方法,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金智英”;譯者尹嘉玄也引用英國女演員艾瑪·沃特森(Emma Watson)在國際婦女節的發言“爭取的不是女權,而是兩性都能自由”“女性主義從不等于厭惡男性,但凡相信平等的人,都是女性主義者”,期盼本書在華人圈能有更多男性讀者,讓男性對女性的處境能夠有所了解,互相體諒、幫助彼此。
顯然,要不要爭取男性讀者,作者與評論家、譯者有分歧,簡體中文版更是火上澆油,特意在封面折頁上印了“她說”:因為身為女性而受到各種限制與差別待遇,導致沒有辦法獲得與付出相匹配的成就,甚至認為那是因為自己無能而深感自責的女性,希望她們在閱讀本書之后,可以獲得一絲安慰。這段話放在作者簡介下面,似乎是趙南柱說的,但并未見于韓文版,不知出處何在?它的要旨是說,金智英這樣的普通女性遭遇的困惑/困境,完全是因為她的性別!即使比作者心胸更寬廣,希望爭取男性讀者理解、支持女性的評論家和譯者,著眼點也只是放在改善兩性關系上。然而,如果只局限于兩性關系來看這部作品,不僅無助于兩性平等,反而會加劇兩性對立——韓國社會對這部小說及其同名改編電影的爭議正與此有關。
韓國拉面式的暢銷書
趙南柱寫小說之前,長期擔任《PD手冊》等時事節目的編劇,該節目是韓國第二大電視臺MBC的王牌節目,主打社會熱點問題調查報道,工作之便顯然為她寫作提供了不少素材,所以小說才會頻繁引用新聞報道、統計數據、網絡熱詞等等,這是《PD手冊》這類企劃型電視節目的制作套路:微觀報道加宏觀分析,也是屢試不爽的收視保證。
因此,小說讀起來更像電視節目的腳本,韓國觀眾習慣了這種模式,加上作者以為女性代言的姿態把眾多韓國女性的經歷虛擬化后投射到“金智英”這個角色身上,只要有一點引起共鳴,便能吸引數以百萬計的讀者——其中多數是女性,韓國大型連鎖書店(既有門店也有網店)阿拉丁統計顯示,購買該書的讀者中,女性占百分之八十三。
然而,這樣的人物塑造等于是一個“全韓國的苦我來吃、全韓國的罪我來受”的高度概念化形象,中文版編者刻意從正文中抽出金智英的抱怨放在每章前面,更讓人覺得她有點像魯迅評論《三國演義》“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述智英之多難而近插滿仇人詛咒針的布偶”,這不是一個活的真人,比如第二章抱怨“就好比大家從不曾質疑過身份證上為什么男生是以阿拉伯數字1開頭,女生則是以2開頭一樣”——可是這種質疑更像迷信,有什么實際意義呢?難道韓國選舉中1號候選人就一定會贏2號候選人?
香港著名的多產作家倪匡在給女作家林燕妮小說《為我而生》作序時談到好小說的標準,首先是好看:要有性格鮮明的人物;要有情節變化多端、豐富動人的故事;要有引人入勝、叫人越看越想看的寫作技巧。其次,對有人問的內涵問題,他說:這樣問的人,目的是要把“社會責任”“人類理想”種種,加在小說的身上,簡單地說,要“小說載道”。他鄭重指出:好小說,必有道在。好小說,可以絕不刻意載道。好小說,也可以大大載道。以這個標準看,《82年生的金智英》很難稱得上是一部好小說:女主角性格刻畫迷糊,勉強可以用忍氣吞聲來形容,即使她的幾次爆發也是以產后抑郁癥患者身份出現的,而且這種“反抗”只對內(婆婆、丈夫等)而不對外(歧視、騷擾她的人),以至于電影編劇都看不下去,在片中修改了部分人設:在帶小孩買咖啡時被陌生人譏諷她是“媽蟲”,她當面懟了回去(這也是一般人自然的反應,小說中卻寫她只是回去跟丈夫說了);在情節與故事方面,也是平鋪直敘,缺乏張力——同是媒體人出身的韓國作家張康明的小說《因為討厭韓國》(簡體版改名為《走出韓國》)也是類似主題:主角不滿身為女性在韓國的壓抑生活,離開韓國去了澳洲打工,其間的經歷一波三折,人物刻畫也遠比本書豐滿;就寫作技巧而言,本書基本是網絡帖子加新聞報道水平。
最后,本書唯一被認可的是主題,如上述“她說”所言,也只是安慰女性而已——這樣一本廉價雞湯小說,因此在韓國累計銷量一百七十多萬本。但文學界反應冷淡,出版三年來僅獲得一個“2017年度作家獎”。請注意,這個獎是“年度作家獎”而非“年度作品/小說獎”,只是表揚作家寫出了話題作品并成為暢銷書,對小說的文學價值顯然有所保留。簡體版出版后,有人聲稱本書是韓國文學變強的證明之一。然而,這種暢銷書盡管一時能討讀者喜歡,卻難以稱得上經典作品,不會永遠銘刻在韓國文學史上(同樣以女性為主角的韓國小說,我推薦千明官的《鯨》,它被譽為韓國版《百年孤獨》),就像韓國的方便面——拉面,盡管可以稱得上國民食品,據說現在也占據了中國進口方便面市場頭號交椅,但也只是肚餓時拿來應付一下的快餐,硬要說它是韓國美食就很荒唐了。
韓國企業規模收入差距遠甚于男女收入差距
回到《82年生的金智英》小說本身,它以時間來劃分章節,分別講述金智英出生到上小學時、讀中學時、上大學時、畢業進入職場、結婚后辭職在家階段的遭遇。以頁數而言,婚后生活分量最重,小說正是以婚后第三年、產后一年的爆發為楔子回顧金智英三十四年的人生路。然而,讀者注意力可能都集中在她經歷的恐懼、疲勞、慌亂、驚慌、混亂、挫折(見韓文版封底宣傳語,似可對應全書六個章節),而忽略了對她及其娘家、丈夫小鄭及其夫家的背景介紹,而這些正是造成她的怕與痛的重要因素。
小說一開篇就介紹了金智英婚后家庭概況:一家三口租住在首爾郊區八十平方米公寓內,丈夫任職中型IT企業,每周上六天班,每天加班到晚上十二點,她在小型公關公司上班,婚后辭職。婆家在釜山太遠,娘家開餐廳太忙,育兒只能親力親為,女兒滿周歲后被送到社區托兒所半托(見第3頁)。女性讀者的感想可能是:家庭育兒的壓力(以及家務)全由金智英一個人扛!話是沒錯,然而,這并不能怪她丈夫、婆家及娘家,他們非不為也,實不能也:丈夫上班比中國一些企業“996”強度還高(我今年5月在首爾向一男一女韓國青年談到中國“996”情況,沒想到兩人并不吃驚),即使下班還有精力想照顧女兒也沒機會了,因為晚上十二點多半都睡了。
此外,一般讀者看不出來的信息是,這個三口之家并不寬裕。她家房子是交保證金的全租房,后面提到,租滿兩年后,房東將保證金漲了六千萬韓元(約三十六萬元人民幣),夫妻倆不得不再次貸款,光靠丈夫一個人的收入,根本不能妄想買一間小公寓(144頁)。這說明,這家人年收入可能低于韓國工薪階層平均年薪(2018年約二十二萬元人民幣,小說故事發生的2016年約二十萬元),更不可能屬于占韓國人口百分之六十五的中產階層,因為韓國中產的一個標準就是四口之家年收入在五千四百二十四萬韓元(約三十三萬元人民幣)以上。即使在夫妻倆都工作時,書中(117頁)大略交代說:金智英和丈夫鄭代賢幾乎同時踏入職場,她住家里開銷不大,但鄭代賢存錢更多,因為他薪水比她高很多,“沒想到會差這么多,不免有些無奈”。其實,韓國每年都會公布相關統計數據,以2018年為例,大企業正式員工平均年薪達六千四百八十七萬韓元,同比上漲二十七萬韓元。中小企業正式員工平均年薪三千七百七十一萬韓元,上漲一百七十六萬韓元。可以看出,韓國中小企業年薪幾乎只有大企業一半略多。而鄭代賢的公司是中型企業,金智英的公司是小企業。他們與大型企業員工的收入差別,遠比書中強調的男女收入差別(見110頁)大。
韓國中小企業員工收入低,不一定是因為其能力不如大企業員工,而是其家庭、畢業學校等因素所限。金智英要上大學時,亞洲金融危機對韓國的打擊剛過,提前退休的父親用退休金和母親的積蓄一起開餐廳,店面是買的,不用付租金,這才勉強撐下去;金智英的姐姐金恩英放棄當電視制作人的夢想轉考學費低就業有保障的師范大學,主要也是因為家里經濟條件不夠好。金智英考上首爾一所大學文科后,也曾為學費發愁。她和學長鄭代賢讀的大學顯然不是SKY(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那樣的名門,這必然會給他們的就業降低機會。
對他們的家庭出身,小說只交代了金智英家的情況(15頁):父親是公務員,母親是主婦,一家六口住房面積僅三十三平方米的兩居室。上小學五年級時搬到買的三房一廳一衛新居,面積大了一倍,原本父親和奶奶提議讓姐妹倆與奶奶同住一間、弟弟獨自住一間,在母親堅持下才改為弟弟與父母住、姐妹同住、奶奶獨住(見38、39頁)——父親與奶奶的想法有重男輕女的成分,但更有屋子仍然不夠大不能每個小孩一間的遺憾。然而,到金智英自己成家,夫妻倆只能租房住,主要原因當然是房價飛漲遠超兩人所能負擔。
經濟狀況不濟,也體現在夫妻倆中秋節去婆家,以前是兩人輪流開車,產后則由鄭代賢一人開車五小時(第8頁)。如果看過同樣由孔侑和鄭柔美擔任男女主角的電影《釜山行》和《82年生的金智英》,就會發現:同樣是2016年從首爾到釜山,前者是坐高鐵KTX,后者是自駕——從時間上看,KTX只要不到三個半小時,如果加上出站后招出租車到家也就四小時,比自駕省一個小時;但是從費用來說,KTX雖然一張成人票+出租車費與自駕的高速公路過路費和汽油錢差不多,但一家三口要買三張票(約合人民幣八百六十元,其中六歲以下兒童票價為成人票價的百分之二十五),金智英一家顯然想省下這筆錢,盡管自駕更費時耗力。
而金智英被長輩們催生時的不情愿與焦慮,其實也與錢有關——韓國有調查表明:第一份月薪多一百萬韓元,生育率提高百分之二點七。由于生小孩,金智英不得不辭職專門帶娃,作者說,“因為鄭代賢的工作相對穩定,收入也較高,最重要的是,當時的社會風氣普遍也都是男主內、女主外”,但是,在電影中劇情有改動:鄭代賢提出自己也可以申請男性育兒假,但在金智英質疑是做樣子還是真心后放棄,其實最重要的原因并非作者說的社會風氣(見130頁)——韓國近年休育兒假者中,男性已達五分之一(見2019年11月16日SBS電視臺《新聞故事》專題片《80年代出生的智英們》),而是作為男性的鄭代賢已接近四十歲,而四十多歲就業者人數從2015年開始在四年內持續減少,到了今年10月,從二十多歲到六十多歲、七十多歲人群的雇用率都提高了,但四十多歲人群的就業者人數減少了四十三萬六千名,雇用率也下降了(見《東亞日報》12月4日社論《被趕出工作崗位、在社會上無處可去的40多歲人群的危機》),假如休完一年育兒假回來,他在中型企業的工作很可能就沒了,那樣一家三口就會變成電影《寄生蟲》中全員無業的家庭。
韓國社會的厭女與厭男癥
另外,金智英對帶小孩、做家務感到心力交瘁,尤其反感丈夫說“幫她帶小孩、做家務”(130、131頁),這就有些過于敏感了:前面已經說過,鄭代賢每天上班時間超長,平時根本無暇顧家,他也是出于好心愿意幫妻子分去一些負擔。
書中有一個反例:當年,金智英的母親要照顧三個孩子,還要在家接代工活,父親抱怨了一句后向她道歉“對不起啊,害你這么辛苦”,母親則很體諒他,說:“不是你害我辛苦,是我們兩個人都辛苦。不用對我感到抱歉,也別再用一個人扛著這個家的口吻說話。沒有人要你那么辛苦,也不是只有你一個人在扛。”(23頁)這話男女都適用,可惜今天兩性往往只想到各自辛苦。韓國社會漸漸衍生出男女對立:厭女的男性,聚集在“日佳”網絡論壇,“媽蟲”等詞就是從那里傳出來的;厭男的女性,也在womad網絡論壇,惡評自殺身亡的男歌手金鐘鉉,甚至有大學繪畫系女模特偷拍并上傳同班男模特裸照,罵他“為錢脫衣”。其實,網絡中男女互相批斗只會加劇對立,現實戀愛中的男女、結婚的夫妻,應該彼此體諒、互相幫助。
《82年生的金智英》不論小說還是電影,在韓國的受眾(讀者/觀眾)最大群體,居然是二十多歲一代女性(三十多歲一代居第二位),她們屬于生理和法律上都適婚的未婚者,顯然,這部作品加劇了她們對男性、對婚姻的恐懼,她們心理上還沒做好準備。然而,更重要的是,如果只是糾結于男女不平等而無視其背后不分男女的經濟、政治因素,恐怕很難走出彼此對立的陰影。金智英曾建議姐姐金恩英在房間的世界地圖上標出想去的國家,姐姐選擇了丹麥、瑞典、芬蘭等北歐國家,她的解釋是“感覺那邊韓國人比較少”,簡直與《走出韓國》女主角如出一轍:因為討厭韓國。其潛臺詞是,這些北歐國家女性地位高。但是,她未必清楚,這些國家高福利源于高稅收,而高收入更是必不可少,其中像丹麥的人均GDP更是韓國兩倍(韓國統計廳2018年數據)。當韓國有更強的經濟實力、政府有更大的意愿時,才能支援國民的婚姻、育兒、養老;而這些,都需要男女老少共同打拼、施加壓力、請愿游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