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作品與作家心中的故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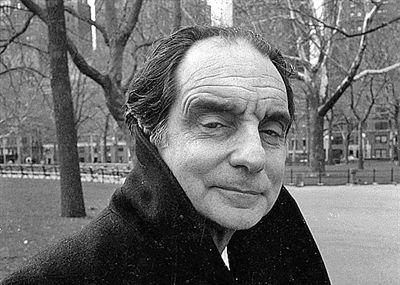
卡爾維諾 資料圖片
生活在當代社會中的人們,面臨著很多無法回避而又似乎無法解答的問題,其中關鍵的一個就是:哪里才是我們幸福的家園?當遇到困難的時候,哪里才是我們可以依賴的那個故鄉?
最近,在中國作家莫言和法國作家勒克萊西奧之間展開的一次關于文學的深入對話當中,勒克萊西奧提到了莫言始終將自己的故鄉高密作為背景進行創作。盡管勒克萊西奧對高密不甚了解,但他完全能夠體會莫言對于故鄉高密的那種深沉的情感。與此同時,在勒克萊西奧的作品當中,我們看到的更多并非他出生的尼斯,而是他在漫長而豐富的人生之旅中足跡所達到的地方:非洲,美洲,中國……甚至是那些未經命名的城市或者鄉村。
在當代的文學創作當中,時間、地點、人物與事件之間的關系,不再像傳統文學那樣四平八穩、邏輯分明,也不再被強行聯系在一起,而是在各自的層面上和彼此的關系中扮演著獨立的角色。故事時間不必連貫或者按照一定的順序發展,人物角色千變萬化,事件也呈現出碎片化的特點,因而讓人捉摸不定。在如此的情況下,事件發生的地點與背景,自然也呈現出錯綜復雜的態勢,時而真實觸手可及,時而又虛實莫辨。無論是其中的哪一種,都來源于作家對真實生活的思考,也體現出他的心靈所向。最初的逃離與最終的回歸,顯得同樣無法避免,因為故鄉代表著一個避難所,一種可能的救贖,是能夠發掘出我們可以依賴的價值的根。
一
192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格拉齊婭·黛萊達(1871-1926)出生在意大利撒丁島,被譽為“撒丁島之聲”。女作家19歲就發表了第一部長篇小說《東方的星辰》(1890)。后來,她隨丈夫到羅馬生活,但故鄉的歷史傳統、風土人情、貧瘠而又旖旎的風光,始終從女作家的記憶中涓涓流出,猶如一幅幅瑰麗的畫卷,成為作品真正的靈魂。其代表作《風中的蘆葦》(1913)通過描述三代人的生活,反映了封建莊園制和封建大家庭的解體,以及從農業社會到工業和科技社會的變革。與此同時,貧窮、迷信、宿命論、家庭榮譽等等傳統問題仍然占有很大的分量。善與惡的沖突,對于人類無法擺脫的矛盾的探索,以及對于救贖的渴望,都是黛萊達作品的核心。選取“蘆葦”作為代表性的意象,正是因為蘆葦的生存狀況和人類的生命非常相似:人類命運如同風中脆弱的蘆葦,我們頭頂上存在著無法戰勝的力量,任何改變命運的努力,最終都會顯得徒勞無功。然而,與這種宿命論相對的,是撒丁島獨一無二的風光、質樸的人民和那種阿卡迪亞式的生活。記憶中那些山川、牧場羊群和牧民,使作品中流動著一種非同尋常的能量,在讀者心里喚起無限遐想,以及對于自然和真實的渴望。同時,無論是與自然的抗爭還是對社會生活的反抗,最終結果都只是無奈,這也成為那個時代撒丁島人民生活的真實寫照。真實主義的表現手法與女作家記憶中魂牽夢縈的故鄉風光彼此交融,構成了黛萊達式的故鄉。
對于故鄉的情感與回歸,同樣是意大利作家切薩萊·帕維塞(1908-1950)的主題,但引發了作家另一番思考。作家在小說《月亮與篝火》(1950)中寫道:“有一個故鄉,就意味著你并非孤單一人。”帕維塞最重要的幾部小說,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他出生的那片土地:《你的家鄉》《山間小屋》《美麗的夏天》(包括《美麗的夏天》《山上的魔鬼》和《三個孤獨的女人》三部小說),以及《月亮與篝火》。在帕維塞的作品當中,位于都靈東南60公里左右被稱作朗格的丘陵地區,是各種故事發生的場所,更為作家提供了人文思考的土壤。農村生活反映出自然界所具有的原始、神秘而又無法抗拒的力量,與城市生活形成鮮明的對比。與此同時,這種對比又與人物從少年到成年的過渡結合在一起,勾勒出一條從探索到發現、失望與挫敗的人生軌跡。城市生活代表著文明、成功,以及個人形象的塑造,但又要面臨兩難的選擇:或者融入城市生態,那就意味著戴上面具,進而失去本我;或者堅守自我,從而過著孤寂的生活,回歸故鄉的渴望也會油然而生。然而,故鄉也并非一成不變,物是人非的感觸在所難免。各種層面上的生存危機,在帕維塞的作品當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也是他個人生平的寫照和對最終悲慘結局的預示。
在帕維塞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說《月亮與篝火》中,主人公安奎拉是一個在朗格地區長大的棄嬰,被一家農戶撫養成人,然后到美洲討生活。20年后,這位游子回到了自己的故鄉。然而,當他回到童年生活過的地方,卻又無法避免地發現,當年收養他的人家已經無從找尋,跟隨樂隊走村串鄉吹單簧管的少年伙伴努托變成了中年木匠,另一個伙伴桑塔參加了抵抗運動,但是被作為間諜燒死,佃農瓦里諾變成了慘無人道的弒親之人,而在其殘疾的兒子欽托身上,安奎拉找到了自己兒時的影子;從牛奶場姑娘們的身上,他仿佛又看到了養父母家的三個女兒。作家恰恰是通過今昔的對比,通過兒時伙伴身上發生的變化,反映了戰爭給人類造成的困難,和戰時人性本身的扭曲與兇殘。與此同時,相對于人類歷史的莫測多變,鄉村生活仍舊遵循著自然界四季的輪回變遷,大地也永遠表現出一種永恒不變的能量。一代代人的命運,仿佛也存在著某種循環往復的規律。對于安奎拉來說,童年在那里的鄉村中感受到的大地、天空、陽光和樹林,聽到的鄉音,品嘗的飯食,都是游子心中的慰藉,滲透著作家對故土的神往,同時也勾起他無法忍受的鄉愁,因此回歸是唯一的選擇。然而回到故鄉之后,見到的仍舊是孤寂與死亡。
類似的故事也出現在帕維塞的詩歌作品《南方的海》中,作品講述的是他一位表兄的故事。大戰之前,20歲左右的他離開家鄉去世界上闖蕩,又在20年之后返回故土。這首詩歌中同樣表現出對童年美好時光以及鄉村恬靜生活的懷念,同時也包含了帕維塞作品中幾乎所有關鍵性的主題:回歸、童年、城市與鄉村的對比、朗格地區的風光等等。詩歌開篇處表兄弟二人登上山丘,暗示著重生與升華。在他們的談話當中,不僅包含表兄離開故鄉后的境遇和家人的反應,也包括詩人本身離開鄉村到城市居住,那里代表著背叛和虛假,與鄉村的真實與親情形成鮮明的對比。在詩歌的最后,回到故鄉的表兄表現出與小說中安奎拉同樣的失望。表兄接受了這種決定著個人生活的古老法則,也就是命運這種超越一切力量的統治,留給人類的唯一可能是短暫的逃避。
對于故鄉的無限眷戀,始終貫穿在帕維塞的作品當中。他所創作的敘事式詩歌,節奏舒緩,富于感染力,而且具有史詩的風格。詩如小說,小說如詩。一草一木,一言一行,間或方言的使用,都如泣如訴,又同樣浸透著深情與無奈。這就是作家帕維塞對于心中故鄉的情感。故鄉既有現實作為依托,又充滿了豐富的想象和文學的再創造。那種情景交融的手法,使自然風光中浸透著濃重的人文氣息,又為人類社會的生存提供了一個具有獨立靈魂和神秘莫測的自然空間。
二
當人類社會走入工業時代,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人們希望在那里獲得事業上的成功,并過上安逸而富足的生活。然而,表面上的繁榮以及對于物質生活的過度追求,無可避免地帶來了各種不安、孤獨、陌生甚至恐懼的心態,以及普遍性的異化。正像20世紀意大利著名文學家卡爾維諾(1923-1985)所說的:“我們住的房子越是明亮和豪華,房子的墻上就越有鬼影,因為進步和理性的夢中往往摻雜著鬼影。”
在這種背景之下,卡爾維諾于1963年創作了短篇小說集《馬可瓦多》。小說的主人公馬可瓦多是一名普通工人,過著簡樸甚至拮據的生活。雖然居住在一座擁有各種大型生產企業的都市(也就是作家自己的城市都靈),馬可瓦多卻有一雙“不適合城市生活的眼睛”。城市里光怪陸離的景象并不能吸引他的注意,但“一根樹枝上變黃的葉子,飄落到屋瓦上的一片羽毛”,都逃不過他的雙眼。然而,如此一個不諳世事的人,最終只能為城市生活所欺騙。他在路邊的樹根下發現了蘑菇,就采集起來給家人改善生活,結果中毒住進了醫院。他在城鄉接合部河流的轉彎處找到一汪清水,于是動手撈魚,但后來被警衛告知這段河水的上游就有一個油漆廠,所以這里的小魚已經被污染,并不能夠食用。孩子們也受到他的傳染,把高速公路邊的巨型廣告牌錯認為書本里見過的樹木(因為在城市里生活的他們沒有見過真正的樹林),于是砍了帶回家生火……終于,孩子們在這種不健康的城市生活中患上了疾病,馬可瓦多不得不帶著他們到城外去,享受山風的吹拂,呼吸清新的空氣,在草地上奔跑。然而,最終他們還是要帶著對鄉間生活的惋惜和依戀回到城市。
眾所周知,卡爾維諾是意大利當代最富想象力的作家。他的虛構作品有的直接采用童話的形式,有的雖似真實可信的故事,其中卻滲透著奇幻的色彩,卡爾維諾也被譽為“一只腳跨進幻想世界,另一只腳留在客觀現實當中”的作家。卡爾維諾的父母都是農學家和園藝學專家,他從小在農藝站長大,對自然充滿了熱愛。正是由于這種原因,他筆下的人物同樣不被大都市斑斕的霓虹燈和各種現代化所吸引,反而作為一個熱愛和渴望自然的人,觀察和剖析城市生活,進而揭露工業化社會的各種弊端。從主人公對一花一葉,一蟲一木的眷戀,反映出人類逃離城市、回歸自然的渴望,因為那里才是心靈的真正家園。
三
假如說在卡爾維諾的作品當中,回歸自然仍舊是居住在城里人近乎奢侈而難以滿足的愿望,那么在《八山》這部作品當中,人類已經具有了更加明確的融入自然的意識,也找到了一條可能的途徑。
小說的作者是最近活躍在意大利文壇的作家保羅·科涅蒂。這位始終以大山為依傍進行文學創作的作家對大山有著深厚情感,而這與他的個人經歷是密不可分的。他的成名作《八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自傳體的作品。科涅蒂的父母因山結緣,但生活習慣和理念上的差異又拉開了他們彼此的距離。書中主人公彼德羅是一個孤獨的男孩。隨著父母關系的疏遠,這個家庭唯一分享的就是對大山的熱愛。在這種環境中成長起來的科涅蒂,自小就有機會熟悉山區的生活,并跟隨熱衷于攀登冰川的父親練習登山的本領。此外,在意大利北部奧斯塔山谷里度假時,皮德羅還遇到了一個充滿冒險精神的當地男孩——青年牧民布魯諾。他們在一起度過了許多夏天,探索山脈的草地和山峰,從而產生了一段真摯而又持久的友誼,盡管他們后來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布魯諾留在山區經營農場,而彼德羅的人生卻通向了意大利以外的大山。
在隨后的那些年里,保羅逐漸對大山產生了深厚的情感,不只是阿爾卑斯,也包括后來他不斷征服的喜馬拉雅。父親去世之后,科涅蒂得知父親為他購置了一小塊土地,便與兒時的朋友一起在那里建造了一棟小屋。從此,那里仿佛成為他的家,同時也是他與朋友匯聚的場所。他們將它稱作“奇巖小屋”。大山也成為他心中的家園,以及他了解世界的方式。隨后,他經歷了朋友的牧場倒閉、朋友與女友的分手、朋友從“奇巖小屋”失蹤并死亡的一系列厄運。
讀者或許會將這部作品與梭羅在《瓦爾登湖》中描繪的小屋和隱居生活相比,但二者之間存在著本質的差異。保羅·科涅蒂并沒有將自己的生活局限在阿爾卑斯山區的那間小屋里面,而是從事著紀錄片導演的工作,與現實社會有著廣泛持久的接觸。只不過作為一個完全意義上的社會人,他始終需要給自己留出足夠的空間,以便與大山對話。在喜馬拉雅山期間,科涅蒂拍攝一些與當地人生活相關的紀錄片。與此同時,攀登雪山是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他了解該地生活、與同行者溝通并進一步了解人生的方式。當然,更多的是他對于山中生活的思考,是一個男人與大山之間的直接對話。
從表面上看,這是一部以山居生活為背景的傳統式小說,但作者以山景、父子親情、友誼與成年為主題娓娓道來,表現了自己對自然界的深刻洞察,以及由此產生的熱愛與眷戀。與前面分析的幾部作品相比,這部小說不再表現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抗爭與無奈,而是表現人類對大自然的融入與回歸。大山就是他心中的故鄉,也只有那里才可以為他提供救贖和慰藉。這種情感同樣體現了當代人回歸自然訴求的真實寫照,因為自然才是人類真正的家園。
四
與以上提到的這些類型的“故鄉”相比,在意大利語之父和文藝復興先驅之一的但丁心中,故鄉則完全不同。在他最偉大的俗語詩歌作品《神曲》中,但丁繼承前世幻游文學的傳統,描繪了一次穿越地獄、煉獄和天堂的旅行。其中最為引人入勝的當屬《地獄》篇。在那里,雖然但丁想象出各種殘忍的方法來懲罰生前犯下各種罪行的人,但敘述中充滿了各種真實生動的人類情感,而且充分體現了但丁作為詩人的巨大想象力。當但丁離開地獄,走上穿越煉獄和天堂的救贖之路后,就較少流露人類的情感波瀾和對塵世的眷戀,因為天國生活要求和諧與安靜。
在一片幽暗森林中迷途的但丁,受到古羅馬詩人維吉爾的引領,首先穿越了大體上分為九層和一個前庭的地獄。那里并非是一個真實的世界,但每個人物都是歷史上真實的存在,通過各自的故事與人世相連。
在這部詩歌作品中,但丁廣泛使用了象征和夢幻式的手法:出現在詩歌開篇之處的“幽暗森林”,象征著當時腐敗糜爛的基督教世界;他所遇到的三只猛獸,豹象征肉欲、獅子象征驕傲,母狼象征貪婪。由于三只野獸的阻擋,詩人不能直接登上那座象征現世的幸福的“令人喜悅的山”,而要在維吉爾的帶領下,經歷地獄、煉獄和天堂,方能得到重生。凡此種種,不勝枚舉。同時,對于其他文學作品和神話故事、民間傳說的引用,也使這部詩歌充滿了夢幻的色彩。各種人類、動物、神鬼彼此交織,真實與虛構的時代在地獄的各層中彼此交織,展開了各種最為不可思議的故事。從古代沒有受過基督教洗禮的異教徒、古羅馬的皇帝和偉大的詩人、古希臘的哲人和顯赫貴族,從歷代著名君主和名人到文學作品以及古希臘羅馬神話中的人物,再到生活在但丁同時代的莫斯卡·蘭貝蒂,甚至仍然在世就被但丁投入地獄第八層的教宗博尼法丘八世,因為他是造成但丁的長期流亡和客死異鄉的罪魁禍首,還有英國亨利二世時期的游吟詩人貝爾特蘭等。
但丁在《神曲·天堂》篇中展現了非凡的宇宙觀,即使是在《地獄》篇,他也憑借廣博的人文底蘊和深邃的思考,令敘事遠遠超出了個人與一個民族內心的戚戚,乘著想象的翅膀肆意馳騁。作為文學家和詩人,但丁具有豐富的想象力和創造力,而作為人文主義者和政治家,他又有超出常人甚至是一般文學家的見識與胸懷。在這部詩歌作品當中,但丁將個人的悲慘遭遇與佛羅倫薩共和國的多舛命運聯系在一起,希望通過個人的迷途、反思與悔過直至重生的經歷,對前世和現世各種“罪過”動情而又生動的展現與再創作,使讀者能夠以此為鑒,驅惡向善,達到社會的凈化和政治的清明,從而在政治和倫理道德等層面引領大家走上復興與救贖之路。但丁所展現的故鄉,并非僅限于他的佛羅倫薩或者意大利半島,也并非是他所生活的那個基督教世界,而是一個現實主義與浪漫情懷相結合的世界。
所謂故鄉,是我們心中那塊最期待與向往的土地。它不必與某個真實的地方相對應,卻又真實地存在,是現實的投射,是我們心靈的歸屬。這種現實與想象之間的交織,為作家的再創作提供了無限的空間,也是只有文學才能夠做到的。文學作品中的故鄉,是作家心靈之所依,心靈之所歸。
(作者:魏怡,系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