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生死場》:“潛能”、動物與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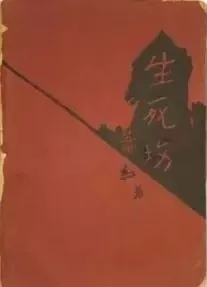
《生死場》(初版) 上海容光書局 1935年12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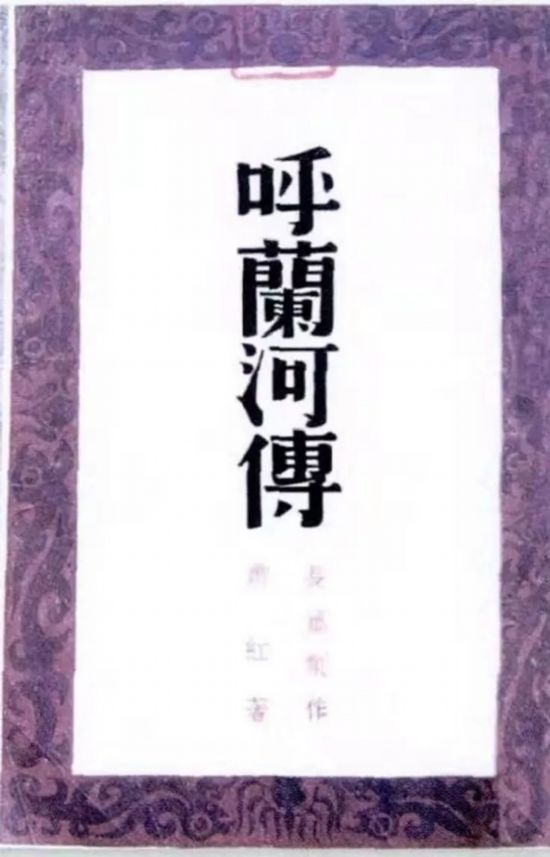
《呼蘭河傳》(初版) 桂林上海雜志公司1941年出版
一
長期以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對于蕭紅的小說《生死場》的解釋,大致由或可稱為“民族主義路向”和“女性主義路向”的兩種闡釋方式主導。如很多闡釋者已經指出的,在該小說出版時,由于魯迅的序言和胡風的讀后感,它立刻被同時代讀者接受為一篇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作品。這一路向的解讀中具有代表意義的,仍然是胡風當年的讀后感:“這些蟻子一樣的愚夫愚婦們就悲壯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戰爭的前線。蟻子似的為死而生的他們現在是巨人似的為生而死了。這寫的只是哈爾濱附近的一個偏僻的村莊,而且是覺醒的最初的階段,然而這里面是真實的受難的中國農民,是真實的野生的奮起。”[1]胡風旗幟鮮明的闡釋為后來許多讀者奠定了閱讀基調。例如,王瑤在上世紀80年代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稿》中關于《生死場》的論述便知:“一切善良樸實的人都站起來了,走上了民族戰爭的前線。這是農民們在最初階段的覺醒反抗的紀錄,從這里我們真切地看到了中國人民的不可征服的力量。”[2]盡管有著幾十年的間隔,這段論述和胡風當年的論斷如出一轍。
進入新時期以后,隨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范式的更迭和新的闡釋視角的引入,越來越多的闡釋者對民族主義闡釋提出異議。在他們看來,這種路向的閱讀根本上忽略了小說的真正關切。例如,劉禾指出,民族主義的讀法粗暴地忽視了蕭紅關于存在于中國社會歷史深處的父權制的反思和批判,而民族主義話語本身也不過是父權制的變體之一:
自打《生死場》作為魯迅發起的“奴隸社叢書”之一種發表后,這部作品的接受與評價,一直受民族國家話語的宰制,這種宰制試圖抹煞蕭紅對于民族主義的曖昧態度,以及她對男性挪用女性身體這一策略的顛覆。大多數評論者將它視為一部“民族寓言”,一部充滿愛國主義精神的反帝國主義作品。其結果是,今天人們如果意識不到那一高度發達的、體制化的、男性中心的批評傳統,就無法真正解讀蕭紅的創作,因為這種批評傳統限制并決定著對小說意義的理解。[3]
民族主義遠遠不是對于女性的解放;相反,民族主義與父權制之間的合謀,加強了兩性的等級制關系,并為男性維持其自身的社會優越地位提供了新的話語支持。《生死場》所強調的不是“蟻子似的”農民的“覺醒反抗”,而是“女性身體的困境”,是將女性的“受傷害的意義落實在此世當下的社會經濟語境中”[4];最終,“貧窮、無知、階級剝削、帝國主義以及父權制皆達成共謀關系,試圖使農村人民,特別是婦女,降低到動物的生存層次上。”[5]在劉禾的闡釋中,小說最后揭示的不是愛國主義的宣傳口號,而是女性的絕望狀態:
蕭紅并非不想抗日或對民族命運不關心——她的困境在于她所面對的不是一個而是兩個敵人:帝國主義和男性父權專制。后者會以多種多樣的方式重新發明自身,而民族革命亦不例外。[6]
如果說民族主義的闡釋傾向于從小說中讀出將農民團結起來的民族主義意識,那么女性主義闡釋,則通過重新強調上述闡釋忽略的作為個體的女性,通過從民族主義話語期待的集體性中撤回,通過強調女性拒絕被“升華”或“移植”為一個民族主義主體的可能性,而重審了《生死場》的關切所在。在這個意義上,蕭紅對女性身體的重視“導致了一種性別化的立場,該立場介入了小說表面上建立起來而實際上予以顛覆的民族主義話語”[7]。
同樣是從女性主義角度出發,并且在時間上稍早于劉禾的,是孟悅和戴錦華的解讀。但她們的閱讀重心與劉禾有所不同。在她們看來,小說整體上揭示的困境是女性身體的困境,也是“主體意識”誕生的困境:“《生死場》描寫的鄉土社會生活是沒有主體的生活,大多數人沒有像主體一樣的行動,相反,他們是被行動的,不僅被自然、被欲望,而且被歷史、被傳統、被因襲的觀念、被他人——行動。他們只能反應。”[8]根據孟悅和戴錦華,《生死場》之所以無法被完全理解為是對于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鼓吹,根本上不是因為蕭紅將民族主義視作父權制的另一種變體,而是因為對于蕭紅來說,“與30年代作品流行的模式——農民從昏睡到覺醒不同,蕭紅筆下的人眾之所以昏睡……是由于他們的生存樣態尚未剝離動物階段,他們的心理結構尚未進入主體階段。而這一切,與歷史輪回的自然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密不可分。”[9]孟悅和戴錦華的解讀與劉禾的解讀之間重要的差異,在于她們各自對于小說中“被壓迫者”的不同理解。在劉禾的解讀中,重要的議題始終是男性和女性的關系,尤其是男性利用父權制的種種話語來占有和攫取女性身體的過程;與之相對,在孟悅和戴錦華的解讀中,從動物向人轉化的主體性生成過程,最終解釋了農村中女性以及男性的悲慘生活。所以,在劉禾那里,民族主義的興起只能為既有的男女之間的不平等關系投下又一層陰霾;而對于孟悅和戴錦華,只有改變傳統的農村生產方式才能最終實現人從非主體向主體的轉化,這一過程的契機(而非完成)便是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路向”和“女性主義路向”這兩種闡釋路向的對峙,表明了《生死場》的復雜性:讀者在其中遭遇到許多相互交織、卻未必能統一起來的線索:傳統的鄉村生活與城市的對峙;日本侵略軍的暴行和由此引發的農村男女的反抗;男性和女性之間明顯的不對等關系;如此等等。讀完整部小說,讀者似乎很難得出一個貫通一氣的結論。如此也便能理解,為什么有論者認為,這部小說有太多的關切,“它們并不有機相連,而是彼此沖突。這種不連貫或不有機統一的根源在于作者對當時社會主次矛盾分得不清晰,或者說,她無力探究時代的三個主要社會矛盾的內在關聯:父權體制下的性別不平等、階級矛盾以及民族沖突。”[10]但反過來也可以認為,小說中呈現出來的“不連貫或不有機統一”,并不是源于作者無力分析(枉論解決)社會矛盾,而恰恰表明這個文本的復雜性無法被傳統意義上聚焦社會矛盾的分析閱讀所把握。
我認為,要貼近并把握《生死場》的復雜乃至“怪誕”,一個切入點是上述闡釋都未能充分考慮、在小說中卻表現得非常明顯的一個問題,即文本中人和動物的“無區分”狀態。換句話說,幾乎所有闡釋都假設了一個重要的、并非不證自明的前提:小說中的人物都有著穩定的身份同一性(identity)。[11]胡風等人的民族主義路向的闡釋自不待言——一種實質性的、穩定的民族身份同一性是民族主義話語的構成性要素;而這前提也可以在女性主義闡釋中找到。女性主義闡釋和民族主義闡釋的對峙,歸根結底只是兩種不同的身份同一性主張的對峙。例如,劉禾如此解讀二里半的“女性特征”:“就連那個離開自己的山羊就無法生活的二里半,最后也成為這樣的主體。與其他角色不同的是,二里半是個跛腳,因此可以說他的男性特征被象征性地閹割了;不僅如此,他同動物之間那種不尋常的依附關系,也使他的身份更接近女性。”[12]在什么意義上人們可以將二里半的“身份同一性”(被認為是接近“女性”而非“男性”)接受為一個給定的事實?“跛腳”何以能夠“象征性”意指“閹割”,而與動物的關系又何以能夠意指“身份更接近女性”——如果不是闡釋者首先在符號的意義上假定了某種“身份同一性”的意指鏈條的話?盡管劉禾試圖質疑民族主義闡釋中出現的那種“從個體通往集體”的平滑發展,強調女性身體對于民族主義話語的抵抗,她的落腳點卻還是“一種性別化的立場”,一種特定的、前反思狀態的“身份同一性”。稍顯夸張地說,劉禾的闡釋最終論證的,正是構成其出發點的“身份同一性”的特定預設。
類似地,在孟悅和戴錦華的解讀中,關鍵問題是改變所謂傳統的生產方式。如孟悅和戴錦華所述:“生命——不是一兩個人的生命而是這片鄉村中的群體生命——失去了任何意義,即便是其最初的、最原始的目的,也已然失落或退化。它們成了一種機械、習慣、毫無內容的自然—肉體程序,它們不再是生命,而是以生命現象顯示的停頓。這種停頓是歷史的停頓。”[13]這種有關生產方式的論述以近乎結構主義的方式規定了“身份同一性”:借助“生產方式”一詞(或借助該詞的含混性),孟悅和戴錦華得以將所謂的“無意義”生存放置到一個本身充滿意義的、從“非主體”向“主體”的轉化過程之中,于是所謂的“非主體”也就回溯性地獲得了“身份同一性”的規定。
因而,在上述種種闡釋中,小說里最顯然、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現之一——人和動物的無區分狀態——恰恰成了一個被輕易跨過的“門檻”,一個需要立即克服乃至遺忘的歷史階段。在這一點上,錢理群對于《生死場》的歷史意義的論述尤其具有代表性。他寫道:“蕭紅所要完成的,正是魯迅曾經提出過的歷史任務:真實地、歷史地寫出我們的民族、人民從‘個人主義’到‘集團主義’其間的橋梁。蕭紅的歷史貢獻也在這里。”[14]從“個人主義”向“集團主義”的轉變,代替了《生死場》中的從人和動物的無區分狀態向“人”的(非)轉變——放在作品發表時所處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高揚的時代背景下看,這一混淆似乎無可避免也無可厚非。
但我們需要問的是:有否可能在字面意義上直面《生死場》里人和動物的“無區分”狀態,有否可能在不預設任何一種給定的身份同一性的前提下接近這部小說 ?這一視角能向我們敞開何種新的閱讀視野?在我看來,這里的問題在哲學的意義上正與西方學界關于“動物性”論題的討論密切相關。
二
法國思想家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在《我所是的動物》中指出,人類社會的政治的成立前提是對動物的馴服:“占有、破壞、蓄養被馴服的家禽,便是人的社會化。人作為個體,為了確定其絕對自由,和野獸一樣要準備與其鄰居開戰。因此,離開了對于野生動物的馴化原則,就無從談及社會化、政治體制,或政治本身。”[15]德里達背后指向的,或許正是現代政治哲學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社會契約論傳統:人類社會進入政治共同體狀態,源于對于一個“前政治狀態”(自然狀態)的拋棄和否定。人性與動物性的分野,在契約論背景下,也可以被翻譯為一種內在于人性的政治分野。“社會契約”要求的對于自然權利的讓渡,同時也是對于(人的)動物性的(內在)克服——克服人在自然狀態下的生存狀態,一種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狀態,一種“人對人是狼”的狀態:一種“人性”與“動物性”在人的內部共存的“無區分”(indistinction)狀態。然而,在德里達看來,現代政治哲學傳統所預設的這種潛在的對于(人的)動物性的否定或克服,本身就需要重新討論,因為“動物性”和“人性”的形而上學區分是一種極其脆弱的區分。德里達介入政治哲學的契約論傳統的獨特視角,便是考察西方形而上學中出現的將人區別于動物的種種“邊界”,以及這些邊界的(非)有效性和多樣性。例如,德里達寫道:
在所謂的“人”的邊界之外(但絕不是指單獨的另一側),[我們能看到的]不是“動物”或“動物生命”,而是已經有多樣的、異質的生命,或更確切地說(因為說“生命”已經是要么意味著太多東西,要么說得還不夠),生命與死亡之關系的多樣的組織方式,這些不同領域之間的組織關系(或組織的缺乏),愈發難以被“有機/無機”、“生命和/或死亡”這樣的形象來分解。這些關系既相互纏繞又彼此隔閡,而且它們永遠也無法被全面客體化。它們彼此之間不存在任何單純的外在性。[16]
如果將德里達的形而上學關切翻譯為政治哲學表述,可以說,需要考察的正是所謂“前政治狀態”和“政治社會”狀態之間由“社會契約”所表征的“門檻”的多樣性和脆弱性,正是政治共同體和自然狀態之間不斷的相互滲透和彼此界定。德里達對于“動物性”問題的考察,向政治哲學提出的問題之一便是:如果社會契約從來就不是一個確定的“門檻”,我們對于政治共同體的理解、對于其中被定義的“政治主體”的理解會發生什么變化?如果從“前政治狀態”到“政治狀態”的轉變總是脆弱的、復數性的、充滿異質的,那么應該如何接近和把握現代性條件下的政治主體性及身份認同?
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批判性地延續了德里達的思考線索,并將問題轉入了另一個方向。在《敞開》一書中,阿甘本考察了他稱為西方形而上學傳統中人性論的“人類學機器”及其演變歷史。不過,與德里達不同,阿甘本認為,所謂“人性”和“動物性”的多重區分,事實上不是人性論的人類學機器的弱點,而是其構成性原則。因為,如果將“人性”規定為與“動物性”的對峙,我們會發現這一概念區分從來就不是清清楚楚的——正因為(而不是盡管)不清不楚,“人性”才被吊詭地“確定”了:人性的“無法規定”成了其本質“規定”。因此,阿甘本認為我們必須考察的問題是:“如果人總是不斷區隔和分裂的場所(同時也是其結果),那么什么是人”?“比起在所謂人權和價值這種大議題上表明立場,更緊迫的是考察這些區隔,追問人以何種方式(在人的內部)被與非人、與動物分離開來。”[17]正如論者所指出的,在考察人性與動物性的形而上學區分時,德里達與阿甘本的差異在于,前者認為“對立隱含了、甚至是要求一種二元差異,即被差異或異在性(alterity)空間所分離的兩項或兩個極端”,而后者則認為這里沒有二元對立,有的恰恰是一種“禁令(ban)關系,它不是一種純粹的他異性,而是一種包容性排斥”。[18]在德里達發現人性和動物性的清晰二元對立下潛藏的難題(aporia)之處,阿甘本看到的是支撐(而非解構)整個人類起源論機器的形而上學的否定性核心。在阿甘本勾勒的歷史中,這一否定性核心的代表論述之一,便是林奈分類學對于“人”的界定:“不通過任何確定性特征,而是通過其自我知識來界定人,意味著人是如其所是地辨認自己的存在,意味著人是必將自己辨認為人的動物。”[19]
人類從來不是通過一種清晰的界定、通過某種實質而與動物形成二元對立;相反,人和動物的概念都是由這架以“排斥性包容”或“包容性排斥”的運作機制為原則的人類學機器(再)生產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運作機制在阿甘本對于主權權力的探討中,構成了所謂“主權禁令”的現代性政治的邏輯。進一步,阿甘本的論述暗示,政治領域中與人類學機器中人性和動物性的“無區分”對應的,便是生命與法律的悖論性結合,這一結合不斷地(再)生產著主權權力下的“赤裸生命”。因而所謂人和動物的“無區分”,指的就不是單純的人與動物的混沌狀態甚或無序狀態,而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對于“動物性”的包括和否定,是政治上的“赤裸生命”背后的形而上學預設。于是,阿甘本對于人性論的人類學機器的探討,對于人和動物的“無區分”的探討,背后的關切就與他對于現代性條件下的政治狀況的思考休戚相關。通過考察“人類學機器”而探究解脫“主權禁令”的悖論結構之道,也成為“人性/動物性”這一形而上學問題的題中應有之義。對此,阿特爾(Kevin Attell)解釋道:“正如從虛假的例外狀態向真正的例外狀態的轉移需要真正打破那在主權禁令中將生命和法律綁在一起的(非)紐帶,此處人和動物的‘真正的’區隔,要求斬斷那個在所有模式的人的自定義(auto-definition)中都發揮作用的虛假連接。”[20]這里所謂“‘真正的’區隔”指的不是一種新的連接/定義人性和動物性的方式(無論人們可以做到多么精準而客觀),而是——再次借用阿甘本探討“主權禁令”時采用的措辭——一個“人類行為的非法律空間”,或者說,是一種“非行為”、一種失效性(inoperativity)。[21]
這種“失效性”關系(如果它仍然可以被看作一種關系),與阿甘本對于“純粹潛能”的討論密切相關。這也就是為什么《敞開》一書在考察了“人類學機器”的歷史之后,阿甘本花了很大篇幅探討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的《形而上學的根本概念》。海德格爾從比較研究的角度出發,提出了著名的三個命題:人是形成世界的(weltbildend),動物是缺少世界的(weltarm),而石頭是沒有世界的(weltlos)。[22]海德格爾強調,他所謂的“缺少世界”,不是一種關于動物比人類低級的等級制的評價;相反,“缺少世界”意味著一種與世界的特殊關系,一種特有的開放性:“世界首先指的是人和動物都可及的存在物整體,盡管在范圍和滲透度上有別。因此,在‘形成世界’的更高價值看來,‘缺少世界’是低級的。”[23]構成動物的特殊存在方式的,是一種“去抑制”的“圈環”:
這一自我環繞是動物的根本能力,所有其他能力似乎都整合到其中,并從中生長出來。有機體的組織方式并不在于其形體的、生理的構型,或其力量的形成和管理,而首先恰恰體現于自我環繞的根本能力,這種能力也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敞開、向一個限定范圍內的去抑制可能性的敞開。[24]
動物被賦予的能力,注定要以特殊的、被規定的方式將它們和它們的環境連接在一起。于是,動物性的能力就只能是本能的;動物的各種能力,總起來說,是一種無法不加以實現的“潛能”。[25]
正是通過對“潛能”一詞的關注,阿甘本介入了海德格爾關于動物和“此在”的討論。與動物的“去抑制的圈環”相對,“人類世界的敞開,”阿甘本寫道,“只能通過一種作用于動物世界的‘非敞開性’的機制而實現。而這一機制的場所(在此,人的敞開性和動物向其‘去抑制’的敞開有一瞬間相遇了),便是無聊。”[26]“無聊”指向的是海德格爾在“研討班”第一部分中討論過的“深刻的無聊”這一情緒;阿甘本認為,這種深刻的無聊蘊含的正是“具體可能性”的“失效”(deactivation),它“第一次向我們展現了那個在一般意義上將純粹的可能性變得可能的東西——或如海德格爾所說,[它展現的是]‘原初的可能化’”[27]。
如果追隨海德格爾的上述思考,那么可以說“此在”的敞開性(向純粹可能性的敞開)也只能通過對于動物的“不純粹的”敞開性的理解而得到間接認識——甚至可以說,“此在”的“敞開”僅僅是對于動物的“非敞開”的認識。為了讓“可能性”作為“純粹可能性(潛能)”呈現出來,“此在”必定要在自身內部以“包容性排斥”或“排斥性包容”的方式保留動物性的痕跡。阿甘本寫道:“敞開不過是對動物的‘非敞開’的把握。人懸置其動物性,并由此打開了一個‘自由而空洞’的空間,在其中生命被捕捉和拋棄(a-bandoned)在一個例外空間里。”[28]“此在”恰恰是通過對于動物性的“禁令”般的否定過程而被生產出來的——“此在”對于“純粹可能性”的呈現是第二位的;在人性和動物性的論題上,面對以“包容性排斥”為原則的人類學機器,經由動物的“非敞開”而通達“此在”的“敞開”,不過是以極端的形式生產了“禁令”結構的又一個變體。那么,如果“此在”構成了人類學“禁令”的形象,“純粹潛能”的形象可以是什么?在拆解阿甘本所謂“人類學機器”的政治—本體論裝置的努力中,文學又可以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三
“一只山羊在大道邊嚙嚼榆樹的根端。”[29]這是《生死場》的第一句話。這只羊是二里半和她妻子在找的走失的羊。自始至終,讀者都不知道這只羊的確切位置;只能說,這只羊既不在它“應有的位置”(羊圈)那里,也不是完全離開了村莊。于是,敘事者的位置和羊在一起,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暗示了敘事者占據的位置:一個既非內部、也非外部的“居間”位置。這只走失的羊在整部小說中始終若隱若現,而它出現時的軌跡似乎也與小說敘述的整體基調相關。例如,敘事者告訴我們:
山羊寂寞著,山羊完成了它的午睡,完成了它的樹皮餐,而歸家去了。山羊沒有歸家,它經過每棵高樹,也聽遍了每張葉子的刷鳴,山羊也要進城嗎!它奔向進城的大道。(第227頁;強調為引者所加)
在第一句話的結尾,山羊似乎是回家了;但下一句話立即“否定”了這一“事實”并給出了另一個“事實”:山羊沒有回家。從小說一開始,讀者似乎便面臨著非矛盾律的形式邏輯被懸置的狀況。與其說這里敘事者給出了兩個同樣成立的矛盾事實,不如說被懸置的是邏輯—語義的必然性:“歸家”的山羊沒有“歸家”,“奔向進城的大道”也不一定意味著“進城”——重要的不是山羊的具體位置,而是其無法被確定位置的“移動性”;同樣,在語言層面上,可以說比起被表達的具體內容,更重要的是文學語言的“可表達性”。正因為占據了一個類似于“會旅行的山羊”(第228頁)的位置,敘事者能夠對于村莊里的人們的生活做出概括性判斷:
在鄉村永久不曉得,永久體驗不到靈魂,只有物質來充實她們。(第254頁)
“靈魂”和“物質”的二元對立顯然超出了小說中敘述的農村男女的語詞范圍,它處于小說的“外部”。由于敘事者占據的是一個“居間”位置,那么在引入“靈魂/物質”這組對立時,敘事者也不能完全站在“外部”對村莊進行價值判斷。所以,與其說作者在一個高處為她所描寫的這個村莊下判斷,不如說她讓我們有機會從村莊“內部”出發,重新審視“靈魂/肉體”這組陳舊對立。于是,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被“物質”充盈、“充實”的世界:一個“充實”的世界,不是“匱乏”的世界。然而,迄今為止的絕大多數闡釋者,都力圖將“充實”翻轉為“匱乏”:例如,女性主義的闡釋者會把“物質”轉寫為男性對于女性的壓迫性權力,而民族主義闡釋者則會強調“靈魂”背后的集體自覺。
物質的充實性,指的當然不是他們生活上的富裕:小說中描寫的農村生活里充滿了貧窮、暴力、饑餓、停滯。這里的“物質”,在最明顯的意義上,指的恐怕只能是農民們的身體行為,其中最突出的兩項便是生育和勞作。人們勞作以求活著,生育以求延續香火。但在小說中,這兩項行為都立即被納入到死亡的范疇之中。歸根結底,充實人們生活的物質是“死亡”這一非物質性的“物質”。
在小說中,“死亡”不僅指向個人的身體性死亡(生育常常直接聯系著死亡),而且“歷史”構成了“死亡”的另一個名稱。例如,在描述被送到屠宰場的老馬時,敘事者強調了歷史對于這個動物的存在方式的規定性:
馬靜靜地停在那里,連尾巴也不甩擺一下。也不去用嘴觸一觸“石磙”,就連眼睛它也不遠看一下,同時它也不怕什么工作,工作來的時候,它就安心去開始……主人打了它,用鞭子,或是用別的什么,但是它并不暴跳,因為一切過去的年代規定了它。(第234頁)
這段描述很容易與敘事者對于整個村莊的判斷形成呼應,并在一定程度上為民族主義的闡釋提供理據——尤其是,小說的第十一節旗幟鮮明地以“年輪轉動了”作為標題,似乎在提醒讀者留意日軍侵略前后村莊里的生活所發生的劇烈變化。不僅以胡風為代表的闡釋者將焦點放在十一節以后的部分,孟悅和戴錦華也寫道:“這一歷史的輪回是在侵略者的踐踏下戛然而止的……在侵略者的鐵蹄下,演出了幾千年的自然輪回的生產方式巨型戲劇宣告結束。”[30]但是,小說中展現的情形卻是:日軍侵略只是為“死亡”賦予了新的暴力形式——
三歲孩子菱花小脖頸和祖母并排懸著,高掛起正像兩條瘦魚。死亡率在村中又在開始快速,但是人們不怎樣覺察,患者傳染病一般地全鄉村又在昏迷中掙扎。(第317頁)
同樣,當金枝經驗了城市生活的可怕后回到村莊,她一眼看到的景象不是日軍侵略,不是村民們的反抗,而是死亡:“金枝勇敢地走進都市,羞恨又把她趕回了鄉村,在村頭的大樹枝上發現人頭。一種感覺通過骨髓麻寒她全身的皮膚,那是怎樣可怕,血浸的人頭!”(第313頁)在敘事者呈現給讀者的金枝的直接經驗中,李青山殺死日本侵略者的愛國行為沒有被直接升華為激情和愛國心,而僅僅是對于一個可怕的死亡意象的感知。掛在樹上的人頭這一怪誕場面既超出了民族主義話語,也超出了女性主義話語的闡釋。
闡釋者們似乎無法承擔如下可能性:在整個村莊中,被死亡收編的生命從來都是沒有意義的,而恰恰是這“無意義”(meaninglessness)構成了整部小說的意義(significance)。那么,在不假設一種積極的、確定的“身份同一性”的情況下,如何理解小說中作為徹底虛無的“死亡”?
四
上述問題的鑰匙便在于小說中人和動物的“無區分”狀態。在小說中,二里半沒有對趙三等人的民族主義熱情抱有絲毫熱情:“只有二里半在人們宣誓之后快要殺羊時他才回來。從什么地方他捉一只公雞來!只有他沒曾宣誓,對于國亡,他似乎沒什么傷心。他領著山羊,就回家去”(第302頁)。在小說的結尾,當二里半也不得不告別自己的羊時,敘事者為其告別場景賦予了一層濃厚的宗教色彩:
這是二里半臨行的前夜。
老羊嗚叫著回來,胡子間掛了野草,在欄棚處擦得柵欄響。二里半手中的刀,舉得比頭還高,他朝向欄桿走去。
菜刀飛出去,喳啦的砍倒了小樹。
老羊走過來,在他的腿間搔癢。二里半許久許久的摸撫羊頭,他十分羞愧,好像耶穌教徒一般向羊禱告。(第322頁)
二里半并不是出于基督徒的負罪感而向他的羊禱告。讀者或許會將敘事者所加的這層宗教修辭翻譯為日常語言所理解的農民與牲口之間的“感情”。可是,敘事者早已告訴我們,這個村莊“永久不曉得,永久體驗不到靈魂”——于是,這里的宗教措辭不僅顯得不合時宜,而且頗為怪誕。
二里半找了公雞來代替羊作為獻祭品的舉止,在《圣經》中可以找到一個不算牽強的對應,即亞伯拉罕獻祭以撒的故事。上帝要求亞伯拉罕將自己唯一的兒子作為祭品帶到山上殺死,亞伯拉罕默默從命。在他將兒子帶到山上準備動手時,從天而降的天使阻止了亞伯拉罕:“亞伯拉罕舉目觀看,不料,有一只公羊,兩角扣在稠密的小樹中,亞伯拉罕就取了那公羊來,獻為燔祭,代替他的兒子”(《創世紀》22:13;和合本譯文)。與之相對,在《生死場》里是山羊被從祭壇上救了下來。如果說在《創世紀》里人和動物的等級關系一開始就被確定了的話,那么這只“不可獻祭”的山羊表明,在一個只有“物質”而沒有“靈魂”的空間,一切看似“自然”的事物都得以被重新考察:人和動物的關系,被從“自然的”理解上剝離開來,進行扭曲、翻轉、顛倒。因此,敘事者略顯突兀的宗教修辭,強調的不是農村的“精神”面向,而是在一個沒有“精神”面向的世界中人和動物的可能關系。
《生死場》有不少地方表明,在這個村莊里,人和動物的界線非常模糊。例如,敘事者在描寫麻面婆時,使用了熊和豬的比喻:“頭發飄了滿臉,那樣,麻面婆是一只母熊了!母熊帶著草類進洞”(第225頁)。同樣,在描述二里半時,我們看到:
[二里半]絞上水桶,他伏身到井邊喝水,水在喉中有聲,像是馬在喝。(第226頁)
咩……咩……羊叫?不是羊叫,尋羊的人叫,二里半比別人叫出更大聲,那不像是羊叫,像是一條牛了!(第227頁)
二里半迎面來了。他的長形的臉孔配起擺動的身子來,有點像一個馴順的猿猴。(第229頁)
在這里,人和動物的類比從來不是單向而確定的。我們面對的始終是人與動物的多重類比。比喻之間的快速轉換,展現的不僅是人和動物之間的模糊界線,而且是人物的“身份同一性”的模糊甚至崩塌。德勒茲(Gilles Deleuze)所論述的“去地域化”,可以幫助說明這里的人和動物的關系:“人和動物都不復存在,因為兩者都在一個流動的結合中、在一個可逆的種種強度的連續體中,將對方去地域化了。如今需要考察的是這樣一種生成過程,它將最大限度的差異都作為強度的差異包括其中。”[31]我們把《生死場》中的人和動物的流動性類比,命名為“成為動物”的過程。這一過程指的不是從一個穩定的身份(人)變為另一種穩定的身份(動物);相反,它勾勒出一條運動和強度的軌跡,使得“一切形式,一切意指,一切能指和所指都在其中被拆解”[32]。其結果,是一個身份同一性在其中無法確立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垂直關系的隱喻、總體化、典型化、集體化都不復存在,存在的僅有水平關系的運動、強度、回響和臨時的組合與折疊。
“成為動物”的過程的典型場景之一,無疑是金枝的性行為場面:
五分鐘過后,姑娘仍和小雞一般,被野獸壓在那里。男人著了瘋!他的大手敵意一般地捉緊另一塊肉體,想要吞食那塊肉體,想要破壞那塊熱的肉。盡管的充漲了血管,仿佛他是在一條白的死尸上面跳動,女人赤白的圓形的腿子,不能盤結住他。于是一切音響從兩個貪婪著的怪物身上創造出來。(第236頁)
如果所謂“精神”和“物質”的聯系在整個村莊中都是缺席的,那么剩下的只能是一個只在“物質”層面、在水平而非垂直層面展開的運動和變形:一個“成為動物”的運動。所以,在這一場景中一開始呈現為金枝和男人的不平等的性別關系的關系,最后變成了“兩個貪婪著的怪物”之間的“平等”關系。一方面,兩個人的性行為生產出“一切音響”,從人的聲音和意指范圍中抽離出來、“去地域化”的聲響——這些聲響的“純粹的”物質性表現在,它們打斷、掙脫、拆除了聲音和意義的聯系,它們是非意指的聲音,是連接兩個“怪物”而不在兩者間架設起任何認同關系的聲響。另一方面,這一性行為將兩個身體化約為各個“器官”或“部分”,轉化為純粹的肉體:金枝是一只小雞、一塊肉體、一具死尸;男人是野獸,是怪物,是充漲了的血管。
“成為動物”的過程不是以某種“主體意識”為基礎進行的過程,更不是“自由意志”的結果;相反,它始終是被動性的產物——在小說中,生育尤其體現出“被動性”。“成為動物”的過程的“推動者”,不是農民自身,更不是動物,而是彌漫在整個村莊、把生命的一切行為都吞噬其中的“死亡”。而就死亡及其帶來的“被動性”來說,《生死場》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關于死亡的場景,無疑是月英的死。出于其重要性,小說中關于月英的死亡的段落值得一段較長的引用:
[月英]的眼睛,白眼珠完全變綠,整齊的一排前齒也完全變綠,她的頭發燒焦了似的,緊貼住頭皮。她像一頭患病的貓兒,孤獨而無望。
王婆給月英圍好一張被子在腰間,月英說:
“看看我的身下,臟污死啦!”
王婆下地用條枝攏了盆火,火盆騰著煙放在月英身后。王婆打開她的被子時,看見那一些排泄物淹浸了那座小小的骨盆。五姑姑扶住月英的腰,但是仍然使人心楚的呼喚!
“唉喲,我的娘!……唉喲疼呀!”
她的腿像一雙白色的竹竿平行著伸在前面。她的骨架在炕上正確地做成一個直角,這完全用線條組成的人形,只有頭闊大些,頭在身子上仿佛是一個燈籠掛在桿頭。
王婆用麥草揩著她的身子。最后用一塊濕布為她擦著。五姑姑在背后把她抱起來,當擦臀部下時,王婆覺得有小小白色的東西落到手上,會蠕行似的。借著火盆邊的火光去細看,知道那是一些小蛆蟲,她知道月英的臀下是腐了,小蟲在那里活躍。月英的身體將變成小蟲們的洞穴!(第257頁)
月英在三天后去世并被葬在荒山下。無論是民族主義闡釋還是女性主義闡釋,面對月英的死亡過程,似乎都只能抽象地從人道主義立場控訴封建社會或男權制度的暴力壓迫——無論如何,月英的死亡的場面過于“怪誕”了。
從頭發、眼睛到牙齒、下體——月英身體的所有部分都在經歷變化。最富戲劇性的變化當屬她的下半身:它在經歷腐敗之后,變成了蛆蟲的巢穴。“成為動物”的過程,在這里達到了一個高潮,因為月英身體的變化不是一個確切意義上的“身份同一性”的變化,甚至不是從活人到死尸的變化;毋寧說我們看到的是“生成”本身的具象化。蛆蟲從月英的身體得到營養和繁衍的處所,同時使月英這具身體不再是“人”的身體——月英自己的身體,這最為“屬己的”部分,變成異己的、外在的東西,變成她所不是的東西:她無法再與自己的身體構成“同一”。月英的身體變化在“生成”的意義上令民族國家話語設想的國民身體和女性主義話語設想的女性身體不再運作;月英的過于細節化的、甚至是過于“緩慢”的死亡,無法被獻祭為辯證法的否定性環節,也無法被確立為反抗父權制的實體性基礎。月英的轉變過程既取消了她作為“人”的身份同一性,也沒有重新為這一怪誕的存在賦予新的同一性。我們當然可以而且應該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譴責農村社會對于女性的冷漠、壓抑;但道德判斷無法穿透和把握月英的身體變化過程:這一怪誕的景象,始終處在道德判斷的彼岸。
在其創作生涯后期寫下的《呼蘭河傳》的尾聲中,蕭紅描繪了一幅與上述“純粹潛能”的文學空間相呼應的、像是“世界盡頭”的景象:一個脫離了意義的世界,一個“潛能”的世界——
呼蘭河這小城里邊,以前住著我的祖父,現在埋著我的祖父。
……
從前那后花園的主人,而今不見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園里的蝴蝶,螞蚱,蜻蜓,也許還是年年仍舊,也許現在完全荒涼了。
小黃瓜,大倭瓜,也許還是年年地種著,也許現在根本沒有了。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還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間的太陽是不是還照著那大向日葵,那黃昏時候的紅霞是不是還會一會工夫變出來一匹馬來,一會工夫變出來一匹狗來,那么變著。
這一些不能想象了。
聽說有二伯死了。
老廚子就是活著年紀也不小了。
東鄰西舍也都不知怎樣了。
至于那磨房里的磨倌,至今究竟如何,則完全不曉得了。
以上我所寫的并沒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們充滿我幼年的記憶,忘卻不了,難以忘卻,就記在這里了。[33]
敘事者似乎列舉了很多記憶里的事項,似乎給出了一個詳盡的描述,可在其描述中沒有一樣事物是穩定而可靠的,盡管它們都是具體的、物質性的東西:這是一個除了“無”之外一無所有的世界。老主人死了,小主人走了,有二伯死了,老廚子就算活著也老了。其他活物的存在也被懸置在空中——就連空中的云都是不確定的。在講述其故鄉發生的事件之后,敘事者最終將一切都收束在一個逐漸消失的空洞之中。《呼蘭河傳》沒有像《生死場》那樣把“潛能”改寫為“死亡”,而是將之體現為“寫作”本身:敘事者的記憶充滿了各種東西,但它們的確定性都懸而未決;唯一確定的,只有留在紙上的這些蹤跡。然而,敘事者并不是出于創造性或想象力而將其所思所想如是寫下,因為這些懸而未決的事物恰恰是她“不能想象”的事物——她寫下這些曖昧晦澀的東西,這些近乎非物質的物質,因為她“忘卻不了,難以忘卻”(這里我們再次見到了《生死場》的敘事中那種纏繞的、近乎自我否定的句法)。敘事者無法不寫作,同時她也無法將寫作作為客觀化的認識事物的手段。于是,這些寫作留下的蹤跡,指向的就不是日常理解的語言與事物之間的指涉關系,而恰恰是將這種對于語言的日常理解進行懸置,將語言的存在、語言的物質性重新變成思考的對象。在如此展現的文學空間內,取消了“身份同一性”之后的人物和取消了存在的確定性之后的事物,都共處于一個無法“前進”,無法“發展”,也無法“辨證運動”的世界之中:一個無法得到“實現”的“純粹潛能”的世界。
但這個既不前進也不發展的非辯證的世界,絕不是一個靜止封閉的世界;相反,它是生命形式的一切翻轉、變形、生成、折疊的可能性前提,將一切“實現”的可能性都塌縮其中的世界:“記憶既不是已經發生的事,也不是未曾發生的事,而是它們的潛能化,是事情‘再次成為可能’。”[34]
參考文獻:
[1] 胡風:《讀后記》(1935年);見《蕭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325頁。
[2] 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第294頁。
[3] 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1900-1937)》,宋偉杰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287頁。
[4] 同上,第290頁。
[5] 同上。
[6] 同上,第301頁。
[7] 同上,第285頁。
[8]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頁。
[9] 同上。
[10] 王曉平:《重讀蕭紅的〈生死場〉與〈呼蘭河傳〉》,載《文藝理論與批評》2011年1期,第88頁。
[11] 有人或許會說:小說中的人物是農民,是男人,是女人,這是再明確不過的事情。的確,這些身份同一性是小說得以展開的基礎和起點,但這一反駁回避了整個問題:我認為需要探討的恰恰是小說中呈現的人和動物的“無區分”狀態對于身份同一性的動搖乃至瓦解,而不是固守于既有的身份同一性來對小說情節進行道德意義上的評價。
[12] 劉禾,前揭,第298頁。
[13] 孟悅、戴錦華,前揭,第179頁。
[14] 錢理群:《“改造民族靈魂的文學”——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周年與蕭紅誕辰七十周年》,載《十月》,1982年第1期,第234頁。
[15] Jacques Derrida, 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 trans. David Will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96.
[16] Ibid., p. 3;強調為原文所有。
[17] Giorgio Agamben, The Open: Man and Animal, trans. Kevin Attel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6;強調為引者所加。
[18] See Kevin Attell, Giorgio Agamben: Beyond the Threshold of Deconstruction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89.
[19] Agamben, The Open, op cit., p. 26;強調為原文所有。
[20] Attell, Giorgio Agamben, op cit., p. 174.
[21] 參考Attell,同上,第173-174頁;第259頁。
[22] Martin Heidegger,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Metaphysics: World, Finitude, Solitude, trans. William McNeill and Nicholas Walker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77.
[23] Ibid., p. 193.
[24] Ibid., p. 258.
[25] Ibid., p. 218ff.
[26] Agamben, The Open, op cit., p. 62.
[27] Ibid., p. 66.
[28] Ibid., p. 79.
[29] 蕭紅:《生死場》,見《蕭紅文集》,前揭,第223頁;以下引自該書處的引文,皆在文中括號內標注頁碼,不另作注。
[30] 孟悅、戴錦華,前揭,第180頁。
[31]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trans. Dana Pola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p. 22.
[32] See ibid., p. 13.
[33] 蕭紅:《生死場·呼蘭河傳》,江蘇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294頁。
[34] Giorgio Agamben, Potentialities: Collected Essays in Philosophy, trans. Daniel Heller-Roaze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