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諾獎周”開啟,漢德克與托卡爾丘克發表獲獎演說,“我們缺乏講述世界故事的新方法”

瑞典當地時間12月6日,2019年“諾獎周”開啟,獲獎者陸續到達斯德哥爾摩,參與為期一周的系列活動,這些活動包括新聞發布會、獲獎主題演講、頒獎儀式、跨界藝術活動、校園交流等等環節。其中,主題演講已于昨日開啟,正式頒獎儀式則定于12月10日。
相比傳統諾獎頒獎活動,如今為了提振諾獎的形象以及提高新媒體傳播效應,諾獎官方近兩年采取了多種措施,包括更新諾獎視覺字體、新媒體視覺設計以及將頒獎活動豐富延展到為期一周的時長。
10月10日揭曉的兩位諾獎文學獎獲獎作家,引發了全球媒體持續的討論,在奧地利作家彼得·漢德克與波蘭女作家奧爾加·托卡爾丘克身上,大家都看到了文學內外不同話題的交織和爭論。
北京時間今日凌晨,彼得·漢德克與奧爾加·托卡爾丘克在現場分別以德語和波蘭語帶來獲獎主題演講。下面我們選譯主要觀點分享給大家。

彼得·漢德克
要允許自己失敗,給自己足夠長的時間去行走去觀察,不要忽略身邊一草一樹給自己的啟示,也不要為了一點人生成就而淪陷其中。
彼得·漢德克在演講開頭首先回憶起了自己四十多年前寫的一首詩歌的開頭,那里似乎隱藏著他早期對文學乃至人生的態度,“觀察世界,不必把所有事情都圍繞著自我;迎接挑戰,但也別預設什么結果”,他告訴自己,同時也在告訴讀者,要允許自己失敗,給自己足夠長的時間去行走去觀察,不要忽略身邊一草一樹給自己的啟示,也不要為了一點人生成就而淪陷其中。
顯然,當漢德克回憶起自己這些久遠的詩句時,他和眼前獲得諾獎產生了某種關聯,從揭曉諾獎消息公布后,他就承擔了無數的爭議乃至非議,過去幾年里他對一些公共事件態度的曖昧,招致了許多批評,認為他并沒有很好地發揮一個世界級作家應有的作用,但他似乎在等待一次解釋的機會,比如這次諾獎主題演講。
他首先回顧了自己的成長記憶,他在現場說,自己的童年時代有大量時間是母親陪伴的,母親一次次對他講述著村莊里的人事,多年后他回想起來,那就像是歌德所說的“獨特的聲音”,這些聲音深深進入了他的記憶里,乃至形成性格的一部分。他依然能夠完整復述其中一些故事,比如一個有智力缺陷的擠奶女工,自己與農場主的私生子被奪走,多年后,那個男孩被農場鐵絲網卡住,她救下之后默默離開,但那雙溫暖柔和的手卻被男孩永遠記住了。
故鄉的時間線里,戰爭記憶同樣是無法逃避的問題,漢德克在之前作品中多次植入了自己親戚參與戰爭而后歸鄉的經歷,但有些人則永遠落在了異國的土壤之中。漢德克提到自己在寫作中扮演了這樣一個鄉村后代者的記憶,這些記憶逐漸形成了某些精神,也支撐起了無數人在新時代的生活,漢德克形容說那之后“真正的絕望”很難再襲來了,“我們可能是世界上最脆弱和短暫的事物,也能化身最包羅萬象的武器”。戰爭與和平不僅貫穿了20世紀,也同樣存在于21世紀的今天,漢德克對此并不陌生,他接下去說到了自己對和平的看法,自然的色彩、個人的創造、孤獨的忍耐、藝術的推動等等,都將推動人類更好迎接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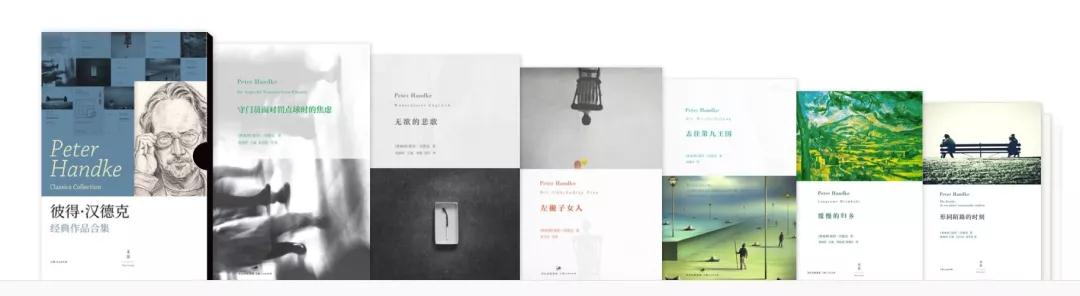
彼得·漢德克經典作品合集(套裝共8冊) 世紀文景2019年
從母親的聲音到藝術的創造,這些都被漢德克視為自己一生追求的動力之源,他感謝創作帶給自己的能量,也同樣感謝繪畫、電影(他提到了小津安二郎的東方影像)、音樂(比如萊昂納德·科恩等人)等藝術形式帶給自己的啟示。漢德克希望傳遞給外界一個信息,他并非如一些人所認為的冷漠乃至難以理解,相反,他時常被一些細微的瞬間感動,只不過,他并不常常公開講述這些。
前段時間,漢德克在挪威奧斯陸旅居,有一個夜晚他在一家海濱的酒吧里,聽到一個男人即興朗誦起了幾首自己寫的愛情詩,之后他走出酒吧,獨自在空蕩蕩的街道閑逛,在一家櫥窗依然亮燈的書店前,他看到一個青年望著櫥窗里的書,他轉過頭欣喜地告訴漢德克,那里面有他的新書。那是一張極為年輕的面孔,充滿了朝氣。這是漢德克演講的尾聲,文學的溫暖停留在這兩個男人的故事里,也是文學落在漢德克的人生里,他最想感謝的部分。

奧爾加·托卡爾丘克
我們缺乏新的語言、觀點、隱喻,用著古老的過時的敘事在形容新世界,我們缺乏講述世界故事的新方法。
奧爾加·托卡爾丘克為自己的演講取了一個標題,溫柔的講述者。她也從童年回憶開始,一張母親誕下自己之前的照片喚起了她無數想象。那張黑白照片上有著柔和如春天的光線,母親坐在收音機旁收聽的瞬間被記錄于此。而那個綠色的收音機,日后也成為托卡爾丘克最棒的童年伴侶,從中她獲知了宇宙的存在和幻化,烏木色的旋鈕,轉出了華沙、倫敦、紐約、盧森堡等地方的故事。有時候不夠穩定的無線電產生了斷斷續續的聲音,這讓托卡爾丘克感到莫名的好奇和震動,她甚至以為,那是神秘的宇宙和其他城市的人們在向她傳遞著某些信息,那時她毫無能力進行解密。直到,她終于成為了一個作家。
至于那張照片,托卡爾丘克說,那一刻,母親一定也在通過旋鈕在尋找她,確定她將何時來到世間。日后,她問母親當時在想什么,母親說在想念她,她反問,你怎么能想念一個不存在的“我”?母親回應說,相反,我知道你在那里,只不過暫時迷路了。
這段發生于上世紀60年代一個波蘭普通家庭里的對話,給托卡爾丘克積蓄了畢生的力量,使她相信自己的存在超越了因果和概率,超越了時間,成為永恒的甜蜜的存在。是母親賦予了她“靈魂”,促使她成為今天自己眼中的“溫柔的講述者”。
面對今天這個由無數新媒體信息交織的世界,托卡爾丘克說那些信息被無數形式所承載,但依然是在講故事,世界仍然是那個由文字定義的世界。但最大的問題是,編織故事的人已經沒有那么有魅力了,“我們缺乏新的語言、觀點、隱喻,用著古老的過時的敘事在形容新世界,我們缺乏講述世界故事的新方法”。
前不久托卡爾丘克參加了法蘭克福書展,她說自己看到了無數新書在講述自己的故事、家族的故事,這得益于這個時代給了所有人表達自己的機會,過去掌握在少數人手里的語言講述如今普遍化了,然而,他們講述的故事卻并不那么具有普遍性,她說,或許他們只是缺乏寓言性,寓言的傳統保證了個人色彩,也能尋求迥然不同的命運的共同點,“但是如今我們忘了這個傳統,成為當下最大的無助”。書展給了托卡爾丘克另一個感受是,越來越細化的文學市場造就了被強行分割的作家和讀者群,讀者不再關心豐富的文學,而僅僅聚焦于自己感興趣的那一部分,“類型文學越來越像一種蛋糕模具,產生了非常相似的結果,其可預測性被視為一種美德,其平庸成為一種成就。讀者知道會發生什么,并確切地得到了他想要的。我一直在直覺上反對這樣的現象,因為它限制了閱讀的自由”。
進一步,托卡爾丘克批評了網絡大數據帶來的知識假象,她認為大眾如今只能看到被編程被定義的定制化信息,卻認為自己看到了全部。信息呈現的虛構部分越來越多,反而讓非虛構文學獲得了更大的發展空間,小說開始失去讀者的信任感,以至于她許多次被讀者面對面問到,“你寫的這句話真的發生過嗎?”那一刻,她絕望地認為小說被終結了。

奧爾加·托卡爾丘克中文作品,包括即將推出的《云游》 后浪|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
因而,對于小說的無數現代定義和劃分,都難以讓托卡爾丘克感到滿意,她只相信一種定義,那就是亞里士多德時代的古老的故事,那時人們相信這里面存在著真理。小說在今天還能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是的可以,并且托卡爾丘克認為是非常重要的角色,20世紀電影電視出現的時候,人們以為文學的講述形式沒必要存在了,但今天回看那是一種假象,今天的新媒體世界也是如此,太多扁平化的信息籠罩大眾,諸如像“地球是平的”、“疫苗在殺死更多人”、“氣候變化是騙局”等等觀點大行其道,世界不是擁有太多東西,而是缺少了某些東西,而這,正是小說需要承擔的責任之一。
過去認為,獲取知識不僅會給人們帶來幸福、健康,還將創造一個美好的社會,但今天的知識被各種方式曲解了,托卡爾丘克承認如今講故事的方式需要從新的科學技術環境里汲取些靈感,但根本還是在于建立在共情共鳴之上的誠實,讓彼此的經驗互相傳遞,甚至到達尚未出生的人。世界已然在淪為碎片,而文學可以激發讀者的整體意識,恢復從細小事物中看見整個星球的能力。
最后,她說,“這就是為什么我認為我必須講一些故事,好像這個世界是一個依然鮮活的、完整的實體,在我們的眼前不斷顯現,好像我們就是其中一個個微小但強大的部分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