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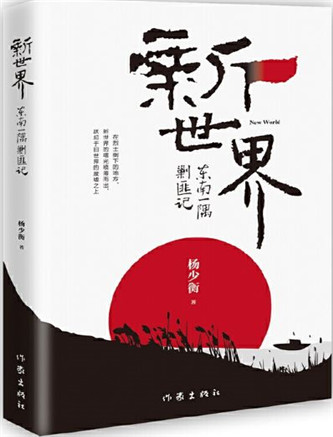
作者:楊少衡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9年07月 ISBN:9787521205060
第一章?小猴子
一個黑衣黑褲男子忽然從巷口閃出,對王拓揚了揚手。
“甲渾甲渾。”男子道。
王拓聽不懂土話,面露詫異。男子朝他舉手,左手掌上有一只煙匣子,原來是請抽煙。王拓剛要說明自己不抽煙,卻見對方突然伸出右手,竟握著一支短槍。王拓驚叫一聲:“干什么!”霎時槍響,王拓身子朝后一彈,仰面摔于地上。
現場另一個人是通信員許志堅,跟在王拓側后,背著一支沖鋒槍。時天未全黑,街巷里依舊行人來去。由于一出衙內巷口就到縣政府門外,兩人當時都顯松懈。王拓中槍倒地時差點撞到身后許志堅,許閃身倉促提槍應對,已經遲了,行刺男子竄入一旁另一巷子,眨眼間不知去向。
王拓左胸中彈,血流如注,倒地抽搐,不一會兒即告死亡。
這起恐怖襲擊被日后地方史稱為“王拓事件”,王拓時任縣民政科長。刺殺發生后,人們在現場發現了子彈殼,還發現一團廢繃帶丟棄于地,繃帶沾血帶膿,散發著惡臭。這繃帶是原本就在那里,或者是刺客無意中遺棄?難道刺客是個傷員?或者該繃帶實為擾亂視線?沒待疑問得解,緊接著又有一起恐怖襲擊大案驟然發生,案中充當刺客的卻是兩架飛機,它們在光天化日之下造訪本縣城關,黑禿鷲般傲慢地在空中盤旋,俯瞰眾生,而后急沖而下,大肆屠殺,制造了時稱的“九二五慘案”,與王拓事件一起成為當年當地一連串重大事件的血色序幕。
多年之后,我來到這座縣城尋訪故事。舊日衙內巷已經被一個嶄新樓盤覆蓋,王拓遇難遺址蕩然無存,只在地方史記載中留有幾筆。“九二五慘案”的若干印記則被刻進一座紀念石雕,悄然立于小縣城外延津河邊舊橋橋頭。我去看了那座石雕。該作品主體為一位臥伏于地的年輕農婦,抬起上身將右掌擋向天空,似乎要阻止什么。一個小男孩從農婦腋下露出半個腦袋,表情茫然。石雕底座說明文字稱:“1949年9月25日上午,兩架美式B-29轟炸機跨越海峽空襲本縣城關,趕集群眾死傷近百。一位年輕農婦將五歲小兒護于身下,背中數枚彈片身亡,小兒得以幸存。時過六十載,延津母親雕像落成于當年農婦蒙難處。”
這座石雕被命名為《延津母親》,當地俗稱“某阿嘎”,即閩南方言的“母與子”。我前來拜訪時,建于2009年的雕像在日出日落中已存在了近十年,蒙上了一層淡淡的歲月風塵。據我所知,雕像說明文中提到的那個時間前后,現代戰史所稱的“漳廈戰役”在近側打響,該戰役涉及福建南部漳州、廈門兩座城市。空襲前數日,漳州已經易手,解放軍陳兵海岸,正準備對廈門敵軍發起進攻。空襲中兩架飛機來得有些奇怪,它們沒把炸彈扔到解放軍前方陣地,而是爆炸于后方一座不知名的縣城城關。難道那兩架飛機飛錯了方位,炸彈扔錯了地方?
這座雕像傳遞的沉重內容令我震撼。或許因為關注之甚,我對它頗為不滿,主要是對刻于石雕底座的說明文字。它們與雕像不太搭,過于簡略,有毛病,或因建設時比較倉促,有關領導過于百忙,未曾細致推敲?我感覺很是遺憾,忽然便有一個奇想:或許我該去找一把鑿子?我可以趁夜深人靜之時悄悄回到這里,打開手機的電筒照明,用鑿子叮叮當當對那段說明做一點訂正。我情不自禁搓手,恨不得立刻付諸行動。
我覺得首先應當訂正數字。說明文中提到的“B-29”明顯有誤,數字偏大,應當減去4,也就是改為“B-25”。雖然二者都是當年美制轟炸機,但其功能有一點區別,前者比后者要強悍得多。在這個故事里,“B-29”其實不是飛機而是一個人。這個人很特別,或者說是正人君子,俠肝義膽,或者竟是殺人不眨眼。
有一支破牙刷應當鑿進石雕,它恰好就在當年的空襲現場。所謂“破牙刷”當然并不真是一把牙刷,它也表現為一個人。這個人像是一個孜孜不倦的擺渡者,他撐著一只單薄的皮筏子,竭盡全力繞開咕嘟咕嘟冒著黑泡的漩渦,要把眾多生靈送過黑暗的地獄深潭,前往他心目中的新世界。而他自己卻已經名列閻羅王的勾魂簿,死神伴著子彈、手榴彈和排子槍,花蝴蝶般在他身邊翩然起舞。
顯然我還應該鑿出一圈輪回。劫難之中會有希望與祈盼升騰,在所有的血與火、死亡與仇恨之上,有國家、民族和永恒的人間真情。
可惜我使喚不動鑿子,只能寫下故事。
1
轟鳴聲自半空中來,由遠而近,迅速變成響雷般巨大吼叫。
有孩子驚叫:“大鳥!大鳥!”
時約上午十時。平常日子縣城延津橋頭集市這個時段最為熱鬧,從墟場到周邊密密麻麻人頭晃動。戰亂初平,城鄉百姓驚魂稍定,趕集人流雖遠遜于平日,但畢竟也算熱鬧。兩架飛機光臨時,人們并沒有意識到即將發生什么。因為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一架飛機從這片天空飛過,此間百姓很少有誰親眼見過飛機,不知道它們有多么親切。
飛機在眾人緊張注目中俯沖,向著集場呼嘯撲來,震耳欲聾的巨大聲響逼得所有人低下頭,捂住耳朵,集場上一時飛沙走石。聲浪逼迫之際,飛機并無其他動作,沒待場上驚慌失措的人們逃開,飛機已經拉起來,遠遠飛走。兩只大鳥在人們眼中變成兩個黑點,似乎就要消失到天邊,忽然又從遠處繞了回來。
侯春生就在這時到達現場。他與三個同伴坐一輛馬車從地區趕來,四人都穿土黃色軍裝,攜帶武器,侯春生除了一支手槍,還背一個黃色皮包。馬車已經穿過延津橋,卻在橋頭受阻于飛機騷擾引發的人群騷動。侯春生讓車上人全部下來,趴于路坡邊隱蔽,他自己卻不躲,一縱身站在車板上,揮著手向慌亂逃竄的人們大叫:“隱蔽!”
眾人茫然。侯春生的北方話當地能聽懂的人不多。
半空轟鳴迅速增強,飛機眼看又要沖到。侯春生當機立斷,從腰間拔出手槍,舉槍對空“砰砰”開了兩槍。
“臥倒!”他大聲呼喊。
人們為槍聲所嚇,一時發蒙,隨即又亂成一團。這時連文正騎著一輛自行車匆匆到達橋頭。連文正穿灰布長衫,長條臉上神情疲憊。橋頭亂哄哄地過不去,他跳下車,張嘴對侯春生喊:“長官!別開槍!”
侯春生一聽連文正說話能通,即大聲招呼:“老鄉來得好!幫幫忙!”
他讓連文正招呼眾人防空躲避。連文正聽命,跳上路邊一塊空蕩蕩的肉攤,用土話對身邊亂哄哄人群大叫:“趴下!躲起來!捂住耳朵!”
沒待大家反應,一架飛機俯沖而至。這一次不開玩笑,來真的,“嗒嗒嗒”一串子彈雨點般打進集場,如狂風掃蕩。彈雨過后攤子倒了一地,買的賣的趕集人或趴伏于地,或站著發愣,或狂奔大叫,哭喊聲在各個角落尖銳而起,到處血肉橫飛。然后第二架飛機俯沖,更猛烈的掃射打得集場火光四起,硝煙彌漫。
侯春生領著同行幾人趴在路坡上,靠橋頭石欄掩護,拿他們的步槍和手槍跟天上的飛機對打,在半空而下嗒嗒嗒狂風般的掃射中,反擊槍聲一響一響,平淡而單調,不自量力有如螞蚱逗雞。兩架飛機視若無睹,表演般掃射、拉起,再次遠遠飛開。
侯春生從地上支起身子,朝路上幾個狂奔的趕集人大叫:“你們!喂!”
那些人聽不懂。
“老鄉!老鄉!”侯春生大叫。
連文正又冒將出來,直起身子拿土話對狂奔者大喊:“趴下!不要找死!”
奔跑者一個個撲倒于地。
“老鄉過來!”侯春生用力招手。
連文正弓著身子跑向橋頭,在侯春生身邊臥倒。這時馬達轟鳴聲又響徹天地,飛機從遠處再次轉彎,繞飛過來,直撲集市。東倒西歪趴在地上的人們心驚膽戰,頭皮發麻,聽著半空中越來越強的轟鳴。又有沉不住氣者從地上爬起來狂奔,試圖盡快逃離險地,接二連三帶起一些慌亂者隨行,羊群遇狼般四散而逃,有的往縣城方向跑,有的往相反方向,奔橋那一頭而去,任侯春生怎么喊都喊不住。
侯春生轉頭命令:“老鄉,幫個忙,借你嘴巴。”
他也不多說,拿右手用力一推,把連文正推到一旁馬車上,隨后一把拽脫拴在樹上的馬繩,縱身一躍也上了馬車。
“招呼他們。”侯春生說,“大聲。”
他一甩鞭子打馬,把馬車趕出路坡,調頭往延津橋急奔。連文正在馬車上大叫,讓逃命者讓開、停步、臥倒,飛機馬上要射擊了,快找地方隱蔽。逃命者有的聽從趴倒,有的依舊沒命狂奔。侯春生使出吃奶之力,驅馬飛駛,很快就越過所有逃命者,奔馳過橋。半空中的飛機發現了馬車,追趕過來,砰砰砰一陣轟炸,彈雨自天而下,馬車近側騰起一排煙柱,眨眼間即被擊中,整個車向邊坡側翻,傾覆于地,馬被當場打死,馬車散架,四分五裂變成了一地破爛。
幸而車上兩人在子彈到達前跳下馬車,逃過了子彈。
侯春生趴在邊坡地上,扭頭四處看:“老鄉?老鄉?”
連文正從一旁探出頭:“在這兒。”
侯春生拿眼睛盯著連文正,眼中有一絲笑意:“還行吧?”
“還行。”
“褲子沒濕?”
“不會。”
“好。”
連文正忽然指指侯春生的黃皮包問:“傷到沒有?”
侯春生低頭看,原來他的皮包中彈了,有一顆子彈扎進皮包下緣,留下一小截彈尾露在皮包外。侯春生伸手拔掉彈頭,“當”一聲扔到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