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希臘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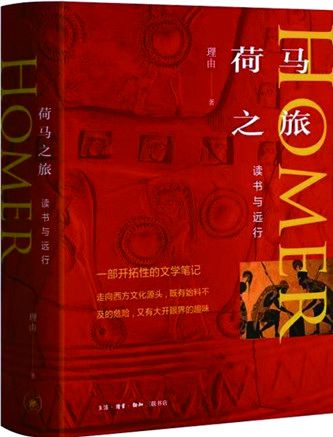
契訶夫說:告訴我你讀什么書,我就會知道你是什么樣的人。
準乎此,似乎可以這樣說:告訴我你讀過什么書,我就會知道你可能寫出什么樣的作品。
因為,一個作家的寫作風格,固然決定于自己的個性和時代的風氣,但也是他所讀作品影響的結(jié)果。作家閱讀的經(jīng)典作品越多,他的寫作意識和寫作經(jīng)驗才有可能趨于成熟。
就20世紀的情況來看,中國作家的閱讀視野和知識構(gòu)成,顯然不夠開闊,普遍不夠完整。我們否定和排斥中國的古典文學,也極大地忽略了從莎士比亞到奧斯丁的英國文學和古希臘文學。尤其是偉大的古希臘文學,我們對它的閱讀和接受,對它的價值和意義的認識,都很不充分。完整地閱讀《伊索寓言》的中國作家也許不少,但系統(tǒng)地閱讀《古希臘神話和傳說》和古希臘戲劇的中國作家,恐怕就不是很多了。至于《荷馬史詩》,一行一行細細讀過,且頗有所獲的中國作家更是屈指可數(shù)。
如果說,古希臘人就像伊迪絲·霍爾在她的那本著名的《古希臘人》(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9年)中所說的那樣,具有質(zhì)疑權(quán)威、渴望知識、善于表達等“十種特殊品質(zhì)”,那么,古希臘文學,在我看來,就具有富于人性、熱愛自由、追求榮譽、悲劇精神、英雄主義、歡樂活潑等精神品質(zhì),以及莊嚴崇高、樸素親切、清晰準確、堅實有力、不尚雕琢等文學氣質(zhì)。用伊迪絲·漢密爾頓的話說,希臘的詩人“喜歡事實。他們對鋪張的辭藻沒有什么興趣,他們討厭夸大其詞”(《希臘精神》,華夏出版社,2008年,第53頁);這樣,他們就始終保持“對事實的敏感”,“對幻想和形容詞一直保持警覺”(《希臘精神》,第54頁)。在藝術(shù)創(chuàng)造上,希臘人傾向于限制而不是放縱自己的自由。他們熱愛秩序,服從法則的約束,致力于尋找將混沌引向秩序的線索。在伊迪絲·漢密爾頓看來,對秩序的熱愛,對法則的服從,乃是“希臘人最大的特征”(《希臘的回聲》,華夏出版社,2008年,第6頁)。
要知道,古希臘的神話和傳說,古希臘的寓言、戲劇和史詩,不僅是歐洲文學獲取靈感和技巧的武庫,而且是西方文學生根和成長的土壤。莎士比亞和托爾斯泰都從荷馬史詩里汲取了豐富的文學經(jīng)驗。1855年,在寫《八月的塞瓦斯托波爾》的時候,27歲的托爾斯泰,就從荷馬那里獲得了深刻的啟示:“為什么荷馬和莎士比亞一類的人講的是愛情、光榮和苦難,而我們的當代文學卻只有‘勢力’和‘虛榮’的無窮無盡的故事呢?”(托爾斯泰:《列夫·托爾斯泰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第119頁)事實上,托爾斯泰的一些藝術(shù)手法,也是向荷馬學來的。例如,他描寫渥倫斯基與卡列寧見面,用一條狗在下游喝被上游的一條狗攪渾的渾水,來比喻渥倫斯基的懊惱心情;他的這種高妙的比喻技巧,就是荷馬最擅長的“事喻”修辭。
如果說,偉大的文學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那么,古希臘文學也應(yīng)該成為中國文學的武庫和土壤。我們應(yīng)該像莎士比亞和托爾斯泰那樣,從荷馬史詩等偉大作品里,獲得豐富的文學經(jīng)驗資源。雖然作為一種指代性的修辭,“言必稱希臘”不過是對教條主義學風的象征性批評,而不是針對希臘文化和希臘文學的具體批判,但是,從后來的情形看,關(guān)于希臘文化和希臘文學,確實很少有人認真對待和熱情稱道了。事實上,關(guān)于希臘文化和希臘文學,中國作家的了解實在有限,所以,縱有“言必稱之”之愿望,亦無“稱引無礙”之能力。就文學實踐來看,我們在中國作家的寫作中,幾乎完全看不到古希臘文學影響的影子。對古希臘文學的疏離和隔膜,限制了我們對人性的理解,也不利于我們的敘事能力和修辭能力的提高。
值得慶幸的是,最近,我終于意外而驚喜地讀到了一本書,一本由中國作家寫出來的討論希臘文學和荷馬史詩的書。
這本書,就是知名的報告文學作家理由先生所著的《荷馬之旅:讀書與遠行》。
作為一部“開拓性的文學筆記”,此書卓異而厚重,包含著作者理由對希臘文學的深摯的熱愛與深刻的理解。
正因為熱愛,理由才肯不遠萬里,走近希臘,走近公元前8世紀的荷馬時代;正因為熱愛,他才會如此耐心地閱讀荷馬史詩——《伊利亞特》16000行,《奧德賽》12000行,他一行行地細讀,用心地體會。
足歷目見,是一種古老而有效的致知方式。在閱讀中行走,在行走中閱讀。理由將行走與閱讀結(jié)合起來,以所見的外部世界,來印證所讀的文本世界。通過觀察希臘的自然環(huán)境和人文環(huán)境,理由為自己闡釋荷馬史詩,建構(gòu)起了可靠的語境和根據(jù)。再加上優(yōu)美的文學表達,遂使他的這部著作,達到了文情并茂、詩意沛然的境界。
理由走近有著2000多座島嶼和13000多公里海岸線的希臘。他行走在這個曾經(jīng)有過22個城邦的國度里。他探訪特洛伊廢墟,登上險峻的邁錫尼城堡,徜徉在雅典的帕特農(nóng)神殿。他眺望眾神居住的奧林匹斯山,凝視陽光映照下的愛琴海。他像一個目光敏銳的藝術(shù)家一樣,發(fā)現(xiàn)了愛琴海獨有的藍色。那不是蔚藍、碧藍、湛藍,也不是瓦藍、青藍或?qū)毷{。用這些形容詞,并不能狀寫出愛琴海所獨有的藍。于是,理由這樣寫道:“哦,它是妖藍!就像魔女勾魂的神秘的秋波在閃爍;那顏色說不上嫵媚,卻極具誘惑力,令人心旌飄搖。”“妖藍”,這是理由的一個發(fā)現(xiàn)。如果沒有足歷,就不會有目見,就不可能窺見愛琴海那魅惑人的別樣的美。
向外,走向自然,走向大地母親的懷抱;向內(nèi),走進文本,走進作者的心靈世界。理由主要從文學性和人性兩個角度進入文本,展開闡釋。他的目的是說明這樣一些問題:荷馬史詩的難以企及的詩性之美是怎樣創(chuàng)造出來的?為什么說它包含著敘事文學的全部奧秘?在人性表現(xiàn)上,它達到了怎樣的深刻程度?在人文精神表現(xiàn)上,它又達到了什么樣的崇高境界?
理由認識到了荷馬史詩的豐富價值。單就藝術(shù)成就和文學價值來看,“荷馬史詩幾乎展現(xiàn)了長篇敘事文學的全部藝術(shù)技巧”。他用生動的例子,揭示了荷馬的兩個最重要的藝術(shù)手法:一個是明喻,一個是直敘。他還揭示了荷馬史詩在敘事上的一個重要特點,即作者態(tài)度的客觀性和中立性。荷馬把所有人都當作人來寫,絕不隨意而淺薄地顯示自己的愛憎態(tài)度,既不明顯地同情自己的同胞,也不簡單地仇恨祖國的敵人。理由根據(jù)自己的理解,并借助克里斯蒂安·邁耶的觀點,完整地概括了荷馬在敘事上的三個鮮明特點,即成熟性、隱匿性和現(xiàn)代性。可以說,正是這些成熟而非凡的敘事能力,使荷馬史詩克服了3000多年的時間阻隔,贏得了現(xiàn)代讀者的強烈共鳴。
人性是理由進入荷馬史詩的另外一個通道,也是他闡釋荷馬史詩的另外一條線索。理由接受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人性觀——“人總是人性的人”。他相信人性是文學的恒久主題。在他看來,久遠歷史上形成的人性,有一個普遍而穩(wěn)定的基本內(nèi)容和基本結(jié)構(gòu);這些內(nèi)容和結(jié)構(gòu),就是“人的動物性加之以語言為標志的靈性”。他對那種未受扭曲的“裸露的人性”,即純真天性和健康性格多有肯定。布克哈特在《希臘人和希臘文明》中說:“在那個時代,情感還沒有被反思割裂開來,道德的準則還沒有被分離到存在之外”。正因為這樣,荷馬筆下的人物,全都“憑著欲望、本能、感情以及情緒行事放縱,盡興宣泄他們的憤怒、恐懼、痛苦歡樂和野性”。他們所表現(xiàn)出來的人性,也許不是充分健全和完美的,但卻是非常自然和可愛的。
在荷馬的敘事里,希臘人將一切都人化了。宗教是人化的宗教,神是人化的神。神像人一樣自然和真實。在理由看來,荷馬根據(jù)人性創(chuàng)造了神,界定了神性,從而最終影響了希臘的歷史進程。然而,荷馬的這一偉大成就,可能被我們低估了。理由因此發(fā)出了深深的感喟:在荷馬之后,“人們不再裸露鮮活的自身”。不僅如此,他還在開闊的比較視野里,深刻地揭示了東方國度民族身心弱化的原因。有必要指出的是,兩相比較,始終是理由的一個研究視角。他時時將目光轉(zhuǎn)向自己的母國,顧盼有情,認真思考那些可與古希臘相互比照的問題,例如,中國人為什么不像希臘人那樣自然而健康地生活?中國人的人性為何沒有朝著希臘人的自由境界發(fā)展?中國為何沒有產(chǎn)生《伊利亞特》和《奧德賽》那樣的史詩?
對荷馬的兩部史詩的文本解讀,是理由這部書最為出彩的部分。他像摩挲瑰美的玉器那樣,摩挲著荷馬史詩的每一行文字和每一個細節(jié)。他還從藝術(shù)上闡釋了荷馬的文學天賦和偉大成就,例如,《伊利亞特》主題的巧妙轉(zhuǎn)換,以及荷馬所發(fā)明的包括“內(nèi)心獨白”在內(nèi)的所有技巧。他最終的結(jié)論是:荷馬在3000多年前所達到的藝術(shù)高度,“不僅難能可貴,而且難以企及”。
但是,如果認為理由僅僅滿足于闡釋荷馬史詩的詩學價值,那就錯了。因為,他也關(guān)注人性,關(guān)懷現(xiàn)實。他從荷馬的敘事中看見了復(fù)雜的人性——看見了攻擊天性、嫉妒心和貪欲,看見了人們對榮譽的渴望、對友誼的忠誠,看見了惻隱之心和高尚的利他主義,看見了體育對戰(zhàn)爭的升華和超越。他試圖從古人的敘事里,尋找療治今世人心的良藥。他反對“性惡論”,因為,人性是復(fù)雜的,而且是可變的。他肯定孟子、休謨和斯蒂芬·平克等人的積極人性論,但也強調(diào)了環(huán)境決定論。在分析中國人與美國人的差異性的時候,理由表達了對某些“蠱惑”之論的不滿,甚至情不自禁地表達了自己的憂慮和對抗意識。
盡管在本書的結(jié)尾,關(guān)于人性,關(guān)于人性所導(dǎo)致的現(xiàn)實沖突,理由并沒有為我們提供一個讓所有人滿意的方案,但是,他稱道和闡釋希臘文學的理由,卻是充分的:研究荷馬史詩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它能幫助我們認識什么是偉大的文學,是因為它能對我們認識人性并升華人性,提供深刻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