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劇研究的集大成者——田本相和他的話劇研究

主講人:祝曉風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審,《人文》學術集刊主編,文學博士。曾供職于光明日報社、中華讀書報、中國外文局、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讀書》雜志等單位。出版有文集《有聲與無聲之間》,新聞作品集《讀書無新聞》,散文集《南開風語人》等。編著《知識沖突》,編輯《南開故事》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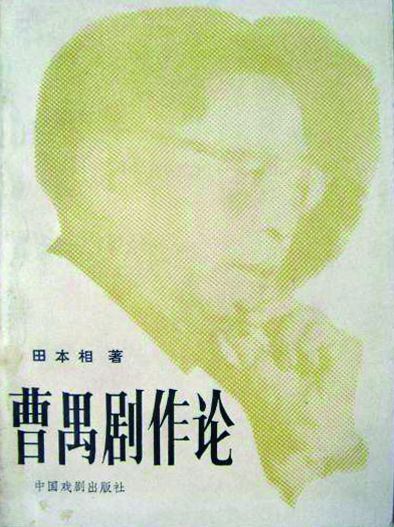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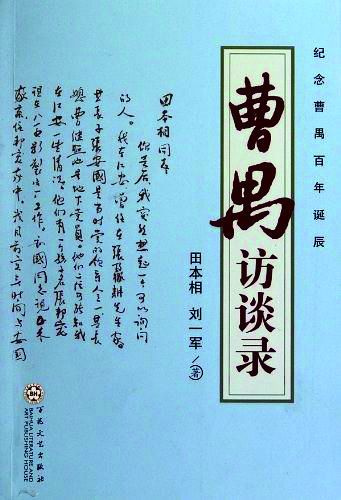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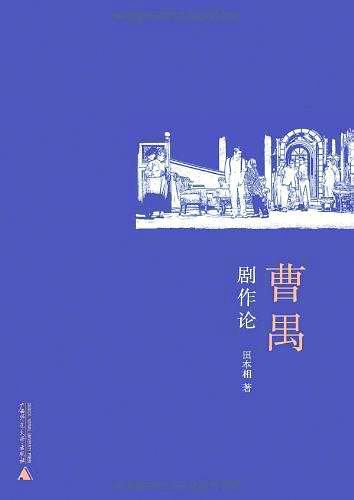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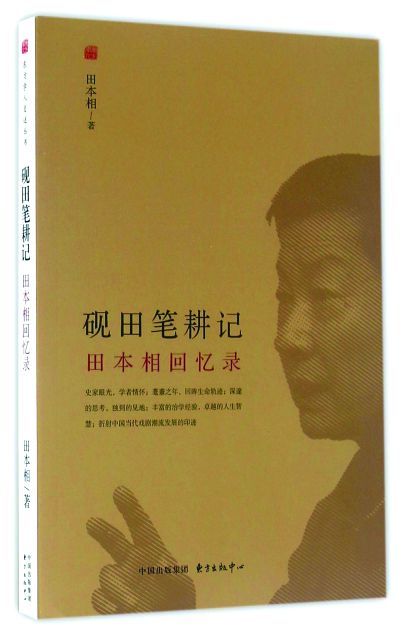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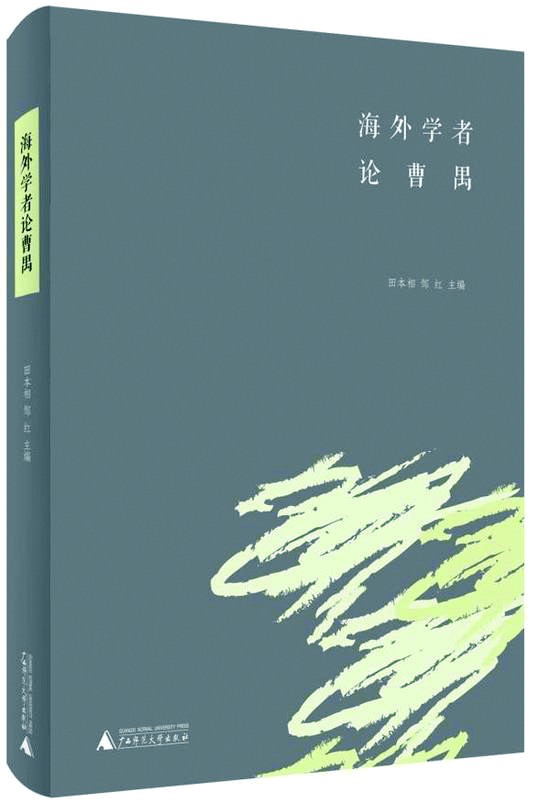
一 很長一段時間,我自認為對田本相先生是比較了解的。這也不是完全沒有理由,一是我們相識已有20多年;二是我和田先生的一班老同學都比較熟,這些人有的又是我的老師,自然親切;三是工作關系,20多年來學術文化的編輯采訪工作,讓我得以與田先生前前后后打過些交道,他在工作和生活上對我都有幫助,自然,我對他也就有一些了解。
毫不夸張地說,田本相先生本人就是一部大書。
這部大書內容豐富,無法在短短幾千字的篇幅中盡述,只能述說其中幾個大的關節重點,而這對傳主本人而言,則是人生幾次大的轉折與升華。一是從軍,上前線。1949年3月23日,田本相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南下工作團二分團,這個四野南下工作團中,當年還有汪曾祺。那一年,田本相17歲,他懷揣著激情與夢想,先是隨大軍南下到武漢,后入張家口軍委工程學院,再調入中央機要處。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不久,田本相被派往前線,到19兵團任機要組長。他親身經歷了這場大戰爭,經受了炮火洗禮、生死考驗。幾年的軍旅生活,他收獲的不僅僅是三等功和朝鮮政府頒發的軍功章,還是成長與成熟、正直與堅強,還有,一個“勇”字。
學者文人,先從軍后從文的,比較出名的有黃仁宇。而田先生的南開同學中,我知道至少也有兩位有從軍的經歷,雷聲宏先生和陳慧先生,這兩位后來也做出了大學問。可見,從軍對青年、對做學問,確實有不同尋常的影響。
二是上南開。南開8年,幾乎就此確定了他今后的職業方向,塑造了他的學術品格,也為他日后不凡的學術成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甚至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田本相此后的人生軌跡。他的學術風格就此打上了鮮明的南開印記。他后來在總結人生經歷時說,在南開大學的學術環境里,他的學術趨向和志趣都形成一種“癖好、習氣和毛病”。
田本相的南開經歷,與他的同學略有不同。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我父母也是與田先生同一年上的大學,而且同在天津。那個年代的大學,沒有幾天正經上課讀書的。一天到晚不是政治學習,就是勞動鍛煉,全國都一樣。據田先生說,當年上了5年大學,有3年多是搞運動。不過,在南開這樣的老學校里,好歹還能有幾位老先生、真學者,當時的老先生有華粹深、許政揚、馬漢麟等。學生多少還是會受到一些熏陶。雖然這些老先生也往往淪為被批判的對象,但是南開畢竟是南開,學術氛圍還是有的。中文系當時在李何林主持下,學術活動也較多,據田本相回憶,李先生就請過方紀、何遲、蔡儀、楊晦等人來南開講座。據家嚴回憶,他們也曾在南開聽過呂叔湘先生的學術報告。就是說,在南開,讀書的氛圍、學術的空氣還是有的。加上田先生本人愛讀書,于是就在這樣的環境中,度過了5年讀書時光。
更重要的是,他是在南開呆了8年,本科5年之后,又接著跟李何林讀研究生3年。多讀的這3年,就決定了田本相與他大多數同學在學術上的差別,那就是系統的、正規的學術訓練,包括系統的讀專業書。就差這3年,完全不一樣。我認識父輩和晚一兩輩的很多人,已經在高校里待了二三十年,卻仍然不知論文為何物,以為搞科研就是復述教材,或者就是跟著一些時政話題發表一點看法。雖然當時各種運動連綿不斷,但在研究生教學這個小范圍內,讀書還是主業。而且,田本相在寫論文過程中,得到清晰嚴格的訓練,在研究和寫作能力上,有了質的飛躍。
三是到北京,先后在幾家高校和科研單位任職,先是在北京廣播學院20年,后到中央戲劇學院,再到中國藝術研究院。幾個不同的學術科研機構工作和研究經歷,又使他獲得了更廣更深的知識儲備。在廣院,他一邊教學,一邊研究新興的電視文化學,對這種區別于純粹文字的藝術形式有了深刻理解。在中戲,他更是直接接觸、研究戲劇表演、舞蹈、美術等舞臺藝術的方方面面,并且寫作、完成了《曹禺戲劇論》。這些都為他以后以更綜合的眼光研究話劇準備了條件。而最后到中國藝術研究院,是他學術成就的集成之地。
回過頭來看,他經歷的這些炮火洗禮,學術訓練,好像都是為了一個大事因緣。他自稱,在北廣和中戲做了20多年的“邊緣人”,但正是這些“邊緣”時光,給了一個學者充分的沉潛時間。他終于走到學術與人生的一個新階段。1987年10月7日,田本相到中國藝術研究院報到,接任葛一虹,任話劇研究所所長。這一天,不僅對他個人是重要的,對于中國話劇史研究,對于中國話劇研究,也是值得記入歷史的日子。
二 一個學科,一門學問,最重要的是基礎性研究。田本相在所長的位置上,把話劇史這一基礎性研究確定為研究重點,全面徹底地推進開來。這就是田本相在學術組織方面的戰略眼光和歷史感,當然,也體現了他的勇氣。
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田本相就明確意識到,中國話劇史是一個未開墾的領域。當年,陳白塵、董健主編的《中國現代戲劇史稿》,葛一虹主編的《中國話劇通史》,都還在醞釀寫作之中,尚未問世。1984年,田本相到中央戲劇學院教書時,發現堂堂中戲,竟然沒有中國話劇史的課程;而一些戲劇評論家、戲劇理論家,對中國話劇史也缺乏足夠的認識,以至于一些所謂“大腕”聲言,中國話劇的歷史沒有留下什么東西。正是在這一背景下,1985年,田本相提出了關于《中國現代比較戲劇史》的構想。進入90年代,陳白塵、董健的《史稿》,葛一虹的《通史》,還有田本相的《比較戲劇史》相繼問世。這三部史,由于準備時間都較長,也注重充分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所以,可代表新時期以來中國話劇史研究的水準,也標志著中國話劇史學科的建立與階段成果。而其中,田本相因為有著曹禺專門研究的根基,他的成果就更富有個人色彩。
曹禺是中國現代話劇的集大成者。研究中國話劇史,必研究曹禺。就如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必要研究魯迅一樣。即使不是專門研究魯迅,也要對魯迅做基礎性的研究。而在曹禺研究這一點上,田本相是下了別人沒有下過的功夫,取得了別人沒有的成就。他的成果,為學界所重,嘉惠后人。他的《曹禺劇作論》《曹禺訪談錄》《曹禺傳》,形成一個系統的、縱深的成果。《曹禺訪談錄》《曹禺傳》是田本相在曹禺的直接支持下,采訪大量當事人,發掘、保存了大量珍貴的一手資料。
田本相的成果遠不止于此。概括地說,田先生本人的成果,一是豐富,涉及話劇史、話劇理論的各個方面,研究了許多關鍵人物,提出了許多引領學術的問題,而且,還有關于現代文學、電視等多個領域;二是宏大,尤其是在話劇研究方面,無所不研,研無不精,在大量深入研究的基礎上,較早地具有了世界眼光和現代觀念;三是貫通,不但是上下貫通,而且貫通話劇中的各個方面,并把戲劇批評和戲劇史、戲劇理論三者打通,把戲劇和文學貫通,在此之上,田本相建立了自己的話劇史理論體系;四是基礎性,他本人的研究,還有他所主持的諸多研究,成為后人進一步研究的堅實基礎。
田本相擔任話劇所所長之后,為了把中國的話劇成就傳播到世界,也有一系列的大動作,其中最為人矚目的,就是連續舉辦了幾屆“曹禺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從第一屆1991年8月在南開大學召開,到2010年的第五屆。這不僅有力推動了曹禺研究本身,還大大擴大了戲劇研究在社會上的影響與中國話劇在世界上的影響。
三 田先生在離休之后,幾乎同時,一邊主編《中國話劇藝術通史》,一邊撰寫《中國話劇百年史述》,兩書前者已出版,后者也交稿給了出版社。但是,田先生仍然覺得這部書未能實現他的想法,自認為它們只是在局部或者某些方面有所突破。他直白地說,“我之所以再主編九卷本的《中國話劇藝術史》,是不滿意《中國話劇藝術通史》和《中國話劇百年史述》”,“不是一點不滿意,而是有著諸多不滿意”。他的設想是,第一,對百年來的中國話劇史作一次全面的、系統的梳理,使之成為一部具有百年總結性質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史著。第二,這部史著,較之以往的中國話劇史著之不同在于:一是使之真正成為一部中國話劇史,把過去忽略了的中國臺灣、香港和澳門都包容進去。二是在內容上,真正寫成一部話劇藝術史,徹底擺脫運動史加話劇文學史的模式,使它成為一部體現話劇是一門綜合藝術的史著,把舞臺美術、導演和表演包容進來。第三,吸收近20年的話劇史的研究成果,并且在創新的理念下,使之成為一部具有較高學術水準、代表國內最高學術水平的話劇史著。第四,這是一部圖文并茂的史著,把重要的歷史圖片收入,使之成為一部形象的中國話劇藝術發展史。
看起來,似乎與《中國話劇藝術通史》原來的設想也差不多,只是從三卷本增至九卷本罷了。但是,它與《中國話劇藝術通史》和《中國話劇百年史述》確有著某些質的區別。田先生簡要地概括是:四個區別,一大關切。四個區別是:第一,還話劇作為綜合藝術史的本體面目。戲劇畢竟是綜合藝術,究其根本是表演藝術,導演藝術、舞臺設計、化妝藝術,以及戲劇文學,都是環繞表演而運作、而展開的。因此,竭力還話劇史以綜合藝術史本體的追求,是九卷本《中國話劇藝術史》的靈魂。第二,單獨立卷的價值和意義。根據歷史分期單獨立卷,似乎還是傳統的做法。但是,這樣的單獨立卷,將每段歷史,更獨立地加以審視和評估,不僅內容豐富了,而且對這段歷史的描述更深化了。第三,把中國話劇的現實主義僅僅概括為戰斗傳統是不全面的,最能體現它的杰出成就和藝術成果的,也是中國話劇的獨特性的,是一批我們稱為詩化現實主義的劇作。第四,圖文并茂的設計。上千幅照片,使話劇史作為綜合藝術史的面貌更為真實生動。一大關切則是對中國話劇命運的關切,具體說來,是對中國話劇危機的關切。中國話劇的危機首先是思想的危機。
此九卷本《中國話劇藝術史》2016年由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在學界引起強烈反響,得到很高評價。
最近六七年間,田本相先生在撰寫評論文章的同時,還有一系列專著和重要成果出版,其中,兩種大型史料集有特別的分量,即由田本相主編的38卷本的《中國現代戲劇理論批評書系》(2014)和由他倡編的100卷的《民國時期話劇雜志匯編》(2017)。2014年,他和鄒紅合編《海外學者論曹禺》出版,還編輯完成《田本相文集》(12卷)出版。2016年,田先生所著《曹禺探知錄》《硯田筆耕錄——田本相回憶錄》出版。2017年還由他主編出版了《新時期戲劇“二度西潮”論集》。
田先生確實有一種對話劇史研究的迷戀,有一種窮追不舍的勁頭。他老當益壯,老而愈勇。九卷本出來,他還不甘心,還想把中國話劇史的精華提取出來,于是產生兩個想法:一是在紀念中國話劇110周年之際,寫出《論中國話劇的詩化傳統》《曹禺——話劇詩化之集大成者》等;另一方面,是向話劇史研究的深化和細化進軍,如《話說“話劇皇帝”石揮》,《論中國話劇表演藝術理論的發展軌跡》,這些都是他撰寫的《中國話劇表演藝術史稿》的有關章節。同時,田先生也開始組織有志于此的學者,撰寫《中國話劇導演藝術史》和《中國話劇舞臺美術史》等。他的想法是,這些研究不僅具有獨立的學術價值,而且為寫出更為精彩的《中國話劇藝術史》準備了條件。
四 現在這本《硯田無晚歲——田本相戲劇論集》,集中了作者最重要的一些理論思考。比如,田本相曾經對中國現代戲劇理論批評史有一個評估,認為它有兩個特點,兩個潮流,一大弱點。兩個特點,一是中國現代戲劇理論的移植性、模仿性和實用性;一是中國現代戲劇理論的經驗性。兩個潮流,一是詩化現實主義的理論潮流;一是實用現實主義潮流。一大弱點,是學院派理論的孱弱。其中,“學院派戲劇批評”是田本相近年特別關注的一個問題。何謂“學院派戲劇批評”?田先生認為,它首先意味著一種精神,即獨立的、自由的、講學理的、具有文化超越的遠見和膽識的批評精神。這是一種不同于政治化的戲劇批評和商業化的戲劇批評的第三種批評。這可視為田先生對于戲劇批評的一個貢獻。
早在上世紀80年代,田本相先生出任話劇所所長,首先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中國話劇的傳統問題。他當時就想,中國話劇難道就是“戰斗的傳統觀念”所能完全概括的嗎?難道真像所謂“大師”和“先鋒”所說的,中國話劇沒有留下什么好的東西嗎?此文集中,就有幾篇文章論述中國話劇的“詩化傳統”和“詩化現實主義”。這兩個概念和提法,不妨看做一個大概念。這是田先生多年研究中國話劇的一大發現。他提出,中國的文學傳統是詩化傳統。《詩經》《離騷》之后,賦、詞、曲皆由詩演化而來。中國戲曲和中國文學傳統有著密切的關系。外來的話劇,進入中國這個偉大的詩的國度,也為這個強大的傳統所融合,就不可避免為這強大的“詩胃”所消化。
“中國的詩化現實主義發端于20世紀20年代的田漢,30年代形成曹禺、夏衍的詩化現實主義主流。它是在吸收西方現實主義、浪漫主義以及現代主義的精華以及中國文學的詩性智慧和中國戲曲的詩化傳統基礎上形成的,更在奮起抗戰的民族大覺醒之際,最終構筑成中國話劇的寶貴的藝術傳統。”“這樣一個傳統是我們最可寶貴的遺產,也是最值得繼承和發展的。中國話劇的希望也在這里”。
這是田先生對于中國話劇傳統的一個總的命題。在這個總命題之下,他還有許多精深的研究,如,他提出“詩意真實”概念,所謂“詩意真實”,“首先是對現實生活中的詩意的捕捉、感悟、提煉和升華”。 他發現,焦菊隱也一再強調舞臺的“詩的意境”。心象、意象,這本是中國傳統的詩學范疇。戲劇藝術所要創造的即是戲劇意象。焦菊隱反復強調的是,沒有演員富有創意的審美感受、審美體驗,就不能產生“心象”。
如果說田漢、郭沫若是中國話劇詩化傳統的開拓者,那么,曹禺不但是中國話劇詩化傳統之集大成者,而且是中國話劇詩化之典范。對曹禺研究極深的田本相先生,是首先研究發現這一點的人。他認為,曹禺是自覺地把話劇作為詩來寫的。首先,曹禺的話劇詩化特別強調“情”,把主體的“情”注入對現實的觀察和現實的描繪之中。曹禺說:“寫《雷雨》是一種情感的迫切的需要。”其次,曹禺創造了一種“詩意的真實”。田先生在有關曹禺的論著中對曹禺的真實觀曾作過概括,即“詩意真實”,他善于發現污濁掩蓋下的美,以及腐朽背后的詩。其三,在曹禺的詩化的戲劇創作中,幾乎所有的中國詩學的審美范疇均化入他的作品中,這些對他并不是理念,而是在中國文學詩化傳統的熏陶中形成的。
五 我與田本相先生相識,準確時間已無從考證,但可以肯定,至少應當在1996年8月之前。1996年8月7日《中華讀書報》第5版,有我采訪田先生的一篇報道,此可為證,標題是:從來沒有完整的《雷雨》——田本相談《雷雨》的改編。文章不長,但信息量不小,對一般讀者了解《雷雨》還是有點兒幫助的,不妨錄下:
原來,《雷雨》從1935年4月在東京神田一橋講堂首演開始,就從來沒有原原本本地按原劇本演出過。但是,這并沒有使《雷雨》的光彩從根本上減損。
近日,記者再次就《雷雨》的改編問題采訪了中國藝術研究院話劇研究所所長田本相先生。田本相介紹說,《雷雨》在日本的首演,是杜宣、吳天和劉汝醴擔任導演,演出時刪去了《序幕》和《尾聲》,杜、吳在致曹禺的信中說:“為著太長的緣故,把序幕和尾聲不得已刪去了,真是不得已的事情。”曹禺對此十分惋惜和不滿。可是,全本演出《雷雨》要長達4小時,觀眾顯然容易疲勞,刪節劇本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上,在解放前的演出中,《雷雨》幾乎沒有過序幕和尾聲。田本相認為,后來的情況表明,曹禺對這一事實也漸漸采取了認同的態度。而學界認為,這樣的《雷雨》已不是原本意義上的《雷雨》了——盡管它仍然很打動觀眾——而是一個在社會接受過程中變化了的文本。
50年代初,曹禺對《雷雨》做了較大的修改,強調了階級斗爭、階級沖突。“文革”之后,這一點緩解了一些。在后來夏淳導演的《雷雨》中,更強調戲中原有的人情、人性。丁小平的《雷雨》,則加了序幕和尾聲,但不是原來的。1993年,王曉鷹的《雷雨》中去掉了魯大海,又做了小劇場的處理,對此,當然也有不同意見。
田本相認為,任何名著都意味著一個被不同時代接受、詮釋的歷史。“為什么說一部作品是經典,就因為它具有可以為不同時代和導演詮釋的可能性。好的劇本會給導演很大的創造余地,可以發掘它的內涵,發掘以前沒有被人認識的東西。但是,改編不是胡來的,不是任意的。改編確實是一種創造,改了它,但又是它。改編名著不是輕而易舉的,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我滿意的《雷雨》。”
田本相最后說到現在的一些名著改編,特別是影視改編,商業氣和匠氣太重,少有曹禺改編巴金的《家》那樣成功的例子。
現在單看這段文字,好像也不少,但當時放在版面上,并不大,連一個巴掌的面積也沒有,占全版面積的1/14左右。當時的版面用的是六號字,字數較多,一個整版排滿字,將近有一萬六千字。
這一版上,還有我采訪萬方的一篇,題為《爸爸說:“我知道那是個好東西”——作家萬方談曹禺和〈雷雨〉》。另外一篇評論,《曹禺對〈雷雨〉不成功的修改》也出自我的手筆,但因為是評論,所以就用了筆名。正好,當時《雷雨》改編電視劇頗受關注,又趕上《曹禺全集》出版;而《雷雨》改編,也引來一些不同意見,有爭議,就有文章做——學術上的主要支持,自然就得靠田本相先生了。
當時,曹禺的身體已經很不好了。版面上配了一張曹禺和萬方的合影,是曹禺在病房里。1996年12月,曹禺就去世了。
第一次見田先生的情景,我至今還記得,是在恭王府,當時中國藝術研究院就在那里。話劇所是在最北邊一排房子。那天下午,陽光明媚,我如約來到。我站在院子里待了一會兒,田先生從走廊另一邊信步走來。這個形象就這樣一直留在我的腦海中。
田先生的目光探尋著歷史、打量著現實。他批判的鋒芒,總是揮向戲劇中的丑,揮向學術研究中的劣,直指戲劇批評中的偽和俗。如此說來,他便有了魯迅先生和李何林先生的風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