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科幻的第二次熱潮
大事記(1976年至1982年)
中國科幻中斷十年之后,于1976年即開始復蘇。第一次熱潮時期涌現出的科幻作家鄭文光、童恩正、肖建亨、劉興詩等紛紛歸來,另外還有新人不斷涌現,如葉永烈、王曉達等,創作出更多更好的科幻小說,使新中國的科幻小說走向成熟,直至1982-1983年,一場批判科幻小說的惡浪使這第二次科幻的熱潮戛然而止。
在新中國科幻的第二次熱潮期,除科普型科幻、少兒科幻繼續發展外,以鄭文光、童恩正、葉永烈、肖建亨、王曉達為首,主張科幻文學首先是文學,寫作了許多成人科幻作品,形成了中國科幻的重文學流派,創作了《戰神的后裔》(鄭文光)、《珊瑚島上的死光》(童恩正)、《沙洛姆教授的迷霧》(肖建亨)、《黑影》(葉永烈)、《波》(王曉達)等文采斐然的優秀科幻小說,向世界水平進軍,鄭文光率先成為公認的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幻大師。
1976年
中興代代表作家之一葉永烈登場,他的科幻小說《石油蛋白》在《少年科學》第一期發表。

《少年科學》1976年第1期
1977年
中興代代表作家之一肖建亨發表科幻小說《密林虎蹤》,是第一次科幻熱潮中最先歸來的老科幻作家。
1978年
葉永烈的科普型科幻代表作《小靈通漫游未來》由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首印150萬冊,開中國科幻小說暢銷書的先河。
童恩正的科幻小說《珊瑚島上的死光》發表,這是中興代科幻作家重文學流派代表作之一。
劉興詩科幻小說《隕落的生命微塵》發表。
1979年
1月20日,童恩正在《文匯報》上發表《幻想是極其可貴的》,以及隨后發表的《我對科學文藝的認識》,闡釋了他對科幻小說首先是文學的觀點,科幻小說的文學性重于科學性,從科幻小說是科普的工具舊傳統中解放出來,開啟了科幻小說重文學流派,并成為這個流派的旗手。他的這一主張,得到鄭文光、肖建亨、葉永烈等中興代代表作家的贊同,并在科幻創作中陸續付諸實施。同時,維護舊傳統的劉興詩等重科學流派的科幻作家,同重文學流派的科幻作家,開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關于科幻小說“姓文”或“姓科”之爭,直至因為政治因素的介入,毀滅了中國的一代科幻熱潮,使中國的科幻發展進入低潮。
鄭文光的科幻小說《飛向人馬座》發表,這是新中國出現的第一部長篇科幻小說。
鄭文光的《太平洋人》在《花城》雜志發表,是鄭文光“復合幻想構思”賞識的代表作之一。
王曉達的科幻小說《波》在《四川文學》雜志發表,這是一篇不以兒童為對象的小說,開“成人科幻”的先河。
吳巖科幻小說《冰山奇遇》發表,當時僅17歲的高中生“小荷才露尖尖腳”,后來成長為中國當代科幻領軍人物之一。
1980年
2月
劉興詩《美洲來的哥倫布》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他科學設想型科幻的代表作。
鄭文光社會型科幻代表作之一《古廟奇人》發表,是他對科幻寫作方法進行多方位探索的重要成果。
12月
肖建亨代表作《沙洛姆教授的迷霧》在《人民文學》發表,這是他突破中國科幻小說以科普為目的而寫作的重文學流派的力作。
《科學文藝譯叢》在江蘇創刊。
《科學文藝》達到每期二十萬份的發行量。
全國發表了超過300篇科幻小說,這是空前的數字。
童恩正的科幻小說《珊瑚島上的死光》在上海電影制片廠拍攝成功,上映后受到歡迎,家喻戶曉,這是國內第一部科幻電影。
1981年
鄭文光社會型科幻代表作之一《命運夜總會》發表。
葉永烈社會型科幻代表作《腐蝕》發表。
魏雅華社會型科幻代表作《溫柔之鄉的夢》發表。
《科幻海洋》在北京創刊。
《智慧樹》在天津創刊。
《中國科幻小說報》 在黑龍江創刊。
用黃金時代的科幻創作沖出亞洲走向世界
歷史見證人:鄭文光(董仁威1980年采訪記錄)
1976年以后,他被時代的精神所激勵,再度鼓起文學熱情投入創作,迎來了他科幻小說創作的黃金時代。鄭文光覺得,自己就像埋在泥土里的瑜珈教徒一樣,被人發掘出來了,而且又能夠復活過來。報刊、出版社,先是試探著,突然之間蜂擁而至約稿了,少年兒童讀物的編輯、文學刊物和出版社的編輯、科學期刊和出版社的編輯……為什么對于科學文藝作品的需要一下子增長得那么快?那是因為新的領導人提出了實現包括科學技術現代化在內的四個現代化的宏偉計劃;那是因為新的領導人召開了科學大會,又領導制訂了發展科學技術的規劃;那是因為新的領導人扭轉了教育事業凋敝零落的慘淡局面,又向青少年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偉大號召。
客觀需要,筆桿子豈能長期撂下?于是,鄭文光又開始寫了。
這以后,鄭文光繁忙而刻苦,他有一個不小的科研計劃,他要寫天文學史的論文和專著,創作只能靠業余,而他,已經是一個精力大不如當年、年已半百的人了。但是,多少人為他們鼓勁啊!首先是熱情的編輯,他們帶來了小讀者的要求和愿望;然后又是一系列會議——兒童文學作家座談會、少年兒童讀物工作會議、兒童文學評獎委員會……少年宮組織了和小讀者的會見,北京、上海、成都和南昌的少先隊員們一次又一次把紅領巾圍在鄭文光和一些兒童文學同行的脖子上。鄭文光的心又變得年輕了,它又回到了他久已失去的童年。他覺得,要加倍努力地寫,要彌補被奪走的10年歲月。其實不止10年了,至少有15年是白白扔了。五分之一個世紀,包括他一生中精力最旺盛的時期是一去不重返了。不過在當時,那些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兒,為了奪回“損失的時間”,不少人都像三、四十歲的壯年人那么干?何況他鄭文光只有50歲!
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鄭文光的科幻小說創作進入了巔峰時期。在這個時期里,鄭文光同全國人民一起,解除了禁錮思想的緊箍咒,開始了深層的思索。為什么會出現那樣一個荒謬絕倫的時代?為什么人們能夠容忍“史無前例”的悲劇演出長達10年?怎樣才能避免歷史悲劇的重演?鄭文光站在高高的山巔,眺望著歷史長河的源流,將過去、現在、未來放在一起思考,創作出一批優秀的科幻小說作品。幾十年觀察人生、考察社會的生活積累,走南闖北的流浪、采訪生涯,南海風情、北國風光,融匯進現代科技成就中,對祖國的愛、對人民的愛化作藝術,一篇篇立意新、構思巧、意境深、人物形象鮮明的科幻小說從筆尖上涌出來。他寫了四本長篇小說和數十部短篇小說,他的小說從對科學的無限贊美到對過去的無窮感嘆再到重新拾回對未來的憧憬,一部比一部更加精彩和具有探索性。美國評論家認為,鄭文光是當時亞洲少有的能在科學和人文領域并行馳騁的重要作家。

《飛向人馬座》鄭文光著
從1978年起,幾年間,鄭文光出版了近百萬字的科幻小說,包括《飛向人馬座》(1978)、《大洋深處》(1980)、《神翼》(1982)和《戰神的后裔》(1983)等4部長篇小說和《命運夜總會》(1982)、《地球的鏡像》(1980)等多部中短篇小說,使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其中《飛向人馬座》榮獲第二屆全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一等獎,《神翼》榮獲1980-1985年中國作家協會少年兒童文學創作一等獎、1990年全國第二屆宋慶齡兒童文學獎銀質獎(當年金質獎空缺)。他的4卷本小說全集于1993年由湖南少兒出版社出版。在這一時期,除科幻小說之外,鄭文光還撰寫科學游記、動物小說、科學童話和科學小品等多種門類的作品,都獲得了讀者的喜愛。他的動物小說《猴王烏呼魯》(1982)獲得第二屆全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一等獎。
鄭文光站在歷史的高度,將過去、現實、未來放在一起思考,創作出的這一批優秀科幻小說作品,標志著他進入了創作的鼎盛時期。這一批作品,無論從思想的深刻性、藝術的成熟性、科學幻想的大膽方面,都可以毫無愧色地進入中國和世界優秀的文學作品之林,引起了中國和世界的注意。
我國的報刊《光明日報》《文學報》《小說界》《科學文藝》《科幻小說報》《明報》《開卷》等相繼發表了評論鄭文光作品的文章。著名評論家鮑昌稱鄭文光為將現實與未來連在一起思考的人。華東師范大學、吉林大學,山西大學、云南大學,安徽大學中文系和上海外語學院英語文學系的5個大學生、3個研究生都將研究鄭文光及其作品的成果作為自己的學士論文和碩士論文。
鄭文光的科幻小說創作活動也引起了美國、日本、德國的科幻小說研究者和記者的注意。美國、英國、日本、港臺和泛美華人地區都對鄭文光的文學活動給予過高度評價。美刊《ASIA2000》稱鄭文光為“馳騁于科學與文學兩大領域的少數亞洲科學家之一”。日本電視臺駐京記者井上孝利采訪了鄭文光,并以題為《中國的科學家兼文學家鄭文光》的長達半小時的專題電視節目在日本電視臺首次播映。20世紀80年代初,香港《亞洲2000》發表長文認為,鄭文光是新中國科幻文學的創始人。西德研究生寫出了《鄭文光傳》。
作為新中國科幻文學的主要開拓者,鄭文光在讀者心中享有極高的聲譽,作為中國科幻小說的代表作家之一,已經沖出了亞洲,走向了世界。
鄭文光還是中國科幻文學理論的主要探索者。早在20世紀50年代,他就撰寫過研究凡爾納和魯迅科學文藝思想的文章。20世紀80年代之后,他與童恩正、葉永烈、金濤等人共同提出的科幻文學新觀念,實現了中國科幻從兒童讀物和科普讀物領域的全面突圍,為中國科幻文學的更大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由于在文學領域中的突出成就,鄭文光曾多次被選為中國作家協會兒童文學委員會委員、中國科普作家協會常務理事、科學文藝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98年,他由于對科幻文學的重要貢獻,獲得了至今為止中國科幻領域惟一的“終身成就獎”。
鄭文光為人謙虛、樸實、真誠、正直。他熱愛自己的祖國,對所從事的科學和文學事業,從來抱有宗教般的情感和專注。他還熱衷于鼓勵和提攜青年作家。從1979年到1985年,他犧牲個人創作時間,主持發行了大型科學文藝雜志《智慧樹》,為發掘新作家,繁榮科學文藝的多種門類,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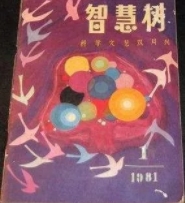
《智慧樹》1981年總第1期
在伯樂堆中成長
歷史見證人:吳巖(董仁威采訪記錄)
1962年12月2日,吳巖出生于北京燈市口的空軍政治部文工團的大院里。他的父親是滿族人,原本是空政文工團的二胡演員,后來當過編劇,搞過行政工作。母親則是漢族人,也是空政的演員,起初是舞蹈演員,后到體工隊當舞蹈教練。
吳巖的母親是重慶人,有11個兄弟姊妹。吳巖的母親是老大,常寄點錢回去貼補家用,但自吳巖出生后就一直沒回過娘家。“文革”結束后,一家過上了平穩的生活,吳巖便求母親帶他去重慶看他那些從未謀面的舅舅、姨媽們。于是,母親批準他自己回一趟重慶。11個舅舅姨媽樂壞了,輪流請客,天天大吃大喝,讓吳巖嘗遍了重慶的各種美食。
吳巖的姓名從何而來?吳巖的父親自然姓吳,吳巖的母親雖然姓嚴,實則也是吳姓后代,母親的兄弟姊妹均姓吳,只因母親“過繼”給嚴姓人為女,才改姓嚴。因此,吳巖的“姓”來自父母,而“名”則來自重慶的“紅巖”。但是,將他取名為“巖”,并不是因為他的母親是重慶人,而是當年由空政文工團演出的《江姐》,使重慶的“紅巖”走紅,空政大院在那一時期出生的孩子,不少均取名“紅巖”或“巖”。
吳巖在位于王府井很近的燈市口空政大院里長大,他同在北京獨特的大院環境長大的孩子一樣,由于大院環境幽雅,有葡萄架,有游泳池,與北京胡同中的那些陋室形成鮮明的對比,院內又住著許多如著名編劇閻肅、詞作家張士燮、作曲家姜春陽和楊鳴、第一代演江姐的名演員萬福湘等名人,使他們產生了一種優越感,自認為他們這一群小孩非同凡響,很了不起。

燈市口空政大院
不過,吳巖并非著名作家王朔在小說中描繪的部隊大院中的紈绔子弟,而是一個聽話的“小乖乖”,成績優異的好學生。吳巖不到十歲便迷上了科普書,使他從小就熱愛科學。他有個只比他大兩歲,但比他成熟得多的表哥,是個科學迷,常常在家里用一些試管和酒精燈做科學實驗。每隔一兩周,吳巖就要到住在美術館附近的表哥家去,同表哥一起搗鼓那些試管、酒精燈和瓶瓶罐罐,并從表哥那里借一些科普書來看。他最喜歡讀的一本書是《元素的故事》。各種各樣的元素真是迷人,它們通過不同的組合,變成世界萬物,乃至我們人類的身體,神啦!
從此,吳巖狂熱地迷上了科普書,迷上了科學。抱上一本科普書,他什么都不管了。若這時,父母親硬要他去做其他事,比如打水洗碗洗衣服什么的,他便會堅決不從,甚至用嚎啕大哭為武器來抗拒。你看,這吳巖是不是個“資格”的科普迷,“賽先生”的超級“粉絲”?
吳巖這個“賽先生”的超級“粉絲”,從小就產生了一種癖好,喜歡追科普名星。有一次,他在空政大院的門房里看到一封寄給著名科普作家、《少年科學畫報》主編郭以實的信。吳巖看過郭以實寫的科幻小說《在科學世界里》,覺得特別好,每次看后他都會哭。吳巖欣喜若狂,他抄了信封上的地址,按照這個地址給郭以實寫了一封信。郭以實這個當時與高士其地位相當的著名科普作家居然給他回信了。郭老師說,他家離吳巖家很近,邀請吳巖到他家玩。
于是,吳巖去了。郭以實是個很好的人,他將吳巖當成小兄弟,將吳巖拉進了科普圈。
那是在中國科學的春天里發生的事。1976年,科學的春天來到了。1978年,中國召開了科學大會。隨之,宣傳科學的科普作家們成了“香饃饃”。他們高舉著“賽先生”的旗幟,進行多種多樣的科普活動。這一年,中國科普創作協會組織了一個科學家與中學生見面的活動,學校給吳巖找了一張票,讓他參加。
吳巖去了,見到了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這個會在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連續開了三天。他記得,每次開會時,癱瘓多年的高士其都要被人用輪椅推進來,并在最后讓人幫他朗誦一首詩,詩歌的名字也很響亮,叫《讓科學技術為祖國貢獻才華》:
“祖國大搞四個現代化,
科技也來報名參加,
他的領隊是數理化,
工農醫學都是他的部下
……
吳巖這個“年方二八”的高中生,不僅在會上見到了高士其,還給高士其寫信。他的第一封信居然是對高士其說,“你應該表揚表揚葉永烈老師,他對科普的貢獻很大,我們都很喜歡他的作品”。高士其說,我可以表揚葉永烈,你也可以自己表揚葉永烈,他就在上海科教電影制片廠工作。
于是,吳巖遵照高士其的“指示”,表揚起葉永烈來了。
在跟葉永烈通信的同時,他還把閱讀葉永烈作品的讀后感,寫了一篇書評:《別具一格——讀葉永烈的科學文藝作品》,寄給光明日報社。
書評發出后,吳巖把這件事情忘了,他并不期望學術性極強、門坎很高的堂堂大報會發表一個高中生的評論文章。大約過了兩個月,一天,班主任把吳巖從課堂內喊出來,急促地問吳巖:“你給光明日報投了稿?”“嗯,是啊。”吳巖回憶起來。“給誰看過?”吳巖想了半天,“我給語文老師看過。”
幸虧這個見證人存在,可以證明稿子確實是吳巖自己寫的。隨后,班主任把吳巖帶到校長辦公室,光明日報的編輯秦晉正坐在那里。校長讓吳巖與編輯見了面。編輯“驗明正身”后,告知這個稿子即將發表,需要自己再確認各種事實的正確性。
吳巖按照編輯的指導,改了稿子寄出去。1978年6月1日前的一個周末,吳巖的文章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這篇文章在葉永烈看來,是一個重要的標志,因為這說明一直活躍在上海的葉永烈已經逐漸受到了北京的關注。
從此,吳巖與葉永烈建立了友誼。起初是通信,以后,葉永烈來北京,總要抽時間看一下這位小兄弟。吳巖與葉永烈第一次見面,是葉永烈出差來北京時。吳巖是由父親陪著一起去的。在葉永烈下榻的賓館,他見到了只穿背心褲衩,正洗完衣端著一個洗臉盆進屋來的科普大師。以后再與葉永烈見面,吳巖就帶上他寫的科學小品、科幻作品等,請葉永烈指導。吳巖給葉永烈看的第一篇作品是寫放射性技術育種及放射性物質泄漏后造成的后果。這篇文章投出去后,被退回來了。葉永烈對他說,他的作品中把放射性當做一個負面東西來寫,是一個“問題”。其實,這個問題正是吳巖的長處,為后來他正確審視反科學霸權思潮打下了基礎。
當時,吳巖聽了葉永烈的話,改寫科學技術的正面效應。經葉永烈推薦,1979年1月,吳巖的兩篇科學小品:《給盲人一雙眼睛》《特殊采礦法》在《少年科學》上發表了。1979年9月,吳巖在《少年科學》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科幻小說:《冰山奇遇》。后來,葉永烈在給國外寫一篇介紹中國科幻現狀的文章中,提到吳巖是中國當時年齡最小的科幻作家。于是,17歲的高中生吳巖,以他的作品,進入了中國科普作家的隊伍,成為其中最年輕的一員。
吳巖與著名科普作家、中國科幻大師鄭文光的友誼也是在那個時期建立起來的。
吳巖想見這位大師,郭以實給了他鄭文光家的地址,叫他自己去找。吳巖騎著自行車,來到和平里鄭文光的家。這位世界著名的科幻大師會不會理一個中學生呢?吳巖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在鄭文光門前徘徊了半小時,不敢敲門。當他鼓著勇氣敲開了鄭文光的門后,結果卻使他喜出望外。鄭文光聽明吳巖的來意后,將他迎進門,給他端茶倒水,受到貴賓般的接待并誠懇地回答了他的問題。
常言道:“半罐水響叮當”,大智慧者卻一般都是為人謙和的。鄭文光就是這樣的大智慧者,對后輩呵護有加。想當年,我去鄭文光家采訪,也受到同樣的禮遇。他對我這個無名小卒,不僅有求必應,還管吃管喝。我在鄭先生家,不知吃過師母做的多少次好菜好飯。同樣,吳巖也常進出鄭文光家,受到鄭文光及師母的親切款待。
吳巖很快同鄭文光結成忘年交,成為鄭文光的“小尾巴”。他同鄭文光一起騎著自行車去出版社拉樣書,自然是“近水樓臺先得月”,首先獲得鄭先生的贈書。吳巖還在鄭文光家參加了他們策劃編輯《科幻海洋》雜志的私人聚會,到會的人包括饒忠華、孫少伯、李夫珍、王逢振、金濤等。討論之后,鄭文光的太太陳淑芬做飯宴請大家,還開了“茅臺酒”。這是他第一次喝這種偉大的白酒,但是,陳阿姨的菜更讓他贊嘆不已。

《科幻海洋》1981年第1期
1980年,郭以實以他兒童科普委員會負責人的身份發通知給吳巖,邀請他去哈爾濱參加中國科普創作協會的科學文藝委員會和少兒委員會的年會,讓他結識了更多的科普作家。
吳巖接到開會通知很高興,就去找他就讀的燈市口中學的校長,校長資助了他一筆差旅費,來到了哈爾濱。在會上,他見到了科幻和科普這個圈子幾乎所有的大腕,童恩正、肖建亨、劉興詩,還有更多很快便在業界響亮起來的名字。這個圈子向這位小兄弟敞開了大門。中學生參加科普大會,這在當年是一件稀奇事,成了新聞,《北京晚報》和新華社都發了消息。
“樂極生悲”。吳巖雖然混跡于科普界大腕之中,且這些大腕個個是伯樂,讓他在科普界迅速成長起來,但作為一個中學生,學業未免有些偏廢。他創作的欲望很強烈,常常在上課的時候寫小說,一部又一部。這一年高考,吳巖承受了重大的打擊,這個少年科普作家,居然在高考中名落孫山!這在科普界造成了一點小小震動,“伯樂”們的面子下不來。但是,“伯樂”們的意見是一致的,吳巖必須上大學,一個科普作家沒有扎實的人文科學功底,是成不了大氣候的。
吳巖痛定思痛,發憤學習。吳巖是何等聰明的人物,只要精力集中,學習成績必然會突飛猛進。只是以前偏科太嚴重,一時無法達到最佳狀態,第二年高考成績只上了普通本科線,沒有進入他想讀的北京師范大學的視野。但是,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系負責招生的丁匯亞老師知道吳巖是一個少年科普作家、難得的人才后,決心要破格錄取他。然而,這時吳巖的檔案已經被首都師范大學(原名北京師范學院)的招生者收留。丁老師去首都師范大學要人,誰知,首都師范學院把吳巖當成了“寶貝疙瘩”,“打死”也不放人。理由很簡單,吳巖報考的第一志愿是物理系,當年考生中物理學及格的人不多,但吳巖卻是少有的及格者。丁老師卻不肯善罷干休,“官司”一直打到當時北京市的高級領導、招辦主任白介夫那里。白介夫一捶定音:吳巖給北師大,北師大另外去找幾個物理及格的考生檔案給首都師范大學。白市長斷案的水平堪比“龐統”“喬老爺”與“張飛”!
什么都寫的葉永烈
歷史見證人:葉永烈(董仁威釆訪記錄)
1940年8月,葉永烈出生于浙江省溫州市市中心的鐵井欄。在他之前已有哥哥、姐姐各一人,他排行第三,父親葉志超,是一個著名的工商界人士。葉永烈出生在抗日戰爭烽火連天的歲月。出生不久,溫州就淪落在日軍之手。葉家的大樓和相鄰的永嘉縣銀行大樓,是溫州當年最好的大樓,被日軍看中,占作司令部,父母只好帶著三個孩子逃難。全家包了兩艘兩頭尖的“蚱蜢船”,沿著楠溪江逃往山區親友家。時值盛暑,又是在水上行舟,蚊子成群結隊朝他這個嫩娃娃襲來。母親舍不得把他放在甲板上,便一直將他抱在懷里,不斷用手驅趕蚊子。整整七天七夜,母親抱著他,盤腿坐在窄小的船艙里。在到達目的地的時候,母親的雙腿僵直,不能動彈,無法下船。父親背著她,這才勉強下了船。童年的苦難經歷,使他產生了一種貫徹一生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強烈責任感。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使他踏上寫出2000萬字作品的漫長作家生涯的,是他在11歲時發表了一篇文章的事。那是1951年4月的事。葉永烈正在上小學五年級。每天,他去上學時,都要路過一家報社——《浙南日報》,見到報社的門口掛著一個木頭箱子,是綠色的,上面寫著白色的三個字“投稿箱”。葉永烈起初不知道“投稿箱”干什么用。后來一問,別人告訴他,你把稿子投進去,如果寫得好,報紙就會給你登出來。葉永烈那天心血來潮,寫了一首小詩投進去。過了幾天,他收到平生第一封信,這封信他現在還保存著。信封上寫著“送鐵井欄29號葉永烈小朋友”。信上是這樣寫的:“葉永烈同學:你的稿子收到了,已經讀過,很好。我們要把它放在下期的報上‘人民生活’副刊上登出,登出后一定送一張當天的報紙給你,好不好?還有稿費。希望你以后多多寫稿子寄給我們,我們十分歡迎。稿子寫好后可以寄《浙南日報》副刊組或者你自己送來,都好。你在什么學校讀書?幾年級?有空望多多通信。告訴我們你自己的感想。祝進步!《浙南日報》副刊組四月十八日”
過了幾天,葉永烈果然收到了發表他的小詩的報紙,這就是1951年4月28日發表在《浙南日報》上的《短歌》,他從芬芳的油墨中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短歌》(十一歲小學生葉永烈)全世界人民,個個都知道:美國法西斯,武裝兩個賊;要問它名字:日本與西德。大家一聽到,憤怒像火海。舉起大拳頭,憤怒變力量。打敗美國佬,給他好教訓:咱們的祖國,不能受威脅!”他欣喜若狂。不久,他收到平生靠自己勞動掙來的稿費:9000元人民幣(舊幣,相當于九角錢)。這首稚嫩的小詩的發表,是葉永烈一生中的里程碑。他自此以后50多年,再也沒放下過手中的筆。從那首小詩發表以后,辦少先隊的壁報啦、墻報啦,油印小報啦,一概是葉永烈的事情。這鍛煉了他的寫作能力,培養了他對文學濃厚的興趣。他在上中學時,暑假、寒假都泡在圖書館里,閱讀大量的文學書籍。也就是從葉永烈看到自己的名字變成鉛字出現在報紙上的那一刻起,他就開始寫稿、投稿,愛寫什么就寫什么,讀者、編者需要寫什么就寫什么,從科普文、科幻小說,到寓言、紀實文學、小說,什么都寫,從寫豆腐塊文章到寫幾十萬字的大部頭,只要能變成鉛字就行。當他成為享譽世界的作家以后,他常常懷念發表了他第一篇作品的編輯,并千方百計地找到了這位叫楊奔的普通編輯、教師,將他當成自己的“恩師”感謝。
1951年,葉永烈進入甌海中學讀初中。他在甌海中學讀了兩年半,在1954年夏提前畢業,升入溫州第二中學高中部。1957年,葉永烈高中畢業,報考了北京大學。他對文學十分愛好,崇拜“無冕之王”——記者這個行業,想考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新聞專業。但北京大學新聞專業招生名額很少,他怕考不上,他的姐姐是念化學的,她幫葉永烈填志愿,報考了北京大學化學系,并考取了。可是葉永烈“身在曹營心在漢”,一直希望能夠從事文學寫作。中文系有時有講座葉永烈也去聽。他課余喜歡寫寫詩、寫寫散文,在《北京日報》《前線》雜志上發表。
讀理科,愛文科,這并非壞事。這培養了一個什么都能寫的“交叉型人才”,造就了一個“雜家”,一個科普作家,一個傳記作家,一個小說作家,一個寓言作家,一個什么都能寫,不喜歡人家在他那“作家”頭銜前面加定語,與那些在“作家”前面加了定語的作家大不相同的大雜家、大作家。
1958年下半年,葉永烈開始走上科普創作道路。那時,葉永烈參加大煉鋼鐵運動,來到湖南邵陽縣,幫助當地舉辦普及化驗鐵礦石的訓煉班,負責寫講義和上課。他寫了不少怎樣找礦石、辨認礦石的快板。在這里,他寫了《兩種礦物肥料介紹》這篇科普文章,發表在1958年12月23日《邵陽報》上。這是葉永烈一生從事科普創作的起點。從此,葉永烈開始轉向科學小品的寫作,在1959年發表了50多篇科學小品。雖說葉永烈在邵陽寫《兩種礦物肥料介紹》一文,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他從文學創作轉向科學小品創作,可以說具有必然性。一是他在北京大學化學系,接受了正統的化學教育。一位又一位名教授為他們開課,成為他的老師——傅鷹、張錫瑜、邢其毅、唐有琪、黃子卿、嚴仁蔭、高小霞……他們之中好多位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亦即現今的院士),漸漸充實了葉永烈頭腦中的化學知識。二是葉永烈本來就具備一定的文學基礎。就純文學創作而言,他也許不如別人,然而把文學與科學結合起來創作科學小品,創作科學文藝作品,則勝人一籌。他寫詩,寫小說,十篇之中能夠發表其一,算是很不錯了;然而寫作科學小品、寫作科學文藝作品,則百發百中,幾乎沒有退稿。就這樣,葉永烈從1959年起,轉向科普創作。1959年5月2日,葉永烈在《科學小報》上發表的關于焰火的《奪目的夜明珠》,文學色彩濃厚得多,是葉永烈發表的第一篇科學小品。
到了大學二年級放暑假的時候,葉永烈沒有回家,沒事就整天泡在圖書館里,此外就是寫文章。那個暑假葉永烈發表了20多篇文章,都是以文學筆調寫的化學小品。發了那么多文章之后,他想把它編成一本書,把書稿投給了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
對于葉永烈這個大學二年級學生的書稿,編輯照樣很認真處理。他們看了以后,決定采用,而且半年后就出版了。這就是1960年2月由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的《碳的一家》。當時葉永烈19歲。這是葉永烈從發表“小豆腐塊”文章,發展到出“磚頭”一樣的書的第一次,他的第一塊“磚頭”。
葉永烈還從《碳的一家》的出版中得到了一筆稿費收入,總共240元。在當時,對于“赤貧”的葉永烈,算是很可觀的收入了。他馬上給父母寄去120元。父母如同久旱得甘霖。父親的牙齒早就該動手術了,收到他寄去的錢,馬上換了一口新的假牙。同時,他也有錢買火車票了,他終于在假期里不再獨自留在空蕩蕩的宿舍里,可以回到遙遠南方的家中。
《碳的一家》的責任編輯叫曹燕芳,現在每年春節葉永烈都要去向她拜年。曹燕芳是葉永烈寫作生涯中的第二個“恩師”。曹燕芳不僅看中了葉永烈的第一本書,而且要求葉永烈參加她正在編撰的《十萬個為什么》。其實,在葉永烈之前,化學分冊已經寫得差不多了。她當時是請了上海好多中學化學老師寫的。化學老師們寫得有點像教科書,不如葉永烈文筆生動,她喜歡葉永烈活潑的文筆,把科學的道理說得這么有趣、明白。她頂著壓力把別人已經寫好的稿子退掉,讓葉永烈來寫。在化學分冊寫完后,曹燕芳又要葉永烈寫氣象分冊、寫天文分冊、寫農業分冊、寫生理衛生分冊……葉永烈就一口氣寫了下去。那時葉永烈只有20歲。于是,葉永烈成了《十萬個為什么》第一版的最年輕的同時也是寫得最多的作者(其中化學分冊163篇,天文分冊27篇,農業分冊93篇,生理衛生分冊43篇,總共326篇,占了全書條目總數的三分之一)。《十萬個為什么》出版后,在全國產生很大的影響。第一版《十萬個為什么》印了500萬冊。此后,《十萬個為什么》一次次修訂再版,總印數超過一億冊。葉永烈為新版《十萬個為什么》增寫了許多新的“為什么”,總共寫了599個“為什么”。以后,葉永烈又寫了一套化學史方面的書《燃燒以后》《化學海洋的燈塔》《看不見的世界》《在有機化學密林中》,以及《金屬的時代》《化學與農業》等書。
《十萬個為什么》葉永烈 等著
葉永烈為了寫《十萬個為什么》,曾生了一場大病。北京大學的學業是夠重的,《十萬個為什么》是他的“學余創作”。沉重的功課加上繁重的寫作,使葉永烈不堪重負。況且那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他連飯都吃不飽,每月能吃到一回水煮的黃豆,就算是“改善生活”了。他差一點累垮了。葉永烈的體質本來不錯,平常很少生病,以病歷卡上保持空白為榮。可是在寫《十萬個為什么》時,他突然發起高燒來,不得不住進北京大學醫院,經診斷,葉永烈患了肺炎。一星期后出院,葉永烈仍咳嗽不已,經醫生透視,他因肺炎引發了肺結核。
醫生勸葉永烈退學休養,但他仍堅持上學。他住進了“隔離”宿舍。每天清早,和病友們在草地上打太極拳,傍晚則做氣功。所幸那時《十萬個為什么》已寫得差不多了。在初版五冊出版后,寫后三冊時,葉永烈就不參與了。經過一年的治療,他的肺病終于結束了“浸潤期”,他又回到了忙碌的寫作中。
葉永烈寫作《十萬個為什么》取得成功,并非偶然。他除喜愛文學外,從小就對科普讀物十分愛好。讀中學時,他便讀了前蘇聯著名科普作家伊林(本名為伊利亞·雅科甫列維奇·馬爾夏克)寫的《十萬個為什么》和《在你周圍的事物》等科學文藝作品,深深地為那有趣的科學故事所吸引,他才知道連小摺刀、衣服、鏡子、鉛筆之類每天打交道的東西,都有著不平凡的歷史和許多奧秘。他還讀了前蘇聯科普作家別萊利曼寫的《趣味幾何學》《趣味物理學》等科普讀物。在高中時,葉永烈讀過《高士其伯伯的故事》,知道高士其是一個與病魔、與敵魔不斷斗爭的不屈戰士。但他對高士其的作品不大了解,只讀過《我們的土壤媽媽》。葉永烈入大學后,開始寫科學小品,則深受高士其的影響。他從北京東安市場舊書攤上買了不少高士其解放前的作品,作為藍本學習。他深為高士其活潑的文筆、巧妙的政治諷刺、淵博的知識所驚嘆。后來,他知道高士其住在西直門外,便于1960年去看望他,并成為高士其的座上常客。此后,葉永烈較詳細地研究了高士其的作品及他關于科普創作的理論,還讀了伊林的科普理論著作,這奠定了他從事科普創作的理論基礎。葉永烈將在他創作生涯中起了關鍵作用的三個人視為自己的恩師。他在《自傳》中說:“我的一生中有三位恩師:第一位恩師楊奔,在我十一歲的時候發表我的第一篇作品,成為我文學創作的起點;第二位恩師曹燕芳,在我十九歲的時候出版我的第一本書,引導我走上創作之路;第三位恩師高士其,在我22歲的時候成為我創作上的導師。”葉永烈知恩必報,一生與這三位恩師保持了不平常的友誼。

《小靈通漫游未來》葉永烈著
葉永烈越寫越有勁,在21歲時,他便寫成了長篇兒童科幻小說《小靈通漫游未來》。《小靈通漫游未來》寫完之后,葉永烈還是寄給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出乎意料,被退稿了。其實,論文筆、論構思,《小靈通漫游未來》比《十萬個為什么》寫得好。為什么遭到退稿呢?葉永烈當時也不明白。后來他知道了,他書里寫的那些奇奇怪怪的關于未來的美好幻想,比如三個小孩在吃大西瓜,那西瓜切開來有圓臺面那么大,吃了半天才吃了一個小坑,而當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飯都吃不飽,顯然這樣作品不符合當時的國情,所以被退稿。
1963年秋,大學畢業之后,葉永烈被分配到上海一家研究所里,在那里不到一個月,他就“跳槽”了。讀了6年大學(北大當時是六年制),葉永烈卻決心棄理從文,自己跑到上海科教電影制片廠去尋找文學工作。當時,葉永烈自我介紹,說他是《十萬個為什么》的作者。上海科教電影制片廠的領導一聽,就說知道了,你來吧。因為那時廠里正在把《十萬個為什么》搬上銀幕,拍成電影《知識老人》,所以早就知道他。就這樣,他“跳槽”到電影制片廠,工作了十八年,先是擔任編輯,后來又擔任導演。在1980年,他導演的電影《紅綠燈下》得了電影“百花獎”,此后他就離開電影制片廠,到上海作家協會擔任專業作家,一直到現在。
1976年,葉永烈在《少年科學》第一期上發表了一篇科幻小說《石油蛋白》。小說的情節很簡單,但卻受到了關注。它是“文革”冷凍期后我國出現的第一篇科幻小說。
1976年1月,葉永烈還躲在上海那間破舊的小屋里,寫了一篇在珠穆朗瑪峰發現“柔軟的恐龍蛋”的科幻小說,題為《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跡》。《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跡》,在當時當然無法發表。直至中國掃除了那四顆“災星”之后幾個月,才在上海《少年科學》1977年第二期至第三期上連載。沒想到,這篇小說后來遭到了非議,有些專家認為恐龍蛋即使被樹脂密封保護起來,經過數千萬年也必將失去活性。他們說葉永烈這篇小說是偽科學。但在20世紀90年代,人們確實發現了一枚保持“新鮮”的恐龍蛋,證明葉永烈是對的。

《世界最高峰的奇跡》葉永烈著
到了1978年,科學的春天到來了,葉永烈把退稿重新投到上海少兒出版社。這時,環境氛圍變了,在科學的春天的環境氛圍中,人人都非常關心未來,《小靈通漫游未來》很快出版了,而且第一版就發行了150萬冊,后來累計發行超過了300萬冊。《小靈通漫游未來》之所以如此受歡迎,是因為它“全景式地展現了未來世界的圖景,適合當時人們對2000年的向往之心”。這說明:一本書的出版與暢銷同機遇有很大關系。科幻小說的發展,“小靈通”的走紅,可以說是時勢使然。
在1978年,葉永烈還寫了一批其他的科幻小說,但影響都遠遠不及《小靈通漫游未來》。如《海馬》和《舊友重逢》,都是海洋開發、海洋畜牧的題材;《傷疤的秘密》寫的是利用生物采集,提煉稀有金屬;《一只奇怪的蜜蜂》以生物學和機器人為主題。
葉永烈是多產作家,作品取材范圍也很廣。在1979年,他繼續著科幻創作。這一年葉永烈的主要作品有《丟了鼻子以后》《龍宮探寶》《蚊子的啟示》《演出沒有推遲》《飛檐走壁的秘密》《奇妙的膠帕《生死未卜》《怪事連篇》《鮮花獻給誰》《“大馬虎”和“小馬虎”》《欲擒故縱》《飛向冥王星的人》《神秘衣》等。作品取材包括了醫學、仿生學、海洋開發、核物理,機器人、宇航等多門學科。
1979年3月12日,文化部和全國科學技術協會隆重舉行大會,授予葉永烈“全國先進科學普及工作者”的光榮稱號,文化部部長黃鎮在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并把獎狀和1000元獎金發給他。會后,全國各種媒體發表了報道,一時間,葉永烈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對一個科普作家,國家如此隆重地表彰,并發了巨獎(當時的1000元人民幣相當于一個技術人員兩年的工資總額),這可是史無前例的事!這給了葉永烈,也給了全國科普作家很大的鼓舞。
進入20世紀80年代,葉永烈推出了繼“小靈通”之后的一對科幻明星——金明和戈亮。在他的一系列小說中,這兩位主人公偵破了許多疑案,成為中國科幻小說史上的第一對福爾摩斯——華生式的搭檔。
葉永烈在科幻創作中不斷創新,在從事驚險科學幻想系列小說寫作時,也寫些其他樣式的科幻小說,包括意識流科幻小說《小黑人的夢》、哲理中篇科幻小說《君子國的秘密》等。他還為上海《少年科學》1981年第1期至12期寫了12篇超短篇科幻小說。以后,他寫作開始強調文學性,創作向主流文學靠近的科幻小說。1981年,葉永烈發表了科幻名作《自食其果》《腐蝕》《黑影》等。
從工程師到科幻作家
歷史見證人:王曉達(董仁威采訪紀錄)
筆者與王曉達幾乎同時跨入科普界。1979年,在四川省科普創作協會組織的筆會上,《科學文藝》主編劉佳壽告訴筆者,說這次四川發現了兩個人才,筆者為諸位前輩錯愛,忝列其中之一,另一個便是王曉達。在這一年,王曉達在《四川文學》上發表科幻處女作《波》,筆者則在《科學文藝》發表科幻處女作《分子手術刀》。后來,他堅持主攻科幻,終成一家。筆者則“心花意亂”,東一榔頭西一錘子,有稿約便寫,不管是科學家傳記文學,還是知識讀物,還有技術普及讀物、科學家報告文學、科學小品、科普文章,乃至百科全書、長篇小說,亂七八糟寫了l000多萬字,出了66部書。雖說得了不少獎,然而,“門門懂、樣樣瘟”,卻不如王曉達雖只寫了200多萬字的作品,卻因集中力量打“科幻小說”,在科幻界成為一家,被人謄為中國硬派科幻代表人物之一,中國科幻的“四大天王”之一。
在此之前,筆者和王曉達雖同在一個城市,也同在工業戰線上賣苦力,卻互不認識,只間接打過交道。他在“文革”中,是四川著名的保皇派“產業軍”的宣傳部長;筆者則有一個短時期參加過造反組織“826”,后來長期當“逍遙派”。四川的兩大派曾在1967年5月6日發生“132廠大戰”,“老產”被打得丟盔去甲,逃往鄉下,找戰友“貧下中農戰斗軍”庇護。此時,服從志愿“分配”從沿海來到成都參加建設的外地人王曉達,雖然因為文革而暈頭轉向,卻得到一個漂亮的造反派姑娘的愛。她尋找被造反派“通輯”而失蹤的王曉達,在一個貧下中農家里找到了他。這時,王曉達“彈盡糧絕”,僅穿著一條露了腚的破褲子。這個姑娘便是后來王曉達的妻子李嘉慧。王曉達成了成都女婿,在成都定居了。
筆者和王曉達有相似的命運,在命運的安排下,不能實現自己的抱負,便把滿腔“報國之心”投向科普,立志用筆桿子為武器,做“賽先生”的戰士,彌補遺憾于萬一。于是,在“賽先生”的旗幟下,筆者與王曉達認識了,成了“莫逆之交”。我們一起搞成都市科普作家協會,一起搞四川省科普作家協會,一起搞科技服務為科普作協籌措活動經費,一起輪番在家里搞聚會團結科普作家,一起為發展成都和四川的科普創作事業搖旗吶喊,一起辦《科普作家》雜志,一起辦《科普作家》網站,一起編《科普畫廊》,一起寫一本又一本科普書,一起為失去良師益友童恩正、鄭文光哭泣。他當成都市科普作家協會的理事長,筆者當副理事長;筆者當四川省科普作家協會的主席,他當副主席。兩個害了“科普”病的人,把一生中最好的年華獻給了“賽先生”,至今仍在頑強地奮斗著。有個年輕的科普部長曾問:“我實在不明白,這批人如此迷戀科普的動力從何而來?”我們一起笑著回答:“有病!”
沒有經過那段歷史的人,是不理解在這個“物欲橫流”的時代里,這批“科普狂”的志趣,更不會明白他們為什么不隨波逐流,去寫那些能賺很多錢的娛樂性“科幻”和“小說”,還要如王曉達一般,當“頑固分子”,堅持在科幻小說里必須要有科學的內涵,不把《星球大戰》之類的“偽科幻”當效法榜樣。
筆者是理解王曉達的,理解他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胸懷的拳拳報國之心,理解他作為地球村的公民,對人類、地球和宇宙命運的終極關懷。
我們這一代人,正的、反的,看得太多了。思想解放的洪流,使我們解除了思想的束縛,學會了獨立思考。我們這一代人從“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思想,發展到從地球村公民的角度,來考慮人類的前途和命運,地球和宇宙的前途和命運。這種終極關懷,用科幻小說的形式表達出來,是最好的方法之一。
王曉達,本名王孝達,1939年8月8日生于江蘇蘇州一知識分子家庭。出生時正值抗日戰爭期間,時局混亂、經濟蕭條,但父親在火柴廠當生產技術股長,母親在中學教書,生活還算穩定。父母對第一個兒子十分珍愛,特別是女師畢業身為教師的母親,對兒子的教育十分用心,不滿5歲就送上了教會小學讀書,1950年考上東吳大學附中,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當時東吳大學附中執教的有范煙橋、程小青等蘇州文化名人。1953年,剛過完13歲生日的王孝達考上了江蘇省蘇州高級中學(今江蘇省蘇州中學)。這所北宋范仲淹范文正公創建府學而立校的江蘇名校,以“名相辦學、名流長校、名師執教、名人輩出”著稱,從范仲淹、俞樾、王國維、錢穆、葉圣陶、胡繩、呂叔湘、錢偉長、李政道到如今30多名兩院院士……都是蘇州中學的驕傲。蘇州中學濃郁的學風、嚴謹的教學和豐富多彩的課余活動,對王孝達今后的人生有著很大的影響。當初他考取蘇州中學報到時,曾因身材矮小被門衛擋住,還開玩笑地對他說:“小朋友,今天開學人多事多,禮拜日再來白相。”把他當成來看熱鬧的小朋友而要拒之門外。氣吼吼的王孝達拿出了錄取通知書,才被放行。為此,報到時他堅決要求住校,以表示自己是能獨立生活的“大人”。其實,剛過13歲的王孝達當時身高僅1.47米,怎么看也是個小朋友。因為身材矮小,班上排座位只能和小女生同桌,連體育課也要與女生為伍。為此,高中頭兩年他一直耿耿于懷,直到高三突然竄高達1.73米,才不再為身高煩惱。但是“小朋友”、“小同學”的印象,一直留在同學、老師心中。
“小同學”王孝達由于基礎較好學習不費勁,做完功課就去圖書館看“閑書”,最愛看的是《西游記》《鏡花緣》《水滸傳》和外國神話、童話。圖書館的老師很喜歡這個愛讀書的“小同學”,居然破了外借一次一本的規矩,允許他一次外借三本書,還推薦介紹他看了很多“非童話”的科幻小說、文學小說和前蘇聯的驚險小說。王孝達后來回憶說,高中時期圖書館這位老師實是我的文學和科幻的啟蒙老師,她沒有給我系統的講什么文學藝術和科學幻想,而是循循善誘地把一本本好書送到我手中——《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年近衛軍》《包利法夫人》《格蘭特船長的兒女》《加林的雙曲線體》……,讓我自己去領悟體味文學藝術和科學幻想的魅力。蘇州中學,還有江南姑蘇給他播下了文學和科幻的種子。但是,高中時的王孝達并沒有想成為什么作家,而是看了前蘇聯小說《茹爾濱一家》后,一心想“科學報國”當個造船工程師,向往著穿著海魂衫在藍色、浩瀚的海洋上乘風破浪。高中畢業時他報考的是天津大學和上海造船學院(上海交通大學)焊接專業,就因為“茹爾濱一家”都是船廠的焊工。到了天津大學以后他才知道,焊接專業三個班一百幾十人,除了近十名是中專焊接專業報考的同學外,第一志愿報焊接專業的竟是鳳毛麟角,廖廖無幾,很多人認為“焊接”就是焊洋鐵壺或水落管。他卻為此暗自得意,依然一心想造大輪船,高中到大學最愛穿的還是海魂衫。
王孝達的“科學報國”,當造船工程師的理想,還與他的科技世家有關。他的父親王尚忠,是化工工程師,家中父親書桌上擺滿了一排排試管、燒杯和化學藥品,父親還多次帶他到當時機械化、自動化較高的火柴廠去參觀配方調制和生產包裝車間,使他對工業生產科學技術產生了興趣。祖父王懷琛,曾是官派德國留學生,后系原國民政府兵工署技正,兵工署重慶大渡口鋼鐵廠廠長,解放后任重慶101廠廠長,為建設成渝鐵路、寶成鐵路的鋼軌軋制立過功,后任上海鋼鐵公司總工程師,是我國鋼鐵冶金業的元老。他對孫子的學習特別關心,高中、大學寒暑假都要孫子去上海向他匯報,并聆聽訓話。王孝達“科學報國”的思想,不少來自這位嚴肅的總工程師祖父。曾祖父王同愈,是清代翰林院編修,曾參與清朝修鐵路、建炮臺等“洋務運動”,當過兩湖大學堂監督、江西提學使和江蘇總學會副會長,在蘇州園林中多處留有詩文、書畫,在當時是一名人。但他1944年誦著陸游《示兒》詩去世時,王孝達還沒上小學,不能直接受到什么教益。但是,從曾祖父“詩書門第”發展而來的科技世家,影響他形成“科學報國”的“造船夢”,一點也不牽強附會。
但是,王孝達的“造船夢”并不好圓。l961年大學畢業時,滿懷理想又志愿到“祖國最需要的、最艱苦的地方”的他,被分配到了四川成都一家鼓風機廠(后改名汽車配件廠),全廠七八百人僅有他這一名本科大學生。當時正值“困難時期”,這惟一的大學生并沒有“物以稀為貴”,廠里對這“分”來的外地大學生的食、宿都覺得是“負擔”,湊合著在工人宿舍中門口擠放了一張床,按月發放21.5斤“定量”糧票,就算生活安排了。工作么,先下車間當焊工勞動再說。這焊工當了近兩年,廠里竟然忘了他是“分”來的本科生,一直在車間當個沒有“任務”的“實習生”,還是焊工老師傅幫他反映,才想起還有他這個大學生。對于剛滿21歲的王孝達,沒想到走向社會、走向生活的第一步是如此尷尬,滿懷熱情地“到最需要的地方”去,結果到了個似乎并不需要他的地方。為此,他接二連三上書市、省乃至中央,要求“到真正需要的地方去”,還要求回天津大學重新分配……年輕的他,認為這是他個人的“用非所學”,并不明白這是當時很普遍的“社會問題”。可能是他幾十上百封信中某幾封信起了作用,1964年一紙調令把他調到了生產推土機、鏟運裝載機的成都紅旗機器廠(現工程機械廠)當鉚焊車間的技術員。這下是“學以致用”了,造不了船造推土機、鏟運機這陸地行舟也可以,王孝達高興地自己拉著板車裝著書籍、行李去報到。不料“需要”他的工廠接待他,也和汽配廠差不多。在住三個人的宿舍門口擠放一張床,連門都不能大開,工作也是先當焊工勞動一陣再說。于是,他又當了近兩年焊工沒人想起……這時他才明白“學以致用”不是個簡單的個人問題,有用沒用要你自己去“表現”,才會有人“用”你。于是他不再申訴、上書,而是實實在在地從學習焊工技術開始發揮自己的作用。一面當焊工,一面幫車間編工藝、改工裝……一步步從車間技術員到廠技術科工藝組、設計組……工程師之路似乎上了軌道。
無奈“天有不測風云”,十年動亂開始了。技術科成了“黑窩”——科技人員十有七八都是“成份”高、家庭出身不好的,造反派“血統論”的大字報從樓道貼到辦公室,從科長到技術員都敢怒不敢言,出身知識分子屬“麻五類”的王孝達忍無可忍,針鋒相對地寫了幾十張大字報對著干,身不由己地成了“造反派”的對立面。鬼使神差的是,社會上是“造反派”反“血統論”,而反“血統論”的王孝達恰成了對立面“保守派”,而且還與省、市“保守派”掛上了鉤,當上了當時四川“產業軍”的宣傳部長。十年動亂本是黑白混淆、是非顛倒,渾渾噩噩的王孝達經歷了被造反派“全國通緝”、衣不蔽體被趕出城、上京告狀、辦“個人學習班”……最后直到1976年以后,才明白了社會和政治是如此深沉復雜。
王曉達在最初從事科幻小說創作時,還沒有想這么多。他開始寫科幻小說,是很偶然的。
20多年前,王曉達這個從“五七干校”回廠不久的技術員正以空前的熱情迎接科學的春天。大亂甫定,國家開始恢復經濟建設,從史無前例的大動亂中“大開眼界、大長見識”的王孝達,一心回到設計桌上繼續自己的工程師之路,參加了新型裝載機的設計、試制工作,因此獲得了全國科學大會三等獎。
正當王孝達暗自得意時,突然一紙調令把他從設計科調往工廠技校任班主任。調令緣何而發,至今不得而知,但對一心想當工程師的王孝達無疑是當頭棒喝,他氣得一天沒有吃鈑、三天沒有說話,但在那個自己無力掌握自己命運的年代里,“胳膊扭不過大腿”,無奈中他不得不“走馬上任”,去技校當班主任。
現在來看,這紙調令正是工程師王孝達向科幻作家王曉達轉變的轉折點,并非壞事。“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事物的辯證法就是如此。“工程師易得,科幻作家難求”。面對那些認為“讀書無用”的學生,王孝達這個書生氣十足的班主任十分無奈。此時他想起了在蘇州中學時讀過的科幻小說,想出了用描繪“科學技術變化無窮、科學技術威力無窮”的科幻小說來“勸學”的招式。由于當時他找不到多少科幻小說來當“勸學篇”,就想自己動筆寫。于是,在技校的第一個暑假,王孝達在工廠筒子樓宿舍里揮汗猛寫,竟寫成了一篇科幻小說《波》。他的這篇科幻小說“處女作”《波》,首先以手抄本的形式流傳,讀者是他的學生和朋友。由于當時科幻小說很少,《波》因“物以稀為貴”而頗受歡迎。約4萬字的《波》他手抄了三本,還“供不應求”,居然有人等他抄幾頁看幾頁,他覺得此“招”助學有效而暗自有點得意。有朋友讀后慫恿他去投稿,王孝達在郵局門前轉了很久才下定決心把稿子投入了郵筒。以后幾天,他一日幾次地在收發室窺探,心想如若退稿回來就趕緊拿信走人,免得別人笑話。不料幾周后,《四川文學》的編輯竟到技校來找他,說準備發表《波》,讓他小作修改,用稿箋紙正式抄寫后送編輯部。當時王孝達真有點發暈,激動得話都說不連貫,引得那位女編輯不時掩嘴發笑。王孝達用了三天的空余時間,就把4萬多字的稿子工工整整抄好,恭恭敬敬地送到了編輯部。1979年4月,《四川文學》全文發表王孝達的處女作《波》。從此以后,他“一發不可收拾”,工程師王孝達漂亮轉身,變成了科幻作家王曉達,以后竟然寫了20多年科幻小說而樂此不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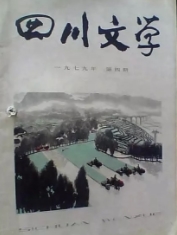
《四川文學》1979年第4期
與其他幾位“少年老成”的科幻作家不同,王曉達40歲才出“處女作”,當稱“晚成”。但是,“處女作”《波》卻“一炮打響”,據說當月北京、上海、江蘇、廣東就有人傳說“四川又出了一篇科幻小說”而爭相傳閱。說是“又”,是指前兩年四川童恩正的科幻小說《珊瑚島上的死光》在《人民文學》發表而引起轟動之后,文學雜志和報刊再未發表過科幻作品。當年年底,《波》在北京、四川、哈爾濱等地報刊連載,上海、廣東、貴州、浙江等地改編成連環畫;四川、上海還以評書、故事形式演出;第二年“八一電影制片廠”編輯專程到成都商量改編電影……一篇“處女作”竟然有如此反響,說明這并不是王曉達自己所說的“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雖然當時除了《小靈通漫游未來》和《珊瑚島上的死光》之外,科幻小說的確是鳳毛麟角,但《波》本身的科幻魅力是引起廣泛關注和興趣之所在。回顧王曉達從工程師到科幻作家轉變的歷程,確有“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之意。從中學、大學到工作,文化、科學積淀,姑蘇文化、科技世家、“科學報國”造船夢、動亂的“見識”,這一切的一切,出人意料的在科幻小說上噴發了,“厚積薄發”而脫穎而出。
后來王曉達在大學任教期間,依然認為自己的主業是材科、熱加工和金屬工藝學的教學工作,以教學科研成績從講師、副教授晉升到教授。即使這段時期他還寫了200多萬字的科幻、科普作品,依然認為“科幻”只是自己的愛好,是副業。但他也不得不承認,他的教學科研雖然也可稱成績卓著,但影響作用遠不及“科幻”。專門向他求教材科、金工學問的并不多,而看了他科幻小說不遠千里寫信、打電話向他咨詢科幻小說中的“科技發展”和索求參考資料的卻連年不斷,甚至有大學生要改專業專攻他寫的“信息波防御系統”。王曉達確實比王孝達更有名、更有影響力。多一個王工程師、王教授當然是好事,但我們更希望有能引發“科技變化無窮、科技威力無窮”興趣的科幻作家王曉達。
當初,王曉達寫科幻小說《波》,是無奈的班主任的“勸學怪招”,頗有“功利”目的,并不像很多“文學愛好者”是為了一展自己的文學才華。但是,《波》發表不久后引起的熱烈反響,使王曉達對科幻的態度有了大大的提升。
《波》發表后,王曉達得到中國科幻界泰斗鄭文光的提攜。王曉達是在1979年成都會議上認識鄭文光的,當時鄭文光在主席臺上,王曉達是列席代表。當鄭文光知道在《四川文學》發表科幻小說《波》的作者到會,專門約王曉達面談,并對他說,“我看了你的《波》,很喜歡。你的路子對,你還要寫,以后把稿子給我,我來推薦。”對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作者予以極大的關懷和鼓勵。接著又把王曉達介紹給《人民文學》、上海少兒社、天津新蕾社和肖建亨、葉永烈、童恩正等人。嗣后,在接受香港《開卷》雜志主編杜漸采訪時,又專門介紹四川新人王曉達,并在以后數篇科幻專稿中評介王曉達的作品。王曉達的《太空幽靈島》《冰下的夢》《方寸乾坤》《記憶猶新》等作品都是在鄭文光直接關懷和指導下問世的。當中國作家協會文革后第一次恢復發展會員時,是鄭文光直接在北京為王曉達填表介紹他入會的。王曉達去北京,鄭文光多次約他去和平里家中敘談并留宿徹夜長談。王曉達一直尊鄭文光為恩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