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周一:“局外人”的堅守與轉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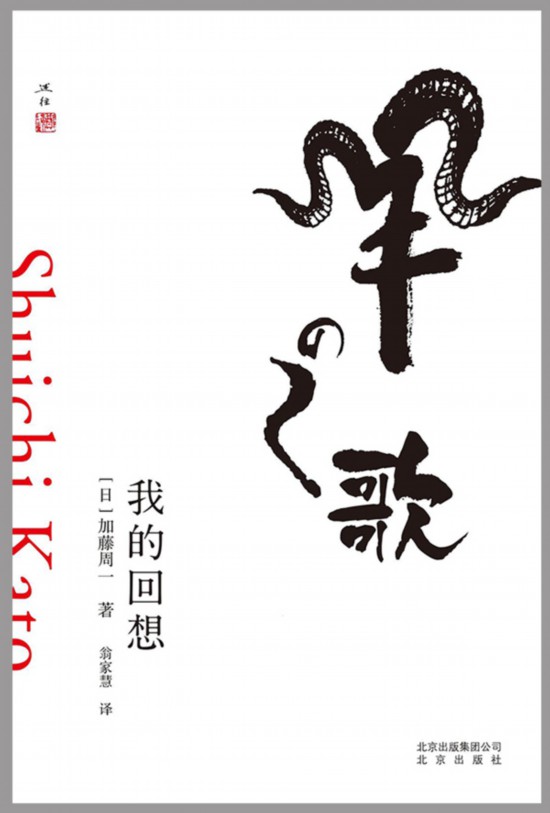
《羊之歌:我的回想》,[日]加藤周一著,翁家慧譯,北京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400頁,59.00元
1968年8月和9月,日本著名知識分子、文學評論家和思想家加藤周一的自傳體小說《羊之歌:我的回憶》(以下簡稱《羊之歌》)和《續·羊之歌》在巖波書店相繼出版。這部作品從1966年10月至1967年12月在《朝日雜志》上連載,頗受歡迎。集結成書后也好評如潮,暢銷不衰。在2018年巖波書店創業一百年之際舉行的“讀者優選佳書”調查中,該書榮登“巖波新書”系列第三名,僅次于齋藤茂吉的《萬葉秀歌》(上下卷)和丸山真男的《日本的思想》。
在《日本文學史序說》(下卷)中,加藤對日本著名經濟學家河上肇的自傳《自敘傳》評價甚高:“河上的《自敘傳》之所以是優秀的文學作品,不單是因為他的文章明了,情景的描寫生動,而且還因為主人公,也就是河上肇本人是復雜而多面的,同時又具備了自己的個性,即一貫堅強的人格的自我同一性。因此他的人格的形成史與思想發展史重疊在一起,這種重疊又敏銳地反映了時代本身。”這段評語用來形容《羊之歌》自也十分貼切。今年恰逢加藤誕辰一百周年。讀他的回憶錄,既是讀個人成長,也是讀時代變遷。
《羊之歌》問世時,出生于1919年9月的加藤還不到五十歲,出版回憶錄似乎為時尚早。當時,后來被譽為“知識巨匠”的加藤已出版《日本文化的雜交種性》《現代歐洲思想注釋》等名作,但尚未開始撰寫“確立其在思想界和文化界的權威地位”的代表作《日本文學史序說》(上下卷)(該書由筑摩書房出版于1980年),距離他牽頭成立著名護憲團體“九條會”也尚有三十六年之久。“九條會”全稱為“和平憲法第九條之會”,最初由俄亥俄大學教授查爾斯·奧弗比(Charles M. Overby)于1991年在美國創立。2004年6月1日,加藤周一、大江健三郎、鶴見俊輔等九名知名知識分子聯名發表“九條會宣言”,九條會在日本正式成立。該團體反對修改憲法第九條,呼吁維護“和平憲法”的原貌。
《羊之歌》僅敘述了加藤的前半生,而且因其自傳體小說的體例,書中不乏虛構和隱匿實情的部分,但仍舊清晰地勾勒出作者的思想和情感軌跡。
“‘局外人’概括了我跟社會的所有關系”
日本的法國文學研究者和評論家海老坂武認為,《羊之歌》的寫作或許受到了薩特出版于1964年的自傳《詞語》的啟發。兩書的開篇的確如出一轍:“上個世紀末,佐賀縣一個資本家的獨子當上了明治新政府陸軍騎兵將校”(第3頁);“1850年左右,在阿爾薩斯這個地方,有一位小學教師為養活眾多的子女而不得不做了食品雜貨商。”兩書在簡潔介紹家庭構成后過渡到傳主本人,對自己的生涯經歷展開剖析。
正、續《羊之歌》各由二十篇散文組成。《羊之歌》從童年寫至求學,中間穿插作者的戰時遭遇以及對日本參戰的感悟,以題為《8月15日》的篇章作結。這篇文章傳達出痛楚、憤慨與欣快交織的復雜心態:“被戰火夷為平地的東京……有的就是那種巨大的徒勞感消失之后的無邊空虛”、“當時的我,心中充滿了希望。我再沒有像當時那樣對日本的未來充滿了樂觀的情緒”(181-182頁)。“終戰日”于國于人都是終途和起點的雙重象征。到了《續·羊之歌》,作者主要將筆墨投注于戰后的留學生活,夾雜對西方和日本文學文化的評論感悟,并以隱晦的筆觸記錄了幾段戀愛經歷。在本書的最后兩個篇章《永別》和《審議未了》中,作者以虛實相間的手法回顧了自己在1960年安保斗爭中積極發聲的動機、經過以及對這一運動的思考。全書戛然而止于1960年,“我對自己的審議還沒有完”(356頁),經歷斗爭洗禮的加藤寫道。他似乎還是十五年前那個站在東京的晴空之下、焦土之上的熱血青年,再一次踏上嶄新的征程。
雖然正、續《羊之歌》的內容側重有所不同,但作者為自己塑造的“旁觀者”/“局外人”的形象卻是極其鮮明且一以貫之的。加藤自幼便對周遭的人事淡漠疏離:“對我來說,不論做法事,還是辦婚禮,這樣的宴會跟我沒有絲毫關系,我就坐在一邊靜靜地觀察。……我是一個局外人,也許會永遠過著局外人的生活。”(21頁)“突然地,沒有任何動機,也沒有任何理由,我的腦海里浮現出一個不容否定、奇特又清晰的想法——這里的一切都毫無意義。屋里所有的人,他們興奮的表情、他們說的話、他們的大聲喧鬧,都像潮水般迅速地退去,退向無垠的彼岸,變得跟我沒有絲毫的關系。”(22頁)隨著年齡漸長,他似乎愈加安然于以“局外人”為自己的為人處事定調:“‘局外人’這個詞好像概括了我跟社會的所有關系。”(171頁)
這一姿態在《續·羊之歌》中也延續下來。在戰局正酣,日常生活朝不保夕之際,加藤形容自己“對所謂的家國天下之類的宏圖大論,卻總是保持冷眼旁觀的姿態,安穩地過我自己的日子”(192頁)。廣島遭受原子彈襲擊后,加藤作為日方醫師代表之一前往當地從事病理學方面的檢驗工作。面對滿目瘡痍,他仍然無法甩脫“局外人”的外殼:“在這次旅行中,我有一種非常強烈的感受。我覺得自己既不屬于當地人,也不屬于占領軍,我只是一個旁觀者,一個見證了當地人和占領軍軍醫相遇這一幕的旁觀者”(201頁)。
加藤出身知識分子家庭,家境富裕,自幼便有與同學格格不入之感。隨著青春期的來臨,這種感觸愈發熾烈。在加藤于十七至二十二歲(1937-1942)記下的八冊《青春日記》中反復出現“孤獨”的字眼。他為“無法逃離這個喧囂的世界”而孤獨。《青春日記》中記載了他的多首詩作,其中一首題為《孤獨》,詩中前四句寫道:“世界喧囂無比/我居住的世界喧囂無比/無法忍受的我/逃往只有我一個人的所在。”他為難以理解日本國民對戰爭的狂熱而孤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加藤在當天的日記中記下醫學部教授鼓勵學生在戰時堅持上課和從事科研的細節,以示對戰爭的反抗。他在《羊之歌》中這樣回憶當天的心情:“我懷著黯淡的心情注視著東京市民的狂喜,感覺自己跟他們之間的距離從來沒有如此遙遠過。”此外,也不乏加藤戀愛受挫后的孤獨寂寥。這種深入骨髓的孤獨感或許可以部分解釋他常年置身事外、冷眼觀望的人生態度。
另一方面,加藤有意識地與外部環境保持距離,與其作為血液學專家的理性客觀也有著密切的關聯。他曾就讀于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后在該校附屬醫院工作數年,直到1946年正式棄醫從文。多年的學醫和行醫經歷使得他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種“只在準確的事實基礎之上得出可能范圍內的所有結論,對無法驗證的所有判斷都持懷疑態度”的“看待事物的思維方式”(165頁)。終其一生,無論是創作還是投身于社會活動,加藤都踐行著這套思維方式。韓裔日籍政治學者姜尚中在一篇題為《超越戰爭的世紀》的評論文章中指出,加藤對法國著名詩人保羅·瓦萊里的作品一見傾心,是被其“知性的明晰性和美感”所打動,并決意效仿。在一篇名為《讀書的回憶》的散文中,加藤曾寫道:“后來上大學預科,我在瓦萊里的作品中發現了采取分析方法來處理語言表現的可能性,以及這種方法的無與倫比的樂趣。”加藤的著作確實兼具“明晰的邏輯與優美的詩性表現”(立命館大學圖書館“加藤周一文庫”介紹語)。作家池澤夏樹也注意到加藤身上并存著觀察者和分析家的特質,“他從不混入私人情感,擁有憑借邏輯立身處世的強大決心”。在《羊之歌》中,將加藤此種特性展現得最為淋漓盡致的莫過于他對日本政府發動侵華和侵美戰爭的反感和批判。
“拒絕為集體獻身是我將為之獻身的事業”
上世紀三十年代,經歷了短暫繁榮穩定期的日本開始顯現出向右轉的不祥之兆。日本著名政治學者丸山真男在《福澤諭吉與日本現代化》一書中概括道:“九·一八事變那年……用經濟術語來表達,是出現剪刀差的一年。亦即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的曲線漸漸下降,右翼的、或國家主義的路線急速上升的時期。”
芥川龍之介的作品為加藤種下了質疑官方宣傳的第一粒種子:“我很佩服芥川(龍之介)的那些短篇小說,但更讓我驚訝的是《侏儒的話》。芥川寫‘軍人猶如小兒……’這句話是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我讀到它的時候,完全是把它當作三十年代中期,也就是同時代人所說的話來看的。不管是學校、家里,還是社會,一直以來所信奉的被神圣化的一切價值,竟不堪芥川龍之介的這一擊,它們在我眼前瞬間坍塌。愛國心變成了利己主義,絕對服從變成了不負責任,美德變成了怯懦或無知。針對同一個社會現象,還有可能做出跟報紙、學校和整個社會所做的解釋完全相反的另一種解釋,我為這一可能性的存在而驚訝不已,興奮得手舞足蹈。”(80頁)“二·二六事件”發生后,無比敬畏天皇的父親對“陸軍在國內日趨增強的政治影響力”贊賞不已,尚就讀于初中的加藤卻能看破新聞宣傳的謊言和欺騙,敏銳地意識到“通向荒涼未來的軍部獨裁之路”(94頁)正在逐步鋪就。
進入舊制第一高等學校之后,加藤在“學生自治宿舍”過上了殘留著民主主義之風的校園生活。他由衷欣賞這種生活方式,同時也并未忽視其中暗含的與外界有所區隔的特權主義。更重要的是,面對日本社會中日漸擴散彌漫的集體主義風潮,十八歲的加藤表達了明確的反感和拒斥,并誓言捍衛個體的自由獨立:“駒場的生活讓我第一次認識到,所有的集體生活可能都需要放棄、妥協和糊弄。在集體生活中我學會了如何自我保護,但我絕不學習如何為集體獻身。拒絕為集體獻身——把這個理念正當化才是我為之獻身的事業。”(102頁)
作為一名大學生,加藤表達憤懣不滿的方式不外乎翻起一對白眼,將瘋狂的時局視作無物。《羊之歌》中有一則膾炙人口的片段。太平洋戰爭爆發當天,東京已開始燈火管制。但加藤若無其事一般依照原計劃前往東京新橋演舞場觀看大阪文樂劇團的演出。這場表演給他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這里早就沒有了戰爭,沒有了燈火管制,沒有了內閣情報局,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個世界,一個任何事物都難以撼動的、固若金湯的世界。……唯有此刻,這個世界才無需通過密匝匝的觀眾,無遮無攔、毫無退讓地展現出所有的自足性和自我目的性。它就這樣色彩鮮明地、威風凜凜地存在著,宛如一出悲劇,與劇場外面的另一個世界——軍國主義日本的概念和所有的一切現實——形成鮮明對比。”(140頁)
因罹患肋膜炎,加藤被免除了兵役,但他的朋友們卻沒有這樣的運氣:“我的朋友一個接一個地離去,戰爭結束前,沒有一個人回來。”(162頁)才華橫溢、從高中起便與加藤共同嘗試文學創作的好友中西哲吉戰死沙場,對他的打擊尤為沉重:“當我得知中西的死訊時,大腦一片空白,良久才恢復意識,我感到了難以遏制的憤怒,而不是悲傷。就算原諒了太平洋戰爭的一切,我都不會原諒中西的死。那是罪,是無法挽回的罪,是罪,就必須抵償……”;“我活了下來,中西死了——這件事情沒有任何正當的理由。”(163頁)值得一提的是,上文雖曾提及加藤那似乎是與生俱來的孤獨感,但他并非孤立無援地行走于世,而是擁有相當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他在《羊之歌》中以詼諧的筆調記敘了“小說之神”橫光利一因鼓吹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而遭到包括自己在內的東大學生“圍攻”的事件,可見當時保持清醒和銳氣的青年人并不在少數。此外,二戰結束后不久,加藤便與兩位友人中村真一郎、福永武彥合著出版了《1946:文學的考察》,其后又邀請更多同伴一起創辦雜志,為戰后的文學界吹入新風。多年后,八十五歲高齡的加藤和八名友人聯名發起“九條會”,令人仿佛窺見他當初與一眾好友攜手重塑文壇的風采。
漢娜?阿倫特在《黑暗時代的人們》中寫道:“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中,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啟明(illumination),這種啟明或許并不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更多地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經常很微弱的光亮。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們的生命,它們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都點燃著,并把光散射到他們在塵世所擁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圍。”要擺脫“黑暗時代”的影響和控制絕非易事。然而,恰恰是這些年輕勇敢、曾點亮黑夜的生命付出了最為無可挽回的代價。這種慘烈的犧牲使得加藤逐漸卸下了“旁觀者”“局外人”的鎧甲。
“我始終都會是一名旁觀者嗎?”
1954年,加藤結束三年的留學生活,返回東京,在一家礦山公司總部的醫務室工作。公司安排他參觀九州的礦山,他很快發現自己在公司和工會的對立中左右為難,無法抉擇哪方更為“正義”。這段特殊的經歷使他在《羊之歌》中首次對“旁觀者”的立場提出了質疑:“從旁觀者角度做出判斷——這樣的判斷很多時候都是做不到的。因此,有時候必須拋開旁觀者的身份……”(323頁)
不過,這并非加藤第一次擺脫旁觀者的束縛,明確發表意見。早在1946年出版的《1946:文學的考察》中,加藤便對“星堇派”,即知識淵博、趣味高雅,卻在戰時對軍國主義政府毫無批判甚至盲從的青年知識分子們進行了嚴厲批評。《1946:文學的考察》還指出,“從戰爭到戰后,日本沒有足以對抗外在現實的、完成內在力量充分成長的作品”,因此有必要反對超國家主義和極具破壞性的“革命精神”,從而培養日本人的“理性和人性”,重燃日本社會已瀕臨消亡的民主主義精神。盡管加藤自詡“跟羊的溫馴性格有不少相通之處”(357頁)——《羊之歌》也是因此得名,但在這批評論文章中卻流露出言辭鋒銳明快的性格特征。
1959年至1960年間,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安保斗爭”在日本爆發。這場運動更加徹底地促成了加藤從旁觀者到參與者的轉向。“當我走到大學正門的時候,在門口突然碰到了一群扛著‘反對安保’標語牌出來游行的大學生。他們慢慢地排成一隊,靜靜地走出正門,朝著三丁目方向走去。……看著他們的背影,我不由得回憶起戰爭末期‘學徒出陣’的情景。……可是我,既不能加入他們的隊伍,也不能阻止他們的犧牲。這是何等無奈!又是何等悲哀!……我把自己培養成了一名旁觀者,但就在那個時候,我黯淡的內心已經產生了一種懷疑:我始終都會是一名旁觀者嗎?”(346頁)那一刻,戰死的友人與蓬勃青年的身影交疊在一處,不難想象這幅景象給予加藤的震撼。他加入了運動的大潮,通過撰寫評論文章和參加座談會宣揚廢除安保條約的主張。《羊之歌》中清晰地歸納了在安保斗爭中與加藤互通聲氣的丸山真男的觀點。即反對安保條約“主要是反對強行表決的程序”,民眾要求政府在對法案進行充分審議,并認真聽取民意的基礎之上再做決定。而且,運動本身恰恰是“民主主義實質化轉變的臺階”(352頁),對建設成熟的市民社會而言,可謂難能可貴的實踐經驗。
民眾的反對并未動搖岸信介內閣通過法案的決心,斗爭以失敗告終。加藤也坦誠此次運動在自己與好幾位朋友和“一些人群”之間“造成了裂痕”(352頁)。然而,這絕不是加藤最后一次出于“道義感”在社會運動中挺身而出。戰后日本的前途走向始終令這位特立獨行的“羊年生人”掛懷不已。
尾聲
在《羊之歌》后記中,加藤說自己想為“平均狀態的日本人”作傳。這種表達與薩特在自傳《詞語》中所寫的“一個完整的人,他由一切人所構成,又頂得上一切人,而且任何人都可以與他相提并論”似有異曲同工之妙。可見杰出的自傳與其說是傳主本人為回顧人生歷程所撰,不如說是試圖將時代精神濃縮于個人經歷之中,為時代作傳,亦為大眾發聲。從局外人到活動家,加藤走過漫長的歲月。他將這一切記錄下來,為曾經或正掙扎于黑暗時代的人們提供智慧與勇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