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心人:驚心動魄求生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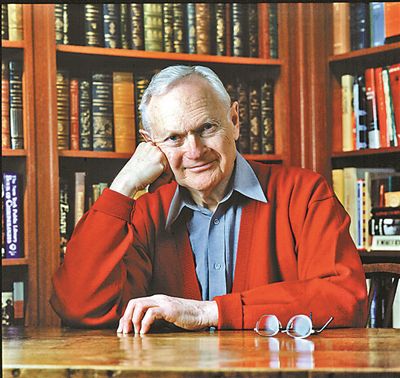
《生命之書》作者舍溫·努蘭
德國醫生、心理學家洛伊曾說:“生命科學中包含的精神價值,是無法用今日科學那種物質至上的態度說清楚的。”醫學是一門科學,更是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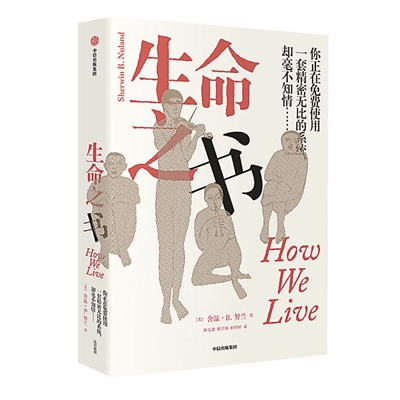
書名:《生命之書》 作者:[美] 舍溫·努蘭 林文斌/廖月娟/杜婷婷譯 中信出版集團·見識城邦 2019年3月出版
《生命之書》是耶魯大學醫學院教授努蘭醫生個人行醫生涯和人生經驗交織而成的記錄與反省。作者以醫生的身份帶領讀者開啟一場探索生命的旅行,以醫生的雙手揭開生命的神秘面紗。以疾病為切入點,從循環系統、神經系統、消化系統,講到生殖系統,用作者處理過的真實病例,讓讀者知道各個系統如何運作。另有章節專門討論血液、遺傳、心臟,以及人體細胞浸泡于其中的組織間液,還有生命的基本單位——細胞……本書不僅為讀者呈現了人體的精妙,更講述了使生命延續,以及人存在的意義。
在醫生的眼中,見到的多半是人體脆弱的一面,但也一定會見證人體對抗疾病時展現出的強韌生命力,各個組織之間緊密合作,達成完美協調平衡狀態的“身體的智慧”。我們的身體不僅僅是一部超級復雜而精密的機器,更能夠不斷適應和調整,一次次重回平衡狀態,一切為了生存。關于身體,關于生命,關于疾病和健康,我們探索得越是深入,就越覺得有更多的未知……
克里特拉住院第3周的星期四晚上,心臟外科主任醫生到重癥監護病房通知他說,終于等到一顆心了。克里特拉告訴自己不要太樂觀,也用不著恐慌,畢竟一個星期前他已聽過同樣的消息,最后卻因那顆心狀況不佳而作罷。然而,這次看來還真煞有其事,進行得很順利。這次,不只是血型,連心臟尺寸都估量好了,那顆心放在克里特拉原來的心臟部位剛剛好。
他太太和三個孩子立刻趕來醫院。他們一踏入重癥監護病房就仿佛置身于嘉年華。克里特拉描述道:
真是熱鬧。每一個人都在歡呼,醫院上上下下好像都發了瘋。這時,我的胸口又痛了起來。護士小姐幫我打了麻醉止痛劑,于是我也跟著樂得飄飄然。
新英格蘭器官銀行已和埃迪聯絡過,告訴她離紐黑文220多千米遠的一家馬薩諸塞州的醫院可能有合適的捐贈者。這個愿意遺愛人間的年輕人已經腦死亡,靠著呼吸器存活。雖然他已沒有康復的希望,但是胸腔和腹部所有的器官都還完好。
過了午夜,移植小組在格雷姆·哈蒙德醫生的帶領下搭乘雙引擎直升機出發了。耶魯的研究員萊特森也一同前往,擔任哈蒙德醫生的助手。正如以往,埃迪也在,密切監控全程。這一行人在12點半抵達醫院,救護車早就在那兒待命了,隨即火速趕到醫院。不料,在凌晨時分,該院只有兩間能使用的手術室,而這兩間都在進行緊急手術,沒有其他空房了,面對分秒必爭的換心手術,真叫人扼腕。
然而,耶魯紐黑文醫院的麻醉小組并未預料到會有延遲,早就把克里特拉送到手術準備室,準備為他全身麻醉。克里特拉的家人送他到手術室門口。在被推進自動門時,他露出笑容,高舉著緊握的拳頭,豎起大拇指,表示志在必得。
凌晨兩點,我來到手術室時,麻醉科的凱文·莫里森醫生正和克里特拉坐在幽暗的室內,莫里森醫生以輕柔的語氣安撫克里特拉,希望減輕他那新生的恐懼。克里特拉慢慢地睡著了,于是我溜到手術室旁邊的醫生休息室打盹兒,身旁的實習醫生正鼾聲大作。過了5 點,護士進來輕搖我的肩膀,告訴我埃迪通知他們捐贈者終于可以進手術室了,哈蒙德醫生和萊特森已準備“收割”。
我實在不喜歡用“收割”這個詞,但就取出捐贈者的器官而言,實在沒有更好的說辭了:移植小組聚集在捐贈者最后待的醫院,時間和程序計算得幾乎分秒不差,然后取出他們寶貴的生命組織,如肝、腎、胰、心、肺……移植到已望穿秋水、命在旦夕的病人身上。這些器官在抗生素和生理鹽水的保護、滋養下,通常不會壞死,還有旺盛的生命力,植入接受者體內后,就可創造起死回生的奇跡。
然而,直到今天,我們還以為器官移植是偶爾聽到的醫療新聞,而不是每天都在進行的事。其實,隨時都有病人瀕臨器官衰竭,他們最后時刻的一線生機就是器官移植。由于社會大眾不清楚這種急迫的需要,許多苦等不到器官的人只好無奈地面對死亡。同時,每年卻有好幾萬可做器官捐贈的人未能捐出完好的器官便撒手人寰,失去繼續造福人間的機會。說起來,眼見一個家庭遭逢不幸,發生白發人送黑發人的悲劇,叫人如何忍心勸說悲痛的雙親捐出孩子的器官?為了解決這個難題,許多歐洲國家制定器官捐贈同意法案,也就是若家屬不反對,因意外事件導致腦死亡的人視為自動同意讓醫生取出器官救助等待移植的人。然而,這種做法在美國還遲遲未能推行,在可供移植的器官嚴重短缺的情況下,很多急需移植的病人只好抱著遺憾面對死亡。除非,我們的社會能深切地了解他們的需要。
克里特拉接受移植那天,由于我一直在他身旁,因而無法親眼看到從供體取心的過程,但我已聽聞許多細節。這位年輕人的家屬只愿意捐出心臟。一般而言,很多捐贈者會同時捐出多個可用器官,這樣心臟則是最后一個。由于沒有繼續延遲下去,耶魯紐黑文這邊的團隊就可按照原計劃進行。埃迪確定捐贈者的心臟已注射正確的靜脈輸液和藥物,且正常跳動后,移植小組就開始取心。
哈蒙德和萊特森先從胸骨正中縱切,接著鋸開胸骨、切開心包膜和旁邊的韌帶組織后,就開始切割腔靜脈、主動脈和肺動脈。可以將心臟移出胸腔時,埃迪立即通知耶魯紐黑文方面,克里特拉的手術可以同時進行了。他們給捐贈者打了類固醇和抗生素,再把抗凝血的肝素注入供體的血液中,以避免阻塞,接著再施予鉀離子溶液,心臟即停止跳動。
埃迪記錄了血管鉗夾住大血管的時間——清晨5點24分。接著,哈蒙德和萊特森以快刀斬亂麻之勢取出心臟。5點44分,埃迪打電話給紐黑文那邊的團隊,他們準備帶心回來了。心臟放在一個有四層同心圓的塑膠盒正中,旁邊三圈都是冰冷的鹽類溶液,盒子外面再以冷凍盒來保護。在救護車飛奔著去往機場時,萊特森小心翼翼地把冷凍盒抱在膝上。他們一到,直升機立刻起飛,很快就在紐黑文降落。之后,他們又從機場沖回醫院。6點52分,埃迪通知手術室,他們已經回來了。這趟從馬薩諸塞州到耶魯紐黑文的沖刺,總共花了58分鐘。
此時,克里特拉的胸腔也打開了,準備迎接一顆新的心臟。醫生已幫他打了抑制免疫反應的環孢霉素和抑制骨髓活動的咪唑硫嘌呤,隨后會再給他打了類固醇。對于抗生素的種類,他們也鄭重其事地幫他選擇。之前,在手術成員開始洗手的時候,麻醉科的莫里森醫生已往克里特拉的靜脈打入速效麻醉劑,再插上氣管插管。在所有動、靜脈的監視管線都安置好之后,克里斯汀·吉爾伯特就在克里特拉上半身涂上碘消毒液,再蓋上無菌手術鋪單。
就在麻醉的幾分鐘前,此次移植的主刀醫生約翰·鮑德溫進入手術室。他是個不茍言笑的人,工作時更是緊抿著嘴。他才41歲,看來雖還年輕,行事卻很老成、實事求是;他那無可妥協的專注展現出十足的自信。
鮑德溫來耶魯紐黑文還不到兩年。他是舉世聞名的心臟移植權威沙姆韋醫生的得意門生。在他任職前幾個月,院內已有許多傳聞,知道將有一位明星人物加入。已顯頹勢的心臟外科對他寄予厚望,希望他的到來能讓心臟外科奮起直追其他頂尖的外科部門。之前,經歷了兩屆主任的努力和研究委員會苦口婆心的勸說,仍舊沒有招募到合適的人選來重振心臟外科。
耶魯紐黑文能延攬到鮑德溫,耶魯醫學院院長可謂鉚足了勁兒,提出了相當優厚的條件:絕對的權威,而且不出幾個月即可晉升教授。因此鮑德溫一上任即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不僅鞏固自己的外科地盤,也讓放射科、心臟內科等團隊臣服。鮑德溫是以優異成績從哈佛醫學院畢業的高材生、羅茲獎學金得主,也是近年來在心肺聯合移植方面貢獻良多的精英,他不但技術超群,更有一流的研究能力。那外表展露的自信更每每令人懾服,只要跟他說上幾句話就知道了。
(節選自《生命之書》,中信出版集團·見識城邦,2019年3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