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雅興與修行 ——讀韓耀成先生譯黑塞之《園圃之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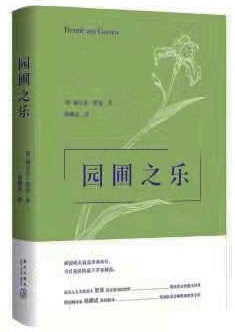
這年頭,想著要有學問的人很多,可是有情懷的文人卻不多了。躬耕園圃需要一種情懷,從青年至暮年不輟,需要大情懷。黑塞的《園圃之樂》字字句句流露出文人的情懷。
在中國古代,小園香徑與通幽的曲徑,實在也是相隔不遠。一條,文人徘徊于其上,觀賞小園;一條,通向禪房的花木。且唯此小園與花木處,可稱得上園圃。所謂園圃,與文人的雅興和修身養性密切相關。其余的,則要么是實用的果園菜園,要么是彰顯財富和權力的赫赫園林。
黑塞的《園圃之樂》是文人雅興和修身養性之作。譯者在“生活奔波和事物羈絆的縫隙中”移譯出來,筆者則是放下“生活的奔波和事物的羈絆”,細細品讀,頭腦中不時浮現出童年時奶奶家門前的田畝、不遠處老城墻的斷垣和落日余暉中的炊煙,才知道童年和故鄉其實一直深埋心底,只待被叩問和喚醒。
黑塞(1877—1962)系德國作家,后移居瑞士,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作品在世界范圍內享有廣大讀者,尤為青年人喜愛。自上世紀80年代,黑塞在我國已有很多譯介(《荒原狼》《彼得·卡門欽特》《喬達摩·悉達多》等),對于中國讀者并不陌生。此番中央編譯出版社將黑塞的《園圃之樂》作為生態文學系列“小綠書”中的一部,使我們得以在炎炎夏日感受到從“園圃”中飄來的陣陣清風,沁人心扉。
黑塞出生于德國南部的施瓦本地區,向東南與博登湖和瑞士連成一片。那片土地屬農耕文化,自然風景優美,是個天生出田園詩人的地方。德國浪漫派中就有一派,稱施瓦本派,專以描寫家鄉田園風光著稱。
然而,黑塞并非單純的徜徉于田園的文人,亦非打坐于“禪房”的隱者,他躬耕園圃,培土灌溉,鋤草施肥,修枝剪葉,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親力親為。《園圃之樂》即收錄了作者所有記錄園圃勞作、園圃情懷的詩文。
那么,與中國古代的文人相比,黑塞的園圃情懷有何不同?
一則,也是最大的不同,黑塞之勞作于園圃,形同在世俗中修行,而非仕途受阻,寄情山水。相反,如文中偶有流露,他一直是位成功的作家,出版社和讀者的來函從不間斷,如潮水般涌向他的鄉間別墅,以致他可以用出版社捆扎郵件的繩子給他的番茄架藤綁枝。西方自中世紀起,便只有修院中才有此類園圃,也稱花園或草藥園,躬耕于其中的是修士。在園圃中勞作是修行的一部分。修士唯有兩項工作:贊美和勞作。于黑塞大抵同樣如此。
黑塞講到,“同泥土和植物打交道,就類似沉思冥想,能使靈魂得到放松和安寧”。他沉思和冥想的,是生命的趣味,是生命的死而復生,是造物主所造自然的奇跡。為此,他“感恩諸神,贊美大地”。他舉目看到的,并非只是莫名的“悠悠南山”,更是雪山襯托下教堂的鐘樓;落日中的繁花在他的眼中,“宛如大教堂里的彩繪玻璃窗”。在如此置身于園圃而非教堂的“禮拜”和“祭祀”中,他獲得心靈的寧靜。
黑塞雖然年輕時逃離了神學院,但不容忽視的是,他是牧師的兒子,生長于虔誠運動(17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一個中心地帶——施瓦本,此地的虔誠運動特別強調內在心靈和內心的虔誠。黑塞的虔誠因此并非經院式的、形式主義的,而是由內而外的、彌漫在日常生活之中的,這給他的園圃之樂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對于黑塞,農事的生活,其基石是“虔誠”,“是對主宰土地、水、空氣和四季的神明的信賴,是對動植物生命力的信賴”。他明言,在園圃的勞動對自己“有著某種宗教意味”。甚至于,“所有的花園和小山/ 都是客西馬尼園和各各他山”。他在鳶尾花中看到的是“上帝和永恒”。
因此,黑塞筆下的大自然,他筆下的山水、植物、花開花落,都具有了神性的寓意。他的詩文出自文人雅興,更是靈修之作。也是在這樣的觀照下,黑塞文中往復出現的童年、故鄉、歸鄉,就如同在他的同鄉荷爾德林那里,都成為某種世俗的神學。
二則,黑塞的園圃之樂,當然是歸隱之樂、隱遁之樂。然而,他的出世并非泛泛地遠避世事的藩籬,而是有著十分具體和明確的針對——大都市忙碌的現代生活。就這一點,因中國的現代化滯后于德國百年,黑塞的園圃詩文恰似寫給今日中國的讀者,無比契合我們此時的心境。
黑塞心中與園圃相對的是什么?是美國。美國是工業、技術、消費文化、時尚文化的象征。對美國的鄙夷不可遏制地流露于字里行間。諸如:美國人的音樂修養“只在于擺弄留聲機”,美國人“認為擁有一輛漆得光亮的汽車是世上美事”,進而,“當代美國人”不過是“容易滿足的樂天派猿人”。如此這般現代的“猿人”,如何有閑情逸致去傾聽、去觀察和描摹自然?如何會把花草樹木當作自己的朋友,與它們同呼吸共命運?
或許只有通過黑塞式的在沉靜中的凝視,才可以捕捉到最細微卻蘊含著無限意趣的生命的脈搏:“一朵褪色的紅玫瑰從枝頭脫落,無聲地墜落到地上,減輕了負擔的花枝便微微往上彈了彈”。這花枝的彈動,與其說出自肉眼的觀察,不如說出自心靈之眼的感悟。試問現代都市中人,何以有此閑暇、何以有此情懷,去感悟一棵花枝的顫動,并由此反觀自己的生命呢?
面對現代化進程,黑塞筆下的“故鄉和花園”成為對已逝的人與自然共融、天人合一的永遠的追憶。望著窗外停車場一般的堵車,城軌站千萬計川流的年輕的碼農,筆者不知黑塞還會怎樣想、怎樣寫。“60后”的我還覺得《園圃之樂》的每一篇文字都會“悄悄在你我心靈里 /溶入久被遺忘的/甜蜜而無可估量的/ 故鄉之愛”,卻不知這樣的文字、這樣的符號,還能否喚起路上行人的記憶,或許他們根本就不曾有過這樣的記憶呢。
黑塞的《園圃之樂》是一本精致的小書。它圍繞園圃,收錄了作家的詩歌散文、敘事作品和書信節選。選文大致以春夏秋冬四季和成文順序為經緯。書中的彩色插圖皆系作家本人的畫作,淳樸而優美;另間有十數張作家的黑白照,記錄了作家在園圃勞作的身影,還有他人手繪的黑塞肖像或速寫,凡此皆與文字相映成趣,閱之不僅不覺乏味,還會常常遇到驚喜。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本書由我國德語界資深翻譯家韓耀成先生擔任翻譯,其譯筆之精湛,文字之考究,令人嘆為觀止。作為業內晚生,我時不常要掩卷琢磨,如何竟有如此神來之筆,是從怎樣的德語原文譯出了諸如“瞬間如飲醍醐”或品嘗半綠變藍的葡萄時的“甘甜生津”。及至讀到“莫問收獲有幾多!”則讓人已經忘卻是譯自西文,倒像是出自精于園圃的文人的創作……不禁慨嘆,此真乃作者的心靈之作,譯者的圓夢之譯。
最后,留下一個開放的問題,給德語文學或黑塞愛好者:《園圃之樂》的諸文作于一戰和二戰前后。作者于亂世之中,流連于博登湖和瑞士的山水之間,尋找內心的平靜,稱“真正至關重要的是內心世界”,并試圖“從內心重建這個破碎的世界”。這是否是以內心世界為借口,逃避對外部世界的責任?因為中立并不是非政治的,如施米特所言,也是一種政治立場和政治表白。
黑塞本人對外界對他的詬病心知肚明,他在六音步格律詩“園圃時刻”中寫道:“專家們稱之為‘內向’,是逃避自己生活的責任,沉湎于享受自己夢幻、一味玩樂的懦夫行徑。”一語概括了戰后德國知識界對所謂“內心流亡”的譴責。對此,黑塞接下來的辯護是:“我們恬淡無欲,在爾虞我詐的時代,謹以心靈的那份寧靜來與世道抗衡。”亦即,潔身自好,不同流合污,是否可謂一種沉默中的抵抗?
《園圃之樂》看似不問世事,但卻無法回避政治態度和政治立場,正如黑塞曾在多處坦然寫道,他在修枝剪葉之時,思索的不僅僅是抽象的神性和生命,也包括現實的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