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人的“巴黎綜合癥”:蘇聯人真的熱愛西方文化嗎?
巴黎可能是一個危險的旅游地。據說日本人特別容易罹患醫學上所謂的“巴黎綜合癥”,這種疾病會使那些期望值過高的人感到人格分裂、焦慮和暈眩。蘇聯人雖然不像日本人那么容易崩潰,但他們將巴黎視作文明、文化的朝圣地,在巴黎投資甚巨。盡管蘇聯對資本主義不屑一顧,但對西方文化遺產的深深尊重已融入了蘇聯體系。唯一的問題在于,蘇聯的邊界是封閉的,斯大林對西方文化的高度欣賞只能等同于對退化的藝術“形式主義” ——也就是現代主義——的排外式恐懼。但在后斯大林時期,在赫魯曉夫的解凍時期,“與西方和平共處”——正如埃利奧諾里·吉爾伯德所說——與人類文化的“普遍性”和“世界文明”的價值一同成為了新的正統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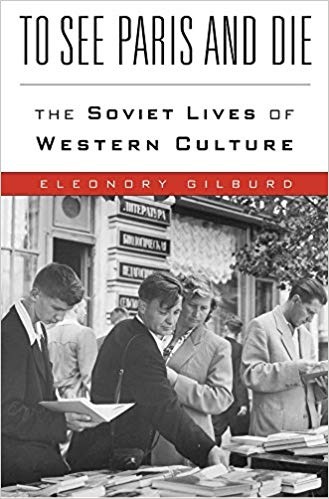
《有生之年看巴黎:西方文化影響下的蘇聯生活》書封,作者:埃利奧諾里·吉爾伯德
由英國文化委員會管理的文化交流活動是通過1959年的一項蘇英協議建立的——1966年還是一名研究生的我是英國文化委員會的受益者。這項文化交流活動補充了此前在全國學生聯合會主持下組織的小規模訪學,同時一項新的、謹慎的、鼓勵性的國際旅游政策將外國人帶到了蘇聯,也將有限的蘇聯游客在嚴密控制下帶到了西方。
《外國文學》雜志向蘇聯讀者介紹了歐洲和美國作家的翻譯作品,廣受歡迎(人們真正想讀的雜志是一種稀缺商品)。在書中,蘇聯讀者如饑似渴地閱讀了斯科特、雨果、狄更斯、大仲馬、巴爾扎克、吐溫和雷馬克的作品。在俄羅斯和蘇聯傳統的鼓勵下,蘇聯人按照文學作品來過自己的生活,并以虛構的主人公為榜樣,他們滿懷熱情地進入了這些文學世界,發現了海明威筆下主人公模糊的情感困境,就像他們與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經典作品中“積極的英雄”宣揚的直接斗爭一樣。當海明威在1961年夏天去世時,蘇聯媒體“哀悼一位民族英雄的去世,這是海明威在美國和古巴之外都沒有得到的待遇”。《麥田里的守望者》發行了幾個版本,發行量很大,但像往常一樣,需求遠遠超過了供給,這本書的黑市價格幾乎是官方價格的30倍。雷馬克的《三個同志》于1958年以俄語出版,正如一位蘇聯當代人所說,成為“一代人的小說”。它對男性友誼(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德國退役士兵之間的友誼)和命中注定的愛情的描述被“視為一種啟示……‘我們在雷馬克中讀到了我們自己,這部小說是關于我們的。'”
1957年8月的“莫斯科青年節”吸引了34000名外國人到莫斯科停留了兩周,對西方的向往終于轉化成了與西方人接觸的狂喜時刻,這是一代人生活的分水嶺。在此期間,對外國人的嚴格控制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消了:邊境無需行李檢查,無需填寫貨幣申報單,甚至不需要正常的簽證,任何被國際青年運動相關委員會選為代表的人只需從他們當地的蘇聯領事館領取一張保證入境的卡。蘇聯無權否決由國家委員會選出的代表,即使他們被告知“可疑人物”正在路上——包括“來自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和來自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黨人、來自西班牙的長槍黨黨員和來自英國的帝國忠誠者,以及來自世界各地虔誠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代表們可以自由漫步到莫斯科郊外的節日場所(比如莫斯科北郊的Khimki,1957年前禁止外國人進入,之后幾十年也禁止外國人進入)。藝術節的藝術策劃者們復興了自20世紀20年代輝煌時期以來的前衛冒險精神,他們靈感迸發,將卡車和公共汽車畫成了“橙色、藍色、黃色、淡紫色”,并添加了“帶有藍色波浪條紋的異國花卉、鳥類和蝴蝶”。對習慣了單調和灰暗顏色的人來說,這是徹底的文化沖擊。一名莫斯科人回憶道:“以前,我們在莫斯科只知道偽裝過的卡車,好像它們都做好了接受緊急動員、開到軍隊里去的準備。”
盡管有三萬名共青團員在街上排隊維持秩序,莫斯科人和西方人之間的第一次相遇依舊是狂熱的。當涂上“不可思議顏色”的卡車把代表們從城市北部的酒店帶到南部新建的盧日尼基體育場參加開幕式時,人們——甚至共青團員——爬上卡車,把花束推到公共汽車的窗戶上,把西方人拉出來擁抱,并被拉進即興的舞蹈和歌唱中。莫斯科街上的一幅標志性圖像顯示,兩個美國女孩手牽手跳舞,其中一個赤腳,而一個美國男孩在班卓琴上演奏著俄羅斯民歌“喀秋莎”。
后續影響是,為了彌補節日期間被冷落的窘境,克格勃加強了對當地人的監視,懷疑當地人與外國人建立的可疑的密切關系。1967年,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那時紫色的卡車早已從街上消失,這個節日也只是一個夢幻般的記憶,但是與西方文化聯系并成為世界文明一部分的沖動仍然存在——有時受到政府限制,但經常是受到鼓勵的。意大利和法國電影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蘇聯上映,使熱拉爾·菲利普、伊夫·蒙當和西蒙·西涅萊成為被崇拜的英雄。費里尼的《八部半》贏得了1963年莫斯科國際電影節的大獎,盡管有些人對這一選擇感到憤怒。據報道,赫魯曉夫在這部電影放映期間睡著了。
伊夫·蒙當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和基輔舉辦了非常成功的音樂會。他的歌曲“C'est si bon”和“Les grands boulevards”反復在電臺播出,是蘇聯版本的巴黎神話的核心。同樣有影響力的是親法派作家伊利亞·愛倫堡的回憶錄,該書于20世紀60年代在《新世界》連載,書中他深情地回憶了世紀之交在蒙帕納斯的日子:“愛倫堡的巴黎在12月有灰色的建筑和綠色的草地。這里住著街頭歌手、接吻的夫婦、在咖啡館消磨時光的可敬老人、戴著巨大羽毛裝飾帽子的女人、淘氣的學生和貧窮的藝術家。”愛倫堡是法國印象派的熱情倡導者,在斯大林晚期被認為不夠現實,但被他描繪成真實和真誠的(都是“解凍時期”的核心價值觀),“渴望看到新的自然,以不同的方式描繪它”。普希金博物館開始從倉庫中取出印象派繪畫,隨后蘇聯和法國的大型展覽接踵而至。印象派的巴黎、愛倫堡和伊夫·蒙當都融合在浪漫的蘇聯城市神話中。
20世紀50年代中期也帶來了比印象派更難理解的東西:畢加索,他的作品(他自己選擇的)于1956年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展出,并引發了激烈的爭議。用蘇聯的話說,畢加索很復雜,因為他既是共產主義者——著名和平鴿的制造者——又是“現代主義者”,其藝術風格對蘇聯畫廊的觀眾來說是陌生的。一些人認為他的作品代表了與斯大林主義歷史的典型決裂;其他人認為它丑陋而反常。這是一個有趣的論點,因為這一次爭論不再由國家主導,激烈的辯論發生在學生宿舍、編輯部,甚至城市廣場,觀看展覽的隊伍非常龐大。“喧嘩與騷動”的氛圍在當時的報道中很突出,因為人們聚集在博物館周圍,聽“古怪的年輕人熱情地捍衛現代主義,而同樣認真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衛士試圖貶低他們”。
吉爾伯德的散文最生動、最能喚起人們對喧嘩與騷動的描述,比如莫斯科青年節和畢加索展覽,而她關于文化接觸機制的章節則是“力量之旅”。以翻譯為例:蘇聯有自己的方法,將翻譯的功能轉換為“再生化身”(perevoploshchenie)的概念,有點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名的表演理論。原則是“外國作品的每一次翻譯都必須成為俄羅斯文學的一種現象”,不僅僅是對文本的再現,“更重要的是對原作的體驗”。這是一種富有想象力的再創造行為,涉及譯者的主觀輸入。編輯亞歷山大·塔多夫斯基在談到詩人薩繆爾·馬爾沙克對伯恩斯的翻譯時說,盡管保留了伯恩斯作為蘇格蘭人的聲音,馬爾沙克仍然“使他(伯恩斯)成為了俄羅斯人”。如果我在20世紀60年代沒有聽到蘇聯吟游詩人尤里·金演唱馬爾沙克版的A·米爾恩的克里斯托弗·羅賓的詩歌,我可能會認為那僅僅是一種華麗的辭藻,對我和莫斯科觀眾來說,這種詩歌竟然奇跡般地轉變成了一種明顯的俄羅斯風格。馬爾沙克的版本去除了原作的矯情,充滿了情感的深度,比米爾恩的要好,這也是蘇聯翻譯家的目標。麗塔·萊特-科瓦列娃翻譯《麥田里的守望者》時從未出過國,但她認為霍爾頓·考菲爾德是“一個激動、溫柔和純潔的靈魂”,將他翻譯成俄語以獨特地表達他“可愛、純潔的聲音”。吉爾伯德通常對自己的個人偏好保持沉默,但聽起來她似乎更喜歡俄羅斯版的童年,而不是原版的:她寫道,萊特·科瓦列娃的譯本“更豐富、更富表現力、更富感情色彩”,而俄羅斯霍爾頓·考爾菲德“比他的美國原型有更廣闊、更精確、更令人驚訝的詞匯:他也更敏感、更深情、更脆弱。”
吉爾伯德說,大多數在蘇聯上映的外國電影都被配音,不是出于審查的原因,而是出于“對形象完整性的美學關注”和從1920年代蘇聯先鋒派繼承下來的“框架總體性”。蘇聯配音演員無法與文學翻譯家的很高的文化地位相比,電影媒介本身限制了外國世界被重新想象成俄羅斯(蘇聯)世界的程度,盡管如此,他們還是盡了最大努力,討論了“音樂性和節奏詞匯”中的配音,并認為他們的工作面臨的挑戰類似于詩歌翻譯的挑戰。他們的任務是讓蘇聯觀眾在情感上和字面上都可以理解這部電影,有時還需要英雄主義的措施。在由杰拉·菲利普和吉娜·勞洛勃麗吉達主演的《郁金香芳芳》的蘇聯配音版中,配音員吉娜·喬特提供了一個完全脫離原著的畫外音敘述者——“一個新角色,一個蘇聯的發明,被創造出來解釋這部電影的表演”——這部蘇聯版的幽默很大程度上歸功于配音員。蘇聯配音導演的目標是讓他們的版本比原版更好,要“心理上更深刻,情感上更易共鳴”。
盡管去西方的蘇聯游客數量相對較少,但也在不斷增加,其中包括許多蘇聯作家。他們通過在文學和繪畫中的再現,將歐洲的大城市描述為一見如故卻不為人知的。巴黎是蘇聯人最了解的城市,從左拉的小說和愛倫堡的回憶錄到1960年在莫斯科舉辦的攝影展《活著的巴黎》,都是蘇聯人了如指掌的文化事件。吉爾伯德寫道,對于蘇聯藝術家、作家和讀者來說,巴黎首先是記憶,然后才是體驗。事實上,有時真實的經歷令人不安(巴黎綜合癥的陰影!),當這座城市的林蔭大道上擠滿了美國游客時,巴黎“喧鬧、無知、自鳴得意、重商主義”,古老建筑的外墻被“花哨的海報”弄得面目全非。
蘇聯與西方的愛情注定以失望告終。一旦俄羅斯人可以自由旅行甚至移民,如果他們負擔得起,還可以永遠住在巴黎,逐漸地,巴黎就不再是蘇聯的文化夢想了。有時候,對于20世紀90年代迷失方向的移民來說,這更像是一場噩夢。新移民把他們喜愛的左拉和巴爾扎克的多卷本譯本拖出俄羅斯后,突然發現它們與現實毫無關聯,甚至令人尷尬。原來,“他們的”巴黎——他們的普世文化——已經變得面目全非。蘇聯對西方的文化想象變成了“與其他蘇聯劣質事物相似的舊垃圾……人們知道他們的文化偏好已經過時,他們的生活方式依然幼稚……他們一心一意地培養文化資本,但發現自己兩手空空。”他們覺得自己是西方文化遺產的“擁有者”,但事實證明,這種擁有只存在于他們的虛幻夢境里。
吉爾伯德認為,“蘇聯和西方的烏托邦一起解體了”——這是她描述的矛盾情況之一。對西方文化的熱愛并不包括對自身主權的否定。相反,熱愛西方文化是蘇聯文化的象征,這是每個受過教育和培養的蘇聯公民都應該具備的素質。任何被問到沃爾特·司科特或西奧多·德萊塞的小說的來訪外國人都會證明,蘇聯公民通常認為他們比西方本地人更了解西方文化(或至少是典型的蘇聯版本),并且更喜歡西方文化——他們是對的。此外,他們覺得這種文化欣賞能力本身就是他們國內文化的產物(他們有時會把這種文化稱為“蘇聯文化”,有時稱為“俄羅斯文化”),他們也是對的。有些俄羅斯人喜歡資本主義,但吉爾伯德描寫的不是受教育的俄羅斯人或蘇聯知識界,她所描述的“所有權”類型,包括對文化商品的非物質的和共享的集體擁有,看上去是資本主義的;但事實上無疑是“社會主義的”——盡管已故的蘇維埃實踐者通常傾向于避免使用這個詞(因為害怕聽起來老套)——它完全符合蘇聯社會主義傳統,這一傳統可以追溯到俄羅斯第一任啟蒙運動人民委員阿納托利·盧那察爾斯基。
《有生之年看巴黎》是一部高度個人化的書,作者是一位年輕的美國學者,她本人就是蘇聯晚期俄羅斯猶太移民的孩子。(20世紀90年代,吉爾伯德和我一起在芝加哥大學學習,她現在在那里教蘇聯歷史。)她的書和電影《再見列寧》中蘇聯/共產主義的懷舊風格一樣。但這個主題不是蘇聯本身,而是對西方的愿景,這一西方文化的光環吸引了后來的幾代蘇聯人。潛在的懷舊情緒是因為蘇聯社會極其看重文化(包括但不僅僅是西方文化),并培養了強烈的集體情感。
讀了這本書,我不禁為蘇聯的宣傳者感到遺憾,他們為讓公民愛上蘇聯社會主義而辛勤工作了這么久。要是他們讀了一點資本主義營銷理論,并掌握了物以稀為貴的思想就好了。蘇聯宣傳者與他們實現使命的機會失之交臂,只有在蘇聯解體、宣傳部門被西式廣告和公關人員取代之后,才出現了對蘇聯社會的懷舊情緒。
本文原載于《倫敦書評》,作者希拉·菲茨帕特里克正在完成一本關于二戰后俄羅斯移民的書,并開始撰寫列寧的妻子娜德日達·克魯斯卡婭的傳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