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楊好:對我而言,文學是一種召喚

楊 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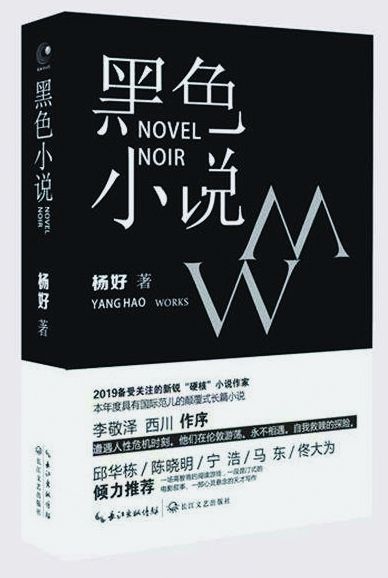
“黑色”承載著我的思考與表達
李英俊:《黑色小說》是你的首部長篇小說,構思了多久?動筆前寫過一些中短篇小說嗎?
楊好:沒有進行過中短篇小說的訓練,整部小說的構思基本是在腦海中進行的,但整部小說是一氣呵成寫完的。寫之前想過小說的結構,因為對我來說小說的結構很重要。而正兒八經的構思可能更多還是發生在電影學院,那時候要完成劇本寫作。我畢業寫的劇本是一個黑色電影,畢業論文也與黑色電影有關,所以《黑色小說》的構思其實一直存在。一個寫作者所能掌控的文學題材的類型其實是有限的,我可能從一開始就選定了這個方向,它或許可以承載我更多的思考和表達。構思《黑色小說》時,我一直就在想要寫一部當代的作品,寫一部我能掌控的作品,一部往內走的作品,雖然真實和虛假的界限往往很模糊。
李英俊:小說的兩個主人公的命名,一個叫M,一個叫W,很容易讓人想到M意味著man,W意味著woman。為什么不取一個中文名字或者外文名字?以字母代替是不是一種折中的方式?有什么獨特的含義嗎?
楊好:我其實沒有考慮到這一層,小說出版后,別人看完才提醒我:M是man,W是woman。我當時的想法其實是這樣的:既不設定它是中文名字,也不設定它是外文名字,而僅僅把它當作符號。整部小說本質上其實是一部寓言,既然是寓言,我就想用兩個符號作為主人公的名字,在英文里挑了兩個互為鏡像的符號,M與W就是一對互為鏡像的符號。特別巧妙的是,我安排的M應該是男孩,因為他更有主動性,而W在整部小說中其實是M的一個投射或者想象,M與W其實是互為補充的,所以就以這樣一種結構將兩個人物用符號并列到一起。
李英俊:小說中有一些詞組很有代表性,或者并列,或者互補,比如:真實與虛構,現實與想象,抵抗與緘默,傾聽與旁觀,親密與脫離,世俗與身份,陌生與熟悉,等等。不管是從小說人物塑造的角度,還是從你作為一個敘述者“切入”小說這個角度,都在與這個世界對抗。小說人物M最終“出走”,W最終“走進了冰冷的海水里”,兩個主人公與世界對抗或者“較勁兒”的這種方式與結局,是由于內心的絕望,還是解脫進而完成了某種救贖?
楊好:這兩個人物最終沒有解脫,因為他們是兩個有問題的人。我的主人公其實不是英雄,他們既戰勝不了世界,也戰勝不了自己,他們最終還是在掙扎,因為他們掙扎,所以他們才選擇了這種方式。當然,也不能說他們在逃避。“較勁兒”這個詞特別對,M與W所有的問題其實都來源于與這個世界的“較勁兒”,而且,他們不僅跟世界“較勁兒”,也一直在跟自己“較勁兒”,從這個角度看,也可以把W看成是M的一個映射,因為有很多“較勁兒”在M身上不能完全寫,那就放在W身上來完成,想象M如果成為一個女性,他跟這個世界的“較勁兒”肯定不一樣。我覺得現在好多年輕人也在跟世界“較勁兒”,這些“較勁兒”有好有壞,所有的這些都是中性的。而M與W這兩個人物,其實也是中性的,我既不喜歡也不討厭,他們就是我塑造的人物,沒有性別,沒有國籍,沒有文化差異,沒有“社會”“歷史”附加在他們身上的東西,他們只是兩個純粹的人,只不過有了問題,從而在尋求答案和救贖。
文學就是要寫真實的狀態
李英俊:M是一個特別敏感、孤獨,甚至有些封閉的男孩,這似乎和家庭環境有關,更準確地講,和M與父母的關系有關,小說中這樣描述,“M從來沒有和父親表態說自己將來要做一個醫生”“M和母親更是淡于交流”“M的父母也不信任任何藝術,或者文學”,但是,M的理想是成為一個真正的作家,M與父母的關系似乎陷入一種“斷裂”或“隔絕”的狀態。就人物關系而言,選取這樣一種角度切入,和家庭環境有關嗎?
楊好:其實M與我恰恰相反,因為我從小到大和我父親一直在交流文學。恰恰是我與父親能交流文學的這種特殊性,讓我從小到大都覺得,原來我在我的家庭環境中并不是孤獨的,我也并不像M。其實寫作這部長篇我做了很多準備,我從十幾歲就習慣性地觀察別人的生活,觀察別人怎么做,觀察別人與社會的關系,我發現身邊但凡是愛好文藝的朋友或者同學,他們與父親之間的關系并不像我與父親之間的關系,這種現象尤其在電影學院更為明顯。以普遍問題的角度去看,寫作的孩子或者想要在文藝方面做出一些事情的孩子,其實他們與家庭之間的關系是非常“隔絕”的,他們沒有辦法跟父母說“我想成為作家,我想成為藝術家”。就親情關系淡漠這一點,我覺得發生在每一個人身上,包括也發生在我身上;不僅發生在中國人身上,也發生在外國人身上。而且,更年輕一代人與他們的父輩的關系跟我與父輩的關系也漸漸不同了,我與父輩還是那種“大家庭”的關系,在更年輕一代人的身上,這種“大家庭”關系會越來越淡。原來存在的“大家庭”關系如果仍然出現在當下的文學作品里,是有些奇怪的,因為這不是一種真實的狀態,而是一種理想的狀態。在我看來,文學不能寫理想的狀態,文學就是要寫真實的狀態,所以,人物關系哪怕看起來好像不近人情、冷漠自私,可我還是想把這種真實的現象寫出來。
李英俊:在上半部分結束時,當M離開貝德福德街的住所,“坐地鐵來到萊斯特廣場唐人街里唯一的一家中藥店”。整部小說充滿了西方元素,在這里突然出現了“中藥店”。在這個細節處理上,為什么會想到“中藥店”?M與“中藥店”是怎么相遇的?
楊好:這個細節是發生在M父親的朋友C叔叔出事以后。其實,從小說整體架構來看,M與W一直處于一種飄浮狀態,雖然說真正的鬼魂是那個17世紀的漢密爾頓,其實M自己也像一個鬼魂,他飄浮在旅游的城市,飄浮在所有的街道上,與周圍的任何事物都不發生太深的關聯,即使M與那個女孩發生過一段愛情,而W與她上司有一些聯系,但都不深入。M與W其實都沒想過要去了解任何一個人,是因為他們的心里一直有一個想法,覺得自己終究是倫敦的過客,而他們在萬里之外的北京或者自己的家鄉又找不到歸屬感。這時候M在倫敦尋找出現的中文字眼兒可能是他唯一能夠抓住的一根稻草,我就想到了“中藥店”。因為這是一個虛假的假象,在一個全英文的社會里突然找到中國傳統的“中藥店”,其實就是一種非常虛假的親情關系。
文學的“實驗性”與作家的責任感
李英俊:《黑色小說》里充滿了大量的哲理化議論式句子,小說里也提到了很多西方作家,卡夫卡、狄更斯、加繆、莎士比亞、弗吉尼亞·伍爾夫、魯德亞德·吉卜林、品欽等等。西方文學藝術對你有什么樣的影響?
楊好:我覺得是一個習慣,和家庭環境有關系。我從小到大看了父親的很多書,西方文學塑造了我的思維方式。我看的也比較早,原來是看一些經典作家作品,比如雨果、巴爾扎克、契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后來隨著自己閱讀的積累,我發現自己更喜歡的是加繆、卡夫卡、品欽等,他們的文學觀讓我覺得文學就不應該是簡單的故事,文學就應該做得更加“實驗”一些。所以寫《黑色小說》時,對我來說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文學是什么。電影的學習也為我帶來很大震動,我發現,在電影或者網劇里,包括一些游戲,故事的整體設計、敘述、細節處理都非常好。故事很好看,而且很完整,這種完整程度包括人物之間的緊張程度,有可能比一部文學作品呈現得還要好。文學不能再重復“說書”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能干些什么?文學的實驗性還是電影、網劇這些無法取代的,而文學無法被任何東西剝奪的一點恰恰就是作者在里面的觀點。
李英俊:作為讀者,其實一直期待M能寫出一部偉大的作品,正如你在小說開頭預設的那樣——他曾非常固執地想過,認為那本小說將會如一顆行星撞擊另一顆行星、撞擊人類文明,而他,將是這一奇跡的創造者,他的名字將不朽。到小說上半部分結束時,M還是沒有寫下一個字。
楊好:其實恰恰是因為M說了這樣的話,他才寫不出一個字。我覺得,M對于文學的態度其實代表了一個寫作者的絕望,有時候寫作者想創造出一部不朽的作品,但這種不朽往往會成為他自己寫作的障礙。其實,我在這里隱喻了一個元文學的概念。M與W是一組被抽離的人物,他們的“黑色”也好,“謀殺”也好,全都發生在形而上的范圍或層面。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M,同樣也包括W,不需要有文字,他們只是符號。
李英俊:小說中有一句話“不行動,文學就癱瘓”,你在后記中又提到了這句話。這句話有什么特殊含義嗎?如何理解“行動”?
楊好:“不行動,文學就癱瘓”其實有一種間離的語境,因為小說中出現的“不行動,文學就癱瘓”與后記中的“不行動,文學就癱瘓”的意義是不一樣的。我故意塑造的M其實是一個偏文藝化的青年,他是一個把文學看得過于崇高的人。我在《細讀文藝復興》中寫下一句話“文藝復興既不神圣,也不世俗”,我想把這句話同樣用在文學上,其實文學也是這樣,既不神圣,也不世俗。我們有時候把文學看得過于神圣或者世俗,其實文學一直就“在場”,它就在那兒。在后記中,“不行動,文學就癱瘓”是說給我自己的,對我自己是一個提醒,因為動筆前我會想很多,而思考有時候會成為行動的絆腳石。我在青春期的時候就產生過寫作的沖動,但一直被壓制著。我漸漸發現,我越來越不想動筆是因為我越來越怕我動筆寫下后不是一部完美的小說。這個念頭其實一直阻礙著我,直到我發現這個世界沒有什么完美不完美,最重要的還是行動,而文學就是行動。(文/李英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