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與昆曲糾纏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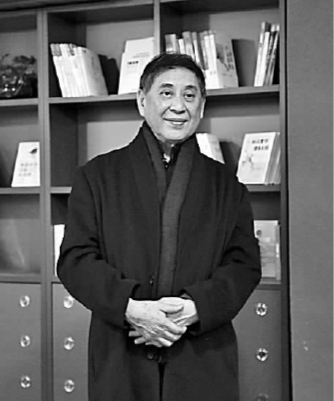
白先勇近照 趙鳳蘭攝/光明圖片
為了在舞臺上呈現昆曲《牡丹亭》精致典雅的古典美,他募集了3000多萬元人民幣,服裝舞美等都用最好的,十幾年為之不惜工本。對于做“昆曲義工”,他甘之如飴,常常為一些賠本的“買賣”樂此不疲。
4月19日,在北京曹雪芹學會和北京大學曹雪芹美學藝術中心舉辦的“曹雪芹在西山——《紅樓夢》程本、脂本及藝術研究”學術論壇上,從臺灣風塵仆仆趕來的白先勇與一眾紅學家圍坐桌前,共同研討學界糾纏已久的《紅樓夢》底本問題。
別人發言時,白先勇總是認真地聆聽并注視著對方;聽到精彩處,常常會滿面春風得像孩子一樣拍手鼓掌。他不厭其煩地為每一個前來找他的讀者簽名并合影留念,嘴里還連聲說著“謝謝謝謝”!從小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他,言行舉止都烙上了儒家“溫良恭儉讓”的印記。
白先勇生于亂世,少年時目睹家族由盛而衰,他的性格敏感多思、內斂悲憫。為了將自己的人生際遇和內心掙扎訴諸筆端,他選擇了與戎馬一生的父親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期望通過文字感受生命的枯榮無常和歲月的滄桑多變,為自己的心靈和情感找到自我檢視和超越的精神出口。
《紅樓夢》恰恰應和了白先勇浮沉的身世命運和他對文學之美的所有想象。“一入紅樓深似海”,他曾在大學教授十幾年的《紅樓夢》,成為一名孜孜不倦的紅樓文化的布道者。
除了《紅樓夢》,與白先勇糾纏一生的怕是昆曲《牡丹亭》了。
小時候在上海,白先勇偶然看到梅蘭芳與俞振飛演出的《牡丹亭》。“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了斷井殘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愿”。這幾句優美的唱詞和著笙簫笛音,瞬間沁入他的靈魂深處,再也無法拔除。
1987年,白先勇重返上海,恰逢上海昆劇院演出全臺本《長生殿》。看到瀕臨衰亡的昆曲重登舞臺,白先勇激動地跳了起來。他開始動心起念,要為昆曲振衰起敝盡文人之力,決不能讓它像元雜劇一樣落入消亡的宿命。
2004年,白先勇攜手蘇州昆劇院,以一部青春版《牡丹亭》為昆曲“還魂”。當時的昆劇已呈頹勢,不僅劇目陳舊老化,演員也是青黃不接。白先勇懷揣興滅繼絕的使命感逆流而上,將古老昆曲帶入了21世紀的時代風口。
談到當初為何選定《牡丹亭》,白先勇說:“《牡丹亭》是一則歌頌青春、歌頌愛情、歌頌生命的美麗神話,我想將這一文化瑰寶打撈并重新孵化出來,使之與21世紀觀眾的審美意識對接,用最美的藝術表現中國人最深刻的情感。”
白先勇本著固本開新、不傷筋骨的原則,嚴格遵守昆曲表演的程式和法則,只在舞美、燈光、服裝、音樂等方面進行現代化創新,最終將原劇55折的昆曲《牡丹亭》濃縮為27折,形成他心目中既有古典美又有現代感的“昆曲新美學”。
然而,昆曲緩慢沉靜的節奏與互聯網時代年輕觀眾的快節奏生活形成極大反差,光男女主角“眉來眼去”就要20分鐘,這種極端含蓄浪漫的愛情對年輕人還有吸引力嗎?白先勇為此承擔了極大的風險和壓力。不過他深信,網絡時代的年輕觀眾也是人,凡是人,心中總潛睡著一則“愛情神話”,只是等待被喚醒而已。
事實證明,青春版《牡丹亭》獲得了極大成功。當杜麗娘、柳夢梅以年輕姣好的面容在國內外舞臺上綻放光彩時,觀眾無不被其“抽象、寫意、抒情、詩化”的昆曲美學所震撼,青春版《牡丹亭》一時間被年輕觀眾競相追逐,在社會上形成了一波文化熱點。之后,白先勇又趁熱打鐵,陸續推出了《玉簪記》《白羅衫》,并與北京16所大學聯袂推出校園版《牡丹亭》。
在白先勇眼中,昆曲演出,與秦俑、商周青銅器、宋朝汝窯瓷的展覽一樣,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為了在舞臺上呈現那種精致典雅的古典美,我募集了3000多萬元人民幣,服裝舞美等都用最好的,十幾年為之不惜工本。”對于做“昆曲義工”,白先勇甘之如飴,常常為一些賠本的“買賣”樂此不疲。
為了守護心中那份對古典藝術最純真的“情”,十幾年來,本不熱衷旅游、尤畏車馬勞頓的白先勇成了“空中飛人”。他自嘲自己像個草臺班班主,帶著戲班四處闖江湖,為昆曲重獲新生不遺余力。
昆曲為白先勇帶來的關注度,讓他原本擅長的文學創作淪為了“背景”。事實上,白先勇在小說寫作上一直有較強的天賦,他不到30歲便寫出了《臺北人》這種老道的文字,該作品在亞洲周刊評選的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中高居第七位。后來,他陸續創作出小說《寂寞的十七歲》《紐約客》《孽子》,散文集《驀然回首》《樹猶如此》等。近些年,他又推出了《細說紅樓夢》等作品。
被問及十幾年來將大把時間投入到昆曲上,是否浪費了在寫作上的時間和才華?白先勇操著臺味普通話說:“其實小說寫好了影響力也蠻大的,之所以轉向昆曲,是因為昆曲沒落了我著急,它需要搶救,這是很要緊的。”
這些年,白先勇一直為他心中“文藝復興”的理想而奔波忙碌。除了致力于紅樓的細讀和昆曲的新生外,他還將改良過的唐裝穿在身上,在生活的點滴之間追求古風雅韻。在弘揚傳統文化的同時,他自己也成了傳統文化的一部分。
(作者:趙鳳蘭,系中國文化報高級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