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飛:為古老喚出生色


與張中行先生。

中日版昆曲《牡丹亭》劇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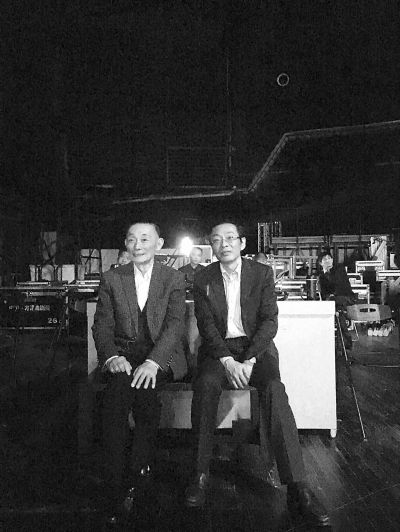
2016年與梅葆玖先生在保利劇院后臺。
每一個時代,都喜歡追新逐異,這個時代尤甚。新街、新樓、新科技,無不在刷新著人的眼目視聽。如果還想在這諸多的新當中穩(wěn)住些心神,大抵還需要另一種力量相抵。每當這時,心頭便浮出一些人來,對自己說,別慌,著什么急,看看,不是還有比你還舊的人,不也照舊活得有聲有色有底氣嗎?往來于東京與北京之間的靳飛,便成了這樣的參照對象。
沉郁與飛揚,很少能在一個人身上融合得天衣無縫,但在靳飛身上并不違和。沉郁的部分,和他內在的作為作家、學者的文章著述很搭;而飛揚而生動的部分,又和他的戲劇制作人、北京戲曲評論學會會長之類的外在身份吻合……但歸根究底在我眼里,他就是新嶄嶄的當下,活脫脫一個染舊的人。那種探不到底的舊,有時會化為無數條通幽曲徑,讓你不自覺想朝著其中一條探進。而他自己,則在不同路徑間輾轉騰挪,交錯織綴。于是乎,那些或早被化為舊的事物,就被他重新喚出本該有的生色。雖不足以蓋過時代舞臺中央那些炫與新,但被他這樣積年累月、緊鑼慢鼓地鼓搗著,慢慢也透出層層新意與美感。
一如他一生都致力于研究探索的中日戲曲的魅力。
說到舊,其實還要再做一層界定。有些人的舊,或許只是一種生命點綴,有些則是出于對現實的逃避而使生命失去活力的蒼白之舊。而在靳飛,它不僅鋪陳出一種穩(wěn)定而厚實的生命底色,而且時時促發(fā)他內在的使命與動力。探究這種使命與動力的成因,自然有很多前塵印記需要補述,連同許多故人、許多往事。但同樣不必急。在某些契機下,靳飛會自己翻騰出來,形于言表,著于文中。都說記憶不可靠,但見他所說所寫,可都歷歷如繪。所以,你認識了靳飛,就好像無形間知道了好多事,認識了好多人。他們大多已逝去。但因靳飛,就還能多少觸摸到他們的聲息。
1.歸去來,北京東京兩探看
靳飛出生于北京,如今與一家妻小定居于東京。
在現在的北京,他有一個住所,但已不是昔日那個家。去國之前的老宅,留在他早年一本隨筆集《北京記憶》里。讀它,基本能在安定門一帶劃一個不出幾里的方圓。靳飛的筆觸,固執(zhí)地鎖在少年、青年時代生活、游走的軌跡里,敘述的中心構圖,是有很多人雜居的四合院。從一個微觀天地識人閱世,靳飛的觀察顯示了他的某種早慧早熟——他能把一個院子的蕓蕓眾生,以及明里暗里的關系都看出個百八十的明白,敘述分寸得當,絲毫不給人揭別人隱私之雞零狗碎。難得的又是,筆調中那種從容閑雅與淡淡感懷,已經頗帶出些閱盡千帆的老文人之味。而這本書出版時,他不過三十出頭。所謂“于方寸之間天寬地闊,分間布白,錯綜其事,其味雋永。”書中這種對治印大家的評述,也可以同樣用到他在這本書的文字運用上。這乍看有些過于老成,但如果深入到他書中所涉及的人情交往——以上歲數的文化老人居多——又便顯得自然而然。書中文字,還顯露出他對曾經與生命有過交集的人與物的心心念念。老祖母、舊鄰居、老恩師(張中行翁),連同一本小人書、一套舊郵票、一枚印章……都透著時間之味。所有這些,又引著他向生命的前后與周邊探尋,并走向歷史的縱深。只是,不舍的舊物在散去,交往的前輩已有人離去。只有生活之流滾滾向前。他,也注定將從生他養(yǎng)他的北京,遷移到異鄉(xiāng)異地中去。
日本,東京,因為一場跨國婚姻,成為他第二個生命安放地。一邊尚有生身父母、故友親朋,那一邊則是妻女,以及另一個大家庭。兩頭拉扯,幾處奔波,怕就是他那句“年來幾經滄海”的慨嘆之緣由。
他并沒有失去與故國之間的情感紐帶。妻子波多野女士與他就是以中國戲曲結緣的,出國前還一起即興出演過《霸王別姬》。戲中,妻子扮虞姬,他卻不是且不喜歡演霸王,只做了旁邊護駕的一位。等于拿臺上的護姬角色,做了生活中的表白。波多野女士的祖父,是與梅蘭芳交情深厚的漢學家。不消說,這個東京的大家庭本身,就有著很深的中國印記。
而靳飛又是怎樣轉換自己,融進這異國異地的氛圍當中的呢?時隔多年后的2017年春天,當他站在北京的日本大使館頒獎臺上,領取日本政府因為對中日交流的貢獻而頒給他的表彰狀時,他承認,這么多年他對日本文化的觀察與學習,用的更多是東方意味的禪宗的方式,放下文字,去聽去看,靜觀默察,直接領受。
而能讓他直接領受的日本的世界,他認為是日本傳統藝術:能樂與歌舞伎。
只是沒想到,在日本第一次看傳統歌舞伎,看的就是國寶級的歌舞伎藝術家坂東玉三郎的戲。他被坂東玉三郎的表演所折服。演出結束后便到后臺找他,想表達自己的敬意。而坂東玉三郎上來跟他談的卻是京劇,“他很嚴肅地問我,中國的京劇為什么不注重男旦了。他說和許多中國朋友都聊到這個問題,但他們雖然也回應著,卻始終沒有人真正出來解決。你們不誠信。”這第一次相見,基本上是一個懟與被懟的場面,想來都夠別扭的。但是靳飛卻從這別扭中一下子窺到了坂東玉三郎對藝術的真心。他回國立馬到深圳找了胡文閣。坂東玉三郎也踐約承擔了一個中國演員到日本學戲的費用。
以和坂東玉三郎的相識相知來推想,靳飛和那些從事日本古典藝術的老藝術家的交往,也同樣應該是充滿了戲外戲的。靳飛后來也帶他們到中國與京劇的老藝術家做過交流。作為親證,我有幸看過坂東玉三郎在中國舞臺上出演杜麗娘的中日版昆曲《牡丹亭》,以及去年日本歌舞伎的來華演出。這些后面,都有他的參與,只是有些顯,有些隱罷了。
我至今仍期待靳飛能以日本的這類藝術家為主體,寫一本《東京記憶》。但由一出中日版《牡丹亭》的實踐開始,他其實已經把另一座城市的氣息,帶到了中國。在那些演出里面,不僅有不同于京劇的另一門古老藝術的精湛,也有東京還叫江戶時的風致。
2.舊風舊雨,同行者誰
這樣的靳飛,對我來說,到底還是既遠又近的。和他那些時常掛在嘴邊、曾經交往過的老人一樣。但有時候又不得不承認,只有保有這樣一種距離感,才能夠有余裕說他——就當說一個記憶中的人。記憶有它的篩選機制,也就無所謂完整不完整。再直說,那個近距離地與你同處于北京,冷不丁打個微信語音電話過來的靳飛,倒是著實讓人有些發(fā)怵呢。因為他叨咕的事情太多,聽著真是千客萬來的一樁樁。縱然無外乎是戲、人,以及知人論世——他一直強調這應視為一件事——但要把它們融會貫通,又需要和他有同樣的眼界與經見。而我們一路走來的人生,有多少人像他那樣,打青枝嫩苗時起,就和老樹勁藤在一起攀纏,然后浸泡出那樣三生三世的老靈魂。但聽著聽著,無疑又讓你忍不住望向他的來路。
很多人知道靳飛,當然是因為張中行翁。他也曾在行翁身后,有一本書結集,叫《張中行往事》。若干年后我讀它,是將它與行翁的《負暄三話》一起互讀。有意思的發(fā)現是,行翁白描了很多同時代人,卻沒有寫到靳飛。這從另一方面理解,離得近的人,或不會想到,或不急于著墨。在這本書的代序中,我還是窺到了這樣的畫面,“先生由那位寫文章有‘凌霄漢閣王’味道的靳姓青年陪著,沒打著車,一老一少悠然地坐上三輪,搖搖擺擺地走了。”
高妙的白描如同高妙的演員在舞臺表演,只給你展示背影,就把該說的都道盡。只這搖搖擺擺的三輪車上的悠然,不說放到它出現的那個時代,就是再向前推,也依舊是某種中國文人才有的風范。這當然像極了《負暄三話》中行翁說事的味道。行翁閑話之所以到今天還耐看,皆因為它融進了行翁一生的學問、智識與閱人的洞見。一個年輕人,從這樣的文字開始熱愛,進而與著述者不離左右,從而開啟一種知人論世意義上的通天地、閱古今的活的學問的深研,這起點怎能不令人羨慕?何況,這樣的老人,還不止行翁一位。
靳飛后來又有隨筆集《舊風舊雨》,出版時已距前書相隔十多年。我們得以見到更多與靳飛生命有過交集的人,但他們入到靳飛筆下,基本都屬于懷人篇。“世上空驚故人少,集中唯覺祭文多。”行到中年的這種孤寂與痛,靳飛比同輩人更早地領略到,而我之所以格外深切地感受到,還因為有相當一部分,發(fā)在我編輯的《北京晚報》的版面上。因為對接這些文章,我們的往來交流自然更多一分,這些人便儼然也走入我的生命當中。這長長的名單中包括:周汝昌、范用、吳祖光、綠原、嚴文井、劉曾復、林連昆、韓善續(xù),乃至梅葆玖、梅葆玥……
我相信在藝術與人生的路上,他們分別給予靳飛不同的生命滋養(yǎng)。這種活生生的言傳身教,已經不是單從文字中就能獲得。這種“活”的豐神,并不止出現在靳飛的筆下,零敲碎打,也通過熱到發(fā)燙的手機,傳送到我的耳朵當中。那種說不出而在心里反復回想的精彩,一定經常發(fā)生在靳飛與老人的人情往來當中,這筆無比受用的人生財富,也可能是靳飛想要努力解析,并傳承下來的中國文化中的一部分。
靳飛最近的戲劇講座,談的是昆劇名家韓世昌。他給講座命名為“韓世昌:中國昆劇中的‘趙氏孤兒’”。我一方面覺得此人陌生,又恍然覺得在哪兒見過此人名字。待翻到行翁三話,韓世昌的名字,早已入到老人筆下。短短的一篇人物素描,在今天的靳飛這里,已經在做一篇昆曲的大文章。
而將韓世昌比喻為趙氏孤兒的標題一出來,我腦子里想的倒是:靳飛自己又何嘗不是某一個意義上的程嬰呢?那么多老文人、老藝術家身上所積聚的東西,不都通過昔日的交往,演示說道給他了嗎?
3.民國京劇,一個重新理解的過程
信而有托,回報以義。靳飛對京劇所投入的熱情,以及從各個方面開啟的探源細究,都有這樣的意味在。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后來有人在其后又加添了“明清小說”,靳飛以為,還可以再添上“民國京劇”。
靳飛把開啟的民國京劇研究,放在了這樣的高度。而從這個高點看過去,民國京劇已不是一面宏偉而內容駁雜的歷史墻,而幾乎是一座立體建筑。這建筑之每一構件、每處的拼接,乃至房前屋后,都有重新探尋、打量、探究的必要。他為此著文,與之相關的群體,已經從藝術界人士,擴展到金融界、政界人士。經此耐心地細細碎碎拼合,這項研究已經接近民國史的性質:它是一部以京劇為主體,折射到方方面面的民國史,最重要的是,京劇是與時代并行的新文化的一部分。
梅蘭芳是靳飛目前研究最深、著墨最多的京劇人物之一。梅蘭芳后面的“梅黨”“綴玉軒”等歷史人物群像,被他推到前臺。人們由此知道,昔日梅派戲劇改革之所以能獲得成功,不僅和這些隱在其后的人有關,還得益于許多藝術之外的運行機制。
做這種學術的大文章,一般的學者面對的更多的是一些戲曲人物的歷史文獻資料。而在靳飛的案頭,多了一些昔日銀行的賬本。多是從販舊書處淘來。靳飛認為:“文字的歷史是容易更改的,不能更改或者還想不起來更改的,是銀行賬本。”而能從一行行枯燥的數字中看到某些歷史的隱約線索,得益于他早年在稅務學校學習的經歷。
靳飛在個案的研究基礎上,已經有《梅氏醉酒寶笈》問世。之后又為《舞臺生活四十年——梅蘭芳回憶錄》,做了十多萬字的導讀。看那洋洋灑灑、幾近一氣呵成的導讀文字,驚訝的其實是,這么一個戲曲人物舞臺生涯的回憶錄,竟然能帶起中國報業(yè)轉折期,一段波云詭譎的新聞史。其中有不少老文化人身影,他們之后的人生起落,也同樣被編綴其中。還端的是寫得像偵探推理探案一樣懸疑好看。怪不得靳飛總說,人要多多看戲。看戲的功力,若用到人生的琢磨上,也是老辣得緊。
而讀《梅氏醉酒寶笈》,我仿又回到幾年前在他的北京家中,看他給弟子董飛說戲的場景。一字一句一個身段地摳,活脫脫一種現場教學。外人所不知道的戲在人身上的意味,在靳飛的這本書中,幾乎也是如此這般,一個唱詞一個身段地在分析再現,以筆追豐神,藝術的法度已可窺見一斑。
“不知大藝術家之大,則不知己身之小也。”我愿意把他最近所說的這句話,作為他為民國京劇所做一切的腳注,并以此理解他生命中飛揚的那部分。
作為戲曲的外行,我竟也被他一次一次拉進和戲曲有關的微信群當中。看著越來越多的陌生名字,在為一個戲曲話題,或者懷舊,或爭論。而他時不時也參與其間。真不知他有多少精力,在百忙之中,還能如此抽身于聚談當中。不僅是參與,而且還不斷為其中添加柴火。數不清的回合之后,再看那些言語的你來我去,猶如看到一盆永不會熄滅的炭火。
這或許正是靳飛所愿。這個時代當中,很多東西即使說得再珍貴,也還需要守護延續(xù)。戲曲在當今,就是這樣一種邊緣上的存在。靳飛讓愿意為它付出心力的人彼此看見,這本身也是一種相互激勵與取暖。
芥川龍之介曾有一部短篇叫《戲作三昧》,摘抄小說中一個片段在這里:
這時,映現在他那帝王般的眼里的,既不是利害得失,也不是愛憎之情。他的情緒再也不會為褒貶所左右了,這里只有不可思議的喜悅。要么就是令人陶醉的悲壯的激情。不懂得這種激情的人,又怎么能體會戲作三昧的心境呢?又怎么能理解戲作家的莊嚴的靈魂呢?
這是芥川龍之介為小說主人公,那個戲作家所做的最后畫像。我想靳飛也是能深諳其中滋味的。
人物小傳
靳飛,上世紀60年代末生于北京,曾任中學教師、報刊編輯。
少年時開始寫作與戲劇研究,師從張中行、吳祖光、嚴文井、許覺民、胡絜青、蕭乾、葉盛長、李天綬等。
90年代初移居日本,先后任教于朝日文化中心、東京大學。2004年至2006年任東京大學第一位外國人特任教授、首任駐北京代表處代表。
2006年至2011年,與日本歌舞伎藝術家坂東玉三郎共同創(chuàng)作中日版昆曲《牡丹亭》,擔任總制作人、導演、編劇,于京都、北京、蘇州、上海、東京、香港等地公演。
2010年上海世博會期間,策劃制作梅葆玖、關根祥六、坂東玉三郎主演的“中日戲劇大師匯演”,被譽為“亞洲傳統戲劇出現在21世紀的第一座高峰”。
2011年至今,歷任北京國際曲社社長、北京京昆振興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北京戲曲評論學會會長。
著作有《風月無邊》《櫻雪盛世》《北京記憶》《茶禪一味》《煮酒燒紅葉》《沉煙心事牡丹知》《張中行往事》《梅氏醉酒寶笈》《舊風舊雨》等,與邱華棟、祝勇共著《日本意象》,主編《中國京劇經典劇目匯編》《梅葆玖畫冊》《梅葆玖紀念文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