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來的古代文學研究:在開放中走向成熟
10月8日,《文學遺產》編輯部邀請部分在京古代文學研究專家,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召開了“改革開放40年古代文學研究座談會”。會議特地邀請了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出生的十四位古代文學研究工作者,作為改革開放40年來古代文學研究的親歷者出席會議并發言。

會議現場
座談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劉躍進主持。他指出,從口述史的角度看,40年是一個時代的重要門檻,而與會的各位學者都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所發表的評述或將影響今后文學史的書寫。“因此,今天我們站在40年的門檻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古代文學研究成就,就具有非常特殊而重要的意義。”
改革開放為古代文學研究帶來的發展契機
1980年《文學遺產》復刊,這一事件可作為古代文學研究又登上學術舞臺的標志性事件之一。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石昌渝總結道:“在此前的十年動亂中,古代文學基本上是被視為是封建的糟粕,除了短時間里開展的‘評紅’、‘評水滸’和‘評法批儒’運動涉及到古代文學之外,古代文學就是一片禁區。改革開放打破了這個禁錮,《文學評論》《文學遺產》復刊,《文史知識》《古典文學知識》以及各種專刊、叢刊的出現,高考的恢復以及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專業的設立,標志著古代文學研究又堂堂正正登上了學術舞臺。”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劉勇強也持相似的觀點:“古代文學身份的確立是與近代文化轉型與現代學科建設聯系在一起的。改革開放之初,由于研究生學歷教育的全面恢復,這一確立得到了最后的強化。 ”他還認為:“身份的確立也有文學內部的原因,對文學功能與意義的認識即是古代文學定位的內在理據。例如古代詩文的抒情言志、述史紀實等,小說戲曲的‘羽翼信史’、教化娛樂等,都是前人對這些文體功能的基本認定,也始終是把握它們文化地位、審美特質、藝術品格的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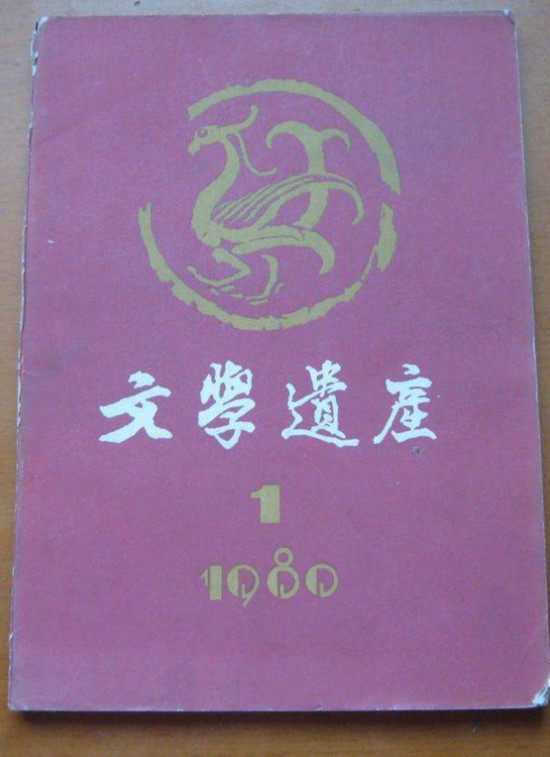
1980年的《文學遺產》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劉寧也認為古典文學研究的“學科化”發展,是近30年尤為突出的現象。她還講道:“研究生教育是學術‘學科化’的核心。中國大學的研究生教育起步很晚,即使是備受推重的西南聯大、清華國學院,其研究生教育無論規模和持續的時間,都很有限。上世紀八十年代,研究生教育迎來全面繁榮,新世紀以后,研究生招生規模迅速擴大,專業設置日趨豐富,古典文學研究在‘學科化’的道路上迅猛發展,呈現兩個突出特點:學術規范意識不斷強化和學術范式影響不斷加強。”
除此之外,改革開放也打破了古代文學研究對象的禁區。國家圖書館原館長詹福瑞講道,“文革”結束后,形成了政治有紀律、學術無禁區的制度規矩,使古代文學研究無論從研究對象到研究方法,都更加自由,更加寬松,更加開放。曾經被視為研究禁區的明清禁毀小說和宮體詩等領域都重新開放。“舊時碰都不敢碰的《金瓶梅》,有了深入的研究,而且在中國文學史上有了它小說經典的地位。”
40年來古代文學研究取得的成就
劉躍進從學科發展變化的角度總結了這40年來古代文學研究取得的成就:“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古典文學研究剛剛擺脫機械僵化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束縛,藝術分析成為一時熱點。葉嘉瑩先生借鑒國外文藝理論,細膩地分析傳統文學藝術特色。袁行霈先生也把研究重點集中到‘中國詩歌藝術研究’這一主題上。他們的研究成果,猶如一股清泉注入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界。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詩人叢考》出版,又讓很多青年人看到傳統學問的魅力所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新方法論風靡天下,宏觀文學史討論風起云涌,直接催生了一大批文學史著作,并推動中國文學史學史學科的建立。九十年代,曾有過一段相對沉寂的過渡時期。世紀之交,古典文學研究界呈現‘回歸文獻、超越傳統’的發展態勢。”
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葛曉音看來,“改革開放前中國文學史的研究集中于有人民性的大作家,以及部分經典作品。40年來,各時段中被忽略的各類文體開始得到關注;大量的中小作家現在已得到初步的研究;很多以前評價不足乃至偏頗的研究對象,都得到了糾偏;相關的文獻資料得到大規模的整理;別集注釋、總集編纂、版本研究、文獻輯佚的成果空前豐富。各類文學作品也從題材、文體、審美等不同角度得到細致的研究。可以說宋前文學史領域中已經很難找到大片的沒有開挖過的生荒地。”
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左東嶺認為古代文學在這40年中形成了“研究格局的立體化”:“在文學史時段的選擇上,逐漸由側重先秦、唐宋而向著元明清時段轉移,從而體現了各個歷史時段研究力量的均衡化。在文體選擇上,傳統學界因受到一代有一代文學之影響,因而各歷史時段研究的文體選擇呈現出單一化的狀況,如唐代偏重于詩歌,宋代偏重于詩詞,元代偏重于雜劇散曲,而明清則偏重于戲曲小說等通俗文學。經過40年的探索與實踐,目前則唐宋之小說、變文、說唱等俗文學也均得到充分重視,而明清之詩文也得以被廣泛關注,形成了與戲曲小說勢均力敵的研究格局。”
左東嶺還認為,“早期學界那種堅決拒斥與盲目崇拜的現象日益減少,像海外漢學提出的所謂寫本時代、早期未定文本的說法,已經被中國學界審慎地加以接受,將其作為問題進行討論而不是作為結論予以肯定。以上這些可以說都不同程度地展現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成熟,從而成為一個可以期待做出更大貢獻的學科領域。”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杜桂萍選取了一個微觀層面,總結了改革開放40年來戲曲研究領域取得的成就,她講道:“戲曲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巨大進展,呈現出系統化的特征,極大推動和促進了戲曲的研究。繼《全元戲曲》隆重登場后,《全明戲曲》已基本完成,《全清戲曲》正全面展開;一些重要的古典文獻整理工程得以繼續,如《古本戲曲叢刊》第六集終告完成,其他各集也在繼續編纂過程中。不僅如此,戲曲目錄學、戲曲文物學等文獻發現和編撰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這一切,為古典戲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和扎實的基礎。”
古代文學研究還有待改善的方面
在總結所取得的成就之外,作為古代文學研究隊伍中堅力量的一部分,與會學者也十分關心目前研究中還需提高和改善的方面。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陶文鵬認為,當前古代文學研究界還存在一些缺乏創新精神的不良現象與風氣,譬如有意回避經典。“因為經典作家作品的研究要求有淵博的學養,有很強的感性思維和理性思維能力;加上歷代的研究成果很多,繼續發掘難度極大。人們有畏難情緒,這就造成了研究經典的成果較少。但也有些令人矚目的優秀新著。例如葛曉音先生在《杜詩藝術與辨體》中,認真深細地探討杜甫古體、近體詩歌的表現藝術與辨體的關系及原理,新見迭出,精彩紛呈,把對詩圣杜甫的研究大大向前推進。”
同時,他還強調應大力加強古代文論的研究。“程千帆先生多次強調,我們不但要研究古代的文學理論,更要研究古代文學的理論。后者就是要求我們從大量的作品中,抽象出為眾多古代作家所認識和運用,卻未經理論家總結的新的理論范疇。這兩方面的研究都是重要的,但比較而言,后者是更困難的,也是更有意義的工作。”
而對于如何抉發古代文論的當代意義,中國傳媒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張晶認為在權威可靠的文獻基礎之上的闡釋是最為重要的途徑。“這里所說的‘闡釋’,并非一般意義上的注釋或校注之類,而是以原典文字含義為出發點,以美學、哲學、文化學或心理學等理論角度進行意義闡發或建構的過程。對于古代文論的當代價值實現,沒有闡釋是不可想象的。這種闡釋對于闡釋主體的理論修養要求頗高,如果僅限于一般的訓詁學能力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是有系統的美學、哲學、文化學、心理學等學科的理論修養,同時具有嚴密的邏輯思維能力,才能對古代文論的文獻作出當代美學價值的闡釋與建構。在這方面,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龍創作論》是最為典型的闡釋名作。”
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趙敏俐認為,現今仍需要重新思考中國文學的本質特征。“一百年前,我們從西方借用了現代的‘文學’觀念,用來闡釋幾千年的中國文學,建成了一個比較完滿的古代文學闡釋體系,功不可沒。但是今天回頭來看,這個體系存在的最大問題是生般硬套,由于從西方借用來的這個‘文學’概念不完全對應古代文學的實際,用它來闡釋中國古代文學,總有削足適履之感。它將一部分文體排斥在主流之外,如六朝以后的賦體文學;它將豐富的文化經典視為一般的‘文學作品’,消解了它那豐富的歷史哲學等文化內容,如對所謂的先秦‘諸子散文’和‘歷史散文’的闡釋。”
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廖可斌看來,還需保持古代文學研究的生機與活力,既要防止過于強調古代文學研究的現實作用的庸俗社會學傾向,也要避免古代文學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我們有必要探討古代文學研究與社會現實生活的良性關系,構建古代文學研究的健康生態。整理文獻是必要的,但要避免為整理而整理,要考慮是否值得和有必要整理;考證作者生平、作品版本等是必要的,但理論研究也不應該被弱化;微觀研究是必要的,但宏觀研究也不應該受到忽視;研究藝術形式和技巧是必要的,但對古代文學思想內涵的研究也不應該偏廢。古代文學研究不應該是一座品種單一的冷冰冰的標本陳列館,而應該是一片溝通古代人的精神世界與現代人的日常生活的百花齊放的大花園。”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劉石對于古典文學研究未來的發展提出了自己的兩點看法:“一點仍舊是充分利用新文獻,此所謂新文獻,既指方興未艾的出土文獻,亦指域外漢籍。此類研究隨著出土文獻的不斷出現和海外交流的日漸便捷,已經蔚然成風,就目力所及,黃德寬近期發表《略論新出戰國楚簡詩經異文及其價值》、卞東波近期發表《域外漢籍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新景觀》,皆可視作最新的示例。”
“另一點是拓展現代科技手段研究古典文學的深度。現階段數字人文研究的主要技術方法,包括機器學習與人工智能、數據庫方法、計算語言學、社會網絡與地理信息系統、數據與文本挖掘等幾個方面。這些技術方法可分別對應于古典詩歌分析系統的嘗試、作家生平事跡研究、古典小說研究、文本與人物研究、文體與文論研究。”
最后,用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郭英德的話作為結語:“可以肯定地說,我們這批60歲上下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者,絕大多數不可能再有40年的學術生命。但是同樣可以肯定地說,在我們這批文化人的身上,天生秉賦了一股‘小車不倒只管推’的精神,自覺自愿地把我們生命的每一年、每一月,奉獻給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