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嶺村編年史》:對自我心靈的再一次救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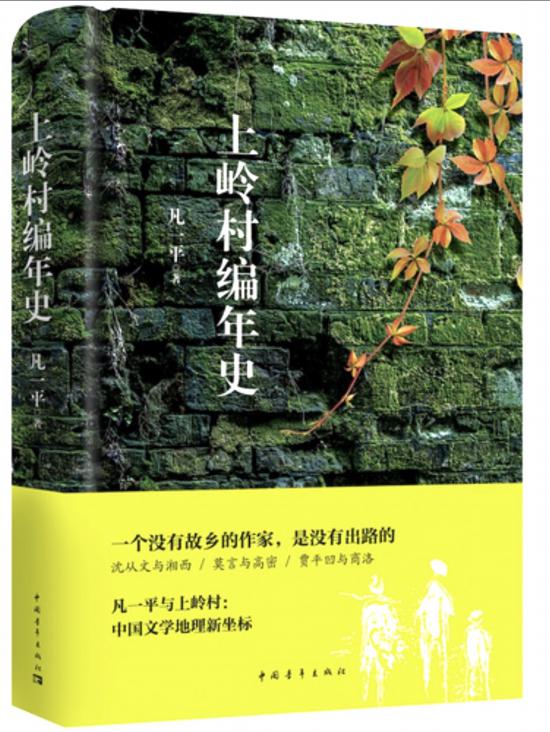
從桂西北都安瑤族自治縣往東13公里,再沿紅水河順流而下40公里,在三級公路的對岸,有一個被竹林和青山環抱的村莊,就是上嶺。它是我生命中最親切的土地或者搖籃。我16歲以前的全部生活和記憶就在這里。對我來說,家鄉是我生活過的地方中最潔凈的土地,我最純真的歲月也是在那里度過的。自從我離開了那里,進入都市,我被各種欲望騷擾、引誘、腐蝕,盡管我努力地進行著抵抗,同時用4部長篇小說對我的都市生活進行批判和解剖。但我還是覺得我已經不天真、不干凈了。我要如何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我為什么變成了現在的我?我能變回去嗎?而我認為最純凈的家鄉這么多年也在變化著,我的村莊生態越來越好,我的鄉親也變得比以前富裕了,但是歡樂卻比以前少了很多。這是為什么?我必須重視這個現狀,就像審視我自己一樣。
2007年的一天,我回到上嶺。此次歸來,距離我上次返鄉,相隔了11年。這次返鄉,對我的觸動非常大。我親切而隔閡的上嶺、熟悉而又陌生的鄉親,讓我關切和疼痛。從那年以后,我年年回家。期間我還爭取到政府的10萬元錢給上嶺修建了一個碼頭。殊不知正是因為這10萬元,差點造成了眾叛親離的后果,因為我不允許我的親戚染指這10萬元錢,而修建碼頭的人又沒有用好這筆錢,建起的碼頭差強人意。我被親戚抱怨,被村民誤解——我大哥和大嫂去給承建碼頭的包工頭打工,一天工錢30元,被旁人嘲笑說碼頭的錢是你弟找的,你卻只能在這做苦力。大哥大嫂當即摔掉了扁擔。村民因為懷疑修建碼頭的錢被人貪污,去縣里告狀,接待的黃副縣長問了一句:“你們知道凡一平嗎?”當晚堂弟便打電話給我,質問我黃副縣長這句話是什么意思?當時我沒有做任何解釋。我依然年年回鄉。依然盡我所能為上嶺做事——丙申年我又找了20萬元,新建了一個碼頭,并找老板贊助了15桿太陽能路燈。從此我的鄉親過河不再趔趄,晚上即使喝醉了也不怕沒人發現。
回鄉,只要我回鄉,似乎這才是我的鄉親所期盼的。如今,只要在每年的某個重要節點,鄉親們總會看到我坦誠的面孔,而他們回報我的,只有熱忱。親善似乎又出現在我的村莊——也是丙申年,我復旦進修時的同宿舍同學徐顏平來到上嶺,因為喝得高興,回到南寧時才發現手機落在了上嶺。這位大商人非常擔心手機里的秘密泄露。第二天,我堂哥騎著摩托車跑了50公里趕到縣城,再乘班車130公里到南寧,把手機交給徐老板。他迫不及待地檢查手機、翻閱手機,然后驚嘆:“上嶺沒有斯諾登!”
是的,我的鄉親個個善良。
但我還是心情沉重。我沉重的原因是我既往的農村生活和現實的農民命運,總是像磐石一樣壓迫著我。它壓迫了我很多年,無論我在金光大道的城里過著似乎很美好的生活,它始終是我掙脫不開的夢魘。忽然有一天,我找到了撬開磐石的杠桿和角度,為此我激動不已,并且不遺余力。
2013年創作出版的《上嶺村的謀殺》,是我正視自己生活的土地的一部長篇小說,它使我獲得了一次藝術的跨越和心靈的救贖。我寫了一部內容與我以往不同的小說。“心靈的救贖”是指我以往的小說總是背離我成長的土地和河流,我愧對我的農村生活。而現在我的筆觸調轉了方向,我回來了。所以我解放了,得救了。
《上嶺村編年史》是我延續“藝術跨越”和“心靈救贖”的又一部長篇小說,其靈感來源于我的一個短篇小說《風水師》。我為這篇6000字的小說居然看了數十萬字的包括《黃帝宅經》在內的風水書籍,而更多的是思考人生的荒誕和沉浮,人性、命運的豐富和多變。
《風水師》寫完了,我把它投出去,發表在《廣西文學》2017年第4期。正值4月清明,我攜這本雜志回上嶺掃墓。我頑皮的孫輩們從我的包里翻出了這本雜志,連同糖果餅干一起拿走了。這本雜志傳來傳去,居然傳到了樊光良的手上。4月的最后一天夜里,我突然接到樊光良的電話。他在電話里跟我說:“你對我的虛構太多了,我哪懂那么多風水呀。其實真正的風水師是你。如果你敢,你能把上嶺村的人都寫個遍,我更服你!”
樊光良的話,像巫師的蠱惑慫恿我,也像神靈的昭示指導我。我當即坐到電腦椅上,打開電腦,飛快地寫下了小說的第一節。我一發不可收拾,從5月1日凌晨,到7月4日,我居然寫完了長篇小說《上嶺村編年史》。而且期間我出差、開會、醉酒,至少耗去一個月時間。對我這樣一個愚笨的作家來說,這個速度簡直就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何況,我對這部小說相當滿意。這是我的第7部長篇小說。在我寫完第5部長篇小說的時候,我覺得我不會再寫了。可我居然又有了第6部、第7部,這多余的兩部是誰送我的?是誰在操縱我的手,讓我繼續寫上嶺、一定寫上嶺?
既然這樣,那索性就讓我寫得更多、更超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