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齊安·布拉加靜默,一如天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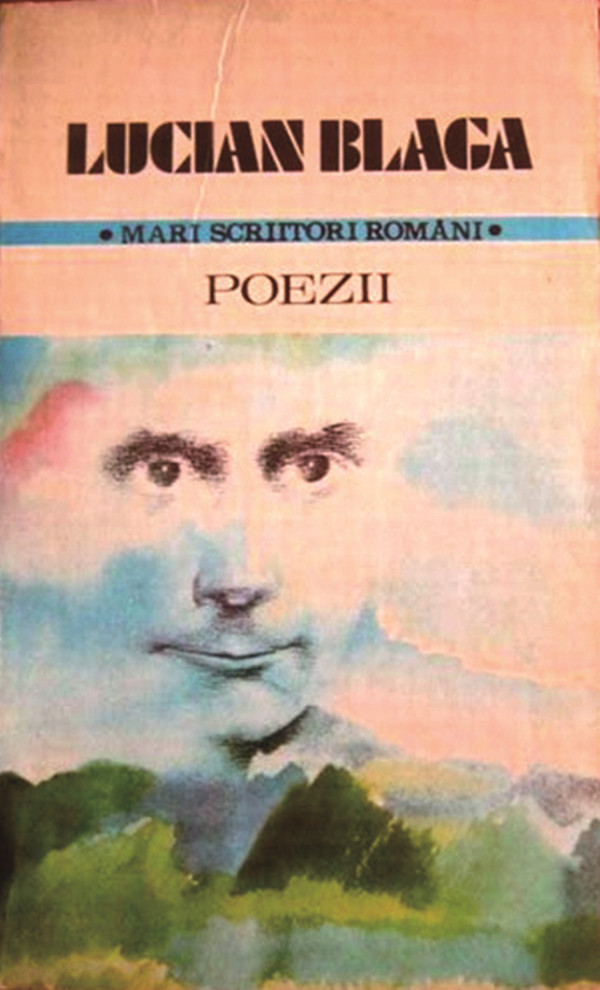
布拉加巧妙地將詩歌和哲學融合在一起。他的詩作在某種意義上正是他哲學思想的“詩化”,但完全是以詩歌方式所實現的“詩化”。認知和神秘,詞語和沉默這既相互對立又彼此依賴的兩極,便構成了布拉加詩歌中特有的張力。
我向來以為,閱讀需要適當的時間、氣候、環境和心情。比如,閱讀布拉加,就最好在晴朗的夜晚,在看得見星星的地方,在寧靜籠罩著世界和心靈的時刻。
倘若能夠到村莊那就更好了,村莊有永恒和神秘的源頭。瞧,布拉加早就發出了邀約:
孩子,把手放在我的膝上。
我想永恒誕生于村莊。
這里每個思想都更加沉靜,
心臟跳動得更加緩慢,
仿佛它不在你的胸膛,
而在深深的地底。
這里,拯救的渴望得到痊愈,
倘若你的雙足流血,
你可以坐在田埂上。
瞧,夜幕降臨。
村莊的心在我們身旁震顫,
就像割下的青草怯怯的氣息,
就像茅屋檐下飄出的縷縷炊煙,
就像小羊羔在高高的墳墓上舞蹈嬉戲。
——《村莊的心》
對于布拉加來說,村莊是根,是基本背景,是靈魂,是凝望世界最好的窗口,同時它還是治愈者和拯救者。這顯然同他的出生地和生長環境有著緊密的關聯。我們有必要稍稍來了解一下布拉加的人生軌跡。
盧齊安·布拉加(Lucian Blaga,1895—1961)是羅馬尼亞文學史上罕見的集哲學家、詩人、劇作家、美學家、外交家、學者于一身的杰出文化人物。他1895年5月9日出生于當時尚處奧匈帝國統治下的阿爾巴尤利亞市讓克勒姆村。父親是一名鄉村東正教牧師,通曉德語,熱愛德語文化。母親是一位普通的農家女。耐人尋味的是,布拉加出生后一直保持緘默,直到4歲才開口說話。這極像某種人生隱喻。后來,有人問他為何遲遲不開口說話時,他的回答是害怕說錯話。在塞貝希上小學時,他接受的是匈牙利語教育,同時跟著父親學會了德語,并且很小就開始閱讀德文哲學著作。13歲時,布拉加失去了父親。在此情形下,母親將他送到布拉索夫,在親戚約瑟夫·布拉加的監護下,繼續上中學。約瑟夫·布拉加寫過戲劇理論專著,對布拉加的興趣培養和人生走向肯定有所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為躲避兵役和死神,布拉加進入錫比烏大學攻讀神學,1917年畢業后,又緊接著前往維也納大學專攻哲學,并于1920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一戰結束后,布拉加家鄉所在的特蘭西瓦尼亞地區回歸羅馬尼亞。布拉加學成后回到祖國,回到家鄉,有一段時間,擔任雜志編輯,并為各類刊物撰稿。他最大的愿望是到大學任教,但最初求職未果。1926年,布拉加進入羅馬尼亞外交界,先后在羅馬尼亞駐華沙、布拉格、里斯本、伯爾尼和維也納使領館任職,擔任過文化參贊和特命全權公使。他的政治庇護人是聲名顯赫的羅馬尼亞政治家和詩人奧克塔維安·戈加。事實上,戈加同布拉加夫人有親戚關系,一度擔任過羅馬尼亞首相,他特別欣賞布拉加的才華,十分愿意重用布拉加,但布拉加的興致卻一直在文化哲學和文學創作上。1936年,布拉加當選為羅馬尼亞科學院院士。1937年,他發表了題為《羅馬尼亞鄉村禮贊》的演講辭。1939年,布拉加終于如愿以償,來到克盧日大學,創辦文化哲學教研室,成為文化哲學教授。1948年,因為拒絕表示對當局的支持,布拉加失去教授職務,并被禁止發表任何作品。為謀生計,他不得不當起了圖書管理員。1956年,流亡巴黎的羅馬尼亞文學史家巴西爾·蒙特亞努和意大利學者、愛明內斯庫專家羅莎·德·貢戴提名布拉加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遭到羅馬尼亞政府抗議。1961年5月6日,布拉加含冤離世,5月9日,就在他生日那天,幾位親友將他的遺體安葬在讓克勒姆鄉村墓地。走了一大圈,布拉加最終永遠回到了鄉村。
可以說,對于盧齊安·布拉加,無論在心靈意義上,還是在創作意義上,鄉村都既是他的起點,又是他的歸宿。童年和少年,在鄉村,一邊讀著文學作品,一邊望著田野和天空,視野變得遼闊,和世界的交流也就成為一件自然而然的事。興許是深奧而又神秘的天空的緣故,加上父親的感染,他幾乎在迷戀文學的同時,又迷戀上了神學和哲學。當他從維也納學成歸來時,既帶著博士論文,也帶著自己的詩稿《光明詩篇》。而他把這些成就統統歸功于鄉村。他在當選為羅馬尼亞科學院院士時發表的演講詞就以鄉村為主題,毫無保留地贊美鄉村。他說鄉村既是他的生活空間,也是他的精神空間。鄉村如同神話空間,有著豐富性、多元性、天然性、自由性、神圣性和無限性。這里寧靜、緩慢,適合思想、觀察和感受,正是永恒和價值理想的誕生地。羅馬尼亞出色的民謠《小羊羔》《工匠馬諾萊》,還有多姿多彩的多伊娜民歌都是在鄉村孕育而生的。他本人就是從鄉村走出來的詩人和哲學家。以鄉村為坐標,我們或許更能貼近他的作品。
布拉加上大學時開始詩歌寫作。1919年,處女詩集《光明詩篇》甫一出版,便受到羅馬尼亞文學界矚目,并獲得羅馬尼亞科學院大獎。接著,他又先后推出了《先知的腳步》(1921)、《偉大的流逝》(1924)、《睡眠頌歌》(1929)、《分水嶺》(1933)、《在思念的庭院》(1938)和《可靠的臺階》(1943)等詩集。后來雖被禁止發表作品,卻一直沒有停止詩歌寫作,即便在最黑暗最困厄的時期,依然懷著童真般的創作熱情。能否發表于他已不重要,關鍵在于寫,在于表達,為詩歌,更為內心。在他離世后,他的女兒朵麗爾·布拉加歷經艱辛,整理出版了他創作于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火焰之歌》(1945—1957)、《獨角獸聽見了什么》(1957-1959)、《運送灰燼的帆船》(1959)和《神奇的種子》(1960)四部詩集。除詩歌外,他還創作出版了《工匠馬諾萊》(1927)、《諾亞方舟》(1944)等八部劇本,以及大量的哲學和理論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文化哲學四部曲《認識論》(1943)、《文化論》(1944)、《價值論》(1946)和身后出版的《宇宙論》(1983)。在布拉加的所有成就中,他的詩歌成就最為人津津樂道。
在羅馬尼亞,人們也處處能聽到他的詩歌聲音,感受到他的不朽存在。那是2001年5月,我應邀來到羅馬尼亞北方重鎮克盧日,參加盧齊安·布拉加詩歌節,還有幸見到了布拉加的女兒朵麗爾。朵麗爾聽說我翻譯了不少布拉加詩歌時,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克盧日是一座異常整潔和安靜的城市,布拉加曾在這里生活了許多年。
在克盧日國家劇院的門前,我看到了布拉加的雕像,大得超乎想象,如一個巨人。他低著頭,望著地面,像在沉思,又像在探尋,栩栩如生的詩人哲學家的形象。我不由得想,無論作為詩人,還是哲學家,宇宙的奧妙都始終是布拉加的內心動力和寫作靈感。
我不踐踏世界的美妙花冠,
也不用思想扼殺
我在道路上、花叢中、眼睛里、
嘴唇上或墓地旁
遇見的形形色色的秘密。
他人的光
窒息了隱藏于黑暗深處的
未被揭示的魔力,
而我,
我卻用光擴展世界的奧妙——
恰似月亮用潔白的光芒
顫悠悠地增加
而不是縮小夜的神秘。
就這樣帶著面對神圣奧妙的深深的戰栗,
我豐富了黑暗的天際,
在我的眼里
所有未被理喻的事物
變得更加神奇——
因為花朵、眼睛、嘴唇和墳墓
我都愛。
——《我不踐踏世界的美妙花冠》
一顆謙卑的心靈,面對奇妙的世界,充滿了愛和敬畏,這是布拉加的姿態。在他的沉思和探尋中,我聽到了神性的輕聲呼喚。那神性既在無限的宇宙,也在無限的心靈。
在羅馬尼亞人的眼里,布拉加就是這么一個謙卑而又偉大的文化巨人。每年的5月9日,在布拉加的誕辰日,無數羅馬尼亞作家、詩人和學者都會從各地趕到克盧日,以研討和朗誦的形式,紀念這位詩人和哲學家。
當詩人同時又是哲學家時,往往會出現一種危險:他的詩作很容易成為某種圖解,很容易充滿說教。布拉加對此始終保持著一份清醒和警惕。他明白詩歌處理現實的方式不同于哲學處理現實的方式。“哲學意圖成為啟示,可最終卻變成創作。詩歌渴望成為創作,但最后卻變成啟示。哲學抱負極大,卻實現較少。詩歌意圖謙卑,但成果超越。”他曾不無風趣地寫道。但詩歌和哲學又不是截然對立的,它們完全有可能相互補充,相互增色。布拉加就巧妙地將詩歌和哲學融合在了一起。這簡直就是感性和理性的妥協和互補。他的詩作在某種意義上正是他哲學思想的“詩化”,但完全是以詩歌方式所實現的“詩化”。他認為宇宙和存在是一座碩大無比的倉庫,儲存著無窮無盡的神秘莫測而又富于啟示的征象和符號,世界的奧妙正在于此。哲學的任務是一步步地揭開神秘的面紗。而詩歌的使命則是不斷地擴大神秘,聆聽神秘。于是,認知和神秘,詞語和沉默這既相互對立又彼此依賴的兩極,便構成了布拉加詩歌中特有的張力。
面帶大膽的微笑我凝望著自己,
把心捧在了手中。
然后,顫悠悠地
將這珍寶緊緊貼在耳邊諦聽。
我仿佛覺得
手中握著一枚貝殼,
里面回蕩著
一片陌生的大海
深遠而又難解的聲響。
哦,何時我才能抵達,
才能抵達
那片大海的岸邊,
那片今天我依然感覺
卻無法看見的大海的岸邊?
——《貝殼》
聆聽,并渴望抵達,渴望認知,卻又難以抵達,無法認知,我們仿佛看到詩人布拉加緊緊握住了哲學家布拉加的手。但哲學和詩歌的聯姻十分微妙,需要精心對待,因為布拉加發現:“在哲學和詩歌之間,存在著一種擇親和勢,但也有著巨大分歧。哲學之不精確性和詩歌之精確性結合起來,會組成一個美滿的家庭,產生出一種超感覺的上乘詩作。可是,哲學之精確性和詩歌之不精確性混為一道,則會組成一個糟糕的家庭。所謂哲學詩、教育詩和演講詩都是基于后面這種婚姻之上的。”有時,為了保護詩藝,就得用上另一件利器,這就是布拉加時常強調同時也不斷運用的詩歌秘密:“人們說詩歌是一種語言的藝術。不錯!但詩歌同時又是一種無言的藝術。確實,沉默在詩歌中應當處處出現,猶如死亡在生命中時時存在一樣。”也正因如此,布拉加給自己描繪了這樣一幅自畫像:
盧齊安·布拉加靜默,一如天鵝。
在他的祖國,
宇宙之雪替代詞語。
他的靈魂時刻
都在尋找,
默默地、持久地尋找,
一直尋找到最遙遠的疆界。
他尋找彩虹暢飲的水。
他尋找
可以讓彩虹
暢飲美和虛無的水。
——《自畫像》
雖然詩人“靜默,一如天鵝”,但他的心卻懷著認知的渴望,始終在“默默地、持久地尋找,/一直尋找到最遙遠的邊界”。這其實也是布拉加一生的尋找和追求,他堅信,詩人之路就該是一條不斷接近源泉的路。或者,換言之,他給詩歌下的定義之一是:“一道被馴服的涌泉”。
羅馬尼亞文學史家羅穆爾·蒙泰亞努說得更加明白:“無論從高處看,還是從低處看,無論向里看,還是往外看,世界對于盧齊安·布拉加都好似一本有待解讀的巨大的書,好似一片有待破譯的充滿各色符號的無垠的原野”,因此,布拉加總是努力地“將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將一個代碼轉換成另一個代碼”,同樣因此,在布拉加看來,“任何書都是種被征服的病”。蒙泰亞努認為,有三種詩人:一種詩人創作詩歌,另一種詩人制作詩歌,還有一種詩人秘密化詩歌。而布拉加無疑屬于最后一種詩人。
沒錯,布拉加的詩歌總是散發出濃郁的神秘主義氣息。他堅信,萬物均具有某種意味,均為某種征兆。詩人同世界的默契是:既要努力去發現世界隱藏的奧妙,又要通過詩歌去保護和擴展世界的神秘。在他的筆下,“光明”象征生命和透明,“黑暗”象征朦朧和寧靜,“花冠”象征存在,“風”代表摧毀者或預言者,“水”象征純潔,有時也象征流逝, “黑色的水”象征死亡,“血”是液體的存在,象征著生命、祖傳、活力、奉獻和犧牲,“淚”意味著憂傷、溫柔、回憶、思念和釋放,“大地”確保人類存在的兩面:精神和物質,本質和形式,持續和流逝,詞語和沉默……“雨”則是憂郁和悲傷的源泉。而當“雨”變成“淚一般流淌不息的雨滴”時,就已然成為憂郁本身了:
流浪的風擦著窗上
冷冰冰的淚。雨在飄落。
莫名的惆悵陣陣襲來,
但所有我感到的痛苦
不在心田,
不在胸膛,
而在那流淌不息的雨滴里。
嫁接在我生命中的無垠的世界
用秋天和秋天的夜晚
傷口般刺痛著我。
白云晃著豐滿的乳房向山中飛去。
而雨在飄落。
——《憂郁》
需要強調的是,在布拉加的詩歌中,這些意味并不是固定不變的,有時也會隨著心境、語境和環境的變化而有所變化。
布拉加的詩歌還明顯地帶有一絲表現主義色彩:注重表現內心情感,激情,傷感,充滿靈魂意識,力圖呈現永恒,謳歌鄉村,排斥城市,向往寧靜和從容。但不同于典型的表現主義作品,他的詩歌神秘卻又透明,基本上沒有荒誕、扭曲、變形和陰沉,語調有時甚至是歡欣的,時常還有純真和唯美的韻味。他不少詩歌中對美的敏感和迷戀就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那組《美麗女孩四行詩》:
一個美麗女孩
是一扇朝向天堂敞開的窗戶。
有時,夢
比真理更加真實。
一個美麗女孩
是填滿模具的陶土,
即將完成,呈現于臺階,
那里,傳奇正在等候。
多么的純潔,一個女孩
投向光中的影子!
純潔,猶如虛無,
世上惟一無瑕的事物。
…………
作為哲學家-詩人,布拉加的目光敏銳而深邃。他很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質,然后再用形象的語言表達出來。短詩《三種面孔》就生動地道出了人生三個不同階段的特質,在某種程度上,也預言了他自己的命運:
兒童歡笑:
“我的智慧和愛是游戲!”
青年歌唱:
“我的游戲和智慧是愛!”
老人沉默:
“我的愛和游戲是智慧!”
在最后的十余年里,布拉加真的沉默了,盡管那時,他在哲學、詩歌、美學、戲劇等諸多領域都已作出非凡的成就。失去了講壇,失去了言說和發表的權利,失去了同讀者交流的平臺,他只能“像天鵝一樣地靜默了”。事實上,他并沒有完全靜默。據羅馬尼亞文學評論家阿萊克斯·斯特凡內斯庫描述,在最后的歲月里,他依然在寫詩歌,在翻譯歌德的《浮士德》,在整理和編輯自己的作品。一個堅信永恒價值的哲人和詩人怎么可能說放棄就放棄了呢?!面對艱難,面對困厄,他似乎早就作好了心理準備:
不容易的還有那歌聲。晝
與夜——世上的一切都不容易:
露是通宵歌唱的夜鶯
因疲勞而流下的汗。
`——《四行詩》
但作為詩人,布拉加明白,他“屬于獨立的民族”,屬于將言說和沉默融為一體的異類,詩人的使命就是要“效忠于一門早已失傳的語言”:
不要驚奇。詩人,所有的詩人屬于
獨立的民族,綿延不斷,永不分離。
言說時,他們沉默。千百年來,生死交替。
歌唱著,依然效忠于一門早已失傳的語言。
深深地,通過那些生生不息的種子,
他們常常來來往往,在心的道路上。
面對音和詞,他們會疏遠,會競爭。
而沒有說出的一切同樣會讓他們如此。
他們沉默,如露水。如種子。如云朵。
如田野下流動的溪水,他們沉默著,
隨后,伴隨著夜鶯的歌聲,他們又
變成森林中的源泉,淙淙作響的源泉。
——《詩人》
讓我們感到寬慰的是,布拉加逝世幾年后,尤其在1965年后,他為羅馬尼亞文化所作出的卓越貢獻得到公認。禁令廢除,他的作品再度出現在羅馬尼亞公眾視野。羅馬尼亞文學評論家們開始閱讀和研討布拉加詩歌,并紛紛給予高度的評價。文學評論家米·扎奇烏稱贊道:“繼愛明內斯庫之后,羅馬尼亞詩歌在揭示大自然和宇宙奧秘方面之所以能獲得如此廣度,盧齊安·布拉加的貢獻是任何兩次大戰之間的詩人無法比擬的。”羅馬尼亞科學院院長、文學評論家歐金·西蒙斷言:“沒有任何一個兩次大戰間的詩人對后世有著像盧齊安·布拉加那樣重大的影響。”確實,在斯特內斯庫、索雷斯庫和布蘭迪亞娜等羅馬尼亞當代最優秀的詩人身上,我們都能看到布拉加的影子。瞧,詩人布拉加曾經沉默,隨后,真的“又變成森林中的源泉,淙淙作響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