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幽冥起伏的心理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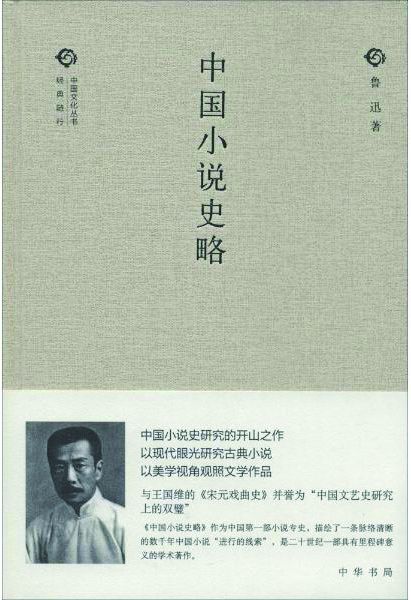
話本是說書人講故事的底本,擬話本則是文人模擬話本創作的小說。作為從話本到文人小說的過渡,擬話本影響最大的是講史作品,如魯迅所言:“近講史而非口談,似小說而無捏合。”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將 “三言二拍”等擬話本作品,命名為“擬宋市人小說”,“三言”也被認為好在“極摹世態人情之岐,備寫悲歡離合之致”。
擬話本既是過渡,自然兩頭相搭,有宋代話本的故事模式,有文人小說的技術雛形,譬如探索敘述語言的書面化,書寫小說人物的心理活動。小說不同于故事已是通識,但小說家和講故事的人,常被誤認為是一種人。本雅明的《講故事的人》被引述時,講故事的人也時常和現代小說家混為一談。本雅明認為,為了故事能被更好地重述和傳播,幽冥的心理分析常常被講故事的人放棄,而對小說而言,幽冥的心理卻別有魅力。
“三言”中有一則擬話本小說《賣油郎獨占花魁》。說是街頭小販賣油郎秦重,某日出去賣油時,看見隔壁青樓女子、名滿全城的花魁王美娘:“秦重定睛觀之,此女容顏嬌麗、體態輕盈、目所未睹,準準的呆了半晌,身子都酥麻了。”賣油郎為其美貌所傾倒,一見鐘情,欲望升騰,心想“若得這等美人摟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自此茶飯不思,此念頭牢牢占據了賣油郎的頭腦,由此開始了一場有預謀有計劃的求愛行動。
擬話本的好,多在局部,就是細節,做得工整和細致,不止趣味盎然,敘述也多嫻熟機巧。以此細讀《賣油郎獨占花魁》這個故事,不但能體味小說的戲劇性,也讀得出小說家的技術之圓熟,已經有區別于話本的講故事了。舉例分析賣油郎遇見花魁后的一段心理活動,真是千回百轉,七八個來回,否定又否定,一個念頭壓著一個念頭,實在奇妙周詳。
賣油郎一路的肚中打稿道:“世間有這樣美貌的女子,落于娼家,豈不可惜!”又自家暗笑道:“若不落于娼家,我賣油的怎生得見!”
一個賣油郎,挑著油桶,發癡般地走在路上,自言自語,不斷找理由說服自己,十足一個癡漢形象,此場景就頗為滑稽有趣。賣油郎先是感嘆,世間怎么會有這么漂亮的女子,這么漂亮竟然淪為娼妓,真是可惜可憐,這是普遍人的正經心態,同情心似有燃燒。轉念一想,要她不是娼妓,我一個賣油的小販子,怎么見得到這等“容顏嬌麗、體態輕盈、目所未睹”的女子,就開始釋然了。可不是嗎?街頭小販想見到大家閨秀?門兒都沒有。這么一轉想,賣油郎原本還算高尚的心理,就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欲望開始超越理智了,也開始越過普遍的倫理了。
又想一回,越發癡起來了,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若得這等美人摟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又想一回道:“呸!我終日挑這油擔子,不過日進分文,怎么想這等非分之事!正是癩蛤蟆在陰溝里想著天鵝肉吃,如何到口?”
待賣油郎的心理建設稍微好了一些,就不再為她感到可惜了,而是過渡到自己身上,理由很是充分,先是給自己降壓,調起得相當高:人生一世,草木一秋。這是多大的詞兒,從人生談到性欲,頗有悲壯之感。不明就里的人,還以為是要干驚天大事情了。也可理解為,人生一世很短暫,就像草木一枯一榮,轉眼就過去了,得及時行樂。鋪墊得真是夠有分寸和節奏,在此基礎上才想,要是能與這個姑娘共度春宵,死也值了。這等引申邏輯,有理有據,頗具自我催眠作用。一個人決定要做的事情,總能找到光明正大的理由。
這個念頭一出,賣油郎稍感不安,馬上譴責自己。先是一番自責,心想你一個賣油的小販子,一天就賺那么一點點錢,竟然還想睡花魁,簡直瘋了。注意,他責怪自己的,并不是出于道德倫理的考量,而是認為自己賺得少,沒錢還想辦大事,真是不自量力。小說中有一個比喻,這好比陰溝里的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后面接的不是尋常的“想得美”,而是如何到口?真是精妙。潛臺詞就是,想吃是想吃,可怎么吃得到呢?賣油郞自責和懊惱的,第一條便是沒錢。這番心理活動,小說家編排得循序漸進,有鋪有墊。
又想一回道:“他相交的,都是公子王孫。我賣油的,縱有了銀子,料他也不肯接我。”又想一回道:“我聞得做老鴇的,專要錢鈔。就是個乞兒,有了銀子,他也就肯接了,何況我做生意的青青白白之人。若有了銀子,怕他不接!只是那里這幾兩銀子?”一路上胡思亂想,自言自語。
想過錢之后,賣油郎接著又憂慮起來,想起他頗為不堪的地位和身份。小小賣油郎,哪里夠得上花魁的接客標準,即使有了銀子,也未必能成,這是第二重困難。小說到此,看似先松一下,再接著緊一下,卻是一步一步給賣油郎的心理進行松綁。他馬上又給自己找到了安慰的可能,聽人說老鴇只看錢,有錢就行,瞧他舉的例子,說就算是個乞丐,只要有銀子,她也得接待。顯而易見,賣油郎對青樓女子的職業要求并不了解,有所低估了,但作為好的心理安慰劑,這次轉折于小說走向而言,頗為關鍵。最終促使賣油郎下定決心的,正是他認為銀子可以解決關鍵問題,所以他才歸結為一個核心問題,哪里找銀子去呢?
這番心理建設,豐饒有趣,一時欲望滿滿,一時又垂頭喪氣,寫得實在是玲瓏剔透,步步有理由。小說家精心設計了這篇心理活動,逐步敘寫賣油郎的心理起伏,當真是嚴絲合縫。這些心理活動只為解決故事的合法性問題,構建文學人物的真實性,即如何讓人相信,這個賣油郎的色膽從何而來,其勇氣從何而來?為接下來的求愛計劃做好鋪墊。要是沒有這番成功的心理建設,沒有曲繞回環的心理起伏,也就沒有接下來令人信服的瘋狂行動。與其說賣油郎跨過的是自我心理難關,不如說是小說家是說給讀者聽的,借此與讀者進行了交流,達成了一份關于敘述的真實協議。有趣之處在于,僅看這段心理書寫,層次之豐富,進退之自如,回合之纏繞,技術之嫻熟,照顧之周全,令人驚嘆。
心理活動描寫是中國古典小說相對缺少的內容,也是話本(故事)較少的內容。因為說書人表演的現實要求,心理活動一般難以呈現。心理描寫也是小說區別于故事的明顯特征。擬話本《賣油郎獨占花魁》出現的心理描寫,可視為話本形式向小說形式的新發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賣油郎這段心理活動所使用的敘述視角,也有意外的獨到之處。那就是與尋常的全知視角(直接引語)不同,賣油郎的心中所想,尤其是他對青樓老鴇只愛銀子、以為有銀子就行的猜想和自我安慰,隱有限知視角的影子。這類技術并非出于明確的經驗化后的敘述要求,而是創作者歷經長期練習的某種自覺。從小說全文來看,敘述者顯然是知道賣油郎想多了,至少敘述者知道賣油郎肯定是要碰壁的。
今天的文學研究和論述,涉及小說創作理論多求于西方,倒也不妨從傳統小說中汲取經驗,與現代經驗進行轉換融合,于細讀中獲得樂趣,也獲得可能的寫作滋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