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小詞、吳越對談:寫作是我在打開心扉說最私房的密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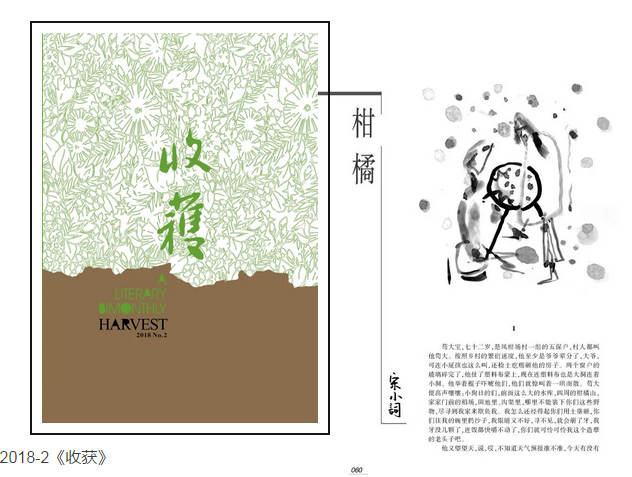
柑橘(宋小詞)
鳳柑場村里的茍大寶把整個青春都奉獻給了水庫和柑橘山的建設,他以為農村的集體道路會一直走下去,但沒想到八十年代農村實行承包,人單勢弱的他被剔除,為了補償,他變成了五保戶。時至晚年,潦倒失意的茍大寶遇上一個被人丟棄的年輕傻女,他視為女兒收留照顧。但村里留守的男人卻打起了傻女的主意,茍大寶為了討回自己與傻女的公道,得罪了村支書和村里所有人,日子處在逼仄狹窄的夾縫中,后來傻女懷孕,村委與村人拒不接納,逼其墮胎,老人心生憐憫,在柑橘成熟的季節中,他們的命運走向了絕境
寫作是我在打開心扉說最私房的密語
——從《柑橘》說開去
宋小詞vs吳越
吳越:小詞你好。對于編輯來說,作品就是作者的投名狀。一個出色、特別的作品,會為它的作者引來無條件的尊敬——無論這位作者此前是不是有名,與編輯有沒有交情。你的《直立行走》《太陽照在鏡子上》《血盆經》等就是這樣為作者掙來響亮面子的作品。先說城市題材,你對城市中人際景觀的觀看與把握,幽微而獨到,表達手法上,潑辣而有味。《直立行走》一開頭就抓住了人,楊雙福與周午馬開鐘點房后去淋浴,“忽然感到羞恥,覺得自己像周午馬的一只夜壺”,又狠又準,一個鄉下女子與城市貧民之間將愛情擠榨到幾乎為零的利益聯姻也就在這樣的譬喻中找到了自己的調性。《太陽照在鏡子上》是我尤其喜愛的一個中篇,同父異母的兩姐妹陶平和陶安,隔膜中隱含著恨意的歷史關系,任性而美麗的妹妹帶著孩子逃離婚姻,投奔姐姐,姐姐則在這個孩子身上看到了曾經發生在自己童年中的忽略與拋棄,她們的血緣關系如同“太陽照在鏡子上”又折射到自身,經過一番曲折,消耗了許多熱量,最終得到某種程度的確認,但妹妹卻用她的生命告訴姐姐,也告訴全世界,什么是“活著”。在這樣一個充滿了爆發-平復-再爆發的故事中,大量場景發生在姐姐的屋子里,“室內戲”一幕一幕,每一幕都完成了它在“核聚變”過程中的使命,經得起細讀和重讀。總之,你有一支非常準確的工筆,又裝上了方言的墨水,莊諧得當,活靈活現,按我們的話來說,就是“會寫”、“有生活”。能否展開談談你如何訓練、養育自己的語言和敘述的?
宋小詞:謝謝你對我的抬愛,讓我所寫的文字在你的敘述里閃閃發光,這是對我的一種鼓勵。謝謝你提的這個問題,讓我有機會敘述我心底的一個小癖好,你知道嗎,我每天都會跟自己做一個游戲,當我看到某個令我動容的場景時,我就會在心里做一番描述,我會給自己出題,如果是寫作,要如何寫才能讓人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有時候我在等公交的時候,我會閉上眼睛,認真感受城市發出的各種復雜的聲音,這些聲音該要如何呈現才最生動最準確,那些帶著急剎的公交車它們停靠在站臺時是什么樣子,那些慌亂過馬路的人們他們皮鞋踏著地面的聲音像什么,如果我用炸豆子來形容的話,形象不形象,還有自己遭遇的一些事情,當你講述給朋友的時候,怎么講,才能還原其情狀。走一條路,一路上之所見所聞,我都會在心里默默做一番描述。這些都是一些很細微的,不足以向外人道的一些笨功夫。凡是涉及到說話和文字表達的都可以作為我日常的一種訓練。而且有時候你身邊朋友的講話,時不時也會蹦出語言的金子,這些金子我都會一一將他們撿進我自己的寶庫里。你也說過,我很擅長用方言,是的,對于我家鄉的很多方言,土話,我都會細細琢磨,我有時候覺得有些方言就像螢火蟲一樣,它有一種光芒,它比穩重的書面用語或是普通話更有嚼頭,更有味道。比方,我們那里說扇了一巴掌,不說扇,說鏟,我覺得這個鏟就比扇更有勁。像這些語言我都會收集起來,然后進行選擇提煉,不濫用,關鍵時候用一下,會更有味。然后日常的收集儲存,閱讀自己喜歡的作家作品,琢磨那些對自己味口的文字,看看它們的內部藏有什么樣的魔力。從經典的文藝作品和日常生活中汲取養分,然后與自己的土壤進行融合,慢慢讓其成為自己的武器。而且就像你說的,養育,養育是一種慢功夫,要一點一點培養。這些都是從日積月累中和有心中得來。
吳越:不知不覺中,我把你視為繼池莉、方方等崛起于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新寫實主義”、“漢派小說”之脈傳的又一女作家。因而我對你的城市題材小說頗懷期待。其實早先我在看到你的《直立行走》和《太陽照在鏡子上》時,以為你近來的寫作已經主要轉移到了城市題材上,不料你拿出的新作《柑橘》是實實在在地寫農村的,可見你還在使“雙槍”。小說中的時間將近一年,讀者也跟著你體驗了柑橘樹培育養護的四季,而柑橘山,養魚塘,山間公路……這些物事被你一寫,像是獲得了新的生命氣息。讓我想起你之前的作品《血盆經》,它寫的是鄉村里一個無依無傍的少年郎去學做個小道士的歷程,先不談情節與主題,這樣的小說如果沒有大量準確、豐富、迷人的細節,譬如你所細細臨摹的鄉村道場的風俗、科儀等,是無法寫成的。新作《柑橘》也是如此,從我的角度看,你寫農村的小說語言上更放松,觸覺更敏感,視野的邊際更廣大——而有數得很。不知道你自己怎么看待寫作題材這個話題?你又如何看待所生活過的城市與鄉村?
宋小詞:你所說的寫作題材,我個人覺得這取決于寫作者個人,一個寫作者經歷過什么,有過些什么深刻的人生體驗,閱讀過哪些作品,研究過哪些領域,接觸過什么人,從事過什么的職業,遭遇過什么樣的事件,行走過哪些地方,思考過哪些問題,有過什么樣的感悟,這些都會一一沉淀在寫作者的心里,等著歲月將它們融化在個人的感受閱歷之中,這些都有可能成為寫作者的寫作題材。像鄉村和鄉村女性在城市的生活是我的寫作題材一樣,因為我個人有鄉村生活的深厚基礎,知道很多鄉村的故事,懂得鄉村人的喜怒哀樂,懂得鄉村生活的禁忌,我寫城市,也寫的是城市里的鄉村女性,因為我本人也是這樣的人,我接觸的很多也是這樣的人,因為這些都是我自己熟悉的,我能細膩的體驗她們各種幽微復雜的情感,因為熟悉,寫作起來就不感到膈應。如果讓我寫一個城市白富美,或是官場賭場之類題材的小說,我肯定是不知道該從那里下筆。我是一個蠢笨又很愚鈍的寫作者,我的寫作必須要從我自己體驗和經歷的東西來寫。就像我當記者時,其實有很多會議稿件,一些有經驗的老記者不用去參加,也能寫出來,但是我不行,無論是多么老腔調老套路的會議或是典禮,我都要親臨現場去實地聆聽感受一番,才能寫出稿件來,否則我一個字也憋不出來,為此,連我的領導都說我是個很呆板不靈活的人。我承認這種評價,這是我的短板,但我只能接受這個短板。我也知道這個短板于我的創作來說,是很危險的,因為它很容易暴露自己,所以我一向覺得寫作對我來說是很隱秘的,寫作是我在打開心扉說最私房的密語,這使我感到羞恥也感到恐慌,可我又不得不如此,因為我覺得寫作更需要坦誠。還有就是有時一個好的寫作題材會毀在一個平庸寫作者的手里,有時一個高超的寫作者會把一個很平庸的寫作題材挖掘出深刻的意義來。其實說這么多,無非是想說有什么樣的寫作者就有什么樣的寫作題材。
對于如何看待我所生活過的城市與鄉村,這也是我近期所思考的一個問題。我從鄉村出來,如今生活在城市里,我有時候會在內心問我自己,我是城市人嗎?不是的,從外部說我擁有了城市的戶口,擁有了城市的房子,擁有了城市的工作,從形式上說我是城市人,但從我口中濃重的鄉音,從我的生活方式,從我的思維觀點,從我的待人接物,這些內容上來說,我還是屬于鄉村的。我不過是居住在城里的鄉下人而已,但我想我的孩子應該是正宗的城里人,這個小小城里人,是我和我愛人這兩個居住在城里的鄉下人孕育出來的,我的父母和我愛人的父母,是泥巴腿子孕育出了我和我愛人這兩個半泥腿子,這樣看,一個農村人想要真正成為城里人最起碼要有兩代人或是三代人的付出和努力。沒有哪一個鄉村人不向往城市,像我們這種出身在鄉村的孩子,當你的家長有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追求,那么賦予你的責任就是要努力成為城市人,城市帶著光環,象征著文明、富有是龍門,是天堂。城市與鄉村向來就是兩個世界,城市越發達,鄉村就越虛弱,城市越繁華,鄉村就越死寂。而對于我個人來說,鄉村的生活并無詩意,城市的生活也沒有多少榮光,我處于尷尬的夾縫中。
吳越:接下來我想說的是,在你深植于生活的工筆之上,則是一種大塊之氣,悲天憫人。這才是講故事而至于成立小說的根本,也是屬于你的現實主義精神。但不知道你發現沒有,無論是寫城市題材還是鄉村題材,你都隱隱會寫到那些卑微、屈辱、忍耐中的人如何付出沉重的代價討回他們的尊嚴,這似乎是一個情感范式。《柑橘》寫一位鄉村孤老茍大寶,本來已經屈服于命運,最大的愿望不過是死后能有鄰人送個終,不要任蟲蟻腐爛咬噬于老屋之中。因為誤撿了一個智力低下的女子,引起一連串欺凌(包含鄉人的“平庸之惡”),而他在討要公道的路上愈走愈遠……茍大寶最后的結局,與《太陽照在鏡子上》中的妹妹陶安,《祝你好運》中的殘廢半截人何志平,有某種類似性,都是求告無門自我了斷。而《開屏》結尾,秦玉朵考慮從書房跳下去,“但她還是收住了自己,她不能用僅有一次的生命來跟生活對抗”和《直立行走》的最后,楊雙福被周午馬當成入室賊痛擊倒地,似也可視為是上述范式的一個變奏。我想說什么呢?閱讀你的這些小說的過程中,就像在隧道中慢慢擦亮了微弱火光,讓人對自己的卑微也生出某種敬意,被火光映在壁上的影子陡然也高大起來,會有一些莊正的東西滲入心底。但這些人物最終的命運,卻讓火光再度熄滅。作家是他筆下世界的造物主,你從一開始就決定了它們都不是“光明”的故事?結合你推崇的作家作品,說說你對現實、對人性、對悲劇的認識吧。
宋小詞:近來我特別喜歡杰克倫敦和安妮普魯的小說,他們的小說都有一種虎狼之氣,粗糙而堅硬的質感,洶涌而熱烈的氣勢。他們對現實對人性的揭露殘酷而深刻。他們的寫作告訴我寫作是需要膽量的,寫作需要拿出格斗士的氣概,面對紛繁復雜,瞬息多變的現實,面對深不可測,九曲回腸幽微如迷津一樣的人性,每一個寫作者身體里都要有一根定海神針,要有勇氣去揭露去審視去批判。我覺得真正的寫作者都不會是軟弱者,他們用一雙冷靜的眼睛觀察這個世界,用敏感而豐富的神經去感受這個世界,力求撥開重重迷霧,力求抵達真實的境地,為人們撥開偽裝的華麗外表。對于人性的光芒要極力贊美,對于人性的黑暗丑陋要堅決撕開,讓其裸露。對于悲劇,我很贊同魯迅先生的觀點,悲劇就是把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我眼見很多美好很多天真很多善良都被世間瓦解殆盡了,我看到我的很多親戚朋友他們都在自己的方寸之地里操勞掙扎,妥協與反抗,那一點點膚淺的活著的快樂不足以消除與生俱來的憂慮與恐慌。有時候我覺得這塵世間就像是壓在人身上的一座大山,各種現實、制度、倫理、條條框框,像一張網一樣把我們緊緊束縛,敏感的我總是時時感覺到被壓迫,被擠壓,被折磨,被盤剝,被煎熬,我們被裹挾著扭曲著矛盾著前進,有時候我們需要出賣一些尊嚴和美好的東西,來獲得生存的空間,由此,我們時常感覺到罪惡,我們一邊救贖一邊犯罪,我們的肉體與靈魂一直處于深深的不安中,然而我們一生抗爭,卻最終也逃不開衰老與死亡。我對生活對人類的絕望感似乎是從胎里帶來的,無論這陽光多么燦爛,無論這花開的多么熱鬧,對我來說都是假象,我依然看不見人生的希望。
吳越:此時正是狗年春節,大年初一,走親訪友的時候,不知你是否在醞釀下一部小說,或是已經忙里偷閑寫了起來。寫作不易,為母不易,一個同時是寫作者與母親的女性更不易了。我時常能感受到你生活中的煙火氣,但艱苦寫作的那一面你是不會輕易示人的。有了孩子之后,寫作風格和寫作作息上是否有變化?
宋小詞:有了孩子之后,寫作作息上肯定是變了。首先寫作時間被大量擠占,整顆心都牽掛著孩子,孩子健健康康的時候,心情還稍微松緩一點,一有個頭疼腦熱,咳嗽流鼻涕的時候,整個人就五心不定,干什么都干不了,只能一門心思去關注孩子。基本上孩子在家我是干不了事情的,一般孩子出去玩和孩子睡覺以后才是我的閱讀和寫作的時間。
對于有了孩子寫作風格有沒有變化,我想應該有吧,因為我能明顯感覺到有了孩子后,我的心胸寬廣多了,以前很多事我都睚眥必報,現在真的沒有了,因為有了孩子,我對這個世界還是充滿了很多善念,對很多身外的物質利益性的東西淡泊了許多。以前在外面碰到事情喜歡去跟人爭論,但有了孩子后,很奇怪,最害怕與人針鋒相對了,總是選擇自己吃虧,讓一讓算了。對人世多了一些包容,也多了一份理解,凡事也愿意站在別人的立場上替別人去思考一下,不再以自我為中心。有了孩子后,我感覺我的心腸一天比一天柔軟,肩膀一天比一天堅硬,像是脫胎換骨一樣。連我自己的風格都變了,我想我寫作的風格也一定變了吧。
吳越:我偶爾知道,你本人又還經過一回遷移,似乎過著武漢和南昌的“雙城”生活,平時也見你在朋友圈中曬些南昌當地的風俗和吃食,想必你正在融入當地的生活。這些變動對你的創作的影響是怎樣?
宋小詞:哦,是的,2015年之前我是沒有穩定工作的,2015年南昌市文聯把我作為高精尖人才引進為了專業作家,進入了體制內,這使我的生活有了一個基本的保障,讓我寫作的時候有了一顆較為安穩的心。目前因為孩子還小,愛人單位也都在武漢,一時難以全部挪過去,所以單位領導對我十分寬容,允許我這樣的“雙城”生活。我每一周總有一兩天會經歷武漢到南昌,又從南昌返回到武漢這樣一個過程。2016年我把小孩和公婆也帶到南昌去生活了一整年,起先很不適應,但漸漸地也適應了,我也挺喜歡南昌的,對于這樣一座能接納我包容我的城市,我沒有理由不去喜歡她,只是真正要融入進這座城市還需要足夠的時間。“雙城”對我創作的影響肯定是有的,這拓寬了我的寫作視線,人生的變動,起起伏伏都會給寫作者不一樣的經歷和感受,這些都會刺激到寫作者豐富而敏感的體驗神經,這些都會有形無形地影響創作者的創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