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深處的火焰》:人性與神性交織的生命贊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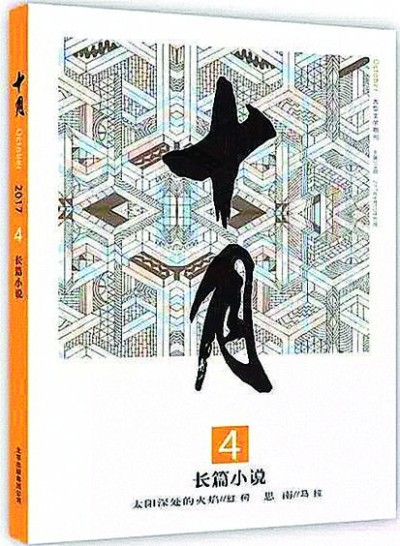
紅柯新作《太陽深處的火焰》首發于《十月·長篇小說》2017年第四期。
紅柯最新作品《太陽深處的火焰》,仍采用復調式敘事結構。小說的一條故事線索是吳麗梅與徐濟云的愛情故事,另一條是徐濟云的學術成長史及其帶領研究生研究皮影藝術的故事。不同于以往作品,紅柯此次創作在延續以往神性寫作的同時,加入了對現實的深度描摹,從而以冷夸張的敘述表現出對現實的批判,他以自己的工作環境為切入,以現實主義的方式揭露客觀真相,淋漓盡致地寫出了學術界在體制化、功利化驅動下的種種丑態。
紅柯的作品聚焦西域大漠。正是在那兒惡劣的生態環境中,生長著生命力極旺盛的楊樹、柳樹,羊群、牛群、駱駝群,以及生生不息的普通人。從《西去的騎手》《大河》《烏爾禾》《生命樹》《阿斗》《好人難做》《百鳥朝鳳》到《喀拉布風暴》《少女薩吾爾登》以及最近出版的《太陽深處的火焰》,都具有這樣的重復性敘述。
小說的闡釋,一定程度上通過重復出現的現象來完成。對作家的解讀,也可從重復這一角度展開。綜觀紅柯的創作,至少有三個方面的重復,分別是非自然敘事、對自然的崇拜、音樂的合理使用。
非自然敘述
藝術符號具有規約性,創作中又須不斷打破規約,完成自我更新。小說創作中,這種反規約主要通過非自然敘述等手法來實現。主流敘事理論建立在模仿敘事的基礎上,即敘事受到外部世界可能或確實存在的事物的限制。而當代敘事學發展的新動向則是反模仿的極端敘事,即非自然敘事。于紅柯而言,特殊的地域環境造就了其獨特的想象,他的作品恣意汪洋,亦真亦幻,具有神性寫作的一面。西域是多種宗教交融之地,民間想象力極為豐富,這也直接影響了紅柯的創作。
紅柯想象力豐富,其作品具有神性,很多詭譎的敘述打破了自然規律。《烏爾禾》中的海力布被塑造成具有神性的英雄,他懂鳥語,與蛇精和諧相處等等,都是非自然敘述。《喀拉布風暴》中關于地精以及武明生家族,作者也大膽地描寫了大量民間的性故事、性傳說和性知識。這些非自然敘述甚至引起讀者關注與質疑。
這樣的寫作,某種意義上與讀者好獵奇的閱讀心態有關。小說須有故事,情節越離奇,讀者越易走進故事甚至產生代入感。雖然許多作者強調并未獵奇,事實卻并非如此。其實,這也是中國文學傳統的延續。很多傳統文學具有非自然敘事的特質,如志怪小說、神話等,包括《搜神記》《聊齋志異》《西游記》,就連《紅樓夢》也有太多的情節超出了日常生活。再則,作家受西方文學尤其是現代派的滋養,西方大量作品采用非自然敘述,如《變形記》將人異化為甲殼蟲,波伏娃的《人都是要死的》和伍爾夫的《奧蘭多》等都屬于非自然敘述。非自然敘述是藝術對現實的提煉、夸張和變形,能使作品更具張力,更具文學性和藝術性。
自然崇拜
在紅柯的作品中,動植物與人一樣成為作品的主體。大漠里的胡楊樹、紅柳等植物,白羊、駱駝、狼等動物以及沙漠、盆地和河流等無生命的自然物,都是作者不遺余力描寫的對象,如《西去的騎手》中的馬,《大河》中的熊,《烏爾禾》中的羊以及《生命樹》中的樹。在《太陽深處的火焰》中,比胡楊更有生命力的紅柳成為“太陽深處的火焰”,這也是紅柯這部新作的命名來源。西域大漠的人和事,包括飛禽走獸、草木砂石,都與主人公共存共榮。在山川、河流、大地以及動物之間,人類找到了生命的根基。
《喀拉布風暴》中的風暴,這一自然現象可謂小說的另一主人公。風暴不僅具有摧毀性和破壞性,而且具有生命力,是自然界檢驗生命韌性的工具。在大西北沙漠瀚海中,肆虐的黑色沙塵暴被稱為喀拉布風暴,它冬帶冰雪,夏帶沙石,所到之處,大地成為雅丹,鳥兒折翅而亡,幸存者銜泥壘窩,胡楊和雅丹成為奔走的駱駝。而在《太陽深處的火焰》中,作者對塔里木盆地的描寫已完全融進小說。紅柯不止一次說過,景物也是他作品的主體。
對于離太陽最近的羊的描寫,則在紅柯多部作品中反復出現。包括作品中多次出現的對放生的描寫,這一切,都表現了對生命的敬畏。
對自然的崇拜,也是對生命的贊歌。《大河》是生命不死的頌歌,《西去的騎手》是有關英雄和血性的史詩式長篇,《喀拉布風暴》表現生命面對苦難時的堅韌與頑強。《太陽深處的火焰》中,紅柳就是火焰,照亮萬物的生命,包括民間藝術皮影,作者將各色人等編進故事置于西域風沙的洗禮中。神性的背后,是現實的書寫,對歷史的書寫,對一代邊疆開墾人的書寫。
音樂元素
小說不乏音樂敘事,當代小說尤為明顯。音樂可充當敘事元素,推動情節發展,與小說文本形成張力,深化主題。音樂還能彰顯風格,強化情感。
紅柯的小說中有大量的音樂元素。《生命樹》用歌曲推進敘事,具有蒙古史詩《江格爾》的風味。小說穿插兩種歌曲,一是蒙古古歌,這是關于靈魂的音樂。蒙古奶歌在文中多次出現,牛祿喜和馬來新的友誼中有奶歌,馬燕紅在擠奶的過程中悟出了佛性,其間多次響起奶歌。另一是時代流行曲,現代文明在大草原的印跡,也是王藍藍、陳輝等人生活的側影。
《故鄉》的情節同樣以歌曲推動,故事極簡單,情感則極濃郁。故事主要講述回鄉探母,情感主要通過歌曲來抒發。歌曲《我的母親》在文中反復出現,濃縮了太多的情感。作者把母親的愛和泉水相提并論,既洗滌了作者的衣裳與雙手,更洗滌了作者的靈魂。文中歌聲第二次響起,是大學生周健在周原老家時,《大月氏歌》與《我的母親》接連奏響。當他默默記下這首古歌時,勾起了對家鄉的無限思念。歌聲第三次響起時,天空中的白云消失,僅留孤零零的鷹。此時的情感又具有另一層色彩,《大月氏歌》是草原的歷史,是人們心中最隱秘的傷痛。
紅柯對民間音樂情有獨鐘,搜集了大量民間歌手專輯。這種音樂情懷延伸到創作中,音樂被廣泛運用于小說中。除了體現作者的立場,音樂還有助于抒發滿腔的情感,凸顯浪漫情愫。紅柯因其作品流露出濃郁情感,而被冠以浪漫主義者。
紅柯游走于西域與關中,勾連起來的是對生生不息的人間萬物的頌贊。紅柯的根深植于大漠,大量事物、人物、傳說、故事、情節、情感等已然書寫、反復呈現,小說結構、敘述手法等技法層面也有諸多延續,后期創作除了筆力的進步,融進了更多的人文思考。總體而言,紅柯的小說是對生命的敬畏,對生命力的謳歌,對苦難的隱忍,對人性的歌頌,對西域大漠的獨特情懷。神性中有人性的呈現,是神性與人性交織的生命贊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