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翊峰、伊格言:臺灣的科幻文學是什么樣的
今年的上海國際文學周以“科幻文學”為主題,兩位臺灣新生代作家代表——高翊峰與伊格言格外受到人們關注,他們都曾被《聯合文學》評選為“20位40歲以下最受期待華文小說家”,此次分別以科幻小說《幻艙》、《噬夢人》亮相2017上海書展。
在上海書展期間,高翊峰與伊格言就他們的小說與對科幻文學的思考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
人會失去“愛人的能力”
《幻艙》是一個有關封閉空間的故事。主人公達利被秘密送入一處封閉的下水道臨時避難所,此地衣食無缺,唯獨沒有時間和陽光,可躲在這里的人“安于現狀,不愿離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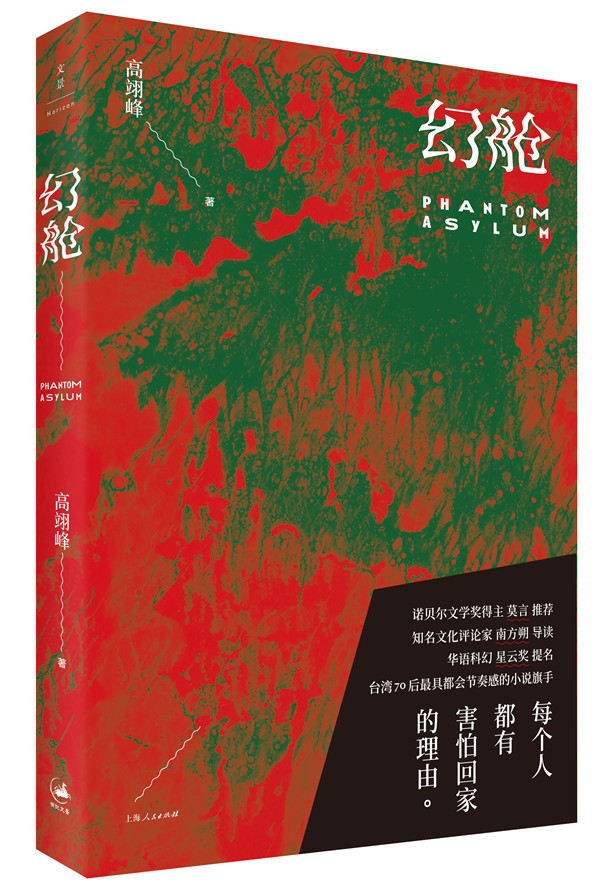
高翊峰著《幻艙》
這個故事有一部分源于高翊峰對城市生活的觀察:住在1層和住在40層的人,每天看這個世界的視野都不一樣,日積月累后就會出現“視差”。住在40層的人更多看到的是縮小比例的城市“有多快”,而住在1層的人更“接地氣”,更靠近普羅大眾。
“在這樣的‘視差’背后,城市人出現了很大的價值觀差異,我們可以把它們稱為twist——扭曲。扭曲之后,人會在城市生活中喪失大量與天俱來的愛的能力。”高翊峰舉例,“比如,在十字路口遇到一個哭泣的孤兒,會有多少人為他駐足,會有多少人主動上前關心他,又會有多少人愿意領養他?”
“再比如,若今天的上海是一個封閉空間,不是你不能走出上海,而是你心里不敢、不愿離開,這就是《幻艙》中除了達利以外所有人的心態。上海有車,有房,有工作,有美食,為什么要離開這里?可當你們的心靈狀態因不愿離開而被它困住的那一刻,它就開始扭曲你了。”

高翊峰。攝影 張超焱
其實早在2007年,高翊峰就有了這部小說的源頭想法,那一年是他寫作的第一個十年。他原本打算寫三個中篇故事,但因為工作關系遷至北京,事務牽絆之下一直沒能好好寫故事。
從2008年到2010年,高翊峰只能零零雜雜地做些記錄。“剛到北京時兒子才三歲,我、太太和他就住在一個一廳一室的小空間里。那時候認識的人不多,我還帶著一個孩子,孩子就是我心靈上的‘幻艙’,我不敢走遠,不敢跑遠。那樣的心理牽掛讓我困在了小小的密閉空間。”
“這樣的感受直接投射到了《幻艙》里。所以在寫《幻艙》時,我也一直在和自己對話。”高翊峰坦言,“所謂密閉空間,小到一個人的心靈狀態,大到一個城市,其實都有羈絆的地方。透過這個羈絆,我一直問自己,在這么劇烈、復雜的生活中,我究竟失去了什么。我發現我失去了愛人的能力,哪怕是面對自己的兒子。我意識到人愛人的能力會消失的,甚至父親會不知道怎么去愛自己的兒子,這就是《幻艙》想表達的核心。”
一開始高翊峰并沒有賦予《幻艙》科幻小說的想象。“其實真正在決定小說題材、素材的時候,我不會特別去分科不科幻,有沒有用到科學知識。”他告訴澎湃新聞記者,“現在我會開始想象這樣的科幻寫作之于我未來寫作的意義。”
高翊峰目前正在創作從《幻艙》出發的第二個故事。據說小說是這樣開頭的:“達利,以后你就繼續用這個名字在這個城市活下去吧。”
“人是什么”這樣的極端問題
和《幻艙》相比,《噬夢人》更有科幻作品的味道。“它還是我的書第一次在大陸出版。”伊格言笑稱,這是一個講述生化人匿藏于人類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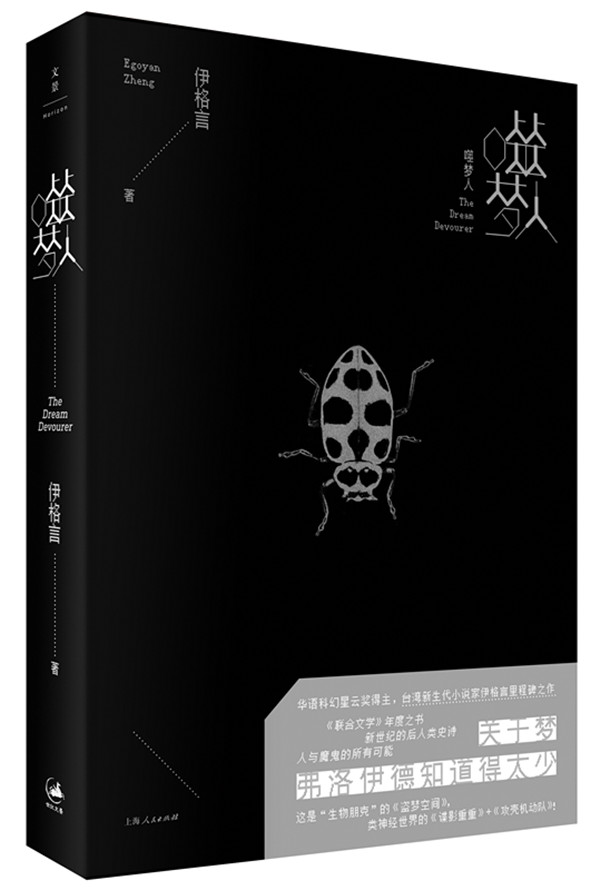
伊格言著《噬夢人》
在這個故事里,人的夢境可被粹取,再通過豢養水瓢蟲保鮮夢境。人類研發“夢境分析”篩檢法,希望借此準確標識出那些偽扮為人類的生化人。國家情報總署技術標準局局長、生化人K匿藏于人群中,卻始終不確知自己真正的來處,終于一道“內部清查”的命令啟動了K的逃亡之旅。
這部在2010年被《聯合文學》評為“年度之書”的長篇小說共33萬字,前后花了伊格言約三年的時間。“其實有沒有‘科幻’這個前綴不是很重要,但科幻作為一種題材有這個題材的優勢。我喜歡科幻是因為科幻最極端。在科幻里,只要你的設定好,你就可以把人的記憶換掉。如果不是科幻,在一般寫實文里,你能把人的記憶換掉嗎?原則上不行,但你還可以用隱喻的辦法。又比如我們常看的韓劇、婆媽劇,主角被車子撞到失去記憶,也可以換掉了,但很大費周章。”
“應該說,我天生就對極端的問題——人的組成部分中究竟靈魂的部分占多少、肉體的部分占多少、靈魂和肉體是可以二分的嗎、人是什么等等很感興趣。《噬夢人》主要聚焦在‘人是什么’這個問題上。”
在伊格言看來,夢是最幽深神秘的領域——有朝一日,當夢用以監視、用以控制、用以鎮壓、用以殖民。當這些技術與人對自我或他人的改造產生連結時——在某些時刻,人自我凌遲。在另一些時刻,外在環境則凌遲個人。
也有人說,《噬夢人》縝密的邏輯堪比一部推理小說。其實為了構思和寫作,伊格言前后做了8萬字的筆記,他有點嘚瑟地說:“都可以單獨出版一本書了。”
而之所以會寫這么多筆記,是因為這個構架的故事體量龐大,稍不注意,便會“前后矛盾”。伊格言還專門制作了一份小說“年表”,也因此長了很多白頭發。

伊格言。攝影 小路
比如,有個科技在年表中是2150年完成。但小說寫到后段,寫到2140年某事件時,卻可能會不小心寫成“該科技已經完成”。“要花時間去一一核對,避免發生這樣的錯誤。”
“我往后的創作,就長篇而言可能就有兩條線,一條是《噬夢人》系列,一條是關注社會議題的。《噬夢人》是一部科幻小說,但我在創作時不會刻意去想科幻是什么、應該怎么樣,就是想把作品寫好。”伊格言如是說。
迥異于本格派科幻文學的作品
近年來,中國科幻作品《三體》等連續獲得國際獎項或被提名,華語原創科幻文學作品日漸受到人們追捧與關注。高翊峰稱,來到上海后,他能感受到滬上文壇對科幻文學的討論熱情。“臺北好像沒有那么熱烈,這或許是兩地對于類型小說的差異。”
“現在興起了‘科幻文學熱’,我想或許可以把科幻文學粗糙地分為兩類。一類是本格派的,會用許多大家易懂的科學知識所展開的科幻小說,讀起來暢快、舒服、過癮,讀者還能通過一部小說理解了什么叫重力空間;另外一種是他(作者)把科幻當做創作題材,但其實還是想解決人的問題。這類作品或許是非常迥異于本格派科幻文學的作品。”
高翊峰直言,他對第二類科幻作品充滿期待。“因為這一塊作品其實還沒有大爆發。這次的《幻艙》和《噬夢人》,剛好是我覺得臺灣過去五年來,從嚴肅文學出發,但卻以實驗、科技、人工智能為素材的代表作品。臺灣文壇并沒有特別對《幻艙》《噬夢人》這類作品進行系統性的討論。其實在本格派科幻之外,還有一群過去嘗試純文學寫作的人用別樣的視角接近科幻文學。”
“就如高翊峰所言,我們都是純文學出身,在我看來科幻比較接近于一種題材。”伊格言說,如果是有藝術價值的科幻,它的未來應該是指向現在和過去的未來,不單純是未來本身。
“比如最近流行的《人類簡史》,尤瓦爾?赫拉利提到截至目前影響人類最大的三個制度——貨幣、國家和宗教都是虛構的。但是我們可以對人類這個物種巨觀的演化進行推測:未來宗教或許會被科學取代,國家也會被貨幣慢慢弱化,最后最強大的會是貨幣。”
在伊格言看來,如果再從“誰掌握了過去就掌握了現在,誰掌握了現在就掌握了未來”這個出發,繼續預測人類的文明走向,科幻就會變成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