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王海鸰:我相信觀眾識貨,相信人人想通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5年04月24日15:50 來源: 北京青年報 劉雅麒 王海鸰(前排中)與部隊官兵合影
王海鸰(前排中)與部隊官兵合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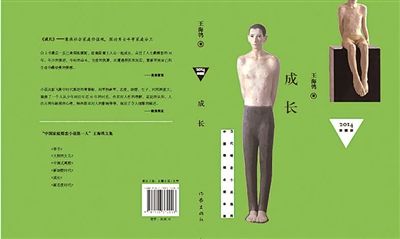
答題者:王海鸰
提問者:劉雅麒
時間:2015年4月8日
1.你被稱為“中國婚姻第一寫手”,對愛情和婚姻的深刻認識是怎樣形成的?
王海鸰:失敗更易使人反思警醒,我的愛情婚姻生活不順。客觀原因是在海島待時間太久,十六歲入伍上島,三十歲方才離開,接觸人有限。主觀原因是擇偶觀有問題:一定要找個比自己強的,追求才華追求地位追求超群出眾。完全是少女心情,是不了解生活復雜性產生的天真,是普遍存在于女人中間的虛榮。靠別人證明自己抬高自己,企望把自己的人生擱別人肩上,這是很多女性易犯的錯誤,我是其中的一個:外在條件至上,其他方面好說;相信自己有能力改變對方,或者為對方改變自己。當然這種改變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有前提,雙方或一方必須非常年輕,年輕才有彈性有可塑性。
我結婚時三十五歲了,思想方法興趣愛好已然定型,婚后發現對方也是如此。同時發現的是,我們之前有著種種的重大不一致,把這些不一致用一個詞概括起來就是:人生觀。不是說誰對誰錯,不一致罷了,夫妻無對錯,只有合適不合適。我的婚姻生活很短,留下的思考較深。
2 你眼中好劇本的標準是?
王海鸰:給觀眾的要比觀眾知道的稍多一點。現在跟制片方談劇本,制片方說得最多的話是:觀眾都是些什么人?這些人喜歡看什么?這種研究有必要,方法待探討。觀眾是什么人——什么人由什么劇決定而不是相反。喜歡《古劍奇譚》和《北平無戰事》的不會是一撥人,創作者跟在觀眾屁股后面跑沒有出路。最好的方法,我以為,面對自己的內心和所擅長的生活創作,吸引、培養屬于自己的觀眾,避免在收視率的喧囂中迷失自我。
3 你從事編劇工作,接觸過很多導演、演員。其中給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幾位導演或演員是?
王海鸰:我合作的第一個長篇電視劇導演是楊陽,合作劇目《牽手》。《牽手》因內容涉及“第三者”拍攝極其不順,有一次都要建組了投資方突然撤資,劇本輾轉幾年方由央視影視部投拍。出乎意料,播出時反響頗大,那些日子主創們天天熱線聯系互通興奮喜悅。但很快,興奮喜悅里悄悄涌動起一股暗流。
這現象廣泛存在于每個領域,簡單說:同一戰壕的戰友為了一個共同目標風雨同舟,并肩戰斗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后,如何分配勝利后的功名?對電視劇來說,接下來是各種評獎,而照慣例,編劇、導演這類重要獎項不會集中給到一部劇身上,戰友瞬成對手。那些日子我心總是惴惴,看到哪篇報道突出導演忽略編劇,就不快就沉重,對評獎來說,媒體輿論導向很重要。直到有一天,一份影響頗大的報紙登出了標題為《楊陽挽救“牽手”》的文章,讓我預感到了這場秘而不宣的博弈的結果。結果是,當年飛天、金鷹電視劇評獎《牽手》劇集、導演、主演全部獲獎,編劇顆粒無收。自此,我和楊陽不來往。一次,《牽手》責編吳兆龍請我跟楊陽吃飯,著重說頒獎時楊陽在發言中特別提出感謝編劇。我毫不客氣地回絕:先把別人踩進地里,再在墓前獻上束花,有意義嗎?
多年后,我和楊陽在一次活動中相遇,我們同時向對方打了招呼,那一瞬間,我心里只有久違的親切。并不是淡泊了名利——本是名利場中人,名不為人所知先就是一種失敗——而是,那時我早已意識到了自己的問題:缺乏移情能力。我只能體會自己為劇本創作從無到有殫精竭慮的辛苦,卻沒能力站在對方角度想對方付出了什么。劇本下馬后楊陽一直不放棄到處找投資,這過程得有多難甚至是難堪?拍攝制作過程中導演如果不是同樣的殫精竭慮,劇本怎么可能得到優質的呈現?我們都盡了全力都做得不錯,兩相比較,我的工作純粹,她的付出要繁雜得多。
4 你一直沒有放棄純文學寫作,為什么?
王海鸰:如果把寫作比做戴著鐐銬跳舞,那么純文學比之劇本,鐐銬要輕得多得多。如果有條件,誰都希望自己身心獲最大限度的輕靈自由。劇本寫作要做各種必須的妥協,資方的,表現形式的,政策的,導演演員的,但,收益多。有了錢就能夠任性一點,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我喜歡純文學寫作。它可以把我經歷的一切轉化為財富,艱難順遂悲傷喜悅痛苦歡欣……可以讓我心安理得地享受一切娛樂,旅行讀書觀影逛街聚餐八卦……回頭想,我對生活能夠一直充滿激情興致勃勃,很大程度上仰仗的是純文學寫作。但近幾年要暫時放一放了,需集中時間精力帶兒子一起寫劇本把他培養出來,讓他先有一門謀生手藝,爾后,他養家反哺,我只做自己喜歡的事——純文學寫作——首先,把沉釀心中許久的那本書寫出。
5 你覺得為什么你的劇大家喜歡?
王海鸰:過獎了,也有大家不喜歡的呢,只不過大家容易記住喜歡的,觀眾終究還是厚道。大家喜歡的那些劇如《牽手》、《中國式離婚》、《大校的女兒》、《新結婚時代》等,我想大概首先是涉及了一個上至達官貴族下至平民百姓共通的領域:婚姻愛情。但最重要的是,我對劇本創作的態度如同對文學創作:尊重生活,直面自己,深入開掘。我相信觀眾識貨,相信人人相通。帶兒子寫劇本后,創作領域寬了許多,性別不同年齡不同知識結構不同,于我們雙方是極好的互補。
6 你認為當下中國影視編劇面臨的困境是?
王海鸰:電影編劇和電視編劇的生存狀況又有不同。我感覺國內電影對編劇依賴過小,像“百花獎”這種重大獎項多年來居然不設編劇獎。很多導演、演員說起來對劇本求賢若渴,但劇本真到他們手上,會很自信地大殺大改。電影劇本短,三五萬字,短就決定了可隨時隨便誰都敢推倒重來。而外行修改劇本的長期結果是,編劇的創作積極性受挫,同時,生存艱難。相比起電影編劇,電視編劇工作要穩定些,辛苦是辛苦,總好過電影編劇有一單沒一單的狀態。前幾天跟一個青年導演聊,他談到了沒劇本的被動,半開玩笑道,對他們導演來說,如果自己媳婦能寫劇本,是最好的了。可見哪個行當都不容易。既然相互依存更需相互尊重,隔行如隔山,好的制作方應善于榨取每個行當每個行家的智慧使其各司其職,而不是由話語權大的人去越俎代庖。影視生產的先后順序決定了劇本會被改動,不是不能改,但不能以為是個人就能改,以為會說話就會寫字兒。從口到筆,那是一個職業。
7 年輕時在海島當兵的經歷,對你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王海鸰:先介紹一下我們那個島。四面環海,通往陸地的唯一交通工具是船,每遇大風,巨浪咆哮拔起一連數日,風停之后還有涌,十天半月無法通航是常事,駐島部隊生活供給常會因此切斷,淡水都得靠船運輸的深海小島部隊更苦。生活上的苦我不在乎,那是一個以苦為樂的年代環境,我在意的是交通不便帶來的封閉和單調。
部隊生活緊張勞累,勞累的只是身體,沒有書讀資訊很少,精神發育如同肉體發育需要營養,那時我常感大腦營養不足的饑渴。美妙如童話的時刻也多:秋季,傍晚,來自八方捕撈對蝦的漁船云集碼頭,我們在各個漁船上跳進跳出跟漁民們討價還價。不要魚,不要蝦,只要螃蟹。螃蟹水產不收購,冰凍了沒人敢吃,活著運出去當時沒這個條件。水產不收購漁民們就會賣得便宜, 最便宜時我曾跟他們講價講到螃蟹七分錢一斤。回到宿舍,點上小煤油爐,將螃蟹用臉盆煮,上面扣一只臉盆做蓋。隨著水溫上升,螃蟹將臉盆抓得咔咔作響,需要人將上面的臉盆緊緊按住。煮好了,就著盆吃,另一只盆吐皮兒用,兩三個人一晚上就能吃出一臉盆的皮兒……還有海上那豪華得令人窒息的月亮,還有島上無風時的靜寂,徹底的靜,靜得仿佛整個世界什么都沒有了,只有你……至今我喜歡安靜,喜歡純粹,知識結構偏窄,不知這跟海島十四年生活影響有沒有關?照理說是有關的,只是無法求證。
8 你怎樣看待名和利?
王海鸰:基本態度是:有追求,更有底線。
9 你對故鄉的情結?
王海鸰:十六歲那年,我穿一身沒有帽徽領章的新軍裝從山東蓬萊乘登陸艇進長島。還記得那天的海是淺灰色的,海面平靜,如一塊巨大的玻璃在太陽下閃閃發光,沒有人告訴我沒有人知道我將要去的地方是我父親的出生地。父母孩子多,工作忙,對我們難有現在家長對孩子的那種周到和交流。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不知道我的老家是哪里,父親母親來自何方。當兵幾月后父親才在信中告訴我,他出生于長島,長島是我嚴格意義上的故鄉。當年,父親參軍離開了它,幾十年后,我參軍回來。十六歲到三十歲,故鄉長島是我青春的見證。父母給我們取名中間都是“海”字,我給兒子取名為“鷗”。鷗是海的孩子。
10 兒子對你而言意味著什么?
王海鸰:昨天下午我參加一個活動,回來很晚。到家時兒子在他房間床上躺下了,但不睡,等我,直聽到我安全進家才放心關門睡了。我房間的窗子窗簾他已提前關好,臺燈開著……曾經我很想要一個女兒,從切身體驗認為,女兒對父母更體貼細膩。現在慶幸是個兒子,兒子既可做到女兒的孝順,還能有女孩兒難以企及的強大。兒女不孝是父母的失敗,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得算是個成功的母親。沉釀我心中的那本書,想寫的就是這一塊我生命中最重的部分。
11 什么時候你感到幸福快樂?
王海鸰:做喜歡做的事,并且做得不錯時。比如寫作和養孩子。
12 假如你可以獲得任何一種特質或能力,你希望是?
王海鸰:讓我的父母復活。
13 生命中你最感激的是什么?
王海鸰:興趣和工作的高度貼合。
14 你可以接受平庸的狀態嗎?
王海鸰:理論上是認同的,價值觀本該多元化。但目前還不能接受我自己平庸,再過幾年也許會。
15 你怎樣平衡工作與家庭之間的關系?
王海鸰:簡單說,依據實事求是輕重緩急的原則。舉兩個例子:1998年特大洪水,領導通知我去抗洪一線。我首先的反應是,我不能去。基于這樣的考慮:那里多我一個少我一個實在無關大局,而兒子才九歲多萬一沒有了我,天就塌了。我去找領導交涉。領導說:“抗洪是大事!”于是我明白必須去了。私心里權衡,違抗軍令極有可能失去安身立命之地,至時,全身心倚賴著我的兒子怎么辦?而去抗洪,不一定就死。走前我專門跟兒子說我曾經為他跟領導交涉過,我必須讓他知道他在我心中很重要很重要。那次抗洪我遭遇九江決堤,好在有驚無險。2008年汶川地震,我主動報名去一線。此時災區余震不斷,但我想即使萬一有什么也不怕,兒子十九歲了,我給他留下的資產足夠他活到自立。百聞不如一見,創作來源生活。1998年抗洪使我出了一部成功話劇《洗禮》,極大豐富了《大校的女兒》小說和電視劇的內容,去現場和不去,很不同。我去了汶川,也是有驚無險:乘直升機和另一架直升機編隊飛行,遇山區地域性大霧,我們平安著陸,那架直升機墜落山里。
16 喜歡什么類型的書?
王海鸰:每個年齡段不一樣。我很幸運,年輕時曾被派到蓬萊參加解放軍支農工作八個月。我去的公社有個大史家村,村里有個圖書館,里頭書很多,好多是當時外頭看不到的禁書。村里有個女子,早年間去了青島,一生未婚無后,死前留下遺囑,把所有積蓄在家鄉辦個圖書館。經過十多年時間,書慢慢積下,“文化大革命”中竟安然無恙,不知是因為大史家村偏僻,還是有人保護。這事至今是謎,當時沒顧上問,現在無處可問。那八個月是年輕時的我讀書最多的時期,饑不擇食,逮著什么讀什么,哲學經濟學數學政治文學歷史……完全是源于自然的求知欲。中年后,搞專業創作后,讀文學方面的書多一些。現在喜歡讀歷史。
17 你喜歡的運動方式?
王海鸰:散步。
18 你最近在看的電影/電視劇?
王海鸰:最近看過的一部電影是《智取威虎山》,感到很親切,對楊子榮斗虎那場戲和少劍波那雙細嫩的手印象深刻。電視劇一般不會跟著電視臺播出看,而是挑前段時間口碑好的劇,集中幾天看,比如《產科醫生》,再如《北平無戰事》。
19 你孤獨寂寞的時候怎樣與自己相處?
王海鸰:孤獨寂寞形似神不似。孤獨是狀態,寂寞是感覺。天天扎人堆兒里也會寂寞,一個人獨處也會充實。寫作使我享受孤獨,少有寂寞,兒子的健康成長更給我的充實平添了一份寧靜。
20 你現在的生活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嗎?
王海鸰:應當不是。年輕時對自己的希望繽紛多變,還曾希望過做一個賢妻良母呢,這愿望倒是實現了一半。但我滿意現在的生活,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有自己喜歡的兒子兒媳。到了老年分析自己,我不適合婚姻。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學術論壇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