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電視 >> 創作談 >> 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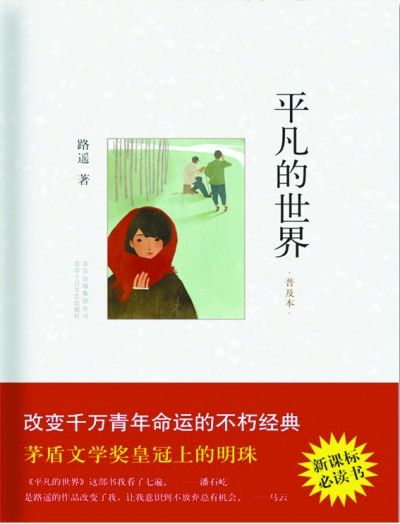
 葛水平在她的工作室
葛水平在她的工作室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繼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和《人生》之后,路遙和他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伴隨著空中的電波,再次走進城市鄉村的千家萬戶,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毫無疑問,《平凡的世界》既是一個作家對當代中國的書寫,也是對那個時期一代人或幾代人的吟唱。有人說,路遙是繼柳青、浩然之后又一杰出的鄉土作家,而在我看來,路遙不僅是鄉土的,更是中國的,他的作品真正的具有了中國氣派、民族風格,是我們當代文學中迄今一座令人無法企及的高峰。
一、故鄉構筑了路遙生命的大后方
我想說,如果路遙沒有那樣的童年就不會有今天的路遙。尊重一個人后來的聲名,首先要關注一個人的成長,其次是關注一個人的故鄉。故鄉是一個人成長的見證。別處的青山綠水,因為是別處,沒有這個人的足跡。
改編《平凡的世界》,要追溯到二○一一年春天,上海文藝出版社魏心宏老師電話找我,希望我改編《平凡的世界》電視劇。他說:“你是農村出來的作家,具備了改編這部作品的首要條件,而且晉陜就隔著一條黃河,古有秦晉之好。”六月,制片方單蘭平女士從上海來長治,我們見面,聊得很投緣。單蘭平說:“在電視劇市場激烈爭奪的今天,我們必須有一個好看的故事去爭取收視率,但同時也必須是一部有品相的大氣之作。很有可能在某個局部或者細節或者情節必須在審美上做個取舍的時候,我主張堅持有品相和大氣的作品。”我們最后達成了共識。
老實說,因為有了《平凡的世界》,我內心對路遙先生充滿了景仰。每當我回想起這部作品的時候,黃土高原上一排排高高低低的土窯,縱橫交錯的山峁溝梁,曲曲彎彎的羊腸小道就會浮現在腦海。溝道里的每一株野草,峁梁上的每一片野棗叢都是那樣熟悉,還有裹著羊毛肚手巾披著羊皮襖的漢子,一手拿簸箕一手拿笤帚的推磨女人……這里也是我祖輩生活的故鄉,這些人也就是我的父母叔嬸。一條黃河與一曲信天游,超越了地理的命名,為我們構筑了一個共同的故鄉。我所有的情懷都仰仗它的浸潤,我所有的寫作都是在這里呼吸。雖然我深知,改編一部作品,其實比獨立創作難度更大。個人創作,就是個人技能與水平的發揮,但改編作品,就需要改編者和原作者的默契配合和心領神會。某種程度上就是與原作者一次跨時空的合作。我們共同的情懷,給了我改編這部作品的最大沖動。
這中間我用大量時間重讀《平凡的世界》。我感到路遙的悲涼不是放在文字中的,盡管文字中平凡的世界充滿了酸澀和磨難,對于生存,人意味著什么呢?路遙的一生是坎坷的,整個社會一路發展過來是起伏跌宕的,人在社會中像微塵一樣,沒辦法,光陰就這樣把一個荒涼貧瘠的社會甩給了一代人。但是,路遙用文字改變人的命運,包括他自己的命運,不再顯得奮斗與夢想遙不可及。如他在作品中所說“天下終歸是識字人的天下”。作品中有他對普通底層努力活著的人的敬畏和疼愛,這也讓我想起了我貧窮的故鄉,當一部黃色的吉普車開進鄉村的土路時,我們追逐著它屁股后的塵土高聲喊著“吉普,吉普”,滿頭滿臉的黃塵,童聲叫響了山外的夢想。黃土地上的人事,沒有欣欣向榮的景象,但那些走過的日子是熱鬧的,也是真誠的。而整個世界的荒涼,一地的枯枝敗葉讓你看不到無血無淚的斷裂,他們就那樣走過來了。因為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還活著。那些人事都太實際,實際得識別不了超出腳步三里以外的地方。貧瘠中的熱鬧,窮又扎不下根,對那個漸漸遠離的世界,是一代人掙扎過的原鄉,從那個時代走出來的許多讀者會明白路遙對這部作品付出的心血和感情。
二、平凡是路遙敬天知命的精神底色
每一次走進陜西感悟都很深刻,這片土地不一樣。秦軍作戰最瘋狂的時候,士兵連鎧甲都不要,如狼似虎,潼關鐵門的啟動聲成為其他六國的喪鐘。如此大地之子,也只有在這里才能感受到來自土地之上追求高遠理想的苦斗精神。
路遙的陜北,既是時空的,又是社會的,點綴在山腳或溝畔的人家,都使人想到自然和人事的滄桑變化。一只烏鴉從老牛的背上起飛,將蒼涼的叫聲帶向黃土塬上,那一聲叫讓所有走進陜北的人對這片土地充滿敬意。陜北,見證了鐵馬冰河的慘烈,見證了短兵相接的血腥,也見證了人類歷史上一種難以想象的苦難。歷史中,饑餓感是我們父老鄉親似乎永遠也擺不脫的噩夢,饑餓是成為斬斷農民生活鏈條的最大惡魔。如今,解決溫飽已經不是我們當今農村和農民的話題。
陜北人有一種青山無處不道場的修行。這并不意味著就是不懂得爭取。他們用菲薄的物質供養著自己的精神,使得它不會過于豐滿和發達。他們對精神的卓越所表現出來的那種靜悄悄的、無師自通的忍耐和理智正是黃土地對他們的恩潤和澤養。路遙給這種平凡的精神賦予了宗教般的自由。我記得我看過一句話,大意是對任何意志的供奉都是一種順從。而路遙將這條拯救之路帶領到中國當代文學前所未有的高度。人只有進入到一種無所為的狀態才能讓過度的自我解脫出來,才能自動克制自己的欲求。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怎么滿足。或者說,一切帶有消極性質的滿足,都是一種惡!我們要去除的是痛苦,而不是一味的需要!這也是《平凡的世界》這部作品最美的地方。當物質匱乏的時候,是人都感覺到痛苦,而且是靈性越高的人感覺越是強烈。路遙就是這樣的人。
人身不凈,心就不能純粹。路遙作品中的陜北人,他們最終并不是什么戰天斗地轟轟烈烈干了多大事業的人物,而是歸于常態,因為平凡,才是人生的常態。不管你干過多大的事,平凡就是陜北人敬天知命的精神底色。《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安憑著自己的打拼,置下磚廠,按理說兄弟倆一起干挺好。我卻理解路遙為啥要讓少平出去。他不是單純的要獨立。這也是路遙的夢想,人只有不斷地把自己放置到一個比較難的位置上才能不斷地克制和凈化,甚至神話自己。否則,你就要被自己打敗。那個年代的人對什么都有一個十分明確的目的。少平作為家里的老二,次子,在沒有分家的情況下,主動地分擔家用。其實他自己也是一肚子難活,人生很不盡如人意。就跟他們清瘦的長相一樣。為啥長得那么克制,是因為心克制。少平如果不是一個從小在精神上有準備的人,他是不能擺脫人窮志短的群體原理,作為一個個體脫離出來,爭取到讀者的視線中,有路遙自己知天敬命的精神底色。
三、中國改革和經濟發展最初的實踐者
《平凡的世界》展開的時間是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五年的十年間。路遙經歷了這十年。這十年,正是中國社會思想大解放、觀念大變革、社會大動蕩的十年。《平凡的世界》所再現的環境,可以說是當時中國農村的一個縮影,極具典型性。中國農村當時經歷了土地改革之后最大的一次動蕩和沖擊。路遙把小說人物擱置在這樣的環境里,以時代和環境影響人的命運,以人的命運透視人的心靈。小說中有一條線是寫官場的,從省級領導、地區領導、縣級領導、公社領導一直到村級領導。路遙通過這些筆墨,力圖再現中國社會的變革中的最核心部分。
魯迅在《娜拉走后怎樣》一文中曾說: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在《平凡的世界》的世界里,如果說孫少安、王滿銀等人是中國改革和經濟發展最初的實踐者,那么田福軍就是中國改革和發展最初的決策者,他們有著與農民緊緊相連的血緣之痛,有著對國家落后貧困的情感之傷。雖然經歷動亂時代依然心有余悸,但他們義無反顧。他們案頭上的每一個決定,都面臨著失去個人前程,甚至斷送身家性命的雷區,這樣的險境是今人很難體察和理解的。像田福軍這樣一批領導人,在歷史發展中的存留時間并不長,但正是他們的承前啟后,決定了我們國家今天的命運,值得銘記,值得緬懷。路遙所寫的雙水村的兩個政治人物,書記田福堂、支委孫玉亭刻畫還是成功的。尤其是孫玉亭,把他當年勒緊褲帶鬧革命以及后來政治的淡化后的那種失落感表現得淋漓盡致。田福堂這個人物,初期刻畫也是很成功的。但小說后面說他進城當了包工頭,之后失落的原因是因為有氣管炎,身體不行了。我覺得沒有抓住人物命運的要害,田福堂內心最終的失落,不是他身體的原因,而是他觀念的問題。試想,一個受黨教育多年的領導干部,在經濟轉型期當了包工頭,他平時的“思想覺悟”,沒辦法適應轉型后包工頭走后門、送回扣的那一套模式,最終他的內心沖突,是他多年思想觀念與社會變革之間的沖突,而不能簡單地處理成身體的原因。
改革開放初期,最先搞活流通、把商品帶回農村的是孫少平的姐夫王滿銀,還有金家的大兒子金富。這組人物是具有代表性的。但小說把金富處理成一個“三只手”,把王滿銀處理成一個“二流子”,削弱了那個時代所應表現的內涵。比如,王滿銀在計劃經濟時期就知道順手販賣“老鼠藥”賺錢(并且還兌了一半假鼠藥)。社會經濟一旦搞活了,一定會給這種人一種施展身手的機會,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有“經濟頭腦”的人。至于他最終落在一個什么結局上,取決于市場經濟趨于規范時他的人品和誠信度。
四、用生命去感知生活再現時代
路遙對故鄉滿眼的黃土坡梁和純樸的鄉親鄉情有著濃濃的愛戀,也對故鄉擺不脫的愚昧和苦不盡的日子有著深深的哀傷,這種情感的多重交織構成了他文學創作中的情愫。路遙把他塑造的人物形象孫少平、高加林等留給了時代,而時代也把它塑造的優秀作家路遙獻給了人民。我想說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西方各種文學思潮一浪又一浪地沖擊著復蘇后的中國文壇,但路遙卻不為這些眼花繚亂的創作形式所誘惑,而仍然以質樸的語言進行著現實主義的表達。這種態度,緣于他對故土的愛戀,對生命的尊重,對文學的虔誠。他作品中的人物,印著他走過的足跡,流著他體內的熱血,裝著他心底的情懷,揣著他懷中的夢想。我們可以把路遙和他作品中的孫少平、高加林做一比照:路遙上世紀四十年代末出生在黃土高原上一個貧困農家的土窯里,溝壑縱橫的貧瘠山村就是他成長的地方,而孫少平、高加林等人同樣生長在這樣一個農家,這樣一個農村;路遙七歲時被過繼給延川縣大伯家,而他作品的故事也總離不開這種叔伯情誼;路遙曾在延川縣立中學讀過書,孫少平和高加林也在縣立中學讀過書;路遙中學畢業后回鄉務農,并做過一年農村小學的教師,而孫少平、高加林也曾在縣立中學畢業后回鄉務農并在農村小學當過教師;路遙的初戀情人是北京女知青,而孫少平、高加林的戀愛對象也都有城里的姑娘……所以說,路遙是動用自己生命情感的全部體驗在寫作,他是用滲透在骨髓里的那份真,流淌在血液中的那份愛,在神圣的文學殿堂里舉行著莊嚴的書寫儀式。
同時我想說的是,路遙那個時代在中國的“文革”后期和改革開放初期,國家和全民族的渴望都是相對單純的,也是十分真誠的,與孫少平、高加林等人的個人渴望一樣,就是改變命運,擺脫貧困,滿足溫飽,進而實現更高的精神追求。真誠的時代遇到了真誠的路遙,或者說真誠的路遙恰逢真誠的時代,這種高度一致讓時代把“杰出”給了路遙,把“偉大”給了路遙。
五、優秀的人專跟命運對著干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民間氣息,老人們說,前頭是黑的,任何一個時代,優秀的人都是專跟命運對著干,不干便不會有時來運轉的時辰。當我們回過頭去審閱那個時代,生命在那種境地里成長,會更加懂得珍重和熱愛世間一切,連同所有的巨大沉重和微小的幸福。現在的鄉村富裕了,似乎種地已經成為一種副業,可是我總覺得,農民承擔著土地的命運,土地卻不是他們的保護傘,雖然同樣過著天經地義的窮苦日子,可精神上已經無法掙脫物質的桎梏了。當下,當村落走向城鎮化的時候,村子被高速公路的高架橋、被有線電視的線路貫通的時候,你會突然覺得濃郁的地氣不存在了。我套用俄國作家托爾斯泰的一句話,叫做“城市的文明都是相似的,而山村里卻各有各的文明”。我們國家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例是非常大的。就算一些現在的城里人,上追不過三代也都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所以說,中國人的臍帶連接著的就是厚厚的泥土,他們的DNA就是農民。所有的農民舉家離開故土的原因,要么是為生活所迫,要么是被政策所迫。城市文明帶給人充分的物質便利和豐富的精神生活,但同時,人們又強烈地渴望從成堆的水泥格子和嘈雜的道路交通網中掙脫出來,回到自己精神的原鄉。農民背離土地除了和自己的命運唱反調還能有什么?
《平凡的世界》重在表現的是一個時代,這個時代在歷史的坐標系上所呈現的人的命運、農民的命運、農村的命運的多維交織,表現出整個國家命運的何去何從。路遙在三十年前渴望表達給世人的東西,也正是現在我渴望展示給今人的東西。唯有不同的是,路遙在思想上比我提早出發了三十年,這就是路遙的杰出之處。
我常聽人講,農民都不愛講話。農民不愛說話,是因為苦大。輕易不說話,但要說出來的話就重。《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平的家教就是這貧瘠的黃土地用苦難的生活教會他的。陜北人傳統,不管外邊怎么變,他們總能夠從這個痛苦中分辨出抽象的是非觀。路遙要找到可以變通但是不能顛覆先人的倫理意義,所以,在物質匱乏的年代他的精神并不脆弱,反而有一種卑微的高善和完人的境界。他能夠將自己和別人的命運放在同一個比較低的水平線上去考慮。這也是他寫《平凡的世界》這部作品最成功的地方。他發現了一個普通人的真理,那就是:只有甘愿和主動承擔痛苦的人,才能最終消滅自己的矛盾。
王國維有一首詞是這樣寫的:“月底棲鴉當葉看。推窗跕跕墮枝間。霜高風定獨憑欄。覓句心肝終復在,掩書涕淚苦無端。可憐衣帶為誰寬。”這首詞用在路遙對《平凡的世界》、對陜北這片土地的鐘愛纏綿,是不為過的。
六、農民從土地上的自發覺醒
農民在土地上的自發覺醒,有時候很艱難。正如《平凡的世界》中所說,“你們都完全是無產階級了?你們身上尋不到一點資本主義。”沒有知識的一群無產者,一個個在底層掙扎著想活出“人樣”來的農民親人,哪個祖墳里“都沒埋進去當官的福氣”!沒有錢財,底氣不足,哪里有話語權?何談道德覺醒?我在劇本里只寫他們的情懷,那種渴望長噓一口氣的夢想,需要付出幾倍的努力。遍地煙塵的四季中,路遙的眼睛里看見的是比戰爭更酷烈的生存,正是他們的生存指引路遙創作了《平凡的世界》。
尊重生活尊重歷史,面對所有經見過的山水、物事,人幾乎沒有資格指手畫腳。我在《平凡的世界》劇本寫作中,每每想到這些,我就理解了歷史中走來的鄉民,他們的人生構筑了路遙的平凡的世界,而我借助《平凡的世界》的劇本創作又一次回到我的故鄉。當物質的發展已經代替了人的整個精神世界,曾經貧瘠的生活中,人們似為一種憤懣的拷問而拼盡全力,孫少安、孫少平是自卑的,也是有尊嚴的。我就想告訴世人,即便是和泥土打交道的普通莊稼人,他們也是出眾的!
路遙英年早逝,他活著時走的是最不平坦的路,但越是這樣的人越有與平常物事、與平凡生命結緣的心。他說“人要對自己狠點”,他不知道前面將要出現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又非常明確,此生肯定有許多驛站,但唯一倒下去的地方才可以叫做驛站。路遙有太重的入世愿望,遂不得不和這遠非潔凈的塵世有深刻的過從,他是一個農民,知識轉換了他的身份,但骨子里依然是一個農民。他從土地上的自發覺醒,讓我想到了“不刮春風地不開,不刮秋風籽不來”這樣一句農家諺語,風吹開了土地的懷抱,農民將有事于田疇了,春種秋收,是簡單的一個勞作過程。沒有比農民對土地的感情更深的,也沒有比路遙對農民的感情更深的,路遙明白他的陜北。歷史上重賦、重征,加上戰爭,誰能理解農民在這個過程中的悲慘呢,當我們更多的作家在無端粉飾太平時,路遙用他的“平凡”寫出了不“平凡的世界”,因為苦難反而激發出了他強大的生命體能,他的覺醒是農民對土地勞作的覺醒。
路遙的出身是農民,我的出身是農民,不出三代誰的出身又不是農民呢?這個國家和農民這個詞緊緊關聯在一起,改革開放相對于幾千年的農業社會只是一瞬,誰敢說自己就擺脫了農民的影子,農民有農民的夢想,農民的夢想就是當地主,農民的政治理想就是管轄土地上的人事,這也是路遙的覺醒。當我在閱讀路遙的時候,我看到了他用十年結束了一代人的歷史,一代不順溜的人生。我們可以選擇一塊好風水,但是找不到農民延續下來的幸福,找不到真正的農業,找不到甘心俯身就地的勞作,我們欠農民的太多。當下的人,很少有像路遙、像路遙那個時代的人一樣有理想、有信念、有追求了。而理想、信念和追求本身就是生命的意義、生活的意義、人生的意義。人一旦沒有了理想和信念,也就沒有了追求,也就失去了覺醒的意義。
七、路遙筆下的秦晉之義與秦晉之好
我是一個出生在黃土坡上的土窯里、成長在山溝里的山西女子,路遙作品中每一句關于山西的話題,都會勾起我心中一份暖暖的親切。我想起了“秦晉之好”,悠久的歷史給了陜西和山西極深的淵源,早在春秋時期就給我們留下了這個美好的成語。路遙作品中的人物,也與山西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平凡的世界》里,孫少平的父親孫玉厚年輕的時候,曾在一家商行吆牲靈,從軍渡過黃河,到山西柳林鎮馱瓷器。當時,柳林鎮一個陶姓窯主家發生了事故,孫玉厚冒死救了陶窯主的性命。老陶感激他的救命之恩,與他結了拜把兄弟。陶兄還說,孫玉厚將來無論遇到任何難事,他都會盡全力相幫。若干年后,當孫玉厚給陶窯主寫信,表達了讓陶家收留弟弟玉亭到柳林讀書的想法。陶窯主爽快應承,叫孫玉厚“什么也不要管,這小兄弟的一切都由他全包了”。他兌現了自己的承諾,這才使孫玉亭畢業后在山西太原鋼廠當了工人。孫玉厚每每想到與老陶義結金蘭的情義,心里都是暖暖的,老陶就是他生活的一座大山,他在風雨飄搖的苦日子里只要想到老陶心中就有了依靠。等到孫玉亭哭著喊著要媳婦的時候,周圍人家的彩禮都要得太高了,孫玉厚萬般焦急中又想起了山西柳林的老陶,老陶又熱心地為玉亭找下了賀鳳英。輪到孫少安的時候,孫家又把一個女方“一個彩禮錢都不要”的賀秀蓮迎進家門,這女子模樣好看不說,進了孫少安家的那個破墻爛院里,沒有一絲的嫌棄,“還滿嘴奶奶、媽媽、爸爸叫個不停,把孫玉厚一家人都高興亂了!”賀秀蓮眨眼的工夫就把自己融入了孫家,嚴絲合縫,水乳交融,這當然與晉陜兩地人身處同樣的環境,過著同樣的日子有關。此后,孫少安一家每逢緊要關口,運磚買騾子,辦磚廠籌款,山西的親家總是傾其所能,慷慨資助。在路遙的心目中,陜西與山西兩省人,有著永也割不斷的情緣。在路遙的文學世界里,山西人知恩圖報,重情重義,有求必應。他在用自己的手中筆,詮釋著山里人的“秦晉之好”。另外我還想說一件作品之外的事,《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在廣州《花城》雜志發表之后,當時的文學界或者說文學評論界,對《平凡的世界》幾乎是一片否定之聲,沒有人說好,第二部沒有任何一個刊物愿意發表,最后還是在山西作協的《黃河》雜志上得以刊出。
山西和陜北兩地人,住的是同樣的土窯洞,喝的是同樣的苦井水,面對的都是黃土坡上的山峁溝梁,行走的都是曲曲彎彎的羊腸小道。從地緣的角度講,我們晉陜兩地人就是血緣上的近親。
因此,我們當今最需要的就是路遙,最需要的恰恰就是對生命的尊重,對生活的真誠,對文學的虔敬。這,就是我改編《平凡的世界》的最大動力。
葛水平簡介:山西省沁水縣山神凹人,山西作協副主席,現居山西長治。出版有長篇小說《裸地》,中短篇小說集《守望》、《喊山》、《地氣》、《過光景》等,散文集《我走我在》、《河水帶走兩岸》等,寫過劇本《盤龍臥虎高山頂》。曾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