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出版人訪談 >> 正文
文學天空的斑斕色彩——對話《小小說選刊》主編楊曉敏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5年03月16日16:00 來源:華興時報 史靜波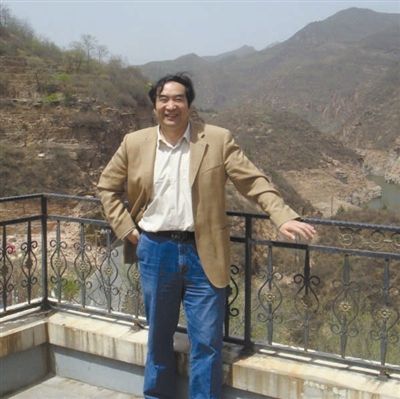 人物簡介 楊曉敏,河南省作協副主席,鄭州小小說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編輯,《小小說選刊》《百花園》《小小說出版》主編。出版有文學作品集《清水塘祭》《小小說是平民藝術》《當代小小說百家論》等多部,與人合作主編《中國當代小小說大系》(5卷)《中國小小說典藏品》(72卷)等小小說叢書、精選本百余種。創意設立“小小說金麻雀獎”,并主持舉辦了“?
人物簡介 楊曉敏,河南省作協副主席,鄭州小小說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編輯,《小小說選刊》《百花園》《小小說出版》主編。出版有文學作品集《清水塘祭》《小小說是平民藝術》《當代小小說百家論》等多部,與人合作主編《中國當代小小說大系》(5卷)《中國小小說典藏品》(72卷)等小小說叢書、精選本百余種。創意設立“小小說金麻雀獎”,并主持舉辦了“? 記者:楊先生您好,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接受《華興時報》的專訪。您主編的《小小說選刊》是一本非常暢銷的文學期刊,也是站立在中國小小說創作前沿的一份權威期刊。在此想向您請教,怎樣才能辦好一份刊物?辦到什么程度算好?
楊曉敏: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能否倡導和規范文體,能否有效地發現、扶持、組織、培養和造就一批批作家隊伍,能否尋找、培育和引導自己穩定的讀者群,對文學期刊來說是其文化含量即精神價值的標準。依我看,只要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出某一種特色,便可謂是找到自己的位置了。
一本文學刊物,作為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精神產品,它首先要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要主題積極,內容健康,有較高的文學藝術追求,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同時,作為一種文化消費品,要體現它的市場價值,就要極大地提高它的發行量和社會覆蓋面。發行是刊物的經濟命脈,是一條流淌的生命線。辦好刊物是為了促進發行,而發行效益又反過來為提高內容質量服務,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文學期刊的生存狀態只有進入自身的良性循環,才能保持其純潔性,真正體現出文學藝術作為精神產品的獨特魅力。刊物的“精品意識”和“名牌效應”正是刊物發行量的保證,也是刊物定價的重要尺度和參照系數。品位高雅,風格穩定,能吸引社會公眾的注意力,擁有一茬又一茬的讀者群,是期刊最為寶貴的無形資源。
記者:面對新媒體的沖擊,所有的傳統媒體都在尋求突圍之路。您認為,傳統媒體路在何方?
楊曉敏:只有把文化產品轉化為廣大群眾的消費,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文化的審美、價值觀、教育功能,強化意識形態屬性,達到以優秀作品鼓舞人的目的。辦文學刊物是社會性行為,是一種公益服務事業。公益事業的本質是為大多數人服務,它需要通過服務對象的成功來體現自身的價值,需要有一種獻身精神和崇高品質。
數字化讀寫的未來趨勢,正在從根本上改變我們以往的文化接受途徑乃至直接進入日常生活,而我們除了亦步亦趨地跟進,幾乎別無選擇。現代傳播注定會改變傳統媒介一統天下的格局,文學作品與網絡、手機閱讀等數字化平臺結緣,是作家的一種自我保護意識和作品開發意識的覺醒。現代傳播手段,也是一種正在萌生的大眾文化權益。
記者:新媒體完全顛覆了傳統的寫作方式、閱讀方式,但寫作和閱讀的本質并沒有改變,根本上還是靠內容取勝。
楊曉敏:是的。誰的刊物能做到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統一,并能傳導出相關文化信息,讓讀者在欣賞中從多方面得到精神享受,誰就具有無形的吸引力。從編輯、調配、插圖、裝幀、印刷、發行乃至策劃、管理、經營等諸多環節均應有“高、精、尖”的要求。一本精美的刊物,應該具有整體的美感,任何一處瑕疵,都會增加一些讀者的失望情緒。解決這個認識問題,是辦好刊物的前提和基礎。
在辦刊人眼里,作家的作品只能是原材料,刊物本身也只能是一座加工廠,刊物操作的整個流程,就是把適宜于自己加工的原材料,重新分揀、組合而打磨成一種新產品,投放到消費(讀者)市場。這過程必須符合市場的游戲規則,要體現產銷對路的經營理念。面對國內外期刊業的市場競爭,單是一家文學期刊社,并不具備做大做強的客觀條件,但如果努力做小做精,也能大力增強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
記者:辦報辦刊,一方面我們要為理想留點時間,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到市場中去搏擊。如何處理“理想”與“市場”的關系?
楊曉敏:我曾經提出過“小編輯大發行”的思路。所謂的小編輯,是指編輯部要精。編輯人員要有較強的策劃能力,懂得如何判斷選題(約稿)的準確性,不但選稿的質量要精,還要會合理利用作者自身正在攜帶或煥發出來的市場影響力。所謂大發行,即發行體現在期刊社自身的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上,也體現在整個辦刊過程中所堅守的發行意識上。期刊發行的靈魂是網絡關系,建立一條由郵局、零售公司、社會發行渠道和單位郵購的立體發行網絡,是占有市場份額的基本保證。
文學期刊大都不具備搞期刊集團的條件,但同樣可以在“小作坊”中做精,可以搞小型的文化立體工程,靠“間作”來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對于整個期刊運營,更需要巧妙運籌,全方位調度,諸凡環境、人才、網絡、渠道、稿源、再生產、深加工等等,都要通盤考慮,深入挖掘,把人的優勢和文化資源的優勢綜合利用,從而達到事半功倍、和諧高效的最佳境界。
讀者的欣賞水平不會長久停留在某一層面上,文學期刊的求新求變要時刻注意讀者市場這個晴雨表。尋找、培育和積極引導穩定的讀者群,實際上是為刊物確立一種定位。刊載讀者最感興趣的內容,是吸引讀者注意力的最快捷辦法。你給哪一部分人辦的刊物,就應該選擇他們最關心的話題,給什么年齡段人看的,就應該在策劃定位上貫以始終。
文學期刊只有在刊物的整體設計、欄目設置、讀者對象的選擇等重大問題的思考上,向社會公眾展現出自身的價值和魅力,才能立于不敗之地。這一切既是刊物質量的競爭,也是辦刊人超前意識的競爭。
記者:您所創意的“小小說金麻雀獎”被視為今天中國小小說的最高獎項。請您向讀者介紹一下這個獎項好嗎?
楊曉敏:多年來,小小說領域設立了多種業界獎項,如《小小說選刊》雙年獎,《百花園》《微型小說選刊》年度獎,還有各學會獎、各種征文獎等,在鼓勵眾多的小小說作家的創作熱情、發現文學新人、推出單篇的精品佳構等方面,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隨著文體成長和好作品的不斷涌現,在民間設立一個從某種程度上能真正代表中國小小說創作水準,并能與長、中、短篇小說全國性評獎相對應的獎項,推出小小說業界的“大家名家”,便顯得尤為迫切。
鄭州小小說團隊在2002年底設立“小小說金麻雀獎”時認為,在文學日趨邊緣化、小說式微的今天,小小說讀寫卻數十年方興未艾,能使文學的原始生命力得以蓬勃復蘇,這些特征和麻雀的生存狀態何其相似。用簡潔的語言最能概括小小說特點的就是這句話——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2002年底,由鄭州《小小說選刊》《百花園》《小小說俱樂部》和鄭州小小說學會聯合設立的“小小說金麻雀獎”正式啟動。
“小小說金麻雀獎”在評選上有兩個特點:一是評選范圍具有全國性,不受一些報刊某次命題征文或具有明顯鼓動性質的年度評選的局限;二是由于單篇的小小說作品畢竟顯得單薄,加上思想藝術容量有限,難以與其他小說品種抗衡,而以一本書參評和其他小說品種評獎方式比較,又有失公允,所以金麻雀獎要求作者以十篇小小說作品為參評單元,來對應長、中、短篇小說的全國性評獎的分量。這樣,既可集中反映參評作者的綜合創作實力,又能增加小小說作品的整體厚重感。
自2003年首屆評選“小小說金麻雀獎”開始,現已成功評選七屆。共有56位作家和6位評論家(第四屆開始增設理論評論獎、第六屆開始獲獎作家可以二次參評)獲此殊榮。這些獲獎作家中,除了少數幾位對小小說情有獨鐘的文壇大家和小說名家,如馮驥才、王蒙、林斤瀾、孫春平、聶鑫森、墨白等,其余均是專門從事小小說創作或以小小說創作為主,而且較為完整地涵蓋了龐大的小小說作家隊伍中的老、中、青三代的代表性人物,其琳瑯滿目的作品,也包羅了各類不同的題材內容、藝術個性和審美風格,基本上彰顯了中國當代小小說創作領域的至高水準與發展趨向。這一獎項填補了國家級文學獎項中小小說品種長期缺席的空白,已成為當代文壇極具影響力的重要文學獎項之一。
記者:您如何看待目前中國小小說創作的現狀與前景?
楊曉敏:當代小小說已蓬勃發展30年,由于參與小小說寫作的人成千上萬,遍布社會各界,小小說的閱讀熱潮持續升溫,仍有方興未艾之勢,正帶動著精短文學(故事敘述、哲理小品等)引領時尚閱讀之先,并拉長了相關文化產業鏈條,它所呈現出來的民間性的大眾文化意義,使小小說現象成為現當代文學史上自白話文運動以來重要的文學現象之一。
當今社會,已形成精英文化、大眾文化、通俗文化的多元格局,各自有著自身的特點與作用。引導和重鑄著人類靈魂、支撐社會文化建筑高度的精英文化誠然不可缺;能夠迎合一部分人休閑、消遣的通俗文化需要加以揚棄。而春風化雨、滋潤心靈的大眾文化,則本身兼有精英文化質地又有通俗文化市場,能夠惠澤普通民眾,引領社會文明的主流。大眾文化具有強大的兼容性,最活躍也最有親和力。
因為小小說文體簡約通脫、雅俗共賞的特征,就決定了它是屬于大眾文化的范疇。我有一個觀點,作為小小說文體,它的文化意義大于它的文學意義。一篇小小說,要求它承載非常高端非常極致的文學技巧,或者要求它蘊涵很大的精神能量,是非常難的,也會限制它旺盛的生命力。如果延伸一步,小小說的教育學意義又大于它的文化意義。小小說是眾多文學體裁中,一種非常受社會各界讀者青睞的文學讀寫形式。對于提高全民族大眾的文化水平、審美鑒賞能力,提升整體國民素質,會在潛移默化的孕育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我國大專以上文化水平的人,與發達國家比起來,比例要小得多,做好基礎的或中等程度的文化普及教育,應該是一個重中之重的大前提。小小說能讓普通人長智慧,對傳統的文化讀寫活動無疑是一種有益的補充。僅以《小小說選刊》《百花園》為例,30年來的發行量已逾億冊,培養和成就了成千上萬的寫作者,影響了兩代讀者,所以還可以認為,小小說的社會學意義又大于它的教育學意義。
我堅持認為,精英化、大眾化、通俗化三種文化形態就好像三原色,共同構成了文學天空的斑斕色彩。當代文壇之所以顯得單調和窘迫,很大程度就在于我們文學的主流話語權把基調定在了“精英化”的一根琴弦上,而一根琴弦又如何能奏響氣勢如虹的交響樂章呢?小小說注重思想內涵的深刻和藝術品質的鍛造,小中見大、紙短情長,在寫作和閱讀上從者甚眾,無不加速文學(文化)的中產階級的形成,不斷被更大層面的受眾吸納和消化,春雨潤物般地為社會進步提供著最活躍的大眾智力資本的支持。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