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guó)作家網(wǎng)>> 舞臺(tái) >> 評(píng)論 >> 評(píng)論 >> 正文
旨在獨(dú)裁 詳略自異——評(píng)傅謹(jǐn)《中國(guó)戲劇史》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5年02月12日09:51 來(lái)源:北京日?qǐng)?bào) 趙建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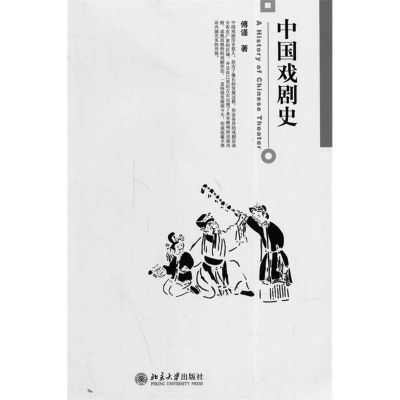 《中國(guó)戲劇史》 傅謹(jǐn)著 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
《中國(guó)戲劇史》 傅謹(jǐn)著 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 針對(duì)歷史編纂之學(xué),章太炎先生曾有這種說(shuō)法:“今修《通史》,旨在獨(dú)裁,則詳略自異。”這里所謂“旨在獨(dú)裁”,并非指史書(shū)編纂者的武斷偏激,而是指要有獨(dú)立的價(jià)值判斷,不為舊史陳規(guī)所束縛,也即要有“獨(dú)識(shí)”。這種治史觀,遠(yuǎn)追西漢司馬遷的“成一家之言”、唐代劉知幾的“獨(dú)斷”之學(xué),近宗清代章學(xué)誠(chéng)的“別識(shí)心裁”等,都主張治史要有獨(dú)立見(jiàn)解,不能人云亦云,淹沒(méi)在既有的歷史判斷之中。
一般歷史學(xué)研究如此,而專門(mén)史的研究也概莫能外。在筆者看來(lái),傅謹(jǐn)先生新近出版的《中國(guó)戲劇史》,就是這樣一部秉持“獨(dú)裁”之史識(shí)寫(xiě)出的別具風(fēng)格的戲劇史著作。
該書(shū)共六個(gè)篇章——序幕:中國(guó)的戲劇源流;奇峰突起:宋戲文和元雜劇;精致典雅:明清傳奇與昆曲時(shí)代;百花爭(zhēng)艷:繽紛多彩的地方戲;波瀾起伏:戲劇市場(chǎng)的發(fā)育;峰回路轉(zhuǎn):面向未來(lái)的中國(guó)戲劇。它全面概述了綿延千年的中國(guó)戲劇發(fā)展歷程。借此,我們既可以知曉中國(guó)戲劇自誕生至今的發(fā)展演變和社會(huì)歷史的變遷,也可領(lǐng)略閃耀其中的著名戲劇藝術(shù)家的風(fēng)采和經(jīng)典戲劇作品的精髓。
作者的“獨(dú)裁”之史識(shí)首先表現(xiàn)在其尊重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性意識(shí)。在“戲劇本體的再發(fā)現(xiàn)”一節(jié)中,作者借用《駱駝祥子》、《曹操與楊修》等新編劇目指出,古典戲劇美學(xué)向現(xiàn)實(shí)題材劇目創(chuàng)作與表演的延伸,是1990年代出現(xiàn)的民族文化主體性回歸思潮在戲劇界的重要表現(xiàn)。不難看出,作者在書(shū)中通過(guò)大量史料和對(duì)當(dāng)代戲劇創(chuàng)作的現(xiàn)狀分析,力圖證明這樣一個(gè)事實(shí):具有獨(dú)特美學(xué)風(fēng)格的中國(guó)戲劇要充分地融入世界,就必須理性地回歸傳統(tǒng)。真正的現(xiàn)代性是立足于傳統(tǒng)的,是在尊重傳統(tǒng)基礎(chǔ)之上的文化充分自覺(jué)。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根基如果不是建立在對(duì)歷史傳統(tǒng)的充分認(rèn)識(shí)和理解的基礎(chǔ)之上,沒(méi)有對(duì)傳統(tǒng)的深知與自信,那么這種創(chuàng)新發(fā)展必然不會(huì)走遠(yuǎn)。這或許是一種文化保守主義的態(tài)度,但如果它是建立在藝術(shù)自律的基礎(chǔ)之上,就會(huì)必然擁有最具現(xiàn)代性的美學(xué)精神,這當(dāng)然是值得肯定的。
一部相對(duì)完備的戲劇史,不只是戲劇文學(xué)史,還應(yīng)該是戲劇演出史,它在展現(xiàn)劇本文學(xué)創(chuàng)作實(shí)績(jī)的同時(shí),更要梳理出舞臺(tái)實(shí)踐的演進(jìn)路徑。把舞臺(tái)表演提到與劇本創(chuàng)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讓劇本創(chuàng)作與舞臺(tái)表演兩相映照,這是傅謹(jǐn)先生撰寫(xiě)《中國(guó)戲劇史》時(shí)遵循的另一個(gè)重要原則。
嚴(yán)格地講,戲劇包括戲曲和話劇,所謂的“戲劇戲曲學(xué)”是一個(gè)混淆了內(nèi)涵和外延的學(xué)科名詞,把“戲劇”與“戲曲”并列,把戲劇等同于話劇,反映了學(xué)科界定上的混亂和模棱兩可的狀態(tài)。很多治戲劇史者也沿此思路,把戲劇史要么寫(xiě)成話劇史,要么寫(xiě)成戲曲史,只有徐慕云一個(gè)人,在其1940年前后出版的《中國(guó)戲劇史》中,首次把話劇和戲曲并列于“戲劇”這一概念下,試圖用現(xiàn)代的眼光和意識(shí)去分析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戲劇的現(xiàn)狀,其學(xué)術(shù)視野無(wú)疑比同代人乃至后來(lái)者更為開(kāi)闊。傅謹(jǐn)先生延續(xù)了徐慕云的治史之路,又對(duì)徐氏《中國(guó)戲劇史》之后七十年間更為復(fù)雜的戲劇現(xiàn)象做了新的梳理,把話劇和戲曲作為中國(guó)文化共同的有機(jī)組成部分,視野更顯開(kāi)闊。同時(shí),他又堅(jiān)持戲曲始終是中國(guó)戲劇主流的歷史事實(shí),在戲劇史的撰寫(xiě)中凸顯戲曲的核心地位,相對(duì)客觀地還原了戲劇史的本來(lái)面目。
幾十年來(lái),很多戲劇史研究者都有意無(wú)意地認(rèn)為,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戲劇的主體就是話劇,而話劇的主體就是左翼戲劇,而最能代表左翼戲劇的就是問(wèn)題劇。之所以說(shuō)“有意無(wú)意”,因?yàn)檠芯空邆兌技w無(wú)意識(shí)般地把意識(shí)形態(tài)領(lǐng)域內(nèi)形成的戲劇運(yùn)動(dòng)作為自己的期待視野,遮蔽了更多更豐富的非意識(shí)形態(tài)的民間戲劇生態(tài)。例如,1930年代到1940年代的戲劇舞臺(tái)上,不僅有慷慨激昂以宣傳鼓動(dòng)為目的的國(guó)防戲劇和抗戰(zhàn)戲劇,還有李健吾、陳綿的改編劇,費(fèi)穆、顧仲彝的佳構(gòu)劇和神仙劇,周貽白的歷史劇,姚克和楊村彬的清宮戲等等。這些戲雖然很多都游離于政治革命運(yùn)動(dòng)之外,但在淪陷區(qū)的演出卻非常紅火,形成一股新的商業(yè)劇洪流。但即便如此,它們也從未取代過(guò)戲曲在演出市場(chǎng)的主導(dǎo)地位。僅以北平為例,正如《中國(guó)戲劇史》中所言,如果僅從京劇班社的數(shù)量看,抗戰(zhàn)時(shí)期無(wú)疑可謂北平京劇發(fā)展的一個(gè)高峰。對(duì)于淪陷區(qū)的戲劇繁榮,說(shuō)它畸形也好,正常也罷,但它確實(shí)就發(fā)生在不過(guò)六七十年前的既往歷史中,這是根據(jù)無(wú)可辯駁的史料所得出的不爭(zhēng)事實(shí),是個(gè)歷史“常識(shí)”,無(wú)需做精深繁雜的考據(jù)和爬梳。而恰恰是這個(gè)“常識(shí)”,我們以往的戲劇史卻對(duì)它熟視無(wú)睹。這種熟視無(wú)睹反映出治史者的微妙心態(tài):不喜歡或不愿承認(rèn)的就忽略它,以偏狹的史識(shí)隨意裁剪客觀的歷史。這也算治史中的一種“獨(dú)裁”,不過(guò)這種“獨(dú)裁”是獨(dú)斷偏激的削足適履,而非客觀理性的價(jià)值判斷。
章太炎先生的原話是這樣的:“今修《通史》,旨在獨(dú)裁,則詳略自異。欲知其所未詳,舊史具在,未妨參考。”傅謹(jǐn)先生之所以能做到“詳略自異”,行文來(lái)去自由,無(wú)不是建立在對(duì)整個(gè)中國(guó)戲劇史了然于胸的基礎(chǔ)之上。史料是固定的,而史識(shí)常新。治史者就要在不變的史料之上,懸起現(xiàn)代性的目光,以“獨(dú)裁”之史識(shí),不嘩眾取寵,在扎實(shí)的史料基礎(chǔ)上撰寫(xiě)新歷史、大歷史。
網(wǎng)友評(píng)論
專 題




網(wǎng)上期刊社


博 客


網(wǎng)絡(luò)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