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wǎng)>>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柳冬嫵:打工經(jīng)歷是文學(xué)的滋養(yǎng)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4年12月15日11:11 來源:羊城晚報 何晶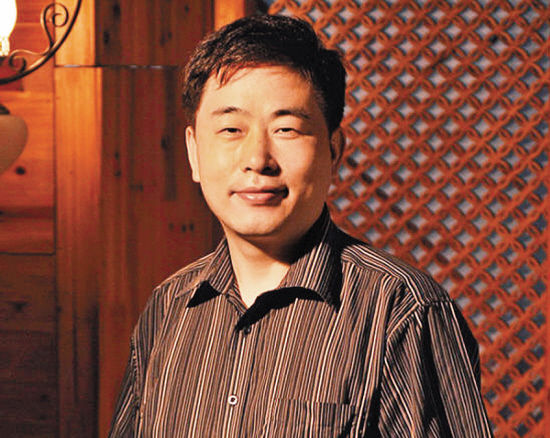
卡夫卡《變形記》是最好的“打工小說”
羊城晚報:近些年,您從打工詩人轉(zhuǎn)型為打工文學(xué)評論者,您對“打工文學(xué)”這個概念是如何界定的?
柳冬嫵:“打工文學(xué)”這個命名大概出現(xiàn)于1990年代初期,當時出現(xiàn)了一批比較優(yōu)秀的打工文學(xué)作品,這和社會的發(fā)展息息相關(guān),當時出現(xiàn)了大批進城務(wù)工者。文學(xué)是形象的人類學(xué),在這個背景下,出現(xiàn)打工文學(xué)作品是正常不過的。這個概念從誕生到現(xiàn)在,對它的評價始終褒貶不一。廣義上講,“打工文學(xué)”既包括“打工作家”,也包括其他作家創(chuàng)作的以打工生活為題材的作品。狹義上講,“打工文學(xué)”主要是指“打工作家”創(chuàng)作的以打工生活為題材的文學(xué)作品。任何一種題材,從文學(xué)的角度來說從來是不分好壞的。文學(xué)的價值并非題材的價值,應(yīng)當體現(xiàn)于藝術(shù)形式綜合處理題材之后的結(jié)果。作為寫作者,不能從題材的角度來夸大自己寫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作為批評者,更不能粗暴地認定“打工文學(xué)”是對美學(xué)的貶抑。
羊城晚報:十多二十年過去,社會結(jié)構(gòu)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寫出優(yōu)秀作品的“打工作家”也已經(jīng)陸續(xù)告別打工身份,您認為這對文學(xué)創(chuàng)作來說,是好事還是壞事?
柳冬嫵:是好事還是壞事,可能因人而異。當年寫知青文學(xué)的作家,很多人也是從鄉(xiāng)下回城之后才寫的。一些打工文學(xué)的作者雖然進入了所謂的編制內(nèi),但打工經(jīng)歷的滋養(yǎng)還在。作家有寫作的階段性也很正常的,以前寫打工題材,現(xiàn)在不寫,也很正常。我自己現(xiàn)在也寫得少了,主要做打工文學(xué)研究。即使是王十月、鄭小瓊的創(chuàng)作,打工題材大概只占四成,他們有更多作品是寫其他題材的。
羊城晚報:其實也意味著“打工作家”這個標簽更多的是某種出身論。
柳冬嫵:對,作家寫作時并不會考慮自己寫的是不是打工文學(xué)。貼標簽是評論家干的活,為了研究和談?wù)撃撤N現(xiàn)象更方便,總要給個定義,以作出區(qū)分和界定。
我最近在研究外國文學(xué),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城市化進程中,它們早就出現(xiàn)過和當代中國的“打工文學(xué)”非常類似的文學(xué)現(xiàn)象。比如卡夫卡的《變形記》,在我的研究視野中,我認為它是最好的打工文學(xué)作品,不僅是西方現(xiàn)代派文學(xué)的代表作,也是精彩的打工小說。現(xiàn)在我們正在經(jīng)歷的,卡夫卡在那個年代都經(jīng)歷過。小推銷員難道不是今天的打工者嗎?
再比如《嘉莉妹妹》寫打工妹從農(nóng)村到芝加哥,進了一家鞋廠打工,里邊的場景描寫,只要換成珠三角的鞋廠,基本是一樣的,非常吻合。嘉莉妹妹最后做了情人,也和我們現(xiàn)在寫的二奶故事是一樣的。今天我們處理的這些題材,實際上在100多年前就有歐美作家處理過了。
很多評論家無視草根寫作
羊城晚報:這可能跟如何定義“打工者”有關(guān),您覺得現(xiàn)在大家對“打工”這個帽子還有沒有先入為主的偏見?
柳冬嫵:“打工”這個詞我覺得是有點被污名化,中國人可能存在某種集體無意識,提到打工者,立刻會覺得這些人沒讀過什么書,文化根基淺,這樣的成見會讓大家覺得打工者寫不出好東西。有作家會排斥這種稱謂,很正常,甚至包括我自己也會,有時候聽到別人介紹我是“打工詩人柳冬嫵”,心里也覺得怪怪的。但其實文學(xué)作品的好壞,和這些稱謂都沒有關(guān)系。如何處理好打工題材,將其變成文學(xué)藝術(shù),這才是關(guān)鍵。“打工作家”不是因為別人的同情、憐憫、特別關(guān)照或降低門檻而進入文學(xué)領(lǐng)地的,而是因為他們本身就具有了文學(xué)的品質(zhì)。
羊城晚報:您好像提過,批評家對打工文學(xué)的關(guān)注不夠?沒有挖掘好作品的眼光?
柳冬嫵:整體來說,沒有根本性變化。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最近郭金牛比較熱,但其實我對他的關(guān)注有二十多年了,他最早用的筆名叫子虛,十多年前我就評論過他的詩,但人微言輕,并沒有引起關(guān)注。我認為批評家應(yīng)該從作品中挖掘出好東西,當一名預(yù)言家。有些評論家簡單地說“打工文學(xué)藝術(shù)品格不高”,這句話放之四海皆準,顧彬就說過中國當代文學(xué)都是垃圾。
羊城晚報:從寬泛意義上來說,打工者寫的打工文學(xué)作品,和專業(yè)作家寫的打工文學(xué)作品,有沒有區(qū)別?
柳冬嫵:任何作者在文學(xué)面前都是平等的,但打工者和一些著名作家在處理打工題材上,肯定有區(qū)別。這是經(jīng)驗上的,甚至是身體經(jīng)驗的。來自底層的打工文學(xué)作家,某種程度可以稱作是“身體寫作”,他們寫身體上最直接最尖銳的體驗,而這是打工文學(xué)寶貴的地方。
“打工作家”的“親歷經(jīng)驗”,“著名作家”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都不是闡釋作品好壞的前提,與文本價值之間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作家生活與作品本身并不是簡單的因果關(guān)系,盡管作品和作家生平有密切關(guān)系,但決不意味著文學(xué)作品僅僅是作家生活的摹本。
羊城晚報:如今在打工人群中,寫作者多嗎?
柳冬嫵:我們最近在編這兩年的《東莞打工文學(xué)作品選》,2012年也編過一套,當時小說卷是600頁,全是東莞打工作者發(fā)表在省級以上期刊的作品。現(xiàn)在編選這兩年的,小說卷已經(jīng)有800多頁,單單東莞這個地級市就有這么多作品,這在199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詩歌、小說、散文、非虛構(gòu),呈現(xiàn)齊頭并進的態(tài)勢。當然,對于打工作者來說,機緣非常重要,依然有很多評論家對草根寫作是無視的,如果不是暴得大名,一般不會進入這些批評家的視野。對于個別暴得大名者,批評界的跟風(fēng)和從眾行為特別嚴重,大多數(shù)批評家的懶惰和無為也隨之自動現(xiàn)形。
網(wǎng)友評論
專 題




網(wǎng)上期刊社


博 客


網(wǎng)絡(luò)工作室
